中国农村的新出路
塘约的新社会主义

-木愉-
塘约不知名,我是从著名左派微信公信号《乌有之乡》上知道这个地方的。跟塘约连在一起的是道路,就是说塘约是作为一条道路而被推崇的。1978年改开之后,作为道路被宣扬的似乎只有小岗村道路,那条道路虽然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本质是单干。小岗村道路在1978年之后成为了主流,只剩下华西村、刘庄等等几个硕果仅存,仍然坚持既往体制,并且活得还好,不过那些地方似乎都只是个案,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决定了这些地方所代表的生产方式难以复制推广。但是塘约不一样。塘约居于穷乡僻壤,只比小岗村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更差,但塘约选择的道路却跟小岗村截然相反,重新回归合作,却又克服了传统合作方式的低效弊端,让集体合作重新显示出生命力。这个过程正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
我对塘约来了兴趣,因为塘约在私有化成为主流的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异类,一个颇有活力的异类。我决定趁回国探亲之旅去看看。塘约就在贵州,就在家乡安顺市的辖区内。回国之前,我就问身处塘约所在县的老同学是否知道塘约,答曰不知。说明塘约虽然得到推崇,却也没有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方。就在回国前夕,老同学来信,说打听到了塘约,并联系到了一个塘约人,可以带我去看看。
在贵阳跟几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们聚会之后,其中几个就陪我一起到塘约去。我们沿着宽阔安静美丽的贵安大道从省城往平坝方向开车驰去,先顺路在平坝小河湾逗留了一下,沿着河湾走了一圈。这条河有个雅致的名字 – 文殊。文殊河文文静静,在这里绕了九道弯,极尽婉约之魅。金黄的谷穗已经沉甸甸的,等待着收割。紫色的花分布成很多方块,装点着小河湾,让村庄美目盼兮。一个农民刚从文殊河里打渔归来,得了两条鱼,放在盆里待价而沽。我们走了一圈,走得神闲气定,然后继续乘车前往平坝。在平坝最负盛名的一家清真馆子吃了又色又香又可口的饭菜,便直奔塘约而去。
塘约离平坝就二十公里,走了不久,就到了。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如同孩童就要看到世面一样。沿着路开下去,就到了一处宽阔的场所,像是小广场,也像是停车坪。农舍格式各异,外观大都是乳黄、浅红等亮丽而又平和的颜色。同学打了那个塘约人的电话,不一会,一个年轻人就来了。他曾经为那个同学搞过房子装修。我跟年轻人握了握手,问了一句:“塘约可以持续发展吗?”塘约道路的引路人是左文学,他之后,塘约是否还会红红火火走下去,的确值得怀疑。年轻人笑道:“肯定会的,已经有了安排。”
年轻人把我们带到一栋二层楼里,一个中年人走出来迎接。他是左文学的搭档,村主任彭远科。上了楼,跟他进到一个房间里,外面是会议室,里面是他的办公室。他把我们直接带到办公室里,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有人建议,不如就在外面的会议室里围着大会议桌坐。于是,大家就走出来,围了长方形的会议桌坐了一圈。
彭主任笑着说:“我还是不用普通话说,就讲本地话吧。”我们一致称好。
他是从塘约道路的缘起说起的。2014年6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深夜来袭,左文学通知了彭远科赶快去全塘约地势最低洼的白纸厂寨查看。洪水已经冲进寨子,从后面进去,前门出来。左文学和彭远科以及其它村干部一起组织群众疏散;天亮后,又一起帮助修房子。市委周建琨书记来现场视察,看到这种场面,很是感动。他对左文学说:你们这里干部了不起,民风很淳朴,可以做点事。做什么事?周书记却没有点明。后来,就有了合作社,大家把土地折价成股加入合作社,组织起来一起干。
改开后,塘约人也分田到户搞单干,年轻人大都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去了,劳动力1400多个,外出打工最多时候达到1100多人。都说,农民出外打工是因为农村劳力过剩引起的,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塘约的土地撂荒率达到30%。不仅塘约,其它地区也一样,村里大都留下的老弱妇孺,种田成了妇女和老人的事。这就是说,其实农村是可以吸纳劳动力的。出去打工,貌似是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到外面去闯出一番新天地。但代价是惨重的。其一,农民在外打工,家里老人孩子无法照料,家庭是破碎的。在外面打工,把吃穿住行的费用扣除,带回家里的并不多。而且,农民工在外面饱受屈辱,没有尊严。
再来说城镇化。城镇化如果是是指农民进城打工,改变农民身份,由此减少农业人口,那这个进程是痛苦的,而且痛苦要由农民来承受。良性的城镇化应该是通过城市的辐射而把周边地区变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样的城镇化也有鞭长莫及之处。这就是无法包容到更广大的农村,同时城市规模过大也会带来噪音、交通拥挤等等城市病。更值得推崇和施行的应该是农村立足于自身的城镇化。塘约所探索的就是这种城镇化。
塘约人的第一步是把已经分出去的土地重新丈量,折价入股加入合作社。第二步是调整产业结构。出去打工的人中,搞建筑、跑运输的很多,可以把回来的人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和运输公司。
把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后,可以做很多之前不能做的事。由于分田单干,以前修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土地入股后,就可以重修水利。塘约村前有一条河,叫洗布河,一下雨,就会淹没周围的田地。1975年,在大干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把河拓宽到8米。但这还是不够,于是在百年不遇的洪水面前,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洪灾。土地重归集体后,这条河拓宽到了35米宽,全体村民一起干,只花了22天就修好了。从此,水患的威胁才远去了。
重走集体化道路,当然是要追求富强,而不是贫弱。塘约人在一批能人的率领下,改变作物单一的状况,广种韭黄、辣椒、西红柿、芋头、香葱、丝瓜、生菜等等经济价值高的蔬菜。建起塑料大棚,即使是冬天,也可以种植好多反季菜。同时,建筑队、运输队等等专业技能队伍也主动出击,到外面拓展业务。仅仅两年,塘约就干得风生水起,集体收入达到200多万,合作社成员平均月工资达到2000多。
那么,领导们工资有好高呢?在许多国营企业,基于所谓多劳多得的原则,管理层的报酬是一线员工收入的若干倍甚至十几倍。但是,塘约不一样。彭主任说:“你有钱,你还是不能修路,不能架桥,不能……”彭主任一连用了好几个排比句,正不知他要如何论证怎样才能时,他转而激情说道:“只有出于公心,带领大家一起干,才能。”接下来,他说领导们的年薪就只有两万多不到三万,而且他们的表现还得村民们来评比,只有达到了100分,才能拿到规定的年薪。
在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社会,谈公心是奢侈陌生也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塘约的领头人们的确就是在这样一种公心的激励下,忘我地工作。连上面给左文学和彭远科1800的月补贴,他们都没有理所当然收下,而是把这点钱放入集体收入里。
移风易俗不仅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层面的洗礼和重建,而且也是一种基于物质层面的考量而推行的措施和行为。塘约虽然是贫困地区,但请客送礼大办酒席一直非常盛行,有的人家经济拮据,不得不贷款送礼。一年下来,塘约人花在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居然是3000万。不错,是三千万。如何根除攀比大办酒席的陋习?聪明的塘约人自有妙计。
由村支两委商议,村民大会通过,塘约出台了村规民约,只有红白喜事可以办酒席,办酒席一律由集体出资出人,喜宴八菜一汤,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丧葬酒,就吃一锅香,五个菜全都倒入大盘里,打多少吃多少。全村酒席总量一下就减少了70%,同时,没有攀比,成本下降,集体一年在办酒席上就花了区区60万元。
彭主任口气高亢起来,说:“下一步,我们要把麻将桌砸掉。”人一打起麻将来,就难免沉溺进去,不只是一个输赢问题,而且还导致人对老老少少不管不顾,耽误正事。村支两委不仅担负着组织生产的责任,而且还有规范村民行为的功能。
听彭主任介绍起塘约来,起承转合,井井有条,跟讲坛上的老师相比,也不逊色,有人就问他读了大学没有,他答就读了初中。我们自然为此感叹了一番。跟很多塘约人一样,他以前也到外面打过工,后来回到家乡来,跟左文学一起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觉得踏实了。要不是他五点还要开会,我们还会跟他继续探讨下去。我们表示要在塘约四处看看,他就叫妇女主任为我们当向导。妇女主任当年也到外面打了多年工,在我们听介绍的时候,不断走进来为我们续茶。
彭主任送我们出来,一起在楼前合了影。我告诉他,我早在回国前就知道塘约了,听了介绍,对塘约道路愈发感兴趣。他就把我领到一旁的图书室,在书架上抽了两本书,递给我。我连忙拿出钱来,要付款。他赶快说:“这是送给你的。”我就连连道谢了,又要他在《塘约道路》这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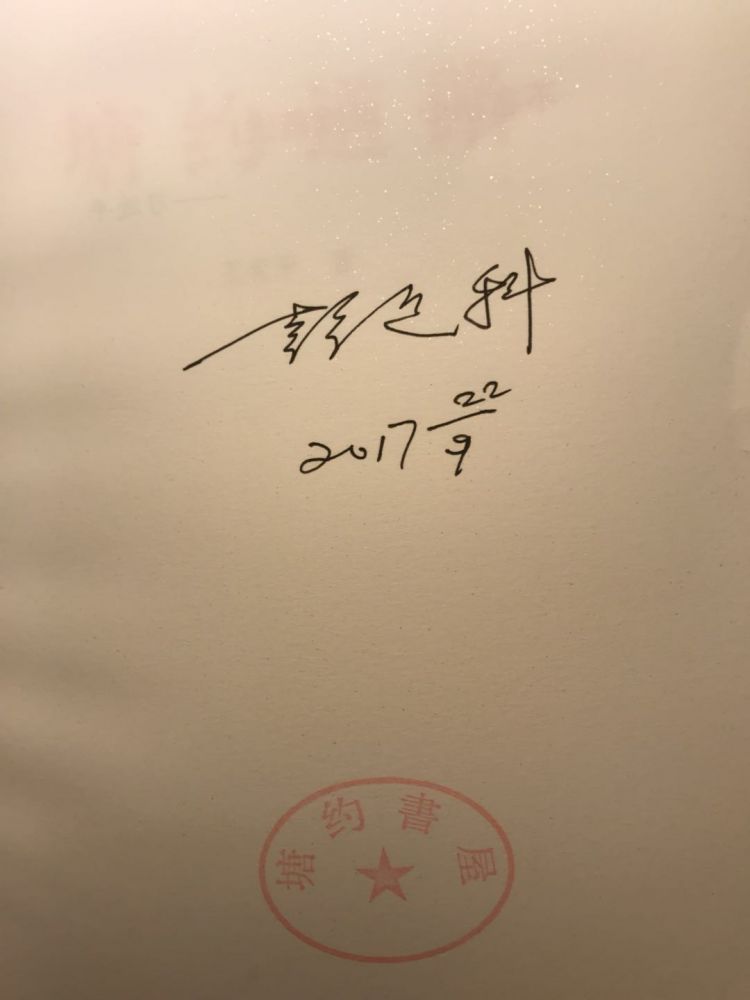
顺着停车坪往下走去,见旁边有一个土木工程在进行,一看说明,知道这栋建筑是市培训基地。看来,政府对塘约模式是认可甚至推崇的。塘约道路不仅为解决边远农村空心化找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且也夯实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政府对塘约的首肯是顺理成章的。

几个学生在有模有样的篮球场上正打着球,而刚才在图书室里还有不少学生在那里读书。从孩子们的活动上,塘约呈现出某种欣欣向荣的风貌。
沿着公路往前走去,看到两旁的地里有种着香葱的,还有种着韭菜的。妇女主任告诉我们:“过段时间,把韭菜埋起来,就长成韭黄了。”又见一片水塘里又大片叶子的植物,就问妇女主任,她说那是芋头。不久,到了几大片塑料大棚跟前,进了其中一个,里面的西红柿长势喜人,正等待收获呢。又到了另外一个塑料大棚里,那是育苗的地方,丝瓜苗正长出来,正往上窜;生菜、菠菜都青翠欲滴,等待移植呢。有一个角落的育苗设施看去似曾相识,细细一想,原来在迪斯尼乐园看到过,那是相当前卫的农业无土栽培吧。






参观完塘约,我们一行都兴奋不已。在当今的中国,看到这个富翁,听到那个富翁,都已经稀松平常。罕见的是在这样一片穷乡僻壤上,当地的人们正拧成一股绳,共同踏实地开创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从广东远道而来的同学说,今后还要来这里,再看塘约的新篇章。我想,我也会再来的。我有着某种担心,怕如此生机勃勃的人类生活不可持续,如同欧文等等空想共产主义者当初的乌托邦试验地一样,成为让人唏嘘的一块历史化石,一记让人叹息的历史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