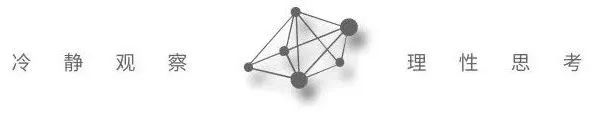
来源:维舟
作者:维舟

又到了节后返城的时刻,翠花们重新变回了Tracy——通常还带着回乡见闻的深深感慨。对穿梭往返于大城市和老家之间的人们来说,春节长假这些年来不仅仅是一个亲友团聚的日子,还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契机来观察故乡的变化。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既能作为内部的知情人察觉那些新的变化,又能从一个外部的视角进行评判。
不夸张地说,这些回乡见闻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下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发生多大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农村和小城市、又是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现象,最能强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以往最难触动的地方也已发生了改变。
这些直观的经验观察所涉及的地域天南海北,话题故事林林种种,除了谈论家乡的新变化外,并没有一致的主题,不过至少有一个常常若隐若现、也容易激发讨论的基调:农村的衰败。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对这一状况的深切忧虑、对自己家乡和亲人不幸遭遇的无力感,通常还有一种“美好往昔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倒似当真印证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
改变自己家乡落后面貌曾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愿望,但当家乡确实发生改变时,许多人的反应却仿佛他们是失落了一个天堂,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乡村。
但这真的是全部事实吗?
在此必须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叙述故乡所发生的变化时,具体有没有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是一种事实判断;但这种变化好还是不好,那可就复杂了,它是一种和我们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价值判断。举例来说,如今人们普遍觉得过年不如以往热闹了,年味淡了(事实判断);有些怀念以往那种年味浓厚日子的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变化,但另一些宁可自己自由过的年轻人却可能觉得这是好事(价值判断)。明白这两点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叙述中都会不知不觉将这两者混杂在了一起——平心而论,完全不夹杂自己的价值判断恐怕也极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并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热切关心家乡、对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怀念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把现在发生的许多变化看成是“问题”,在与以往那个“淳朴”的乡村作对比时也就更难以接受这些变化,进而忧心忡忡地认为农村是“衰败”了。问题在于:这个“农村凋敝”的图景常被(包括这些观察者在内)误认为是“事实判断”,但其实它们却常常是“价值判断”。不过,每次这样的话题都激起广泛热议,至少在客观上说明,许多已经离乡的年轻人仍然在情感上相当认同农村老家。前些年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能是近年来最完整系统地从这个角度进行叙述的一本书。作者黄灯以两湖平原的三个小地方为观察点,展现了自己乡村里的亲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命运。乡村风俗摇摇欲坠,缺乏自身恒定的价值观,而被城市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攻陷,新旧价值观交替之际风气败坏,带来精神上的绝望与无奈;农村组织溃败,缺乏有效监督使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结构的瓦解,造成老无所养和留守儿童,亲情、责任感和爱的缺失在代际传递;债务、赌博和买码等造成的人伦悲剧和利益纠纷,进一步破坏了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本侵蚀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年轻一代虽有农民身份,却没有了土地,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时功能的下降,农村家庭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心态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乡村“垃圾处理的无效和无力”,又承认村里的卫生条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她希望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又忧虑19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使得原先那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眼看着难以维系下去。她一方面哀叹现实中教育已越来越难有助于人改变自身命运,回报率似乎越来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断强调应重视教育,然而,最终她又承认现代教育的结果“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说,教育越成功,优秀人才就越会离开乡村,而不是留下来滋养乡村。不难料见,她在对比之下的基调相当悲观:“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风气良好的地方”,“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对此,她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村民,重建起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来抵御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激发村庄的内生活力。客观地说,她所说的很多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这些年来像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等社会学研究,也讨论过乡村社会出现的劣质化,至于留守儿童问题、赌博风气盛行、人际关系疏离等等,则更是人们广泛承认、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鸣的话题。不过,她把故乡原先的状况描述为“人情味极浓、风气良好”,而现状则是“无序、污浊和浮躁”,则是一种宣称为事实判断(“真实图景”)的价值判断,因为她在比较时,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面——例如,原先那种人情味极浓的社会,可想而知也是对个人束缚更大的社会,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却能容许个人拥有大得多的自由。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洪流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对此的反应则因人而异。历史学家王尔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说过,中国保守倾向有一种共通的感觉,就是社会退化观,认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试图以其使命感力挽颓风。但他强调,近代世势本就在快速嬗变,“递新之变化或足以充实原有文化质量,此类情形,粗观则只见人事日非,则必视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适应或不能适应,遂并视为世衰道微。实本观察之错误,乃慨叹今不如昔,衡量社会之变动,又误以为转向退化,则不免自陷蔽锢。此亦反映保守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们扼腕痛惜的社会变迁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种把文化变迁现象视为退化,是历来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错觉,同时也正是一时代观念冲突的重要关键”。确实,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没有“坏的一面”,何况这“好”和“坏”的判断原本就基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好坏兼有的无情历程,有时甚至很难说它究竟是好是坏。只有接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村的确“衰败”了,但这却不见得是坏事。这种“衰败”,最首要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祖祖辈辈以来作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经济学者胡景北论证说,中国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1978-2015年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从92%下降到了59%——也就是说,许多人即便仍生活在乡村,也不再务农。这本身当然就是四十年来乡村变迁的结果,但又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既然那么多人离开了土地开始流动起来(不然何来那么壮观的春运大潮?),那么原先那种血缘群体在一个小地方密切频繁互动的状况就不可能了,家族乃至大家庭肯定会逐渐瓦解,亲情势必淡薄——你一年才难得见一次堂哥表嫂,彼此除了尬聊还能做什么呢?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也从原先那种家庭结构中逐渐脱嵌出来,获得了相对更大的自由度。个人自由的增长与人伦亲情的淡漠,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件事,你不可能既想要前者,又痛惜后者——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小资产阶级在每一对象中看到两个方面,一好一坏,并试图将好的保留而与坏的战斗”,这毕竟是不可能的。对现代人来说,流动是最重要的一项个人权利,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阶层无法获得自我改善的机会,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侵害;与此同时,也只有赋予人们这样的权利,一个社会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让他们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甚至梦想买码发财,都只是许多人试图实现这一点的不同做法;由于刚获得这种自由,许多人还不懂得怎么恰当地运用,也许看上去急功近利乃至不择手段,但毫无疑问地,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有权得到更好的生活。既然别处有着更好的机会,而种田带来的收益又如此显而易见地少,一年下来忙死忙活也赚不了几个钱,那么土地撂荒、乃至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普遍不愿也不会务农,那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理性选择了。在土地抛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对土地进行更高附加值的开发,这看起来确实像是在“侵蚀”农村最后的资源,然而在老路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这也是匡救之本。虽然很多人担心这会让“农二代”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没了务农这一生存手段,甚至担心冲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后谁来种地”),但现实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舍此别无他途。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国和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都低于2%,中国也不例外,未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恰恰相反,历来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就是过密化,劳动力的不断密集投入造成边际效益递减的停滞状况,因为根本不可能让那么多劳动力都耗费在农业上,还能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那个“珍珑棋局”:原先棋盘上子太多太密,复杂到根本无法解决,结果无意中死了一片后,反倒局面豁然开朗,有了腾挪余地。可以说,如果不依靠现代化的力量把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壳打碎,那就吃不到现代社会这个煎蛋。虽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许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许也渐渐没人种了,但从另一面看,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终于开始逐渐摆脱以前那种只能依靠土地糊口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其它变化才有可能随之而来。十多年前,已故翻译家孙仲旭兄曾和我说起他回河南邓州老家的经历,他感叹很多老宅倾圮,草长得老高,田间忙碌的身影少了许多,但最让他惊异的一点,则是村里居然出现了卖包子糕团的店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这确实是中国农村以往的普遍景象:人们过的都是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很多手艺是普遍的技能,因而专业化的分工也就很难出现。就像二三十年前很多妇女都会自己打毛衣做鞋子,那时也就不会去买来穿。只有把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年的回乡见闻不论如何,至少都承认一点:打工或其它非农业收入能极大地改善经济状况。越来越多买车或到县城买房的村里人,毕竟不是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钱。近些年的回乡记中,很多人都注意到农村基础设施变好了,甚至还比以前干净了,连移动支付和嘀嘀打车都普遍渗透到了各地,这些若没有组织力量和市场机制的深入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年春节的另一个特点是:电影在各地小城市都非常火爆,以中国电影的高票价,这种非必需的文化活动正可折射出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了。这些显然是那种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很难出现的现象。就此而言,农村人口流失即便不完全是“好事情”,至少也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壮劳力都出走了,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势必衍生出新的问题,冷冷清清的村庄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衰败”和“凋敝”,村庄的空心化由此让许多人痛心,但如果要把那么多人继续束缚在土地上,那带来的问题只会更大。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城乡交流破坏了原先的乡村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确出现了各种失范行为和无序现象——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宋代和晚明都因城市繁荣而出现了不少脱离土地的游民,他们不事农业、游离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但却也代表着一股新的活力,官府的反应却是竭力想把这股危险的新兴力量塞回到宗法社会的紧身衣里去,其结果是中国始终未能打破固结的农业社会结构,自发走向现代化。如果误以为把农村劳动力从城市里重新赶回去就能重建秩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那不仅因小失大,而且还将重蹈历史覆辙。要想从历史的循环中挣脱出来,那现在应该做的是顺应新的变化,制定新的规则来匡正新出现的问题。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每一场革命性的变迁之后,在通向新繁荣之路上,总要穿越一个“泪谷”,那包含着瓦解、痛苦的自我否弃与最后的重生。这么说并不是为了以最终目的来把过程的痛苦合理化,只是说,在面临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时,既不要片面地归罪于现代化本身,也不要相信回头会是更好的选择。现代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继续加深现代化、建立新的应对机制,并对现代化加以反思来获得解决。这种反思当然也很必要,对传统衰微的抱怨也会带来复兴,但它不可能再回到原先那个样子,恰恰相反,当那些乡村被怀旧的人们重建起来后,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了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