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yings:
4 月 6 日,我们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共同举办了一场谈话,嘉宾是你很熟悉的喜剧大师陈佩斯,和他的儿子陈大愚。上一秒陈佩斯说自己拍短视频,能明白里面的笑点,下一秒陈大愚就拆穿:“拍之前得问半天”。当陈佩斯说自己紧着跟但也有不太适应时代的时候,手机总是输错密码,陈大愚却吐槽说,这是他爸不想请客吃饭的借口。别以为笑笑就完了。这场谈话一直围绕着一个有点悲壮, 又很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梦惊已是新天地”。——当一个人赖以吃饭的行当、技巧、本事,正在被新时代轰轰烈烈地碾压,除了眼睁睁瞅着,他还能怎么办?我们把活动的精华部分剪辑成了一个视频,就在下面,强烈推荐你笑过之后,好好品一品。陈佩斯也被“新时代”“碾压”了。他坦承,作为一个喜剧工作者,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梗、段子、流行语,他很多都弄不明白。但他从来没停止研究能逗乐当下年轻人的东西。“喜剧就等于是一种承诺。”笑,是陈佩斯对观众许下的承诺。69 岁的他,依然活跃在喜剧舞台上,依然受人喜爱。上次我们官宣活动后,票几乎秒空。“承诺”赋予人原始的动力和野心。想一想你曾“为了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事”,无论目前怎样过程怎样,你都能打起精神来把它实现。以下是精华内容文字版。当熟悉的环境在崩坏,你一定能从中找到你的支点。 “观众在哪儿乐,
我得弄清楚了。”

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谁了。看过陈佩斯老师和陈大愚老师一起演的作品的人,还是有不少的。看过他们在社交媒体,在抖音和视频号上拍的短视频的,比刚才的多。陈佩斯老师,您自己对于拍的这些短视频,这些剧情您理解吗?


您确定吗?您每次拍之前都得问我半天:“陈大愚,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不解释他是不知道的。

我就得弄清楚了,因为现在很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这个年纪是糊里糊涂的,我听不懂什么卷不卷,还有很多网络流行语,有些乐现在我都看不明白了。有些年轻人看着挺逗的事,我看着,没说什么呀,没什么呀。但是他们听着都很乐。所以有些是他们觉得特可乐的事,我看着不可乐,我得请教一下,你们看着哪儿乐呀?我得问问年轻人,观众在哪儿乐,我得弄清楚了。弄不清楚,演的时候就容易糊涂。弄清楚就好办。

顺着刚才那个话说,您说有些年轻人的笑点,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好笑了。现在排练也面对很多年轻的观众,您有什么感受吗?

我看不懂是对的,是好事。年纪大的看不懂了,这是好事,这是社会的进步和变化,社会永远要变化。如果社会二十年前大家看什么,二十年后还看什么,三十年后必须看什么,这个社会没法进步了。该过去、该翻篇的,就得让历史过去才行,不能老往回翻历史。所以,我特别喜欢看现在我看不懂的那些,现在都是脱口秀、短视频,我特别喜欢看、特别喜欢听。我力图去接近今天的社会,接近这些年轻人,我要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

不可能,那是不可能,我没那么笨、没那么蠢。我怎么能那么蠢?要不然能有今天吗?我不是自夸,这是一个喜剧人起码的艺术素质。我必须得跟上时代,我要跟不上,随时会被淘汰掉,这错不了的。
02、
“我们都知道,
它最后还是要归于湮灭。”

今天这个主题叫“梦惊已是新天地”,也是出自父子俩一起出演的舞台剧《驚夢》。因为“梦惊已是新天地”这句话本来就是在《驚夢》这个宣传册里面看到,我很喜欢。大家先跟各位说一说《驚夢》是一个什么戏,它有什么特点?
剧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留给大家到剧场里面观看会更好,我只是泛泛聊一下我作为一个演员从创作到演出整个的感受。《驚夢》这个戏里有战争对于人的摧残、有昆曲的美丽、有别离时的悔恨和痛苦,也有生死的考量。很多很多的元素汇合在一起,都是很冲突、很极致化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旧的价值观和新的价值观的碰撞,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碰撞,这些东西都汇合在一起,我感觉这个戏突然之间就会有一种悲悯感,它会很慈悲地看着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角色在台上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像烟花一样炸开、美丽、消失,炸开了又美丽、又消失,最后感觉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感觉这是艺术。《驚夢》还是很厚重的一种艺术的感觉。它富含的艺术元素非常多,这是我粗粗的一种感受。
它写了战争的残酷、人生命的无常,还有生命的宝贵,还有那一个一个为了自己理想牺牲的人,他们精神的崇高。同时还有艺术的瑰丽,美丽的艺术、美丽的艺术形式,我们又同样能够感受到它也在战争中被摧残、被戕害。一直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它最后还是要归于湮灭。所以,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怀旧,像一场梦一样。

其实像《驚夢》、包括《戯臺》(陈佩斯率大道文化于2015年推出的舞台喜剧),相似之处都是在讲年代转换、新旧交替。新天地马上就要来了,而且这个叫“瑰丽”的东西、旧时代的东西正在被抛弃掉,或者在被碾压的感觉。

对,《戯臺》在高一层的主题里也有这个东西,它再好、再美也是将要过去、将要逝去的一段历史了。所以,每次自己演到这儿的时候都会很伤心。其实我对京剧也好、对昆曲也好,都不甚了解,我就是了解一点皮毛、捡一点皮毛为我所用而已。但是我每次演它们的时候,每次演到这种时候,内心都会是一种伤感。

这种伤感是,比如说从您心里来看,是对于那些东西的失去的遗憾?


刚才您说到昆曲,在《驚夢》里面昆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您怎么样来理解昆曲,怎么看待昆曲的美?

我看昆曲跟别人看不一样。别人一般看都是说,它很美、很漂亮,它确实是形式美、形式美美到极致,无论从戏剧文学、从词曲,到演员的表演、身段,所有身段的各种细节到唱功,无可挑剔,应该说是艺术的顶峰。
因为它不能在广大的人群中去传播,普通人看不懂,也不需要这么看,它不符合艺术规律。严格地说那么美的东西,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东西。为什么呢?这个艺术形式只存在于三百年前、四百年前的那些高端的知识分子阶层里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士人的家里和他们之间应酬的小范围演出。所以,它的没落是必然的。而且它的形式为什么能到这种程度?也是因为一个畸形的社会造成的。我们能推断,当时明朝的文化市场肯定是有问题的,老百姓不能正儿八经地看戏了,所以只在这些精英的家里面养着的班子,它慢慢养育出这么一些东西来,它确实做成了精品,可是它没落又是必然的。我要是解读昆曲,我就说,从它的生就注定了它的灭。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悲哀的事情。

所以在《驚夢》里面,推翻这个时代的是为老百姓演戏的要求。

推翻这个的是《白毛女》,是有普适价值的。人人要有土地、人权的要求。一个有钱人把白毛女就买去了,对这种旧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就成了老百姓要看的东西,迅速地就传播出去,然后就改变了历史。我有点剧透了,不说了。关键是它是一个革命文化的传播,它这种力量从哪来的?它赢得人心,这就没办法。所以,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您在戏里面演的这些角色本身,可能不一定理解或者谈论时代这么大的话题。而是,他自己坚持了很久的,他很热爱这个事,热爱自己的行当、喜欢自己的班子,但突然碰到了一个自己适应不了的时代变化。因为您也是经历过很多变化的人,一个人突然碰到这样的状态,觉得自己跟时代格格不入了,他应该怎么自处?

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前年上云南丽江去,下了飞机进不了门了。我拿出手机弄不出绿码来,进不了门了。很多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同志们,他们边问,边在手机上鼓捣鼓捣进去了,就我这年纪大的就不行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哪儿跟哪儿?谁跟我过不去我也不懂。在那儿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关键那些保安守着你走不了,有一个人在外边,他们最后帮我弄,一点一点给我捅出来。这种事情还特别多。吃饭扫码也是,经常有时候请客吃饭,我大大咧咧的,说好了,我请客,都别走。一会儿回来了:“你们看谁去。”就扫不出去了,银行卡(密码输错)三次以后就锁死了。有时候你知道,但是你越想这个东西有点高科技看着它你就捅不准。错一次,第二次就刁难你,三次,锁密码了。尴尬几回,行了,我也不请客了。
03、
“喜剧是一种承诺。”

陈佩斯老师,您在台上面对过很多不同年代的观众,您觉得在笑,或者在逗观众笑这件事情上,不同时代的观众有变化吗?

有变化,而且一直在变化。某些地方一年不去,可能你再去的时候,笑声就变了。时代在变化,你在变化,他们在变化。笑声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性别变化。九十年代以前剧场里的笑声多是男性的,女性的少。逐渐地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你会发现,首先,这个笑声是从八十年代突然回到我们身边了,回到百姓身边了,这是一个基本条件。然后你会发现,一开始是男人们在笑,女人们笑声少。到了2000年以后,逐渐地女性的声音在多、在增长。到二零一几年以后,女性成了笑声最大、最多的声音了。我老提醒他们,搞喜剧一定要号时代的脉搏。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听听,现在女性笑的成分多。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将来在创作的时候是给谁创作的,谁给你饭吃。

这个变化是陆续发生的。您会有时候发现自己的笑点变得不那么好笑了,有这样的时刻吗?


所以是不是说明,观众也许在变,但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方式是不变的?

这是其一,其二,我认识喜剧和别人认识喜剧不一样。我去从根上认识、从包袱上去认识,别人永远追着时髦的东西。最近时尚是什么话题,他也说什么话题。

最重要的还是观众的价值评判、观众的道德评判。因为确实会以百年为进程去调整、去变迁。一百年以前的戏肯定是紧扣着当时时代的脉搏。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戏已经变得有点悲情。不是戏本身的问题,是观众的道德标准有变化。最简单地来说,男女平等了、恋爱自由了。过去莎士比亚的戏,男女之间的恋爱是很禁忌的事情。社会在不断调整,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变迁。喜剧人唯一不能变的就是抓住观众的价值判断,还有公序良俗,别的没有什么特别不能变的。观众的价值判断是人们的普适价值观,不是说金钱观、爱情观,不是能单拎出来的东西。

价值判断特别重要,人类的笑声行为里面,本身就包括价值判断的元素在里面,它组成人类的笑行为。

很多喜剧都会有反转。喜剧是让人笑是重要的,还是让人思考,还是说让人带着泪的微笑?

我们俩可能会有意见不同,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先说剧,喜剧两个字,终究剧是最重要的,剧就有剧的评判标准,大家还是要了解怎么样创作故事,故事的要求就是让人思考、给人以力量。喜剧就是引发笑声,我感觉是看各种各样事件的态度。

可能这个题目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谈到的,以及今天搞创作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甚至要探讨这个问题。当你问他喜剧应该是以什么为第一,要侧重你故事的教育意义,还是要侧重笑声,其实这个问题是伪命题。第一,喜剧就等于是一种承诺。对吗?我说我要演一个喜剧,你要演一个喜剧,首先你有一个承诺在先。要么你就说我就演悲剧,我就要用戏来教育你一段,给你一个教育戏剧。不是,它一定要拎出来是喜剧,我们要把这个事分得很清楚,逻辑上要清楚。当我们确定它是喜剧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了,再说能不能表达清我要讲的议题和我要表达的思想,是不是这个?如果你第一个没完成,我拼命地说我要表达教育意义,这是没有意义。其二,我一共十分钟的作品,我把后三分钟、五分钟全切下来给了教育。前面哪怕我用什么包袱都行,后面三分钟我要完成教育目的,这就有点生硬了。其实它是讲不好故事,所以才用了这种方法,叫做省力、偷懒。它是一种偷懒的方法,我又完成了我领导的任务、主家给的任务。我又把这个任务给了观众。这种东西它在喜剧艺术上永远进步不了。一个十分钟的作品只能讲八分钟,只能凑合五分钟,它只有这个能力。
Q&A环节:
Q1:一位观众的问题,问陈大愚,做话剧演员是从小的梦想吗?有没有想过别的生活?

有,有想过。经商、做科学家,都想过,想着玩,演员肯定得想象力丰富。但是做话剧演员真不是我从小的梦想。做演员也算是半路改行之后定的一个目标,跟梦想谈不太上。我小时候,16、17、18 岁的时候,我跟我爸争执,我们俩争执的问题集中在,人的物质生活更重要,还是精神生活更重要。他觉得精神食粮更重要,我觉得物质生活更重要。我要当科学家,要让大家吃饱穿暖,他就做艺术家,提供精神食粮。后来确实是出国留学,受了“洋插队”的苦,慢慢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个人慢慢地接受了他的想法,觉得精神食粮还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改行了,就走了演艺这一条路。之前想试试当演员,如果不行,往编剧上走一走,再不行(转)出品人、投资人。
说到根上,我是真的不想让他做这一行。他也是因为没经历过,他都从旁边冷眼看过我们排戏,没有亲身参与过,一进来就知道有多难。Q2:从你的角度来说,现在你可以跟他同台演戏,可以一起做创作,一起讨论这个戏应该怎么排、怎么做。你难道不发自内心地高兴吗?

那是另外一件事。首先,我不愿意他做这一行,这是过去。既然他选择了,我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培养他、帮助他,这是一定要去做的。尤其是不容易。我们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子承父业的很少,到他这儿,他又是第三代了,就更少了,他是特别的“濒危物种”,就因为他太难了。他又难,收入又不相匹配,这个难上加难。在北京曾经很多年,花钱买票看戏是一种耻辱。世纪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看戏花钱是耻辱,全中国都是这样。走到哪儿去,一说陈佩斯他们演戏,我要看《托儿》,打电话,全是这个要票,互相要,票房就在那儿开着窗户,他也不去。因为几十年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你能怪他吗?几十年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们在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们在重建社会秩序,我们在重建社会良好的公序良俗。还有一个是人与人对等的关系。喜剧要建立在什么上?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你能够看我的戏在笑,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上,就是人与人平等的关系。Q3:有一位观众想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您执着于话剧舞台艺术,而不再是之前影视作品的创作?

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电影不好玩儿,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会很少。只要这个东西一滚动起来,你得受资金的限制,得受工作进程的限制,整个流程都在限制你。你突然发现我这个戏从剧本上有问题,你想改,改不了。印到胶片上了,现在是放到数字系统里了,所以你不能再重新做。你想把它再精致、再完美,不行了。所以,不好玩儿。搞艺术的希望做一个最精美的东西和观众一起切磋。因为我设计这些喜剧包袱的时候,都是设计给他们笑的,他们用笑声参与一起完成这个喜剧,这是最美好的。但面对观众,姿态又放得很低,说自己搞艺术,就是为了给老百姓看。大众看这场戏能不能觉得开心,能不能笑出声来,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能在一场喜剧表演中真正得到快乐,这应该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大的尊重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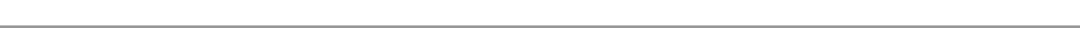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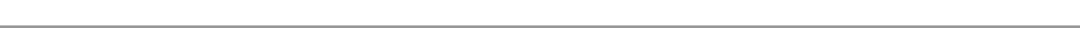 晚祷时刻:
晚祷时刻:
“我设计这些喜剧包袱的时候,
都是设计给他们(观众)笑的,
他们用笑声参与我一起在完成这个喜剧,
这是最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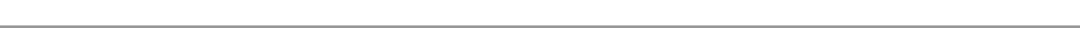
喜剧工作者最喜欢的赞美声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晚祷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