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作者:我是艾公子
获取更多好看文章,请关注最爱历史。
文章已获授权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廿七日(1906年7月18日)夜,万籁俱寂。突然,京师东北角、地安门外小菊儿胡同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凄厉哭声。由于时值亥末子初,几乎没什么人在意胡同内的这声异响。直到天明时分,接到镶黄旗旗人领催文光的报案,镶黄旗甲喇厅管事德勒额才带着手下火速赶到事发现场。原来,昨夜那阵凄厉的哭声,是文光家的新妇春阿氏发出的。满人习惯称名不带姓,阿氏的丈夫是文光的长子,名叫春英,嫁给春英的阿氏也就随了夫家的惯称,改称春阿氏。春英深夜离奇死在房中,脖子上还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刀口,显然这件事与春阿氏脱不了干系。于是,办案的官差将春阿氏列为头号嫌疑人,交付管理京师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事务的左翼公所从严查办。“春阿氏杀夫”由此被立案,经左翼公所、外城巡警总厅(步军衙门)、刑部、大理院(大理寺)层层审理,终因证据不足,比附“强盗罪”定案,判处终身监禁。清末司法判决的荒谬,致使“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纭,莫明其真相也久矣”。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1909年3月31日),春阿氏入狱仅两年多,就“瘐毙狱中”,成为乱葬岗中的一缕孤魂。
▲1941年上海《申报》内页里的《春阿氏》戏剧广告。图源:网络春阿氏的暴毙,让这起悬疑命案的真相一同长埋地下,但背后的诡谲大局却始终若隐若现。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生活在晚清旗人社会里的春阿氏便是这样不幸的人儿。据清末司法档案记载,春阿氏原名“三蝶儿”,是镶黄旗满洲松昆佐领下阿洪阿之女。父亲阿洪阿早年在旗下做过一阵子的“公务员”。靠着父亲的俸禄加上旗人固定的旗饷,春阿氏在原生家庭的日子虽称不上富裕,倒也算是小康。春阿氏有兄弟常禄、常斌二人。旗人成家早,哥哥常禄刚满十六就离开八旗学堂,去往步军统领衙门巡捕营谋了一份差事。这本应是春阿氏一家奔向幸福生活的信号,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阿洪阿却突然病故。家中顶梁柱一夜崩塌,哥哥那点微薄的收入加上日益缩水的旗饷根本撑不起这个四口之家。春阿氏的母亲阿德氏表面上为人拘谨朴厚,言容郑重,一举一动都颇具章法,可实际上却是个毫无和蔼之气、对子女态度冷漠的母亲。家道中落,春阿氏刚满十六,阿德氏就着急把女儿“脱手”嫁出去。不过,阿德氏将嫁女儿看作是一门“生意”,尤为看重未来亲家的财力。直到春阿氏19岁那年,将女婿筛了一遍又一遍的阿德氏才相中了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文光,把女儿许配给文光的嫡长子——有些呆傻的马甲春英。文光一家在镶黄旗下虽然也是小门小户,但文光是在任的旗下“领催”。每逢朝廷按期发旗饷,领催都是这笔巨款的经手人。可以说,只要清朝还继续维护着旗人的“铁杆庄稼”,春阿氏嫁给春英就能让娘家在衰世里吃穿不愁。
▲“春阿氏案”案发地小菊儿胡同位于今天北京南锣鼓巷一带,如今已是著名商业区。图源:摄图网显然,文光一家也很清楚亲家阿德氏是在“卖女儿”。因此春阿氏嫁给春英后,白天给文家长辈当丫鬟,晚上还得负责给丈夫暖床。文家一日两顿、浆洗衣服、洒水扫地,通通成了她婚后生活的点点滴滴。春阿氏任劳任怨,以尊重长辈、爱护丈夫为己任,默默地为这个新家付出,只待深夜才敢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可即便如此,打从心底里瞧不起春阿氏一家的文家人还是没给她好脸色看。春英的生母文托氏是文光的正妻,仗着大婆母的身份,她总嫌春阿氏伺候人的动作太慢,有事没事就给儿媳立规矩。而文光的小妾文范氏就更劲爆了,据跟踪报道“春阿氏案”的《京话日报》披露,文范氏早年曾是八大胡同里诨名“盖九城”的妓女。跟文光从良后,她又迅速出轨了文光的好友普云。普云与文范氏的“多人运动”,曾不慎被春阿氏撞见,故文范氏一直视春阿氏为眼中钉,肉中刺。春阿氏每回被大婆母训斥得抬不起头来时,文范氏总会在旁边落井下石。在这种长期压抑的家庭环境下,“自思过门不及百日”的春阿氏萌生出了“乘间寻死”、一了百了的想法。春阿氏的心态变化,阿德氏不知,文家人不知,春英更不知,可老天爷却似乎有了预感。“春阿氏案”案发前一周,春阿氏的大婆母文托氏的娘家长辈过世了。按照传统,文托氏得回家奔丧,披麻戴孝。临行前,文托氏习惯性地命令春阿氏替她浆洗孝服。春阿氏敢怒不敢言,只想洗完这最后一遭,当晚就自杀。
▲1989年电影《春阿氏疑案》里的春阿氏。图源:电影截图
但,这回不巧,文托氏不知出于何故,竟让春阿氏陪她回娘家给祖辈上坟烧香。一来一回,让春阿氏的自杀计划耽搁了一个星期。正是此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让本来无关此事的春英,在这时被卷了进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廿七日夜,春英像往常一样进入春阿氏房中倒头就睡。此时的春阿氏已打定自杀的念头,丈夫在床上呼噜声震耳欲聋,她的内心却平静如水。简单洗漱后,她缓步走向厨房,拿起菜刀准备朝自己身上砍去。但终究没下得了手,她又拿起菜刀走回了睡房,来到春英的床边,对着他哀叹。没想到,习惯侧睡的春英这时突然转身,从背对春阿氏变成面向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春阿氏一时慌乱,站立不稳,拿着菜刀直愣愣扑到春英身上,以致刀口精准命中春英的颈部大动脉。鲜血喷涌而出的那一刻,春英也被痛得跳了起来。而春阿氏则被自己的失手,吓得哭了起来。但哭声除了惊醒熟睡中的文家人外,对倒在血泊中的春英并无帮助。很快,因失血过多,春英丧命。春英死后,春阿氏立即将菜刀搁置在外间的桌子上,自己冲进厨房,投入泔水缸内,意图自杀。此时,已被惊醒的文光和文范氏也冲进厨房,救下了寻死的春阿氏。至此,案发后,春阿氏是第一个从房中跑出来的当事人,而且她还在慌乱中磕伤了头部,最后又意图淹死自己。种种不合理的行为,似乎都在向文家人昭示,是她杀了自己的丈夫,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畏罪自杀。
文光到底是一家之长,文家与阿家又有亲戚关系,他只想知道事实真相。于是,他连夜写了封信,请阿德氏前来陪护女儿,并劝说春阿氏说出案发经过。结果,寻死不成的春阿氏拒绝了夫家最后的“好心”——她坚定地称自己愿一命抵一命,只求速死。春阿氏对杀夫供认不讳,还想照顾两家面子的文光只能将她解送左翼公所公开审理。如果按春阿氏在档案交待的那样,她杀亲夫,不过是意外所致,在法律上属于过失杀人。按照《大清律例》,凡过失杀人,应按“六杀”中的“斗杀”为标准处罚,最高判“杖一百,徒三年”,怎样都达不到春阿氏借杀夫案寻死的程度。再者,承审官员们认为,既然春阿氏早有寻死的打算,从五月廿日到春英毙命的五月廿七日,有7天的时间,足够春阿氏求死。况且,文托氏是激起春阿氏自杀的诱因,在陪文托氏回其娘家上坟时,春阿氏内心应该是最挣扎的,可她却始终没有自杀,一直拖到五月廿七日夜才拿着菜刀回房,失手杀了丈夫。在丈夫毙命后,她也没有第一时间自杀,而是从容淡定地放下菜刀,跑到厨房,投入又臭又浅的泔水缸中,实在不合常理。承审官还根据仵作的验尸报告提出误杀无法成立的推论:“春英咽喉近右一伤,横长二寸余,深至气嗓破,显系乘其睡熟,用刀狠砍,岂得以要害部位深重伤痕诿为误碰?”
▲《刑部题定验尸图》。图源:网络
承审官的推论可谓有理有据,春阿氏是站立拿刀对着横躺的丈夫,两人几乎呈90°姿势,倘若春阿氏惊慌失措致使菜刀掉落毙杀春英,那致其死亡的刀口多半只会留在胸、腹之间。即使春阿氏真的精准命中了春英的颈部右大动脉,以她惊慌失措的状态分析,春英的尸身也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刀口位连续下几刀,直至“气嗓破”的可能。
既然春阿氏不可能误杀亲夫,那她为什么要对杀夫之事供认不讳?于是,承审官依例就春阿氏与文家日常关系、春阿氏品行及案发详情等传召文光一家及小菊儿胡同的左邻右舍上堂质询,打算从中抽丝剥茧,还原事实真相。可文家人及左邻右舍给出的供词,又再一次将春阿氏杀夫案推向了“疑案”的一端。据小菊儿胡同的左邻右舍交待,春阿氏平日里品行端正,夫妻恩爱。因为年纪尚小,春阿氏还有点稚气未脱、童心未泯,实在看不出她有杀人的动机。文家的“大家长”文光的供词也与左邻右舍差不多。他称,春阿氏嫁到他家不过百日,平日里对公婆恭敬有加,也未曾与儿子春英有过什么争执冲突。对于儿媳为何要自杀,儿子又为何死在房中,他属实不知。对于春阿氏在供词中倾诉怨恨的文托氏和文范氏,承审官也进行了重点盘问。文托氏交待,在新妇过门的百日里,她是嫌弃过儿媳手脚慢,伺候老人不卖力,但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未施以体罚。春英的祖母德瑞氏尚在,老人家对这个孙媳妇疼爱有加,所有人都不会自找不痛快。即使自己言语上刻薄了些,那也属于正常的管教儿媳。文范氏则坚称,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致春英身死而后快”。但对于春阿氏的奸夫是谁,春阿氏如何与奸夫相会等细节,文范氏却给不出合理的证据。
▲文范氏与情夫普云。图源:电影截图
这时,文光之母德瑞氏给出了她的目击证词:“伊因老病,每晚睡宿较迟,是晚十二钟后,伊听见西厢房春阿氏屋内响动,伊恐系窃贼,呼唤春英未应,复闻掀帘声响,并有人跑过东屋脚步行走声音,伊遂唤醒文光等,点灯走至西屋,见春英躺在地上流血,业经气绝。春阿氏不在房内,至找东屋厨房,始见春阿氏倒身插入水缸,当由文光等救起控活。至春阿氏因何杀死春英,伊等均无从知晓。”由此看来,在没有发现其他嫌犯的前提下,春英是怎么死的,恐怕只有春阿氏才知道内情了。于是,左翼公所根据案件进展,初步给春阿氏判了个“绞监候”,交付上级依规审转。或许春阿氏真的是命不该绝,案件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时,清廷内部也正忙着为“预备立宪”作最后的刑律变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沈家本、伍廷芳联名上书《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朝廷很快予以了“照准”的批复。至此,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酷刑重法——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配等均被废除,中国的刑罚也由野蛮朝向文明迈了一大步。次年,也就是“春阿氏案”的同一年(1906年),清朝又采纳了沈、伍二人的建议,对实施了逾两百年的《大清律例》进行删减与修改。除了前面提到的凌迟、枭首等古老且带有侮辱性质的人身伤害刑罚被彻底废除外,清廷也就《大清律例》中原有的戏杀、误杀、擅杀等应被判为绞监候、斩监候等虚拟死刑的法律判决,进行了新的司法解释。
按照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的意见,轰动京城的“春阿氏案”应该适用于新司法解释中“误杀”这一项。新司法解释中的“误杀”,实际上仍沿用《大清律例》中“误杀”罪名的解释,即:“凡因戏而杀伤人,及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各以斗杀伤论。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伤者,验轻重坐罪。”不过,“春阿氏案”最大的疑点还在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者春英生前与春阿氏发生过“斗殴”。也就是说,春阿氏如果要按误杀罪判其“绞监候”,缺少合理的司法判据。况且,基于清廷比照西方法律体系作出的这次刑律变革,西方法律思想里的“疑罪从无”也是清末法律界人士改革判案思想的重点。因此,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一批法律界“巨公”的干预下,春阿氏未能以“绞监候”罪获得秋后勾决。在“监候刑”之上,《大清律例》中还有一项更重的刑罚——“立决”被新法保留了下来。《大清律例》原有的司法解释是:“凡妻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决;死者,斩决;故杀者,凌迟处死。”像“春阿氏案”的状况,春阿氏“殴夫”至死,即便实情可能有误,但就结果本身而言,官府判其“斩立决”也算是有理有据。然而,负责修订新法的沈家本、戴鸿慈、刘若曾等法学家又认为,清廷新法应该删除“重法数端”,即“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仍入于秋审,分别缓实办理。”如此,原先本应适合斩立决的春阿氏也就一路被递减罪名至“绞监候”。▲清末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图源:网络
但,“绞监候”规定的罪名解释又不符合“春阿氏案”的现状。两相矛盾,致使此案从“有法可依”走向了“无法可判”。一桩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误杀命案,就此变成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悬疑公案。“春阿氏案”判又判不得,放又放不了,不仅让清廷各级承审官头疼,也很快引起了京城百姓的街谈巷议。在清朝“预备立宪”的浪潮推动下,各地改良派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也成为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判决前后的非官方发声渠道。其中,在北京,《京话日报》便独家追踪了“春阿氏案”的审理进程。
▲《京话日报》。图源:网络
这家报纸自创刊之日起,就确立了以白话文的报道形式“开民智”的办报宗旨。从该报就“春阿氏案”发出第一篇“编者按”起,民间知情人士纷纷给报社发去秘闻,一步步揭露明面上看不到的内幕真相。据说,春阿氏对“杀夫”供认不讳,实是公堂严刑逼供的结果。爆料人称,他们在公堂外亲眼看见承审官“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磺,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他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对于上述爆料人的说法,《京话日报》还收到另外三封匿名来信证实此事。匿名信称,承审官这样屈打春阿氏,与“盖九城”文范氏有关。她用钱贿赂了本案相关的三名承审官,“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京话日报》随后又发出一则“编者按”:“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正凭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很明显,《京话日报》介入此案,不单是为了给春阿氏发声,更是在践行“开民智”的办报理念。紧接着,一则带有争民权、反独裁意味的读者来信被刊发于该报上。该信件是由一位名叫“琴心女士”的人所写。信中说:“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他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什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这下可好,如何判决“春阿氏案”,上升为官方在“预备立宪”背景下如何看待民权的风向标。为防止有人借突发的公共事件干扰朝廷立宪进程,“琴心女士”的信件刊发一周后,《京话日报》即被清廷勒令停刊,“春阿氏案”也被正式提到大理院进行终审。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距离“春阿氏杀夫”案发已过去近两年时间,大理院迟迟未就春阿氏的罪名提出最终审理意见,这不禁令慈禧太后大为光火。她以光绪帝的名义给大理院发了道圣旨,要求承审官员“务令按限清结,严定考核劝惩之法”。“春阿氏案”这才进入了实质性的终审阶段。对于这宗“死无对证”的案子,承审官们都知道,“仅据(春)阿氏口供,万难断拟”。可圣旨在前,即使该案事实模糊不清,真凶实难辨明,这个时候也必须要定谳,给上头一个交待!于是,根据此前左翼公所、外城巡警总厅等各部门的办案结论,大理院的承审官们给朝廷联名上奏:“臣等查核所供情节,系属误伤,尚非有心干犯。按照律例,得由妻殴夫至死斩决本罪,声请照章改为绞候。惟供词诸多不实,若遽定拟罪名,一入朝审服制册内,势必照章声叙,免其予勾,迟至二年,由实改缓;如逢恩诏查办,转得遂其狡避之计。且万一定案以后,别经发觉隐情,或别有起衅缘因,亦势难免追改成狱。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据,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尸棺即饬尸亲抬埋,凶刀案结存库。再,此案因未定拟罪名,照章毋庸法部(刑部)会衔,合并声明。所有杀死亲夫犯妇,他无佐证仅就现供,酌拟办法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请旨。”“春阿氏案”虽然有春阿氏的口供,但案件存在许多疑点,在当时的办案条件下无疑是疑案一桩。而承审官员最终的逻辑却是,既然上头制定的司法解释无法囊括本案不合常理的方面,那就先随便找个罪名把人关起来,日后再慢慢破解,找出真相。如果真相始终找不到,那就把春阿氏终身监禁。如此,不管未来结果怎样——有罪则杀,无罪则放,至少承审官们自己是安全的,永远无需付出错判的代价。至此,春阿氏免于一死,但从此住进了阴森腥臭的监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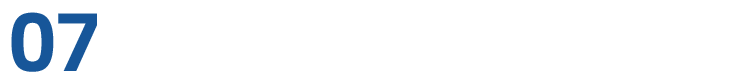
那么,“春阿氏案”到底存不存在第三人作案的可能呢?据清末文学家冷佛所写的长篇纪实小说《春阿氏》记载,在“春阿氏案”移交大理院审理时,最初侦办此案的左翼尉乌珍并没有放弃对该案的推理与追凶。
▲清末民初旗人作家冷佛(1888-1946)。图源:网络
经过多番调查,乌珍证实了“春阿氏案”的真凶为春阿氏的表弟聂玉吉。聂玉吉之所以对春英下杀手,全因他早年与春阿氏青梅竹马,也有过一纸婚约。但,后来聂家家道中落,春阿氏的生母阿德氏看不起聂玉吉这个穷小子,遂把女儿连嫁带卖送到了文光家。在文家,春阿氏与聂玉吉始终未断联系。听闻曾经的恋人在夫家受尽婆婆刁难,聂玉吉决定带着春阿氏远走高飞,不承想他们准备离开的当晚,被春英无意间撞破。为免丑事外扬,聂玉吉失手杀了春英,而后春阿氏不想聂玉吉遭受杀人罪的指控,遂在房中大喊大叫,逼聂玉吉离开,并决定顶包背下“杀夫”罪名。乌珍本已查清真相,关键就是要承审官捉拿聂玉吉对质,但大理院给出了终审意见,“春阿氏案”一时没有平反的机会。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年仅21岁的春阿氏病死狱中。这桩牵动着百姓情绪及清廷“预备立宪”进程的大案、要案、疑案,彻底落下了帷幕。几天后,朝廷承诺各省会在当年内完成咨议局选举,听取民意,让天下人看到朝廷施行议会政治之决心。可明眼人都知道,清廷发起“预备立宪”的元年,正是“春阿氏杀夫”案发的同一年。刑律变革领议会政治之先,“春阿氏案”却迁延三年而未决,“预备立宪”又岂有一帆风顺之理?是的,自从答应天下人要筹建咨议局开国会,清廷又上演了一出“拖”字大戏。参考文献:
冷佛:《春阿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黄源盛:《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
徐忠明:《办成“疑案”:对春阿氏杀夫案的分析——档案与文学以及法律与事实之间》,《中外法学》,2005年第3期
安忆萱:《“春阿氏案”与晚清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