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贼喷射的墨汁中追问西藏——《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自序
在乌贼喷射的墨汁中追问西藏
——《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自序
(瑞典)茉莉
即将出版这本文集时,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话:“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内容了。自从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我的全部涉藏写作,都是在如乌贼喷射的墨汁中,力图揭露谎言,引起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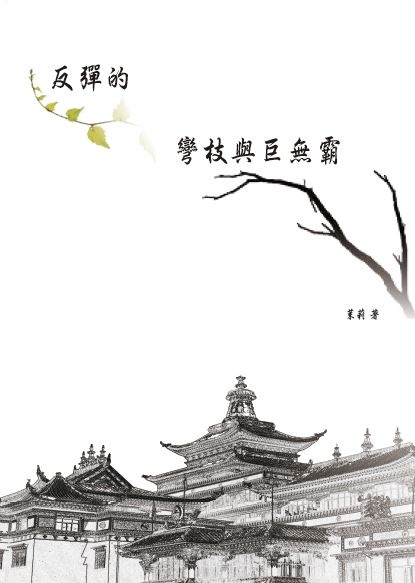
用惊人的洞察力揭破这个世界的谎言,这只是作家奥威尔写作的一个方面。更令人向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写作境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于2007年在台湾允晨出版《山麓那边是西藏》后,十年又过去了,我是否在写作中获得了审美体验,是否给自己的政治性写作增添了一点艺术性呢?这是我在出版新书时所沉思的。
@ 用真实的文字与强权分庭抗礼
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感谢《开放》、《争鸣》和《动向》等几个坚守民主人权立场的杂志,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我发现写于不同时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来就有了一种整体感。
书名“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指的是中国强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伯林的一个比喻。伯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在评论2008年的拉萨抗议事件时,我曾借用这个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义”,觉得很贴切。
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时,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时,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去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
巴尔扎克说:“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他指的是,作家出于一种对于更高原则的忠诚,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对抗黑暗。写作者要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尽责,必须敢于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书写西藏时,满怀认识的激情去探索一个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对于他民族的同情与理解,以及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的能力。
@ 身为批判型作家的瓶颈
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长期的写作中,往往会产生某种疲惫无力感。我曾在涉藏写作中遇到一些瓶颈。因此有很长时间转而去写其他题材。
首先有一个自我重复的问题。 在涉藏的文章中,我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些相同的观点。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为人权呼吁的写作者也就只能针锋相对,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样的思路去揭露、抗议和批判。尽管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却因此耗损了不少,其重复性的批判落到低于历史水平的地步。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感慨:“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头来把自己都变小了。”
中国的老子曾说:“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我的另类理解是,为学者追求的是知识,可在自己的专业里日益增长其学问;而为道者却试图改善社会,需要在公共领域传播其理念,以抵抗统治者的谎言。由于为道者宣传的大都是常识,因此无法使学问精深。
汉娜.阿伦特在面对习以为常的恶之时,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认为,邪恶除了平庸之外空无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创。身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思考。
当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问题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为了表达一点正义的声音。在批判的同时,我也尽量吸取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获得另一种视角去看西藏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
@ 用论据逻辑诚实地说理
重读自己的书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较上一本《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本书显得较为理性,在分析论说上更为透彻有力。写上本书时,我初涉西藏问题,作为第一批汉藏协会的成员访问达兰萨拉,开始了解藏人的流亡。同为异乡流亡客,当时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动,笔下的文字也就比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所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过去的涉藏写作,我较多地谴责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较少。现在我的年龄不轻了,这本书的风格较为沉稳,自己觉得有所长进。
感谢北欧的流亡生活,给了我一个纵观世界的立足点,使我获得一种特殊而不狭隘的目光,在观察研究西藏问题时,能做到多角度观察、对比、质疑与分析。这本新书里因此有不少的比较与对比,例如,关于北欧萨米、苏联车臣、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与西藏的异同。
以真诚交流为目的,我尽量以论据、逻辑和朴素的文字来说理,和读者一起去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在,使自己不被各种表面喧嚣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视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这样诚实说理的目的,在于找到真实和公正,质疑那些被中共当局灌输的熟悉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关于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们所期盼的更好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观念的变化”这一过程。而观念的变化有赖于每个写作者的努力。一位汉族读者告诉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写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文字,从而认识到西藏的苦难。这令我想起一个佛家用语:“功不唐捐。”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