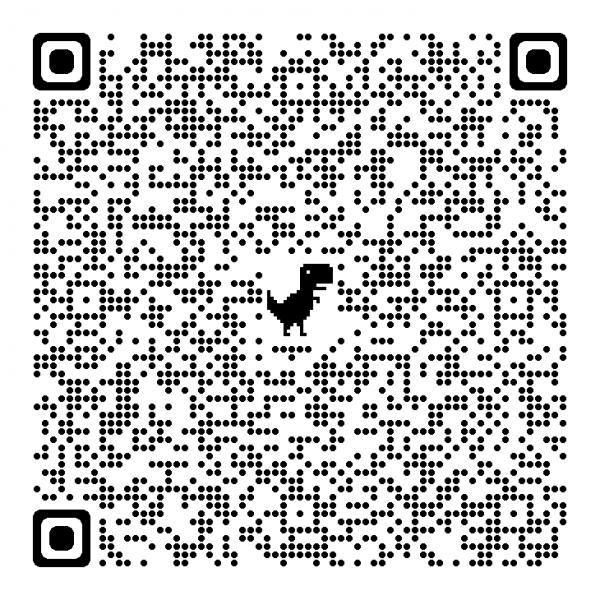又见银杏,黄金满地




当年写《黄浦江》要描述罗家老屋前的银杏落叶,网上查了一些关于银杏的材料,可是写了几稿,终究难以得其神韵。一天走到后院,忽见几株巨大的银杏,顿时来了感觉。书已经于去年四月出版了,那书里的银杏印象,应该来自2021年秋天。这几天又走过后院,发现今年银杏落叶景致更胜于两年前。难道这一段又要重写?
村南头罗家老屋门口,几株不知纪年的银杏树,树干已经如屋子的外墙,斑驳干枯,却依然枝叶满树,落叶把老屋的前半个屋顶和门前的泥地,铺陈得一片灿烂金黄,像一张绣毯,让人不舍得踩上去。
门前沿槛的大青石上,疏密有致地散落着黄亮新鲜的银杏叶。两条陈旧的裂缝已经把青石分割成一大两小的三截,却依旧整齐地铺在一起。
大门半开着,门里一条板凳上,坐着一身褐色土布短打的屋主罗龙兴。
去四十还有好几年呢,罗龙兴已经像个半老头子了,弓着腰,驼着背,一条疏松的辫子没精打采地盘在脖子上。
他从小就长得老气,十几岁时就得了个“老龙兴”的绰号。当年是乡里小子们恶意的笑话,如今却越发的人如其号了。
老龙兴一手捧着烟斗,另一手抚摸着那捧拉拉杂杂地堆在颌下,掺着些许白丝的胡子,眯缝着眼睛,默默地看着一地青砖。
“呆什么呀?又有什么心事了?”正在窗前给儿子孝成梳理辫子的龙兴嫂问。
老龙兴心不在焉地朝母子两个瞟了两眼,眼睛又慢慢转到屋顶横梁上,看着挂在上面的菜篮子,喃喃地自言自语:“松江,嗯,松江,我一定要去看看。”
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了,走进来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冲着老龙兴大声吆喝:“起来起来,阿弟啊,不要像个懒猫啦!”
老龙兴还没搭腔,龙兴嫂对来人笑道:“孝贵他爸你急吼吼的干什么来?我男人正在想计划呢,你别吓着他。”
孝贵他爸抬起手,把一串螃蟹递给龙兴嫂说:“九雌十雄,尝尝鲜,阿妹你拿去弄干净吧。”
“阿哥,谢谢你,不好意思,吃你的好物事不止一次了。”老龙兴坐起来对孝贵他爸说。
“阿弟不要客气,自家人。”孝贵爸说着在旁边板凳上坐下,抬头朝房梁上看看,又朝四周打量了一下老屋。
龙兴嫂拉着孝成,一手提着螃蟹,走出门去,边走边向身后吆喝:“孝贵爸你多坐一会啊。”
孝贵他爸走出门时,龙兴嫂还在门外屋檐下慢吞吞地洗螃蟹,孝成拖着编了一半的辫子,在一边看他妈干活。
老龙兴跟着送出来,对孝贵他爸不断地点头,一边嘴里说:“我有数的,阿哥,我有数的,你不用急,早晚的事。”
铺满银杏黄叶的绣毯上,留下了一条被踩烂的痕迹。

微信公众号同步连载:

本书由南方出版社2022年出版
免费查阅: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Library of Congress
网购:Amazon, Barns & No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