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到1921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受邀成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前往中国讲学。在大约10个月的时间里,这位日后因其“卓越的活力、勇气、智慧和感受性代表了诺贝尔奖的原意和精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共知识分子游历了大半了中国,发表了63场公共演讲。
回到英国后,罗素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后于1922年出版了他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荣誉教授、麦克马斯特大学伯特兰·罗素编辑工程(Bertrand Russell Editorial Project)前主任Louis Greenspan认为,罗素在华期间密切关注着知识界关于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政治体制的激烈讨论,而他本人则对找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径”兴致盎然。
《中国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这种关切。罗素看到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困境,但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学者Charles Argon则在《伯特兰·罗素研究期刊》(Journal of the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上刊文指出,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与其说是其对在华游历经历的分析不如说是其生平哲学思想的一贯延续。这位曾不断撰文“为中国请愿”、于1922年表示“愿为中国竭尽微诚”的哲人虽然意识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的窠臼,却不可避免地复制了一些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

找寻新希望
1916年,罗素被解雇了。
他的雇主剑桥大学无法容忍他参与反对英国政府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非法示威活动,因此罗素在继续手头的写作之余,于1920年前往苏俄深入观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展。同年,他收到了北京大学“讲学社”前往北京讲学的邀请,邀请函于1920年5月发出。“讲学社”由梁启超等人发起,有四家团体参与: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社和中国公学。最早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访华讲学的,是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傅铜。
对于罗素来说,接受梁启超的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想要寻找解决西方问题的答案。
彼时的罗素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相信一战是日后所有悲剧的根源,“如果不是因为它,我们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它,我们就不会有日后所有的这些暴行”。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引发这一出人类惨剧的,居然是象征着进步、知识和理性的西方文明自己。
在对西方失望后,罗素前往苏俄考察,然而他发现自己并不认为列宁的革命专政会是人类的出路。在《中国问题》中,他流露出了这种失望情绪:“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
他用优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他在伏尔加河畔的那个夜晚,记录下他在前往中国之前难以言喻的疑惑与孤寂:“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忍受一切而不置一词的痛楚,那种无法言传的孤寂在整个熟悉的谈话中一直萦绕在我心间……但我找不到答案……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他写道。
中国的理想嘉宾
在罗素访华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对他有不少了解了。他的不少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均已有中译本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以及他一些重要著作的梗概。、加上同期访华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介绍,罗素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已被誉为“新时代的大哲”和“世界哲学泰斗”。北京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出版了《罗素月刊》。
罗素的访华日期是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来华后,他作了五大讲演,分别题为“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讲演地点大多在北京大学,只有“哲学问题”于1920年11月14日之后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院举行,听众多达1500人,场面热烈非凡。除了这五大讲演之外,罗素还马不停蹄地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地做了多场讲演。
Greenspan研究罗素思想数十年,其博士论文的主题即是罗素。他于上个月在上海纽约大学主持的讲座中告诉听众,身为颇受知识界欢迎的外国学者,罗素最为惊人的演讲记录是曾在48小时之内发表了4场演讲,一场在早餐后,三场在晚餐后。
罗素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来到了中国。
1911年,清政府灭亡,中国正式结束帝制。8年后的1919年,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仍在艰难地寻找前路。终结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特权、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呼声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顶峰,而北大正处于这场政治和智识风暴的中心。
“在那个历史时期,罗素正是中国知识界的理想嘉宾。当时的中国学者正在苦苦设计一个能够妥善采用西方现代最佳思想的共和国。”Greenspan说。
正因为罗素被认为是“世界哲学泰斗”,中国人对他访华的期待尤其地高。罗素很快发现,中国人想听的不是技术哲学,而是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1920年10月18日,罗素在给英国作家、演员康丝坦斯·麦乐森(Constance Malleson)的信中写道:“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这要求他到处行走“假装圣贤”,因为“他们(中国人)似乎认为我一定能通过灵感迸发知道他们需要的答案”。
为此罗素改变了他的讲演重点,提出了中国应大力发展西式教育培养有智慧和科学知识的青年才俊并着力发展实业。与此同时,他自知自己无法给出确切的、令人满意的答案。罗素在1920年发表的文章《第一印象》中承认,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要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介入讨论是非常困难的。其后的数次讲演中,他也反复强调了自己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
不难想象的是,中国的听众对此不无失望。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说,罗素的政治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与罗素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式的物质资料再分配是必要的。鲁迅则在1925年发表的《灯下漫笔》中批评了罗素对怡然自足的中国农民的赞美,声称这种“传统的中国式生活”才是中国积重难返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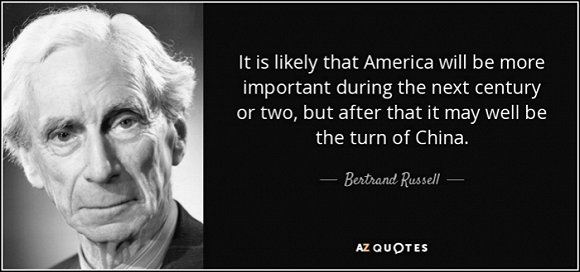
第三条路径
罗素在华期间发表的讲演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及其可能性的溢美之词。“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彻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徐志摩在《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一文中这样写道。然而在旅途中意外感染上差点致命的肺炎令罗素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当时的英国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他的讣告)。
回到英国后,他继续书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彼时的他已确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已自取灭亡,急需获得重生,而中国就是挽救人类命运的钥匙。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说:
“我们的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热爱进步、传教狂热、扩张势力、控制和组织社团,这一切都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我认为,从人类的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来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罗素在中国找寻的是第三条路径,一个处于当时世界上已存的绝大多数政体力量之间、即资本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路径,”Greenspan说,“罗素相信中国是个有着值得尊敬的历史文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尽管中国需要西方科学,他相信传统中国文明能够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它或许能规训西方世界的毁灭性机制。”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孔、佛两教并存的结果,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趋于孔教。因中国的政治一直操纵在有文化的宗教怀疑者之手,他们没有西方执政者的那种活跃和破坏的素质。Greenspan指出,罗素认为中国更具有宽厚慈善的观念和知足常乐的观念,这使他们有能力阻止自己陷入西方资本主义无休无止且毫无意义的竞争。
Greenspan发现,罗素甚至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提议:他认为中国应该由一万名道德才能兼备的贤者以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统治,让中国免于外国势力的干预,为中国引进其迫切需要的工业化。“罗素是否是在说中国需要回到被儒家贤者统治的时代?他们冷酷又仁慈,而且知道美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有趣的是,在21世纪有西方学者再次提出类似的论断。加拿大政治学者、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2016年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提出,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也比较适合面临复杂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国。
“所以他(贝淡宁)现在在推崇儒家中国。有趣的是这是罗素在1921年提出的观点。他在找寻介于资本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径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观点,而它如今成了中国的一个智识风尚。”Greenspan说。
东方智慧和西方问题
Argon认为,罗素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有两个目的,一是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二是基于这个基础对西方社会提出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一面将中国“去神秘化”,一面将中国“再神秘化”。诚然,他批判了西方人将中国视作文物博物馆和“可欣赏的国家而不是可生活的国家”的态度,但他使用中国来批判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做法又像是延续了西方知识分子“到东方寻找答案”的传统,“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对于罗素来说是个批判西方的出口,这让中国问题的讨论再一次事关西方政治辩论,而不是中国的境遇本身”。
“他(罗素)的描述是杂糅的:中国人孱弱,但也因此人道仁慈。这完成了他的第一项任务:概括精炼中国的本质,并将之固定到政治地图中。接下来,他以此为基础支持中国,反对西方势力。罗素对中国的概括性描述化为了对西方的批判,这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Argon说。
罗素认为,中国文明本质性的不足在于缺乏科学传统。尽管他对中国大家赞赏,但他认为科学的缺失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致命的。在《第一印象》一文中,罗素将中国描述成即将被“毁灭”的国度、将东方描述成一成不变且被动消极,这样的评论遭到了杜威的批评。
然而复制东方主义修辞没有妨碍《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程度。林语堂就在《吾国与吾民》中引用《中国问题》的观点,赞扬罗素是少数几个无知的“中国通”中的例外。当然,他对罗素的赞美更多是出于认可罗素的文化敏感度,而非他的论断的准确程度或建议的洞察力。
在整个1920年代,罗素一直在用中国的例子批评英国政策、发表政治观点。1931年,当罗素在撰写自传时,他充满感情地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称中国具有“古老文明的美感”、本质的“对智慧的尊重”、“充满了哲思的冷静”和“不可思议的对比”。尽管他本人否认中国是亘古不变的。
“他(罗素)使用中国作为批判西方的出发点。罗素的中国之行,因此更多的是‘东方化’(Orientalize)中国,而不是‘改变中国’,”Argon总结道,“罗素的写作让我们看到思想家是如何将东方和西方互作对比并用之陪衬强有力的内部批判的,然而这个过程具有简单化彼此的风险。”
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指出,在1620年至1960年期间,诸多西方人出于自愿或受邀前往中国,试图使中国按西方人所理解的定义改变,却终究明白想以某种手段控制中国的命运不过是自不量力,痴心妄想。而罗素的故事则是在告诉我们,把中国作为衡量西方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所具有的知识中,关于共相的知识正像关于殊相的知识那样,也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凭亲身认识而来的,只凭描述而来的,既不凭认识也不凭描述而来的。
让我们先考虑由认识而来的共相知识。首先,显然我们都认识像白、红、黑、甜、酸、大声、硬等等共相,也就.是说,认识感觉材料中所证实的那些性质。当我们看见一块白东西的时候,最初我们所认识的是这块特殊的东西;但是看见许多块白东西以后,我们便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把它们共同具有的那个“白”抽象出来;在学着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怎样去认识“白”了。类似的步骤也可以使我们认识这类的其他共相。这一类共相可以称作“可感的性质”。它们和别类共相比较起来,可以说不需多少抽象能力就能够被人了解,而它们比别的共相仿佛更少脱离殊相。
我们接下去就讨论关系问题。最容易了解的关系就是一个复杂的感觉材料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正用来写字的这页纸张;所以这一整页纸就包括在一个感觉材料之内。但是我觉察到这页的某几部分是在别的几部分的左边,有几部分是在别的几部分的上边。就这件事例而论,抽象过程似乎是这样进行的:我连续看见许多感觉材料,其中一部分在另一部分左边;我觉得就像在各个不同的白东西中一样,所有这些感觉材料也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通过抽象过程,我发觉它们所共有的乃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一定关系,也就是我称之“居于左边”的那种关系。我就以这种方式逐渐认识了共相的关系。
根据同样的方式,我也逐渐觉察到时间的先后关系。假定我听见一套钟的和声:当最后一座钟的和声响起的时候,我还能在我的心灵之前保留着整个的和声,而且我也能觉察到较早的钟声比较晚的钟声先来。在记忆方面,我也觉得我现在所记忆的一切都在现在之前。不论根据上述的哪一点,我都能够抽象出先和后的共相关系,就像我曾抽象出“居于左边”的共相关系一样。因此,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一样,也在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关系之内。
又有一种关系,也是我们以极其类似的方式认识的,那就是相似关系。假使我同时看见两种深浅不同的绿色,那么我便能看出它们是彼此相似的;倘使我同时又看见一种红色,我便能看出,两种绿色彼此之间比其对红色来更为相似。我就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共相的相似,或说相似性。
在共相和共相之间就像在殊相和殊相之间一样,有些关系是我们可以直接察觉的。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我们能够察觉出深浅绿色之间的相似大于红与绿之间的相似。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存在于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就是“大于”这个关系。我们对于这类关系所具有的知识,虽然所需要的抽象能力比察觉感觉材料的性质时要大一些,但是,它仿佛也一样是直接的,(至少在一些事例里)也同样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对于共相,正和对于感觉材料一样,我们也有直接的知识。
是唯心三个的终极问题,哲学的三个终极问题分为唯物三个终极问题和唯心三个终极问题。
唯物三个终极问题:
1、如何更好的认识宇宙世界、并解决关于宇宙的问题。
2、如何更好的认识人类社会、并解决关于人类的问题。
3.如何更好的认识自我人生、并解决关于人生的问题。
唯心三个终极问题:
1、我是谁?
2、我从哪里来?
3、我要到哪里去?
____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少厌烦,但却更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兴奋的足够强烈的追求而得以避免。
女孩们现在大多已经自己谋生。多半是由于这能够使她们在晚上去寻求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的时光。
在美国,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家家有了收音机。
青年男女们约会比以前方便多了,家庭女佣们每星期至少可以有一次令人振奋的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长久期待了。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往另一处,走到哪里,就把兴奋带到哪里;他们狂歌劲舞、开怀畅饮。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期望着在一个新的地方享受更多的快乐。那些必须靠挣钱才能养活自己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那些有足够的钱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我决无低毁之意。不过我担心,这种理想,与其它的理想一样,比起理想主义的想像来,是一种更难获得的东西。与欢快的前一天晚上相比,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20岁时人们以为30岁生命将会结束。我已经58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把人的生命当作货币资本来花费也许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各个民族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表露出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干涉,否则他们便会酷配大醉,一死方休。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强。所以说,对于道德家来说,厌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恶行中,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
价值观的标尺,或许同样不是真正地理解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