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音综《我们民谣2022》收官,周云蓬拿下了冠军。那个夜晚,我们在酒后朗诵《不会说话的爱情》。一旁做音乐电台的DJ朋友说: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荡开。
……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第一次见有人能把分手炮写得如此唯美。
唯美之下,伤痕累累。
离开屋旁一起种下的小白菜,也是心如刀割。
像这样的作品,老周写下了太多。
写的是诗,唱的是歌。
虽是瞎子,眼和心却无比透亮。
云游大地,走过半生,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老乐迷应该记得,当《乐夏》中乐队们纷纷陷入疯狂之时,他泼下的一盆又一盆冷水。
连发了11条微博质疑《乐夏》,字字珠玑,不说得罪同行,上节目的老炮们不爽是一定的。老周不是哗众取宠的人。归根结底,是担心资本过分干预独立音乐。比如,新裤子在《乐夏》后档期全满,跑各种通告,忙得要死,在微博一通抱怨。结果上个月,老周自己不仅上了综艺,还在综艺上夺冠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起老周是何原因,本以为会有搪塞或者犹豫,但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三年前,我站在众人的对立面,怀疑综艺难道就是独立音乐的唯一出路吗,三年后我发现,恐怕真是这样。我从不保证自己的观点一直不变,也许三年后,我又会站在现在的对立面。因为生活反反复复,正如从某天开始,我们突然就不用做核酸了。”上综艺归上综艺,老脾气没变,说出了《我们民谣2022》中最锋利的一句话,对同行,也对挚友。在舞台上少说点话,用音乐本身来呈现舞台,饭后甜点不能比主菜还丰富。总要有人站出来,不合时宜地打破表面的一团和气,为了能好好唱歌。他怀疑节目的同时也怀疑自己,在他眼里,怀疑是自由的一体两面:“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中国人这辈子最难的,就是自己打自己脸。所以即使大错特错,父亲也不可能给儿子道歉。
在许多人看来,老周关于《乐夏》的怀疑往好听了说是“乌托邦”,往难听了说是“幼稚”。在这个大家都太“聪明”的信息时代,他舞着剑,显得笨拙。他不满当下过分娱乐化的音乐市场,摇滚乐沦为夜总会。“无病当然可以呻吟。在生活中我有时候就是烦,你说烦是一种病吗?它不是啊,但它就是烦。崔健也说,‘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他也是在无病呻吟。厌倦也是巨大的痛苦,是痛苦的另一面。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要尊重每个人的感觉,不要着急去解构他的感觉,不能说我看见你有血了你才能呻吟, 没看见你就不能呻吟,无端去揣测太恶意了,这样不好。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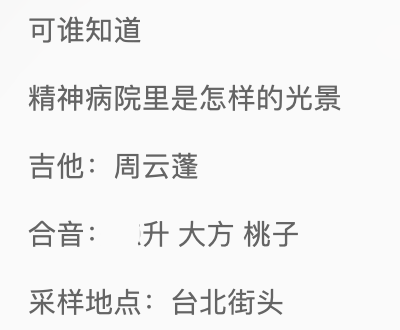
我与他提起武汉,聊起在群中为支援武汉的志愿者们唱歌:人们喜欢什么他就唱什么,《九月》、《不会说话的爱情》,一遍又一遍。称自己起码还有力气做回“战地文工团”。都没有“偏见”,也就都没有观点。没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只剩下投机取巧的模仿。“万马齐喑究可哀!没有人说话的时候,一声叹息,也算刺耳的叛逆了!”不屑去谈什么偶像idol,如今所谓摇滚明星们也一个个活得跟AI似的。周云蓬在瓦尔登湖。资料来源:遇见“民谣诗人”周云蓬周云蓬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蓬”的意思是“蓬草”,一种没有根的草类。没有根,随风飘摇,了无牵挂,像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比风筝自由。他曾在随笔集《绿皮火车》的扉页上如此写到:
“保佑我暂时成为小孩子专注地一笔一画的写下去,别长成个面目可憎疲于应酬的傻大人。”
多年以来,他任性地让一个孩子住进自己的身体,不停戳破皇帝的新衣,不管大人的时宜。
任性,本就是侠的一部分。
老周反对的从来不是娱乐,而是顺从,无休无止的顺从。顺从到成为规则的帮凶。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于是我们把他的诚实定义成“愤青与偏激”。
跟小河跑去幼儿园录童声,买糖贿赂孩子们,可孩子们还是不肯唱悲伤的词,因为心里不明白。最后就是唱“呀呀呀,呀呀呀……”,录进专辑里,和老周的人声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这种不顺从造成的反差,将“让领导先走”的主题痛上加痛。“任何道德解释与宗教解释在孩子的苦难面前都无比苍白。他们没有原罪,也没有前因后果、报应轮回。孩子的苦难没有任何意义。”谁歌颂苦难,谁就怀揣着最险恶的动机,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不是知道他生于东北铁西区,我会以为他是草原上的孩子。一首取调蒙古民歌的《随心所欲》响起,眼前满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马走马的路,羊走羊的路
命运的车轮子翻来覆去的
爱上我还是不想再爱我,这一切全都随心所欲了
不愿长大。他没陷于征服命运的宏大课题,心甘情愿做天边一朵云彩。将一个孩子装进大人的躯壳,即使现实中涌现太多黑暗时刻,但他始终将自己是种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之中。
资料来源:遇见“民谣诗人”周云蓬如今,周云蓬孩童般的纯洁像一把剑,挑断了我们身上的麻绳。“我宁愿埋在黄土里,也不愿意让他们把我放在案板上从内到外,一寸寸的拿去交叫卖。”与作品给人“苦大仇深”的印象不同,老周其实是一个极幽默的瞎子。十多年前,柴静问绿妖为什么跟周云蓬在一起, 她的回答是:“王小波小说里写,一个母亲对女儿说,一辈子很长,要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由苦难锻造而成的幽默感,得以让他在生命深邃的黑暗中喘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肯,还说,妈妈,要跳你自己跳吧。
资料来源:遇见“民谣诗人”周云蓬记者问:
“你九岁失明,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轻飘飘地回答:
“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得太早,它扑了个空。”
“我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抿恩仇罢了。”命运要和9岁的周云蓬玩拔河,然而小周自说自话,玩起了老鹰捉小鸡。
为了听到平常自己读起来很困难的书,他跑去做盲人按摩。胳膊一块五,后背两块二,赚钱来雇佣别人读完《山海经》这类古籍。有时候是请女生读,读着读着卡壳了,后来才知道原因:《山海经》不仅字难,还有许多关于性器官的描写。于是只好更卖力地去做盲人按摩,为了能在“尴尬的时候支付给人更高的费用”。听书,不知从哪一页起风起云涌,这是盲人独有的乐趣。某次在深圳演出,主办方是老友,于是提前和老周商量:“今天重要的领导坐第一排,要看完整场演出,《中国孩子》能不能不唱?”用老周的原话说,冥冥之中,他听见老友的心脏怦得一声停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害怕一首真实的歌。可能领导们的自尊心都比较强吧,咱们也要尊重他们!”柴静采访他,要进公园拍外景,一位工作人员见他们扛着相机,阻拦到:“公园今天维修。”
柴静说:“拍鸟,不拍人。”
工作人员没松口:“那也不行。”
老周站在边上,轻声地问:“鸟也修吗?”
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人们的笑声中渗出荒唐。
该修的是鸟儿还是人心,在笑声中不言而喻。
在那座失明的城市 所有的公厕都会唱歌
你可以任性地离家出走 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
陌生的路上不用担心 一个人找不到厕所
我想,对于习惯背个包在地球上飞来飞去的他来说,找不到公厕的情景一定时常发生。于是在这座他幻想出来的城市中,跟爸妈吵架了可以放心离家出走,尿尿也不会很麻烦,因为公厕们都会唱歌,指引着方向。些许轻松的旋律听上去,仿佛是自由撒尿时的痛快弧线。
2017年,他学会了用手机照相,还呼朋唤友办起“摄影展”。他听着朋友的描述,靠听觉分辨出好看的照片,挑出来,拿给明眼人看。瞎子照相原本只是说笑,而被挑选出的照片却意外呈现了一种“歪”打正着的美感。

资料来源:微博@周云蓬
“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他听了一会儿,根本没接茬,重新另起了一句:
“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结合人们之前的感叹,觥筹交错的场景瞬间转变成葬礼开场白。
哄堂大笑。
懒得当悲剧英雄,没意思。还容易把自己套进去。
他从一片黑色中筛出幽默,而在这幽默的后段中又总能品出黑色。
绝不是简单的搞笑段子,这四两幽默劈出的白,才让他挑起生活的千斤重担。

资料来源:一席,周云蓬《行到水穷处 偏要大声唱》
因为看不见,所以看得清
每年三月,人们分享起《米店》。到了九月,却鲜见《九月》。
因为这首歌太咄咄逼人。
逼你离开卧室,进入草原,面对生命。
逼你承认,众神死亡的草原上,自己只是那野花一片。
逼你琴声呜咽,泪水全无,然后只身打马过草原。
词者海子卧轨死,曲者张慧生自缢亡,歌者周云蓬双眼盲。
海子和慧生没看开,自杀了;周云蓬看不见,但是看得开,因此活得痛快。
只剩下尚未看开的听者独断肠。
这并非歌词与歌曲的简单结合,而是罕见的诗歌与音乐的共同追问:
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每到九月,戴上耳机播放《九月》静悄悄的仪式,只身打马过一次草原。
一曲毕,宛若重生。
资料来源:爱奇艺,《我们民谣2022》
残忍地说,甚至是因为看不见,所以看得清。
柴静曾与他谈起对爱情的理解,他的回答是:
“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天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做瞎子,爱情清楚到没有门第,没有相貌,只剩下味道与触摸。
看不见你如何美丽,只知道你的心是善良的。
这里没有目光,不需要彼此打量。
因为看不见,所以不垂涎权利皇冠的金光灿灿。
因为看不见,所以不嫉妒别人精心伪装的胶水羽毛。
他关心的,是每个地方的口音和味道都不一样,比如鸡叫声,河南的鸡叫声比西藏的更暴躁些。
是用耳朵听出一幅中国地图,火车驶过钱塘江时是一种空洞的过桥声。
读《绿皮火车》时,看他走过的路,听他唱过的歌,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瞎子。
反倒以为,自己才是那个失明的人。
本文已完结
作者:马拉松
主编:滚君
防火防盗防失联
快关注我的小号“公路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