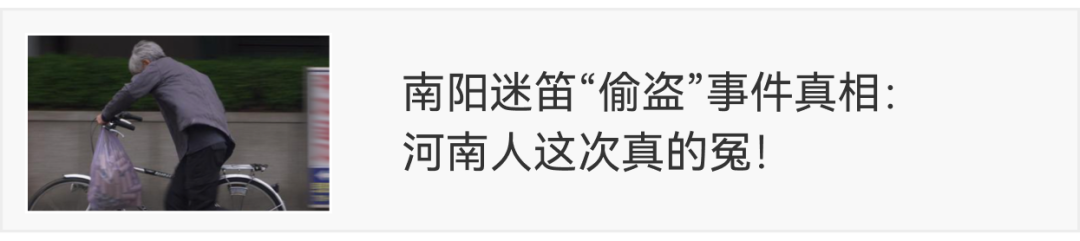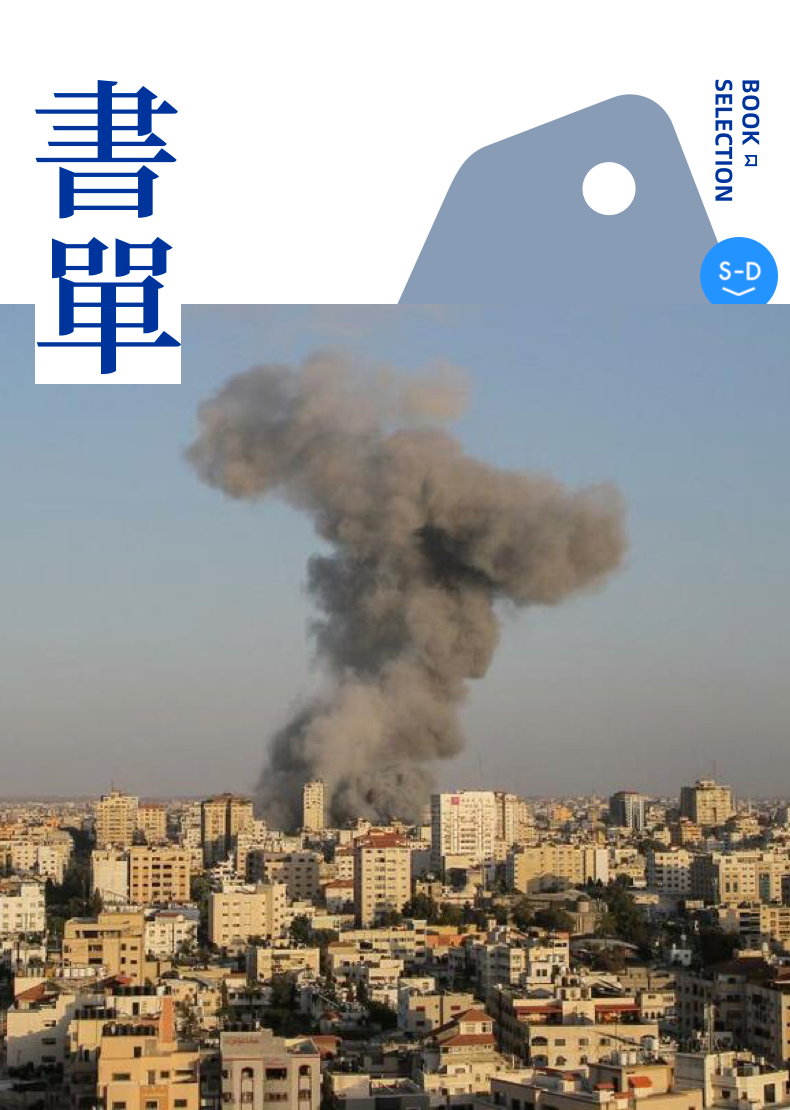
截至书单君写文,巴以双方死亡人数突破4200,我们也有4名同胞不幸遇难。如今或者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巴以冲突的新闻,我们看到的可能依旧会是满屏马赛克的画面,还有一边报导一边崩溃痛哭的记者,以及在废墟中给孩子洗澡的父亲……到底该怎么看待巴以间延绵数十年的战争?以及巴以和平为什么就那么难?这大概是我这段时间朋友圈看到的最深的焦虑之一,书单君是个安静的读书人,本想忽略,却也不得不卷入深思。但是我想,人们也许说不清战争双方的对错,但一定看得清战争带来的血泪。说起来,相对今天炮火连天的局面,巴以也曾经出现过一霎那的和平曙光。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同坐一席,为这片土地签署了象征和平的《奥斯陆协议》。只可惜,当初促成这个协议的拉宾死于以色列极端右翼之手,而阿拉法特也在和平的祈望中郁郁而终。如今的巴以,双方阵营各自的主导者,均为激进派别,前为极端组织哈马斯,后为右翼势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所以今天的局面要如何解,说实话,再伟大的政治家恐怕也很难找到答案,而朋友圈更是难寻。书单君今天不想多谈现实,倒想跟大家聊聊历史,聊聊阿拉法特这个人。我并不期望大家能从历史中找寻到解开现实困局的钥匙,但希望能从这个曾经致力于和平的人身上得到一丝善的启迪。作为致力于巴以和谈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个人命运中,或也能看清楚今天巴以冲突为何难解。阿拉法特,并非一出生就是和平使者。相反,他跟拉宾一样,都是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后,才觉察到了和平的可贵。他曾被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称为“现代恐怖之父”,却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自认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死后却被查出留有10亿美元财产。● 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宾,1993年签署第一份《奥斯陆协议》后,于1994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直到2004年过世,伊朗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日报》为他盖棺定论:他一生充满起伏和苦,尝过很多失败,犯过不少错误,但从未背叛过巴勒斯坦。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相当中肯。阿拉法特身上充满争议,但为巴勒斯坦长达半个世纪的殚精竭虑,才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在这半个世纪里,他用前20多年浴血拼杀,却用后20多年争取和平。正因如此,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一个老兵对战争残酷的深刻体会,也能从他的结局,看到和平这个词,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的遥远和沉重。#01
我们已经撤出祖国,
我们还能撤到哪里?
1933年一个深夜,一群英国士兵闯入阿拉法特叔叔在耶路撒冷的家。几分钟后,英国士兵扬长而去,留下客厅里鼻青脸肿的叔叔,和到处被砸烂的家具。在此之前,他父亲做着跨国生意,母亲拥有穆罕默德的直系血统;在此之后,他发现哪怕自己家境优渥,在殖民统治下依然没有尊严可言。后来一位中学老师跟他说:除非独立建国,否则我们永远抬不起头来。可14年后,当阿拉法特等到朝思暮想的建国机会,他发觉自己的头更抬不起来了。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将巴勒斯坦超半数的土地划给犹太人,哪怕他们只占当地总人口三分之一,此前占据的土地不过6%。剩下来留给原住阿拉伯人的土地本来就少,还被切分成三块。1948年5月15日,埃及、约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集结联军,在以色列庆祝建国后的第二天送上了第一次中东战役。在阿拉法特看来,大家是情同手足的阿拉伯弟兄,出兵是不愿坐视巴勒斯坦的同胞被如此欺负。但其实阿拉伯联军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关心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能否争取到更好的建国条件,而是自己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能否捞到更多好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期以色列被联军打得措手不及时,率先攻下耶路撒冷老城的约旦国王,迫不及待就要自封“耶路撒冷之王”。后来以色列在美国支援下一波反推,把原本“六四分”的土地,直接打到“七三分”。阿拉法特在联军败退后前往埃及,站在当时的革命领袖纳赛尔面前,满含热泪请求:“请您帮助我建立一个国家吧!”很快,纳赛尔为了拿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答应帮助以色列逮捕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作为纳赛尔的坚定崇拜者,阿拉法特感觉到了深深的背叛和失望,骂骂咧咧狼狈地走了,后来许多次,他都在公开场合将纳赛尔称为“阿拉伯民族的叛徒”。1957年,土木专业的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开了家建筑公司。这家公司为他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足够他获得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是资助巴勒斯坦境内的游击队,二是创办杂志《我们的巴勒斯坦》。凭借这两件事,阿拉法特声名渐隆,并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简称就是“法塔赫(Fateh)”。一切仿佛都在孕育着希望的种子,但殊不知,这恰是阿拉法特人生悲剧的启幕。1965年新年前夕,6名法塔赫成员潜入以色列,计划在元旦当天炸掉当地一处蓄水池。阿拉法特自信满满,提前将“法塔赫第一号军事公报”寄给各国知名杂志,以便第一时间,向世人展现他们武装建国的决心。结果,以色列人欢庆了一整天的元旦,愣是没有一个炸弹炸响,而各大杂志,却已如期刊登法塔赫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光辉战果”。然而更为荒诞的是,看报纸的人,根本不关心这次行动的实际情况。所以法塔赫的人数,反而在这次不达预期的行动后,从几十人激增至600多人。接下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6天击溃了阿拉伯国家的30万大军。第二年,在一片失败的萧索的氛围下,阿拉法特带着不到300人,在约旦的卡拉梅,跟以色列军队展开巷战,炸毁17辆坦克,击落1直升机,歼敌400余人,迫使以色列撤退。
“我们已经撤出祖国,我们还能撤到哪里。这时候应该有个组织站出来,证明阿拉伯民族是有人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黑色九月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法特开始得到阿拉伯联盟的认可,其中约旦更是直接开放国界,收留了巴勒斯坦难民和游击队。“这个国家完全被占领了,游击队员以难民营为基地,甚至在首都安曼的街头,开着皮卡架着重机枪招摇过市,警察也不敢管。”
约旦国王侯赛因喊来阿拉法特,警告他:“管好底下的人。”当时人们将阿拉法特视为巴勒斯坦游击队的领袖,事实上这些武装力量统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就是“巴解”,而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只是其中一员。巴解中每个成员组织,背后都有为之站台的国家,自然也就代表各自靠山的利益和态度。例如巴解中的“人民阵线”和“人民斗争阵线”,和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国家走得很近,便一直主张采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政治诉求。而从人民阵线中分裂出来的“民主人民阵线”,则跟民主国家关系密切,就比较倾向于同以色列和谈。作为巴解名义上的话事人,阿拉法特对自己的法塔赫与组织内一些温和派,兴许还有较大的号召力,而对激进组织却是鞭长莫及的。在这样一个团队中,统一纲领是不能指望的,其结果就是,原本崇高的建国理想,在不断的失控中走向扭曲、涣散。阿拉伯人骨子里刻着“以牙还牙”的文化因子。这在松散的巴解组织肆意滋生,以至于到了失控的地步,因此那个需要长期奋斗的建国目标,也就逐渐沦为炮火和鲜血迸溅瞬间的情绪宣泄。
1970年9月,“人阵”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的3架飞机到约旦,将300多名乘客囚禁沙漠,要求欧洲各国释放巴勒斯坦的囚犯。劫持过程中,因为飞机迫降,约旦机场发生大爆炸,而“人阵”成员最后更是在沙漠连续引爆3架飞机。劫机事件一出,约旦政府的国际名誉一落千丈,各国纷纷指责约旦和恐怖组织沆瀣一气。约旦也是积怨已久,原本看在阿拉伯同宗的份上,好心收留巴勒斯坦的难民和游击队。这些人却在自己的地盘肆意妄为,出了事情却要约旦政府出面背锅。不仅如此,巴解部分成员,还相当执着于道德绑架,平时在公路上设卡向平民索要财物,不给就是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就是阿拉伯民族的叛徒。结果,就连侯赛因这个约旦国王,都被一些极端分子视作“帝国主义走狗”,险些在某次庆典上死于刺杀。劫机事件后,侯赛因最终下令军队开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一阵炮火交锋后,阿拉法特跟巴解组织,被驱逐至黎巴嫩,4000多名游击队士兵和数万平民的尸体则留在了寂静的难民营。但巴解中的激进派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觉得受到背叛而变本加厉。他们将约旦军队突袭他们的1970年9月称为“黑色九月”,还以此为名成立新的恐怖组织。
1972年慕尼黑,所有人都沉浸在第20届奥运会的欢呼声中。几声枪响过后,以色列代表团中的2人,被当场击毙,其余9人被“黑色九月”劫持为人质。以色列短跑女运动员罗特·沙查莫洛夫,至今记得恐怖分子和德国警方的谈话:“如果不满足要求,我们每隔两小时将一名人质扔到楼下。”最终,在慕尼黑机场,德国警方营救失败,“黑色九月”的5名成员和余下的9名以色列人质同归于尽。一直背着正义光环的阿拉法特,不仅在非阿拉伯世界恶名昭著,即使在阿拉伯地区,也开始被人人喊打。在黎巴嫩呆了不到两年,阿拉法特又辗转至突尼斯,因为巴解几乎在黎巴嫩复制了他们在约旦的恶劣行为。
从埃及到约旦,从黎巴嫩到突尼斯,30余年的颠沛流亡,阿拉法特没有完成建国的理想,却在身后留下一座座废墟,和一条条生命。望着满目疮痍的土地,曾在战场上振臂高呼“战斗到底”的阿拉法特,突然感到一阵身心俱疲。或许也是在这一刻,他意识到,是时候改变了,武力火海、无穷无尽的恐怖袭击,换不来真正的和平。巴勒斯坦
强人的困局
必须承认,巴解组织在阿拉法特领导下制造的恐惧是真实的,这点是他无论怎么解释成“底下人不听话”,也难辞其咎的。但作为局外人,并且从更长的时间视角来看,对于一个用20多年进行武装斗争、又用20年致力和平建国的人,我们又很难将其视作一个纯粹的恐怖战争的爱好者。阿拉法特建国的决心,从他舍弃优越的生活,转而投身行伍就能看出。
在这条路上走过几十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恐怖袭击不会给敌人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损伤,只会让巴勒斯坦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在建国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然而,阿拉法特面临的人生困境在于,由于自身力量的单薄,又注定他不可能离开极端武装的支持。这也就能解释,他多次下令不能伤害平民,却一再对巴解成员的恐怖袭击保持沉默。1985年,”解放阵线“成员阿巴斯和其他3个同伙,劫持了埃及的一艘客轮,并将船上一名坐轮椅的69岁美国裔犹太人丢入海中。
后来被当面质问这件事时,阿巴斯回答:“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是想游泳。”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法特在慕尼黑惨案后强行解散”黑色九月“,是他面对内部压力所能为和平做的最大努力。1974年,在解散”黑色九月“后一年,阿拉法特接受了联合国的邀请。“今天我带来了橄榄枝,也带来了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上掉落。” 
那是巴以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联合国会场掌声雷动,一位西方记者激动地说:这是唯一一位值得国际尊敬的“恐怖分子”。阿拉法特在大洋彼岸的演讲话音刚落,巴解武装突袭的炮火便响彻夜空。第二天,以色列刊出18名在突袭中死亡的妇女儿童的照片,将他带来的橄榄枝狠狠拍落。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和平这条路上让他面临新的困局。1984年,他提出”土地换和平“,打算在1947年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建国。他说:“这个方案和我们设想地领土规模相去甚远,但这或许是一个新解放事业的开始。”可是激进派却再次给他迎头一击,高呼:”要将以色列人彻底从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
4年后,历经多年努力,阿拉法特的和平探索,终于取得了一丝成效。他宣布,在约旦河西岸正式建立巴勒斯坦,而当选总统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为争取和平停止一切恐怖行动”。可在他战友看来,既然他贵为总统,他口中的“和平”一词,就蕴含着“犹太人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之意。经过多年探索,阿拉法特非常明白,建国只能依靠自己发展出来的实力,这点毫无疑问,但要获得实力,只能先和平先妥协,取得稳定的根据地,才能发展长远的实力。
然而就是这点常识,有太多的巴勒斯坦人,不能明白和理解。以色列,自然也千方百计地阻挠,让这常识无法成行。在以色列的不断攻击和骚扰下,身处仇恨泥潭的巴勒斯坦人,只能看到眼前和以色列的仇恨。这份仇恨能让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战场上为祖国献身,这令人动容更让人沉迷,但有些事显然比死去更难,也更加有意义。中东“不死鸟”的陨灭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有意改变中东战略,打算通过调解巴以冲突,跟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以色列高层也出现呼吁和平的声音,总理拉宾更是说出那句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几万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战死儿子母亲的眼泪给我的震撼。”
对于促进巴以和平,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节点,阿拉法特没有错过这个节点。1993年9月,他和拉宾正式签署《奥斯陆协议》,并代表巴勒斯坦接受按1967年以色列实控线为准进行边界划分。要知道,这个疆域划分比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的划分还要少许多,而阿拉法特当初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拼死反对第181号决议。面对巴勒斯坦方面释放的巨大善意,以色列作为回应,归还前几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可以说,阿拉法特和拉宾以博大的格局和胸襟,为巴以双方的和平做出了各自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两人也因此分享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就在协议签署当天,两人就被各自国家众多游行示威者称为“叛国贼”。2年后,拉宾在以色列国王广场上胸口连中两枪,在手术台上不治身亡。凶手是一名以色列极端右翼组织成员。以色列民众迅速通过《民族国家法》,规定“以色列土地是历史上犹太人建立国家的大小”。以色列撕毁协议,巴勒斯坦群情激愤。作为昔日国父,阿拉法特面对冲上街头的人民,只剩下无声和无力。1973年,亚辛还是一位在加沙扶贫济困的慈善家,如今20多年过去,他坐在轮椅上,身边簇拥着信徒,高喊“发动圣战,直到敌人被赶入大海!”在亚辛身后有一面旗帜,旗帜上的标志,便是今天的哈马斯。以色列继续侵占巴勒斯坦超过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激进的哈马斯迅速崛起,缺乏高新武器的他们,开始频繁使用人体炸弹对以色列进行自杀性袭击。亚辛对此说过一句话:“使用人肉炸弹是每个巴勒斯坦人的民主权利,而以色列只懂得这种民主。”2001年,曾在1982年主持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阿里埃勒·沙龙,当选以色列新任总理。上任前一年,他强行登上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尊贵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引发了长达5年、双方伤亡过万的持续冲突。在这段期间,阿拉法特一直被软禁在约旦河西岸的总统官邸。2004年10月,他身体状况恶化,被送往法国贝尔西军治疗,最终在当年11月去世。在他的衣袖上,人们检测到246.7毫贝克的钋210,这个剂量是致死量的20倍。阿拉法特,素有“中东不死鸟”之称,指的是他一生中遭遇过57次已知的暗杀,但他都一一幸免于难。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假如奥运会有躲避暗杀这个项目,我一定会代表中东来参赛。”可当这只不死鸟最终消亡,他没有办法用凤凰涅槃的姿态,让自己生长的土地焕发新生,只留下血与火背后的无尽困局。他肩负着建国的使命,在斗争和妥协中寻求一条狭隘的路,然而战友的不理解,盟友的不可靠和民族仇恨的不可协调,给予他以殉道者的宿命,让他为内心的理想死而后已,却最终什么也改变不了。阿拉法特希望自己死后,遗体能被安放在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但这块地方至今仍被以色列控制。最后,伊斯兰教领袖穆夫提,捧起一抔阿萨克清真寺的泥土,轻轻撒在他的灵柩之上。结尾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亚细亚北部一座城市,在宙斯神庙中看到“戈尔迪乌姆之结”。亚历山大解了半天没解开,直接拔剑把结砍断,然后他拥有了亚细亚。
● 《亚历山大斩断戈尔迪之结》【法】Jean-Simon Berthélemy
“解不开就劈开”的史诗固然豪迈,却碰不到现实的边角。当历史、宗教、仇恨等众多因素耦合的绳结,横在巴勒斯坦上空,每次欲理还乱,都会增加矛盾与隔阂,而至死为和平奔走的人,只能带走无尽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法特就像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当他用尽毕生力量看似将巨石推到山顶,枪响过后却又随着巨石滚落更深的深渊。想要从头再来,且不说要承受更艰巨的重量,就连阿拉法特这样的西西弗斯也难以再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拉·卡茨尼尔森,曾在《恐惧本身》一书中提过“集体恐惧倾向”:当一个群体长期受到压迫或威胁,恐惧就会超出原有的心理防御机制,而成为这个群体各种社会活动的心理导向。如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俨然就是这个概念的深刻诠释,哈马斯将消灭以色列作为纲领,以色列执政者将剿灭哈马斯作为对民众的交待:他们想的不再是消除恐惧,而是将对恐惧的渲染视作生存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个世界仍有阿拉法特和拉宾,他们为追求和平而受到的反噬,只会更甚于30年前他们所遭遇的。伊拉斯谟曾说:“最勉强之和平亦胜过最正义之战争。”毕竟和平的天平一旦倾斜,想要再让它回到平衡,就不是扶一下那么简单的事了。而身处已经和平70多年的国家,我们也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和平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们关心几千公里外的巴以冲突,所能得出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珍惜和平。面对万里之遥的血与火,相比在网络上和意见不同的人吵得面红耳赤,这显然来得更有意义。
[3]《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英]伊恩·布莱克;[4]《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民族之魂》,人民网,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