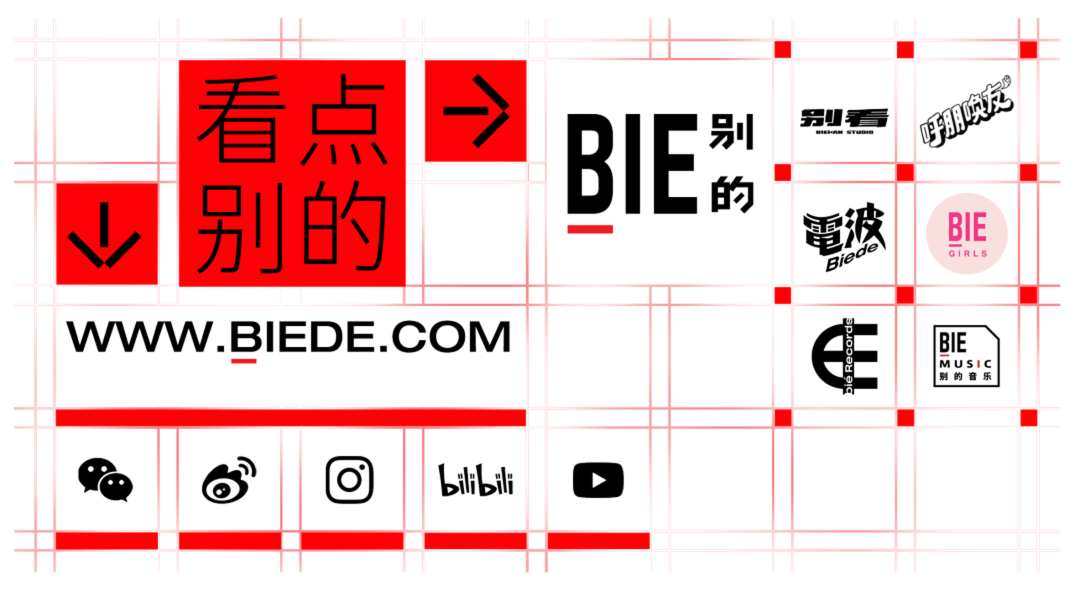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叫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写了一本名为《元素周期表》书,但这不是一部科普著作,而是一部小说集/回忆录。他通过对二十一个元素特性的独特理解,以每一种元素引领了一个故事。在这部著作里,我们感受到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与来自自然的基础物质强烈的关联。美凯龙艺术中心的展览《元素小说》受此启发,以“元素”为线索,串联起15组艺术家的作品及背后的跨学科故事。只是在这里,“元素”不仅限于化学元素(铜、锡、铅、金等),也扩展到人工或自然的物质原料(塑料、沥青、云母、沙等)与哲学本体论元素(火、水、土,以太)。展览借此探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看完展览之后,继续沿用这个格式,以展览中涉及的几种“元素”为联想起点,又重新写了四个故事——塑料是曾经风头十足如今跟不上时代的中年人,铅与沥青象征着一种似乎无法挽回的颓丧情绪,上头了的单相思女孩遇见冷酷男孩如同在水中点火,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俗语何尝不是宣布了金子的宿命。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有时甚至也与某种物质特性有隐秘的相似之处。在“物化”自己的乐趣中,我们似乎也得到了新的启示。路易斯·亨德森,《一切坚固的》 单通道高淸影像,有声,15 分 40 秒,2014 图片来自网络
加纳籍艺术家,XX奖获得者拒绝加入X国国籍。日前,艺术家通过其本人社交网络账号发布声明,全文如下:去年12月,得知自己获奖的那天,我正在位于中国广东的一座海边城市的美术馆里参加开幕式,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国家举办个展,双喜临门,我非常高兴。当天,美术馆为我安排了好几个媒体专访,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我不得不把许多话说了很多遍,但他们的热情使我感动,因而并没有觉得特别疲惫。最后一个访问结束时,美术馆负责宣传工作的梅女士十分为难地问我,是否可以再插入一个访谈,她说,这名记者因为之前没能约到专访,已经对她软磨硬泡了一个下午,她说,只要15分钟就可以。我当然同意了。接着,门后那个瘦小的身影走了进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十分羞涩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没能记住她的名字,但她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改变了我今后的生活,她说,中国有一句俗语,“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想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过表达类似含义的俗语,这句话能够给人带来安慰和鼓励,在它还没变成绝望之前。但当天,它给我带来一种强烈的宿命感。之所以如此,与这名记者所讲的故事有关——那时我才明白她急切地想完成这次访问并非只是为了职业目标。她告诉我,她出生在距离美术馆3小时左右车程的一个小镇,那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地。在政府介入整治,并严格禁止进口固体废弃物之前,那是一个空气中布满了刺鼻气味,并流淌着可怕的黑水的地方。街道上随处可见坐在电子垃圾堆中拆卸电器,在废弃楼房里烤电路板的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其他省份,她的父母也在其中。这是我没有见过却丝毫不难想象的场景——在我的家乡,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城中心西侧,阿格博罗什电子垃圾场上,能看到儿童推着三轮车从垃圾山旁走过,不远处是原地焚烧垃圾引起的阵阵黑烟。他们大多因为放弃了农业生产或为了逃避部落纷争而从北部到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之一。虽然我从未踏上过那片被称作“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之地,但我的第一台电脑应该与倾倒在阿格博罗什的废弃物同乘过一条船,从某一个西方国家,很可能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到来。我们的家庭十分不富裕,但我的父母努力为他们的子女带来了这台仍然能够运作的旧机器。与一台新电脑相比,它只需要十分之一的价钱。而我似乎是我的兄弟姐妹当中唯一对它感兴趣的人。我把它当成了一个交换秘密的朋友,它让我相信,我必须从家乡离开,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母亲说,她一直知道我有某些特别之处,或许并不是那台旧机器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命运将它带到了我身边。我想命运以相似的方式启发着这名年轻的记者。她的父母从那个小镇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她刚刚5岁,却比大多数当地的小学生都能更好地读写。她记得在父母工作时,是两三本被丢弃的小学课本陪伴了她大多数时光。通过这样小小的门,我们分别到达了与我们出生地完全不同的世界,并终于感到如鱼得水。就在这时,她说出了那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15世纪起,加纳就被称为“黄金海岸”,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来到这个地方,开采黄金。时至今日,加纳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黄金出产国。出口的黄金中,应该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作为特定电子元件上的镀金层又回到了加纳——在我所不知道的确切年份之前,应该也有一部分去到了那位记者的出生地——成了垃圾场的工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我开始想象,如果我是一块金子,当我以为自己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或许有这样一艘无形的船,早已等待着,将我运送到安排好的目的地。然后我在这里完成我的事业——生产这里的人们所需要的某种精神物质。大约一年前,我向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政府提出了成为本国公民的申请,如今我的到了批复。但我知道,在去年12月,我就已经放弃了这个计划。我或许不会回到我的家乡,我或许还会继续在这里生活,但我想我至少可以拒绝金子仅仅成为金子的命运。以上3图:路易斯·亨德森,《一切坚固的》 单通道高淸影像,有声,15 分 40 秒,2014 图片来自网络
朱利安 • 查理埃,《烈焰之下,静水深流》(静帧),2019,超高清影像,有声,11分13秒
“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
五千和小邱坐了下来,对面的喷泉在喷水,哗啦啦地洗刷着初夏的热气。
“啊?”小邱猛地缩了一下头,看了一眼五千又立刻把脑袋转了回来,一幅“你在搞什么鬼”的样子。“跟我睡觉吧,”五千接着说,身子往小邱那边凑了凑。小邱用余光测量着两人之间的距离,说:“这样不太好吧,我们不是朋友吗?”“我还不惊讶吗?我下巴都没了,”小邱终于转过身,仿佛为了展示他作为证据的下巴。“你只是惊讶我会说出来,但对于这件事实,你早就知道了,对吧?”“我真的不知道,你可能误会了,我真没想那么多。”他向前俯下身,胳膊撑在大腿上,脸扭向另一侧。五千看见,他后脑勺有一小撮头发翘了起来。又来了,五千想,男的就是可以这样光明正大地逃避现实。“那你说,你不喜欢我,”五千对着他的背影说。“你别闹了,根本就没想过这些啊,本来不是好好的吗?”小邱边说边站起来,往喷泉边上走去。五千没有跟上去,抱着手,镇定着自己,思索着小邱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在脑中回放了几遍刚才的一幕,判断小邱的反应是由意外引起的本能退缩,接近于条件反射。可能太直接了,应该稍微铺垫一下的,她想。五千决定今天不再谈这件事。她是一个理智成熟的女人,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上大学时她给自己起名“五千”,跟原名“吴倩倩”比起来,立刻多了一丝老辣的江湖味道。小邱双手抄兜,盯着喷泉的水柱,像陷在青春心事里的高中生。五千走过去,掏出火柴点了一根烟,随手把火柴弹进池子,火苗顷刻间熄灭,一根半焦黑的木杆在漩涡里打着转。五千吐一口烟,把烟盒往小邱眼前杵了杵。小邱抽出一根,刚才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如果把一万根燃烧的火柴一起丢进去,喷泉会不会变成火泉?”五千找话说。“不会的。燃烧需要温度和燃料,水是冷的。最多也就是烧沸被蒸干,火也就灭了,”小邱跟着说。五千从来没追过男孩,也没跟男孩表白过。以往她总是通过一些暗示给男孩传递信号,再等待对方开口。但现在,她对于这种诱惑者的角色产生了厌倦。近来,她感觉自己各个方面都处于顶峰状态,想主动捕食,想立刻就谈恋爱。小邱长得好看,品味好,会打扮。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显得有点羞涩,甚至有点不自信,而正是这一点吸引着五千。开始,她以为那是新男性的自我修为,后来又猜测那是某种感情创伤带来的习惯性躲闪。或许帅哥总能轻松地追到女孩,但女孩们最后总会为了平凡的日子和安全感而背叛他。让我打开你的心扉,让我给你带来一些滚烫的真爱,五千想,真爱无所保留,燃烧一切,我就是你需要的那个女孩。这一次之后,小邱两周都没找五千出来吃午饭散步,只是发信息说,太忙了,脱不开身。五千开始还关照他叫外卖按时吃饭,逐渐便心生怀疑。她发现自己开始在上班时幻想冲进小邱公司与他对峙的场景,甚至计划下班后在他写字楼下的便利店守株待兔。她对小邱的火苗被一盆冷水浇得更旺了。“不用躲着我,我不是那种会纠缠人的女的。”五千按出一条信息,又删了。这一整天,她魂不守舍,什么也做不下去。每过一会儿,就打开跟小邱的对话框,无意识地往下划,似乎期待能加载出什么新内容。对话框又弹回原处,两人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三天前,五千说“天气真好啊”,小邱说“嗯”,然后五千拍了拍“小邱”,说对不起认错人了。就在这毫无交流的72小时之内,五千对小邱的热情升温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两周前她还自问喜欢上小邱是否只是因为寂寞,而现在她确信自己喜欢小邱含蓄又骄傲,以及他一切的缺点和优点。昨晚,她靠在枕头上把跟小邱认识两年以来发过的所有信息全部看了一遍,惊奇地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上过一次头,只是当时她还没准备好恋爱。今年年初,小邱告诉五千会来她隔壁写字楼面试新工作的那次,两人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个钟头,讨论附近有哪些餐馆和咖啡厅。这难道不能说明他喜欢我吗?五千想,明明应该多跟新同事相处,却三天两头来找我吃饭,这还不够明显吗?我主动先打破僵局,免得他不好意思,他到底还在躲闪什么?就算有顾虑,不能好好地说清楚吗?我是全世界最通情达理的最成熟的女孩了,这样躲着我,也太小看人了。五千感到胸口发闷,她真想立刻就见到小邱,把刚才所有的问题都一股脑儿抛给他。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六点,五千逃出办公室,蹓跶到了街心公园。他穿着常穿的那件水蓝色T恤,五千一眼就看见了。她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尽力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快步向前走去。啊,五千?你怎么来了?我有种感觉会看到你……其实,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她的脑子自动想象着小邱会对她说些什么,同时紧紧盯住他的身影,仿佛怕他原地蒸发。人影闪动了一下,从喷泉后面走了出来,五千的心沉了下去——不是小邱,是一个穿着蓝衬衣的房产中介,正在拍摄晚霞。五千愣住了。她感到血液正迅速从自己的脑部流失,眼前的景象开始慢慢变形。夕阳夹在两排写字楼之间慢慢下沉,落在喷泉中心,从五千的角度看过去,金红色的水柱跃动着,就像一座火泉。 朱利安 • 查理埃,《烈焰之下,静水深流》(静帧),2019,超高清影像,有声,11分13秒“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图片致谢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
阿伦·雷乃,《苯乙烯之歌》,1958,图片来自网络咔哒,咔哒咔哒,咔哒,金属片中间的小圆口里冒出一个火星,就再没了动静。透明的黄色塑料壳里只剩下一层油,依旧在底部保持着左右两边不同的高度。老冯使劲儿晃了晃打火机,凑到鼻子跟前,左手紧紧罩在右手上方,小心挡住西北方向吹来的风。咔哒。香烟像是嘴的延伸,抻长了身子,徒劳地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等到。去你妈的。老冯一挥手,把打火机甩了出去,在路边垃圾箱上撞了一个粉碎,过路的行人和狗投来不满的目光。他叼着一根蔫头巴脑的烟,强迫受到尼古丁挑逗的神经镇定下来,一边摸遍身上的每一个口袋,一边四处张望起来。没有一个人在抽烟,甚至没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会抽烟的人。这倒霉的高档街区,一切整洁、有机、健康、性冷淡,跟刚吃完的素牛肉一样让人扫兴。他想直接走人,不,要进门对着苏明的粉框眼镜吐口唾沫,然后在他和那个假洋鬼子马丁惊慌失措的目光中离开。去你妈的“拙朴感”,去你妈的“别太具象”。他忍住了。老冯把烟塞回去,再塞进后裤口袋,紧了紧衣服,深深吸了一口气,让冰冷干燥的空气充满肺泡。然后他转身推门回到了餐桌前。事情聊完了,两幅方形油画,每幅一米二边长,总共三万块,预付一半。风格要禅意,寂寥,可以有一定的联想空间,但要避免任何具体的形象。下周先看小稿,一个月后完成。三个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苏明送完马丁,回来时老冯已经把外套穿好了。苏明拍了他肩膀一下,一屁股坐下。“急什么呀?再来杯咖啡?咱俩多久没见了?”“啤酒?他们这儿精酿还不错。”苏明看了一眼手机,“两点半,是不是早点儿了?”老冯往外走,“不喝,谁在这儿喝啤酒,烟也不能抽。”苏明套上衣服跟出去,“唉,你什么时候戒啊?现在都不兴抽烟了。我刚还跟小马丁好一顿解释。”“不是,现在,高端的一点儿艺术家都没有抽烟的,万一人家以为我找了一个骗子……”苏明愣了一下,“不是吧老冯,那是二十年前小屁孩说的,你有病吧?不赚钱,你那破手机还要用几年啊?”“你才有病。看你戴的那个破眼镜,娘里娘气的,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注意发言。你现在怎么这么保守?以前可是数你离经叛道啊!”“不是你说人不能一辈子上班,要追求艺术,追求个性的吗?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你是不是跟我闹着玩呢?”老冯越走越快,苏明的喘息声伴着一小团幽灵似的白雾在他右后方一上一下地浮动。他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是在厂里食堂门口说的。当时,他和苏明都在县城里的塑料模具厂上班,他从小就对色彩特别有感觉,每天在车间看着那些五彩斑斓的塑料颗粒,经常兴奋地想要跳进去。不上班的时候,他就在家画画,工作服上溅一身彩点儿也不洗。其他工人都把他当神经病,只有苏明崇拜他。那一天,一个据说是艺术家的年轻女孩带着几个摄影师和助理来厂里拍电影,老冯看着他们一队人马出了神。吃完午饭,跟苏明凑在一起抽烟时,他便说了这句话。一个月之内,他和苏明就先后辞职了,两人到省城开起了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真赚了一小笔,买墨镜买皮衣,谈女朋友,花钱不眨眼。后来,广告公司卖给一家当地的房地产集团,苏明去了总公司,老冯靠着收购金,什么也不干,搬到城郊一个画家村,天天画画。如今,苏明搞起了室内设计,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他继续跟在老冯后面吐气,说,“现在吧,土老板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客户里好多都是小马丁这样的。你刚也听见了,人家不搞艺术收藏,就是为了挂在家里,但也不想弄那种没有灵魂的、现成的装饰画,对吧?所以现在非常需要你这种,有自己的想法的,真正的艺术家。可是,你得进步啊。思想跟时代同步,审美才能跟得上,才符合市场的需求。你看你大我一岁,对吧?今年也才四十七,要是还能再画——”老冯突然冲到马路对面,朝一辆出租车伸出手。苏明在对面喊,“别拦啦,那都是人家叫的车,我给你叫一辆!”刚解锁手机,抬起头,老冯已经坐上了车。 老冯看见苏明跑过来,在外面敲车窗,指指自己手机,又指指老冯。老冯没理他,叫师傅开车。几分钟后,手机震动,老冯收到苏明转账,备注“预付款”,点一下,显示“接收”或“退回”。老冯关掉屏幕,把手机在手里转了几圈。那是一部如今已经难得一见的 iphone 5c,果绿色的塑料壳上满是划痕,一条条黑乎乎的。离开厂这么多年,老冯对塑料还是有感情,那是廉价的,也是实用的,是快速的,也是耐久的,是人工的,也是未来的,像二十岁的小伙子,永远色彩饱和,永远期待明天。当然,明天终究会成为昨天。现在的人们,不管几岁,不再歌颂未来,他们害怕未来。老冯把手机揣进口袋。他闻了闻车里的空气,从后裤兜里摸出半包烟,对司机说,师傅,您有火吗? 以上2图:阿伦·雷乃,《苯乙烯之歌》,1958,图片来自网络阿伦·雷乃,《苯乙烯之歌》,单通道影像,有声,13 分 11 秒,1958“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 王思顺,《深渊》,铅,240×170×110,厘米,2014“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一阵孤独感经过了我,就像几个假期里无所事事的青少年经过了坐在小区门口的老太太。他们漫不经心地踢着小石子儿,沿着一条长长的下坡路走远,一两句叫喊声从地平线以下飘来,然后一切重归于静。十二点半,吃饭的念头令我烦闷不堪。做饭的那些重复而琐碎的动作,并不因为我现在有了大把的时间就显得有趣一些。昨天下午三点以后我就没有吃过东西,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大脑拒绝调动身体,将力气集中在水龙头、砧板和打火灶上。我坐在地毯上,靠着沙发腿,刷起了外卖软件。吃外卖的感觉像吃广告。如果一段时间内连续吃外卖,胃就不再信任眼睛。溜光铮亮的豉油鸡酥皮,黄澄澄的掉渣炸猪排,翠绿饱满的荷兰豆配黑木耳和白莲藕,盖上浮夸的综艺字体和划线标价,都不会再引起口水分泌,只能引起反酸。放进购物车,选择一套餐具,使用免费膨胀优惠券,等待数字的跳动——资本为了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交钱而进行的一场抚慰人心的小小表演——结束,然后提交,跳转到另一个app支付,返回商家,盯着萌态的骑手小人在虚拟世界缓缓接近我的位置,一个机械跳动着的红色圆点儿。一切将结束在被撕烂的手提纸袋,挂着汁水的保鲜膜,一团团纸巾和成分略有改变的空气中。我会感觉饱了,但不会感觉更好。我的身体会得到更多用以延续自身生命的能量,但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自然消耗、补充、延续、再消耗……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补充。我查了一下银行账户,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个月。我还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就停止补充,这样可以将进程加快到一周左右。我还可以有更快的选择,也许一个下午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个方案需要付出相当的动力,那是我所没有的。我更像一棵植物,可以慢慢枯萎,却不能拔出自己的根。我所知道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死法,是在华丽的城郊度假别墅中暴食而死。在顶级厨师所烹饪的装饰成小小吸血鬼的烤鹌鹑,能当床垫用的厚厚的苹果派,和能覆盖一片私人狩猎园的动物腊肉中,破坏自己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然后暴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在践行这种死法,只不过更漫长些,我们的凶器是一个中世纪人几辈子才能消化掉的信息,装满几个集装箱的物品,和无尽的优惠方案,我们选择下手的是自己的神经系统。辞职三个月了。最初的快乐已经消耗殆尽。大脑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集中精力之后,似乎立刻卸载了这个功能,它现在只会散漫地,温吞地动一动,像一大坩锅浓稠的汤,在一直没有熄灭的小火的烘烤下,随机地、偶尔地冒出一个泡泡。我曾有过一些美好的想象,自由地支配时间,去完成我的计划。但我很快便发现,阻碍我的并不是时间。如果可以用空间做一个比喻:曾经我在一个狭小的,仅够一个人匍匐通道里,没有掉转身体的余地,只能往前爬行。前方似乎有光,但它从未因为我努力爬行而显得更近。终有一天,我对管道说,放我走吧,它于是打开了一个洞,我便从洞口掉了下去。如此,我来到一片平原,一片绝对的完全的荒原,没有任何遮挡,也没有任何边界,抬起头,天是圆的。我发现无论走到哪个位置,抬起头来看天,都没有任何变化。于是我没有必要继续再走了。世界也许是用一个巨大的铅块打成的结构,正在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坍缩,或者像烤化了的沥青那样缓缓融化,其幅度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体会,可能在世者谁也没有机会看到它崩塌的一天。可你一旦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就无法再忽略它,你的心也随之变成一个铅块,除了缓缓向下沉,别无选择。我继续往下滑了滑,几乎是平躺在了地毯上。这种沉重的想象现在幻化成了一丝睡意,向我压来。我的身体逐渐开始麻木,地板也从我的背后消失。也许这就是最终的告别吧,我的意识挣扎着形成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然后我便睡着了。再次醒来时,海豚站在我的肚子上。他饿了,他说,喵。 郭城,《倒数 No.1》,沥靑,定制木拖车,定制电路,钢丝绳,尺寸可变,2023“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
王思顺,《深渊》,铅,240×170×110,厘米,2014“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一阵孤独感经过了我,就像几个假期里无所事事的青少年经过了坐在小区门口的老太太。他们漫不经心地踢着小石子儿,沿着一条长长的下坡路走远,一两句叫喊声从地平线以下飘来,然后一切重归于静。十二点半,吃饭的念头令我烦闷不堪。做饭的那些重复而琐碎的动作,并不因为我现在有了大把的时间就显得有趣一些。昨天下午三点以后我就没有吃过东西,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大脑拒绝调动身体,将力气集中在水龙头、砧板和打火灶上。我坐在地毯上,靠着沙发腿,刷起了外卖软件。吃外卖的感觉像吃广告。如果一段时间内连续吃外卖,胃就不再信任眼睛。溜光铮亮的豉油鸡酥皮,黄澄澄的掉渣炸猪排,翠绿饱满的荷兰豆配黑木耳和白莲藕,盖上浮夸的综艺字体和划线标价,都不会再引起口水分泌,只能引起反酸。放进购物车,选择一套餐具,使用免费膨胀优惠券,等待数字的跳动——资本为了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交钱而进行的一场抚慰人心的小小表演——结束,然后提交,跳转到另一个app支付,返回商家,盯着萌态的骑手小人在虚拟世界缓缓接近我的位置,一个机械跳动着的红色圆点儿。一切将结束在被撕烂的手提纸袋,挂着汁水的保鲜膜,一团团纸巾和成分略有改变的空气中。我会感觉饱了,但不会感觉更好。我的身体会得到更多用以延续自身生命的能量,但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自然消耗、补充、延续、再消耗……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补充。我查了一下银行账户,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个月。我还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就停止补充,这样可以将进程加快到一周左右。我还可以有更快的选择,也许一个下午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个方案需要付出相当的动力,那是我所没有的。我更像一棵植物,可以慢慢枯萎,却不能拔出自己的根。我所知道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死法,是在华丽的城郊度假别墅中暴食而死。在顶级厨师所烹饪的装饰成小小吸血鬼的烤鹌鹑,能当床垫用的厚厚的苹果派,和能覆盖一片私人狩猎园的动物腊肉中,破坏自己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然后暴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在践行这种死法,只不过更漫长些,我们的凶器是一个中世纪人几辈子才能消化掉的信息,装满几个集装箱的物品,和无尽的优惠方案,我们选择下手的是自己的神经系统。辞职三个月了。最初的快乐已经消耗殆尽。大脑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集中精力之后,似乎立刻卸载了这个功能,它现在只会散漫地,温吞地动一动,像一大坩锅浓稠的汤,在一直没有熄灭的小火的烘烤下,随机地、偶尔地冒出一个泡泡。我曾有过一些美好的想象,自由地支配时间,去完成我的计划。但我很快便发现,阻碍我的并不是时间。如果可以用空间做一个比喻:曾经我在一个狭小的,仅够一个人匍匐通道里,没有掉转身体的余地,只能往前爬行。前方似乎有光,但它从未因为我努力爬行而显得更近。终有一天,我对管道说,放我走吧,它于是打开了一个洞,我便从洞口掉了下去。如此,我来到一片平原,一片绝对的完全的荒原,没有任何遮挡,也没有任何边界,抬起头,天是圆的。我发现无论走到哪个位置,抬起头来看天,都没有任何变化。于是我没有必要继续再走了。世界也许是用一个巨大的铅块打成的结构,正在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坍缩,或者像烤化了的沥青那样缓缓融化,其幅度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体会,可能在世者谁也没有机会看到它崩塌的一天。可你一旦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就无法再忽略它,你的心也随之变成一个铅块,除了缓缓向下沉,别无选择。我继续往下滑了滑,几乎是平躺在了地毯上。这种沉重的想象现在幻化成了一丝睡意,向我压来。我的身体逐渐开始麻木,地板也从我的背后消失。也许这就是最终的告别吧,我的意识挣扎着形成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然后我便睡着了。再次醒来时,海豚站在我的肚子上。他饿了,他说,喵。 郭城,《倒数 No.1》,沥靑,定制木拖车,定制电路,钢丝绳,尺寸可变,2023“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 安妮·格拉夫(Ane Graff),《失忆与其他缺失》,土壤,高脚杯,尺寸可变,2023乌苏拉·比尔曼&莫·迪纳(Ursula Biemann & Mo Diener),《百分之二十一》,单通道影像,有声,17分钟,2016
安妮·格拉夫(Ane Graff),《失忆与其他缺失》,土壤,高脚杯,尺寸可变,2023乌苏拉·比尔曼&莫·迪纳(Ursula Biemann & Mo Diener),《百分之二十一》,单通道影像,有声,17分钟,2016图片由艺术家和美凯龙艺术中心提供
如果你也想受到元素的启发,可以前往美凯龙艺术中心观看这次信息量丰富的跨学科背景展览,了解关于铜、锡、铅、金、塑料、沥青、云母、沙、火、水、土、以太、岩石、真菌的奇怪一面。展览《元素小说》将展出至2024年2月5日。“元素小说”展览现场,MACA美凯⻰艺术中心,2023。摄影:杨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