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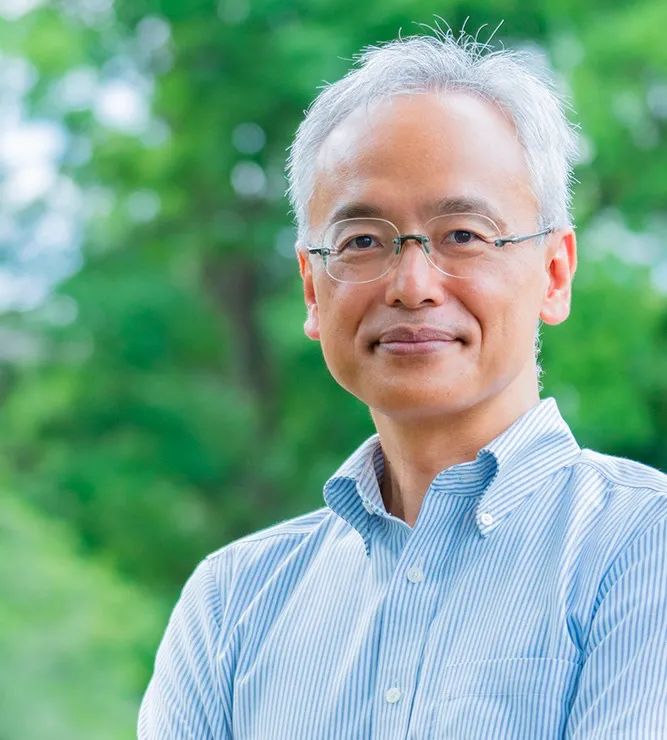 日本科学家中村泰信和同事在24年前演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极大地推动了量子计算领域的可扩展性,让人们看到量子计算未来落地的巨大潜力。最近,他又领导建造了日本第一台量子计算机。Credit: RIKEN
日本科学家中村泰信和同事在24年前演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极大地推动了量子计算领域的可扩展性,让人们看到量子计算未来落地的巨大潜力。最近,他又领导建造了日本第一台量子计算机。Credit: RIKEN
图源:https://rqc.riken.jp/
在科学漫长的历史中,“小幅”进步的积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能为之增加一点点增量,我会很高兴。我并不希望成为科学的霸主。所以,如果有人能认可我的工作,并在我的成果基础上开展他们的工作,我已非常满足。我没什么野心,除了建造量子计算机!
——中村泰信,物理学家,2021年“墨子量子奖”得主
量子沙龙|来源
1997年秋天,29岁的日本电气公司(NEC)研究员中村泰信(Yasunobu Nakamura)和同事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报告了一个新发现:他们在一个微米大小的超导电路中,观察到了量子叠加的证据[1]。
中村泰信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他一直对量子物理和量子现象充满兴趣,这个实验解答了他的一个重要疑问:能否在尺寸远远大于原子的宏观器件中,创建量子叠加态。中村泰信意识到,他的超导器件经过改造,很有可能实现量子比特。那么,什么是量子比特?量子计算又是什么?中村泰信之前并不了解这些术语。然而,他忍不住开始着手研究这些概念,然后跳入了量子计算的世界,一个充满奇妙可能性的兔子洞。一年半后,他和同事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成功展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导量子比特。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2],轰动世界。“当我们第一次进行超导量子比特实验时,这是首次在固态器件中实现量子比特的相干控制。这就是人们兴奋的原因。人们更容易想象这种技术未来的发展,就像(已有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样。”2023年秋天,在合肥举行的第二届新兴量子技术国际会议(ICEQT2023)的间隙,中村泰信向我回忆道。现年55岁的中村泰信,是东京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教授,同时也担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量子计算中心的主任。他在2023年3月成功建造出日本的第一台量子计算机[3]。他与米歇尔·德沃雷(Michel Devoret)、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一起荣获2021年“墨子量子奖”——一项由中国企业家捐赠的量子信息和量子技术领域的国际学术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开创超导量子电路和量子比特领域的领导作用。
2023年9月底,他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第二届新兴量子技术国际会议,并出席了因新冠疫情推迟了一年多的“墨子量子奖”颁奖典礼。 中村泰信在“墨子量子奖”颁奖典礼的照片
中村泰信在“墨子量子奖”颁奖典礼的照片
颁奖典礼第二天,中村教授准时出现在了会场外的走廊上。他的头发自然灰白,整齐利落,身穿藏青色的夹克衫,搭配卡其色的休闲裤,脚下是透气的棕色凉鞋,深色袜子隐在鞋后,给人一种亲切而放松的感觉。
中村教授告诉我,在1997年的时候,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涉足量子计算领域。“我当时无法预测自己未来几年会做什么,”他说。同样地,如今他也无法预测未来是否会实现通用量子计算,也不知道何时可能会发生,尽管许多机构都已经制定了看似清晰的发展路线图。“突破是无法预测的。”
他说,量子计算是物理和技术领域的终极挑战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自然遵循着量子力学的规则。“如果我们能够在量子力学的层面控制一切,我们就可以做到无所不能。”
“因此,量子计算和其它量子技术实际上是在最基本的原理层面操纵自然,进行精细的控制。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终极技术。”中村教授说,“我认为这正是这个领域如此令人兴奋和充满挑战的原因。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1987年,是高温超导领域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两项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将高温超导推上了科学界的巅峰。
首先是当年春天,美国华裔科学家朱经武与中国台湾物理学家吴茂昆把临界超导温度提高到90K以上,突破了液氮的“温度壁垒”(77K)。中国大陆科学家赵忠贤领导的研究组,获得了100K以上的超导体。日本科学家则获得了123K的超导体。接着,两位发现一种陶瓷性金属氧化物存在超导电性的科学家柏诺兹(J.Georg Bednorz)和缪勒(K.Alexander Muller)获得198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他们二人,在1986年1月首先报告成功将超导现象出现的温度提到了30K。超导电性是指材料在低于某一温度时,电阻变为零的现象。超导领域的挑战在于,自超导性在1911年首先被发现,超导现象出现的临界温度都极低,如果能够找到温度更高的超导材料,其应用场景将充满想象力。这些重大突破的发生,让人们看到了超导研究进入高温超导时代的可能性。回到1980年代末,高温超导研究的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加入这一领域,也包括中村泰信。“当时高温超导研究热潮汹涌,仿佛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研究高温超导。”中村教授回忆道,“我就是在发现不久后的1989年加入了那个团队,我们仍然对高温超导充满兴奋。连续三年,我都在钻研这个领域。”硕士毕业后,中村泰信加入NEC公司的基础研究实验室,在那里研究纳米级的电子器件。其中一种器件是单电子晶体管,它在两个引线之间有个不到一微米大小的“盒子”电极。因为电荷效应通过隧道结的电子流,经连接两个电极的“盒子”,强制一个一个穿过。需要注意的是,与单个原子和电子相比,单电子晶体管仍然大了四到五个数量级。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当冷却到低于1K的温度时,铝制的单电子晶体管会变成超导体。然后,电流由成对移动的电子组成——这些在超导状态下出现的特殊电子对,被称为“库珀对”。这时,单电子晶体管就变成了单库珀对晶体管,逐个输运库珀对。“当我们研究这种器件在超导状态下的行为时,我们产生了创造量子叠加的想法, 仅仅是出于对物理的好奇心。”中村教授说,“正如我昨天在演讲中提到的,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在宏观物体中实现量子叠加,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量子叠加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光子、原子和电子等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两种或多种状态的奇怪行为。举例来说,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存在于这里和那里,但直到我们测量它,它才会确定为其中一种状态。在数学上,这种微观粒子的奇特性质可以用薛定谔方程来表示。1985年,理论物理学家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J. Leggett)提出,可以利用一种含有约瑟芬森结的超导器件来观察宏观尺度上的量子现象(macroscopic quantum phenomena),也就是宏观尺度下的量子力学效应。约瑟夫森结是由两块超导体和中间一个极薄的绝缘层组成的固态器件。在这个结构中,一块超导体中的库珀对可穿过绝缘层进入另一超导体中,这是特有的量子力学的隧穿效应。中村泰信和同事设法观察到,在微波辐射下,由一个约瑟夫森结和另一个连接到库珀对盒的外部偏置隧道结组成的“库珀对盒”电路,其电流峰值可以随着微波频率的变化而改变,揭示了能级的分裂,成为一个二能级系统。 这些实验结果显示,库珀对盒的两个电荷数状态可以相干叠加。这篇论文发表在1997年9月的《物理杂志快报》上。随后,来自德国(1997年9月,1999年3月)[4]、美国(1998年6月)[5]和法国(1998年1月)[6]的多个小组预言,单库珀对盒可以用来制造量子比特。如今,中村教授可以非常轻松地向我介绍,量子比特是量子信息处理一个非常基本、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如比特在经典计算机中的作用一样。在经典计算机中,我们使用比特来处理信息,一个比特表示0或1。“比特是用晶体管表示的,例如,晶体管是否打开,意味着电流是否通过晶体管(这样可以来表示0或1)。”中村教授说。而在量子计算机中,处理信息需要用到量子比特。“与经典比特相比,量子比特可以表示它们的叠加态,不仅是0或1,而且有时是0和1,这就是叠加态,一种非常反直觉的状态,它使我们感到困惑。但是,如果你相信量子力学,那么就知道叠加态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属性,量子比特可以支持0和1的叠加态。”中村教授解释说。然而,在中村教授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没有‘qubit’(量子比特)这个词”。关于量子计算的起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198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第一届计算物理学会议上做的一个预言[7]。他当时指出,没有任何经典计算机可以模拟大型量子系统,也许只有利用量子力学,我们才能模拟出一个量子世界。尽管量子计算的概念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相关研究一直不温不火。直到199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Peter Shor 提出量子算法[8],用于质因数分解,使得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做出超越经典计算机的任务。这引发了人们对量子计算的广泛兴趣。很快,许多来自物理学不同领域的人开始思考如何实现量子计算机。光学和原子、核磁共振以及固态物理学领域的研究者纷纷涌入了这个领域,他们相继利用困在电磁场中的离子、原子核的自旋、甚至核磁共振的分子等实现了量子比特。然而,这些早期的进展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而当时身在日本的中村泰信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些进展,甚至在 1997 年秋季发表的论文中,他和同事根本没有提到“量子比特”(qubit)这个词。中村教授回忆道,“我听到了一些传闻,然后我明白了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作量子比特。所以,那是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方式……在那之前,我周围没有人认真讨论量子计算。”最终,中村泰信和尤里·帕什金(Yuri Pashkin)、蔡兆申利用包含约瑟夫森结的超导电路,来控制“电荷量子比特”的基态和激发态之间的相干叠加,并观察到两种状态之间的量子振荡,这是固态器件中量子比特的首次演示。“1999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时,我们被来自日本的一个惊雷‘炸’到了。来自NEC的蔡兆申和中村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单库珀对盒中宏观量子态的相干控制’的论文。通常情况下,我们对我们领域的实验室中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即使工作还没有发表。NEC 小组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但更遥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遥远。”2017年,荷兰物理学家汉斯·莫伊(Hans Mooij)[9]在一篇回顾超导量子比特发展历史的文章中回忆道。莫伊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荣誉教授,曾经担任卡维理纳米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长期从事纳米尺度量子效应的研究。此外,当时的人们对于固态量子比特的可能性并不太看好,因为与单个离子、原子、分子相比,固体系统包含大量电子,与周围许多不可控制的自由度相互作用。理论上,要选择一个特定的自由度进行操控更加困难。然而,无论是俘获的离子,原子,还是核磁共振分子,都是在真空或液体中实现量子比特。如何将它们与现有的经典计算机基础设施相结合,以进行控制以及扩展它们,即增加量子比特的数量,也存在许多实际挑战。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在固态器件上的成功演示,让人们看到量子计算未来落地的巨大潜力。“要构建计算机,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量子比特,对吧?不仅仅是单一的、少数的量子比特。但是要把数百万个量子比特集成在一起,人们很难想象,就像要把数百万个原子精确对齐一样。但当时,硅技术已经非常普遍地用于晶体管和计算机芯片。因此,想象在芯片上构建量子计算机要容易得多。这才是它吸引了大量关注的原因。”中村教授说。但是,中村泰信对于超导量子比特的前景并不乐观。存储在量子比特中的信息只能存活最多1纳秒,相当于1秒的十亿分之一。如此短暂的时间,意味着只能执行几次量子门操作,然后信息就会丢失,更不用说模拟复杂的量子力学世界了。如今,在全球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之下,超导量子比特的寿命已经大大延长。事实上,它们最近可以持续数百微秒,比24年前整整提高了六个数量级。更长的寿命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做更多的精细操作,从而帮助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直到今天,中村教授仍然认为,演示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是超出了他预期的事件,而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遇到了好人。
“我的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朋友和同事,如 Michel Devoret和John Clarke。从我研究的非常早期的阶段开始,我就认识了这些领域的伟大人物,他们总是非常友善,乐于助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我认为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在生活中,结识好人很重要。”中村教授说。Michel Devoret是法国物理学家,现为耶鲁大学应用物理和物理学教授。他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ohn Clarke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宏观量子隧穿效应。1985年,他和Clarke教授,以及Clarke教授当时的博士生John Martinis共同证明了约瑟夫森结电路中能级的量子化。之后,他回到法国,在萨克雷原子能委员会 (CEA) 从事量子力学电子学方面的研究。2002年加入耶鲁大学。中村教授说,Devoret教授和Clarke教授在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宏观系统中的量子力学了。“他们对量子力学感兴趣,而不是量子计算,因为那时还没有量子计算……后来,他们也开始研究单电子晶体管,这是我在 NEC 刚开始时做的工作。当我刚到NEC 工作时,基本上周围没有人熟悉那个领域。所以,我不得不从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论文和博士论文中学习。Michel Devoret 的团队是世界顶级团队之一。所以,我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直到1996年,中村泰信第一次前往欧洲旅行,才见到了Michel Devoret教授。“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有了很多交流,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一开始,没有人谈论量子计算,因为它还不那么普遍。我们只是对物理学和宏观尺度上的量子叠加有共同的兴趣。”1999年,Michel Devoret教授访问了中村泰信所在的NEC实验室,那时中村泰信和同事恰好刚刚完成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的实验。“我向Michel展示了结果,他当时非常兴奋……我真的很高兴与Michel 和John一起获得墨子量子奖。我们从未直接合作过,也从未共同撰写过论文,但我们一直在同一个领域工作,并且分享了很多想法。我们就像合作者一样。”中村教授说。中村教授说,他遇到的另外一位好人,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Hans Mooij。“当我在 NEC 开始单电子晶体管研究时,我从其他团队学到了很多东西,代尔夫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团队之一,类似于Michel Devoret的团队。”中村教授说。2001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访问的中村泰信,本图由受访者提供大约在1995 年,中村泰信与在日本访问的Mooij结识。六年后,当中村泰信有机会学术休假一年时,他想到了三个可以访问的课题组,分别是代尔夫特团队、萨克雷的Devoret团队、瑞典的查尔默斯大学。最后,他选择了去代尔夫特。“因为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类型的超导量子比特。我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从2001年到2002年,中村泰信和Mooij的合作取得了超导量子计算的重大突破:2002年夏天,他们首次实现了对磁通量子比特(Flux qubit)的相干控制。这种类型的超导量子比特,在相干性方面优于电荷类型的超导量子比特,可以运行的时间更长。
2002年夏天,中村泰信和Hans Mooij合作,
首次实现了对磁通量子比特的相干控制,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关于经典计算机的发明,一般认为是数学家引领的信息革命。无论是阿兰·图灵,还是冯·诺伊曼,他们首先都是数学家,通过逻辑运算和程序思维,为经典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到了量子计算,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物理学家主导的一场革命。中村教授说,“也许从外界角看,量子计算研究似乎基本上是由物理学家领导的,这实际上是因为只有物理学家对关心量子力学有深刻的兴趣。”
他继续说道,“也许最初将量子力学应用于计算的想法来自物理学家。但后来,更多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加入了这项研究。这非常重要,因为物理学家通常不会像他们那样深入理解计算。你知道 Peter Shor,他更多的是数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所以,实际上,我认为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领域,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新领域,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加入其中。与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交谈是非常令人振奋和兴奋的。”中村教授说。他表示,一开始,他们遇到了语言障碍,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使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类似的概念。“有时很难理解彼此。但在同一个新领域一起工作后,我们开始使用量子信息科学的新语言更好地相互交流。这确实创造了新的想法和新的突破。”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中村泰信喜欢与研究理论的同事交流。“在我们的RIKEN 量子计算中心,我们有几个由理论家领导的理论团队。在我的研究小组中,虽然没有100%的理论家,但有些人擅长做理论工作。我一直很喜欢与理论家合作,因为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研究者,我的方法有点更像是一种直觉的方法。我不擅长写出严格的理论。所以,我需要合作。”他解释说,量子计算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技术专业知识,每个层次涉及理论和理论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建立理论,描述实验和理解基本物理非常关键。自2018年以来,中村泰信一直担任日本“量子飞跃旗舰计划”(Q-LEAP)下的“超导量子计算机[10]研发项目”的负责人,致力于超导量子计算的实现。Q-LEAP是日本政府投资的一个大规模量子技术项目,包括量子计算、量子测量与传感、下一代激光器等。中村教授介绍说,日本与中国、美国等国家一样,加大了对量子技术的投入,这一变化正是始于2018年的Q-LEAP计划。
他认为,日本量子计算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到这个领域,但需要更多的人员来运行项目。他也表示,这一挑战不仅是日本所特有的,而是全球社区所面临的。“由于量子计算和量子技术是真正的新兴领域,而且发展很快,人力资源供给还不够。所以,每位教授,每一个小组负责人都在寻找优秀的研究员、博士后和学生。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初创公司和大企业,他们也正在大量招聘人才。这意味着竞争非常激烈。”中村教授说。因此,他认为,鼓励更多的人加入量子领域非常重要。“也许还不是在日本,但在一些国家,他们已经在大学中开设了量子技术系,以培养更多的学生。这是很重要的。”当被问及给对量子计算感兴趣的年轻人的建议时,中村教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量子科学领域既有趣又充满挑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同工作的领域,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对做一般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他认为,坚持和韧性对于追求量子计算事业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我们不应该害怕失败,因为在研究中,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也无法保证成功。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失败很多次,但有时我们也会成功,这需要辛勤的工作和持续的努力。”他继续说道:“但是,如果你有很好的朋友和良好的合作伙伴,那将让你的生活轻松许多。与他人的讨论和交流总是带来新的想法和新的线索。这是我在科学中最喜欢的部分。我总是喜欢与人们交谈,即使是像你这样的记者。”作为一项国家项目的负责人,中村教授认为量子计算是一个需要个体科学家和团队之间大量合作的研究领域。“当然,政府希望促进国际合作,有时他们制定一些自上而下的合作计划。但我认为这种合作研究应该更多地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进行。最终,真正做实际工作的人是研究人员。因此,我认为最重要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之间的互动。当然,如果有了一些总体方案来简化合作流程,那就更好了。”他还提到,过去几年的COVID-19大流行使旅行变得困难,这确实令人难过。此外,地缘政治问题也对科学家的正常交流和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我认为如果不相互交流,这对我们全球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非常不利。在中国,我看到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如果彼此断开了连接,那将会非常糟糕。所以我很高兴被邀请来到这里。当我收到邀请的电子邮件时,我立即就答应了。”中村教授说。2023年3月,中村教授带领的RIKEN量子计算中心推出了一台64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机[11],这是日本建造的第一台超导量子计算机。今年,也就是2024年,中村教授告诉我,他们团队将把它扩展到 144 个量子比特。 日本第一台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https://www.riken.jp/pr/news/2023/20231005_1/index.html
日本第一台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https://www.riken.jp/pr/news/2023/20231005_1/index.html
他承认,在扩展方面,他们可能无法一些国际巨头竞争——有的公司已经在运行超过一千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12],但他仍然对开发扩展量子比特的架构或方法感兴趣。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芯片尺寸的增加,(量子比特的)布线布局无法简单地进行扩展……在我们的方法中,我们设计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垂直布线架构,这样使得扩展变得简单。我们定义了一个2×2的四量子比特单元。对于64量子比特,我们只需将它们平铺16次。要制造144量子比特,我们只需更多的单元格,”他解释说。他也承认,虽然垂直布线的设计很有意思,但要实际扩展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这就像我们知道量子计算的路线图可能是什么样,但现实的进展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在国际学术界,量子计算机研究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阶段,首先,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其次,开发量子模拟机,可以解决超级计算机无法胜任的问题,如量子化学、新材料设计、优化算法等;第三,研制可编程量子原型机,包括可编程的通用量子计算原型机。当中村教授在2023年ICEQT会议中做墨子量子奖获奖人的报告时,他提到了IBM公司关于量子计算扩展的路线图,并介绍了量子计算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例如量子纠错,量子退相干、噪音和干扰。“老实说,我自己没有这么明确的路线图,因为我们有许多挑战需要解决。其中一些看起来非常困难,我还不知道如何解决。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突破,但突破是无法预测的。幸运的是,它们通常会通过社区中的人们的累积努力最终发生。”中村教授强调,半导体行业会根据技术细节和社区输入共同建立路线图,但在量子技术领域,“我们的技术成熟度仍然远远不够。所以,预测未来并不容易。”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他从未对自己研究的重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而是谈到了他对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能够研究量子物理的深切感激和欣赏:“量子物理学是如此奇怪,它告诉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这个领域的有趣部分……”“在科学漫长的历史中,‘小幅’进步的积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能为之增加一点点增量,我会很高兴。我并不希望成为科学的霸主。所以,如果有人能认可我的工作,并在我的成果基础上开展他们的工作,我已经非常高兴了。我没有别的大抱负,除了建造量子计算机!(I don’t have any big ambitions, except for building a quantum computer!)” 致谢:感谢曹思睿博士对本文的讨论与修改建议,感谢王雨丹对本文采访部分内容所做的校对。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原标题为“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中村泰信的奇幻之旅”,《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致谢:感谢曹思睿博士对本文的讨论与修改建议,感谢王雨丹对本文采访部分内容所做的校对。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原标题为“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中村泰信的奇幻之旅”,《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参考文献:
[1] Y. Nakamura, C. D. Chen, and J. S. Tsai, Phys. Rev. Lett. 79, 2328 – Published 22 September 1997
[2] Nakamura, Y., Pashkin, Y. & Tsai, J. Coherent control of macroscopic quantum states in a single-Cooper-pair box. Nature 398, 786–788 (1999). https://doi.org/10.1038/19718
[3]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scienceatechnology/51868-2023-03-27-05-15-29.html
[4] Alexander Shnirman, Gerd Schön, and Ziv Hermon, Phys. Rev. Lett. 79, 2371 – Published 22 September 1997
[5] D.V. Averin, Adiabatic quantum computation with Cooper pairs, 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 Volume 105, Issue 10, 1998, Pages 659-664, ISSN 0038-1098, https://doi.org/10.1016/S0038-1098(97)10001-1.
[6] V Bouchiat et al 1998 Phys. Scr. 1998 165
[7] https://s2.smu.edu/~mitch/class/5395/papers/feynman-quantum-1981.pdf
[8] P. W. Shor, "Algorithms for quantum computation: discrete logarithms and factoring," Proceedings 35th Annu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Santa Fe, NM, USA, 1994, pp. 124-134, doi: 10.1109/SFCS.1994.365700.
[9] https://blog.qutech.nl/2017/11/04/the-first-delft-qubit/
[10] https://www.jst.go.jp/stpp/q-leap/
[11] https://group.ntt/en/newsrelease/2023/03/24/230324a.html
[12]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10/511012.shtm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日本科学家中村泰信和同事在24年前演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导量子比特,极大地推动了量子计算领域的可扩展性,让人们看到量子计算未来落地的巨大潜力。最近,他又领导建造了日本第一台量子计算机。Credit: RIKEN
中村泰信在“墨子量子奖”颁奖典礼的照片
日本第一台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https://www.riken.jp/pr/news/2023/20231005_1/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