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你心中抽出的线织布做衣,仿佛你所爱的人将要来穿。/纪伯伦《论劳作》
花了近 30 年积攒下的碎布头,已经 150 岁的老衣服,九旬老人口中用了一万年的被子……上个月,服装设计品牌“布言布语”把它们都搬到了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
置身于书店二楼的展览和沙龙现场,这些来自深山手作的织物们展示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指尖的温度留下痕迹,在每一件成衣或布片上留下实体的情感。

“布言布语”今年已经 29 岁,创始人何燕儿将自己称为“做衣服的人”,会为客人修补穿着多年的衣服,从不按春夏秋冬的时装标准来发布新款。
现代社会让许多坚固的事物消散。当象征祝福的“百家衣”消失,计算机不断强调“补丁”的另一种概念,“布言布语”还在年复一年地回收边角料,寻找重新利用的可能;他们探访远藏深山的年迈手艺人,邀请他们重新激活古老的技艺。
这是何燕儿首次向海外介绍“布言布语”的服饰,在沙龙现场,她还分享了酝酿多年的“Mengji Nongga”系列:这是一句来自贵州少数民族的方言,意为「回家吃饭」。
从女性长辈那里传承而来的技艺,织物中流传的精神信仰——美的感召跨越了代际,何燕儿和策展人高煜分别讲述了布与时间、布与人、布与灵的故事,以及器物中留存的关于回归的召唤。
#布的故事里有一种归属感
「Asian Talk 034 Mengji Nongga 回家吃饭」沙龙回顾
嘉宾/何燕儿(布言布语创始人)、高煜(策展人)
她们都是我的“外婆”
何燕儿(布言布语创始人):我做衣服其实有一个渊源。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外婆是一个很有名的能干的妇女,我就记得她不停地在做东西,做衣服做鞋子,尤其是看到她年轻时候绣的枕头顶、绣的鞋子,太惊叹了,这么精细这么美。 ㊟沙龙现场我一直守着外婆,看她做手针活,记住她所有的动作,一针一线地穿梭,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痴迷。等我可以去动针线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动作就是复刻了我外婆的动作。
㊟沙龙现场我一直守着外婆,看她做手针活,记住她所有的动作,一针一线地穿梭,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痴迷。等我可以去动针线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动作就是复刻了我外婆的动作。
1993 年,我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习服装设计。有一堂课是少数民族服饰欣赏课,其中有一条少数民族的裙子。当时我看到那个裙子,我就想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裙子,展开以后是一个大大的圆,有很多很多的褶皱,好像自然里面美好的颜色都在那条裙子上。那条裙子就是照见了我的内心的渴望,好像是一种召唤。 1996 年我去广西,走的那条线路是苗族、侗族聚居的地方,非常原始,一路走一路看,看到他们的服饰,看到他们的木屋,看到他们劳作,各种节日都那么盛大。她们织的布让我很喜欢,她们也愿意把好的东西给我看。在服饰的图案里面,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每个人的血脉里面都有我们的祖先,都有这样的记忆,不论是手的记忆,还是大脑的记忆。在贵州有一句苗语,Mengji Nongga,是“回家吃饭”的意思。Mengji 是回家,Nongga 是吃饭。不论走到哪里,“回家吃饭”都是我最熟悉的声音。曾经的那种记忆,带着这样温度的衣服或者是生活用品,这种制作也叫 Mengji Nongga,这个品牌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地生出来的。在过程中,慢慢地成为了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只是需要很沉静的状态去做这一切。 ㊟沙龙现场Mengji Nongga 这个品牌的出现,我会很不自觉地和我的外婆勾联上,慢慢追溯到外婆的外婆。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血脉传递、基因传递,我会找到更远。我外婆的外婆可能和苗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是同一个源头。
㊟沙龙现场Mengji Nongga 这个品牌的出现,我会很不自觉地和我的外婆勾联上,慢慢追溯到外婆的外婆。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血脉传递、基因传递,我会找到更远。我外婆的外婆可能和苗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是同一个源头。所以当我去到贵州,这种非常原始、非常古朴的地方,我就会发现她们都是我的“外婆”,会有一种回家的声音在召唤,回到最清净的地方,最初始的地方,最源头的地方。
做衣服做到 30 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是被这种强烈的感觉召唤,让我重新去思考做衣服这件事。 ㊟何燕儿儿时的衣服我为什么要做衣服?其实应该从这件小衣服开始。这件衣服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婆给我做的,距现在是六十年。这个小孩是我,那是我的妈妈,这是外婆,这个是外婆的妈妈,外婆的外婆。这些照片从妈妈那传给我,我在家里就把这个照片按照顺序装在一个相框里面。
㊟何燕儿儿时的衣服我为什么要做衣服?其实应该从这件小衣服开始。这件衣服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婆给我做的,距现在是六十年。这个小孩是我,那是我的妈妈,这是外婆,这个是外婆的妈妈,外婆的外婆。这些照片从妈妈那传给我,我在家里就把这个照片按照顺序装在一个相框里面。
何燕儿(布言布语创始人):介绍一下我们上海的一个店铺,在同仁路上。这个店铺的外观的是有尖顶的,内部结构也有几个同样的尖顶,构成了这样的自然的、像部落一样的,有这样的家的气息。这个店铺把布言布语和 Mengji Nongga放在一起。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分不清做出的衣服应该是布言布语,还是 Mengji Nongga。
后来我就这样区分,有贵州的少数民族的妇女参与的,这样的很慢的、更加慢的,带着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就归到 Mengji Nongga。这是我们做衣服的工作室的日常,每件衣服一定要有手工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扣子、手工钉、扣眼儿,手工锁,我们没有那个机械的锁扣眼儿的机器。所以我们的扣子是衣服穿烂了,它也不会掉的。即使很现代的设计,也要用最传统的方式去做,就像酿酒一样。这位老人已经九十六岁,这个是她的被子。她结婚的时候,她的妈妈没有什么送,就送这样的被子,补了又补、补了又补的被子。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因为世世代代的衣服都在里面。然后我问这个被子已经用了多少年了,她们说一万年。因为她们不知道有多少年,她觉得一万年就是很久很久。但这些被子的结果是会被烧掉。因为年轻人不会再住这个木屋了,他们会建成水泥房。他们觉得这个被子又脏又破,没有面子,就会把它烧掉。

㊟老人和“一万年”的被子
我像宝贝一样地把它带回家,然后去洗、去清理,从上面清洗下来很小很小的一批料,然后做成了这些展品。那个小布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再让老人帮我缝在上面,这些都是老人做的。我们从 1994 年开始做衣服,到现在所有的面料的碎料废料都会报给我,然后我们把这些面料进行再设计。这边的衣服,还有那边织的布,全部都是用这种碎布设计的。这些衣服都是带着这样的风格,带着这样的情感。我们怎样才是满怀仁爱地劳作呢?
那就是用从你心中抽出的线织布做衣,仿佛你所爱的人将要来穿。
那就是满怀热情地建造房屋,仿佛你所爱的人将要来住。
那就是满怀温情地播种,欢天喜地地收获,仿佛你所爱的人将要来吃。
那就是把你心灵的气息灌输到你所制作的一切之中去。

㊟妹爸,55 岁,在用竹子编织马尾斗笠

她从 2008 年开始织布

㊟这一个垫子差不多要编一年的时间

有对祖先的怀念
高煜(策展人):我会开始接触到织物,其实也是和我妈妈做的苗族收藏有关系,然后是阿城老师写的一本书,叫《洛书河图》。
他在里边把苗族刺绣的部分和青铜器进行了对照,然后又从这个太极里面推出了八角星的图案——这个八角星的图案也大量分布在苗族的服饰上。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有可能还保存在贵州的这些衣物上。织物的起源是什么?比如西方说亚当和夏娃是为了遮羞,才用衣服来遮来遮蔽身体,东方会说有避寒的需求,那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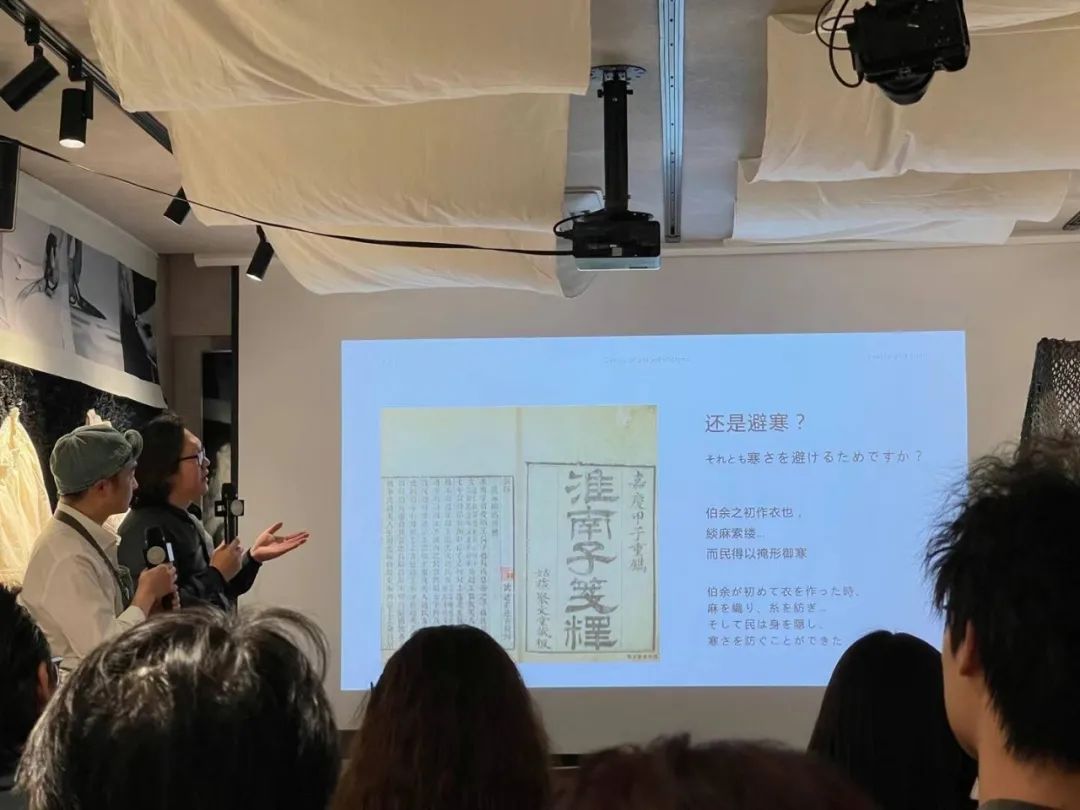
㊟沙龙现场
当我走过太平洋这些小岛之后,我觉得织物可能不完全是为了遮羞或避寒而做的。这些小岛上的部族依然保持着传统,其实他们并没有遮羞的必要,也没有御寒的需求。他们这多数的地方都相信万物有灵官,穿着衣服也完全是为了仪式,为了去和神灵沟通。大概是在 2015 年的时候,我去到印尼的弗洛勒斯岛。我和他们一起去出海,一起去打渔,在他们的船上发现了这样的一块布,很长很长,大概有 8.3 米。他们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就会把自己裹在这个布里边,然后祈求自己能安全地回到家乡、回到岸边。这个布上边会有一些祖先和船的图案,保佑他们能平安归来。这块长布也是由这个村子里边的所有妇女,为她们的丈夫安全归来去做的。

这块布是我收藏的开始,我对它的技法、来历和用途非常感兴趣。在我收集船布的这个岛上,我发现很多年轻女性会穿着一种叫拉乌布图的筒裙跳舞。这些筒裙,其实只有村寨里头地位最高的女性才有资格穿着它,但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不一定是年长的,而是年轻的、生育能力强的,这主要是跟生殖崇拜有关联。但现在的情况是它们在每一个村寨只有一个,因为做这个的人越来越少了。
㊟叫拉乌布图的筒裙
接下来是在苏拉威西岛,这个岛上的葬礼非常有名。他们的葬礼很繁琐,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需要宰杀大量的牲畜。我们 2018 年去采访一家人的时候,这家的妈妈去世了,因为她的地位很高,就需要宰杀二三十头的牛,每一头要七万到八万人民币。他们会用这样的布来包裹尸体,这个尸体会被存在家中,等到攒够了钱才能去办葬礼。这个布料上会有一些勾连的图案,有人解释说它像祖先的手,来招呼这个新的王者加入祖先的行列,加入可以被崇敬的行列。他们会认为人死了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病,只会不会说话了而已。只有当这个人举行了葬礼,举行了社会性的仪式之后,这个人才能被真正地接纳到祖先的行列里。因为要攒够很多很多很多的钱,这个过程大概要三四年、五六年。所以他们会定时清洗、更换这个衣服,包裹在逝去的人的身体上。然后他们那边有比较特殊的防腐机制,就像木乃伊一样,气味也不会很臭。这样的布也会对我的生与死的观念产生影响,它会拓展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然后接下来到婆罗洲,他们比较有名的是关于猎头的习俗,大概在 1920 年都还存在。男性要去猎头,女性就要制作这样的织物。女性在制作这样的布的时候,她需要进入一个通灵的状态,在一个小屋里头自己待三天到四天,不吃不喝,才能接受所谓神的启示,把图案织成布。她织成这样的布所获得的荣耀,和男性去猎头所获得的荣耀其实是相等的。而且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她要在精神的领域里面去和不好的东西搏斗,可能会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很危险。
像我之前介绍的这些布料,它其实是有很强的精神力量在里面。大家会把精神、对神明的敬仰、对祖先的怀念都倾注到这个布料里面。这些布料也会反哺回制作的过程本身,带来护佑的力量。这种由布产生的灵、由布产生的这种归属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想最后用费孝通老师的这一句话来结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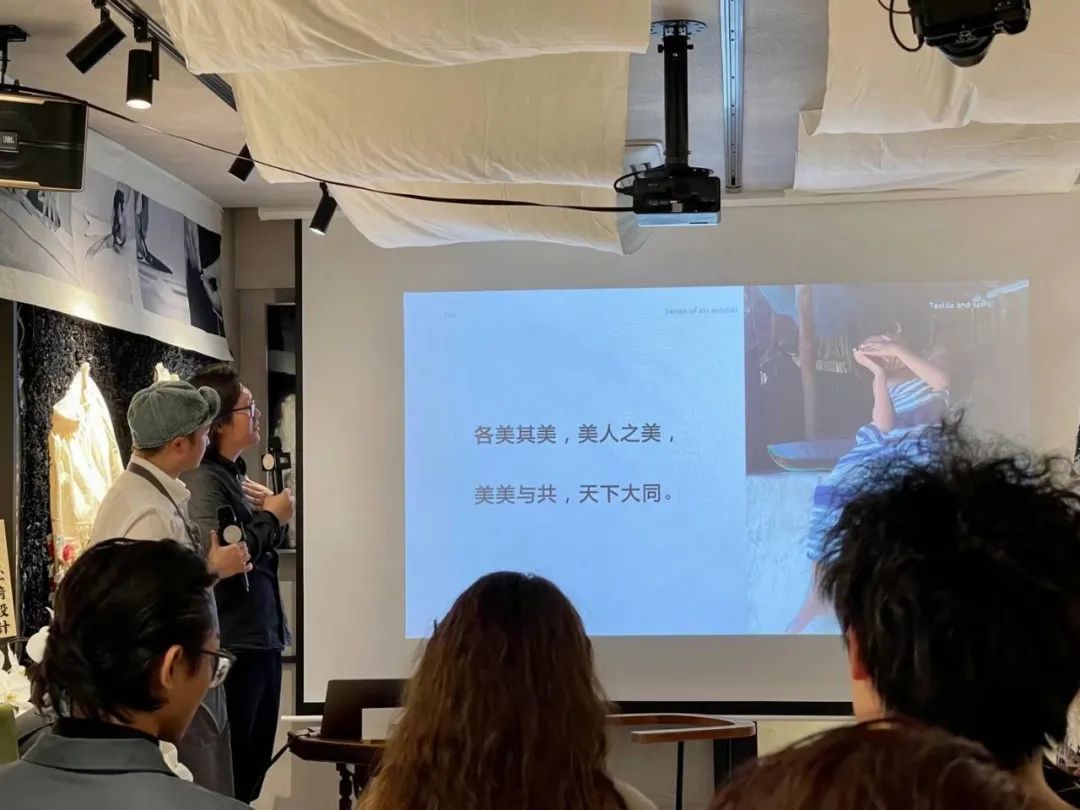
它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去欣赏与我们自身相关联的美,也可以去欣赏他人之美。这句话就点醒我,这两种美之间是共通的,我们最后可以达到天下大同、天下是一家的概念。我认为这个美,其实和 Mengji Nongga“回家吃饭”的这个“家”是一个概念,这个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它可能是精神上的这种归属感,有安心的感觉。这个家它也是美,“回家吃饭”,就是回到这个美的地方来。所以我发现我和我妈妈所做的东西是有共通之处的。与其说是我受到了家族的感召,不如说其实我们都是受到了布的感召,向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