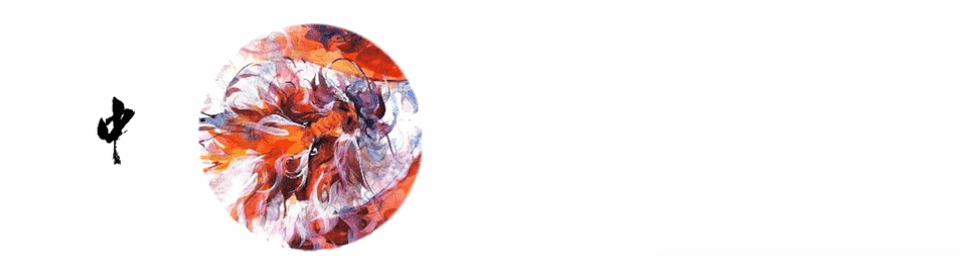

橘树并非河北之物产,是从南方不远万里移植到邺城的“珍树”。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株“异乡来客”面对剧变的环境,无法适应,因而枯萎。但它的死牵动了一位诗人惆怅的心绪。庭园之中,曹植凝视着枯木,专门写了一篇《橘赋》,其中提到:“飏鸣条以流响,晞越鸟之来栖。”这棵橘树经历了“江洲之暖气”到“玄朔之肃清”的变化,无法开花结果,却依然希冀南方的越鸟前来栖息。事实上,孔雀已经来到了北方的园林。杨修便曾写过《孔雀赋》:“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眡。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曰:有南夏之孔雀,同号称于火精。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首戴冠以饰貌,爰龟背而鸾颈。徐轩翥以俯仰,动止步而有程。”根据这篇赋的序言,我们知道,孔雀同样引起了临淄侯曹植的感触,他先写了一篇赋,然后才让杨修也写一篇。可惜曹植的孔雀赋今已不存。曹植和杨修感慨的是士人的命运如同庭园里的孔雀,这些异鸟一开始因其“奇伟”而受到追捧,可时间一久,人们习以为常,便不去瞧它。再美丽的事物,也敌不过人情冷暖。温暖和煦的南方,是一个奇妙未知的世界。那里的珍异物种进入中原,虽然命运“凄惨”,却在北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曹植。图源:影视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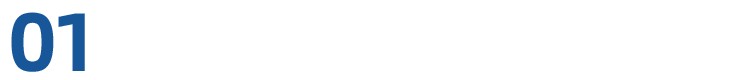
古时候,孔雀被视为文禽。它有着华丽的外观,羽毛晶莹透亮,要么深蓝,要么翡翠,还会呈现出绚丽的眼纹。人们尤为喜欢孔雀的尾屏,清代黄濬《红山碎叶》说:“大开屏时灿烂且久,独其冠有毛一丛,状如小翎……声亦清亮而宏达,真尤物也。”孔雀永远昂首挺胸,目视前方,举止优雅。因此,古人认为,孔雀有九德:“一颜貌端正;二声音清彻;三行步翔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作为受人追捧的瑞鸟,孔雀在古代并不罕见。文焕然、何业恒发表的《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中指出:“目前中国孔雀的分布仅限于云南省南部,但在历史时期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孔雀主要来自于南方之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滇地)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三国志》也记载:“(交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但遥远的西域其实也产孔雀。《汉书·西域传》有罽宾国出“孔爵”的记载,孔爵就是孔雀。《后汉书·西域传》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直到清代,乾隆看见哈密进贡的孔雀,兴致大发,写了一首《孔雀开屏》,诗中云:“西域职贡昭咸宾,畜笼常见非奇珍。招之即来拍之舞,那虑翻翱葱岭尖。”乾隆赋诗距今也就两百六十余年,那时新疆还有孔雀生存。
▲【清】郎世宁:《孔雀开屏图》。图源:网络
《魏书·西域传》说,龟兹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在龟兹国,既有在山谷间“群飞”的野生孔雀,还有如鸡群一般养殖的家禽孔雀,最大的规模竟达到了一千多只。《艺文类聚》载,西晋司马炎在位时,“西域献孔雀。解人语,驯指,应节起舞”。可见,西域各国精通饲养孔雀之道。南方也一样。《岭南异物志》 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这说明南方人食用孔雀乃是常态。宋代学者周去非曾说过:“孔雀,世所常见者。中州人得一,则贮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贱于所产者如此。”在西域和南方摆上餐桌的孔雀,一来到中原,便摇身一变成了金屋里的瑞鸟。人们兴致勃勃地观察来自远方的“异物”,主动将它们融入中国的精神世界。孔雀在文人笔下,要么傲然独立、引吭高歌、轻舞开屏,如同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要么因其美丽,象征着爱情与姻缘。前者如唐朝诗人王建所作的《伤韦令孔雀词》:“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池边凤凰作伴侣,羌声鹦鹉无言语。雕笼玉架嫌不栖,夜夜思归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盘泥金彩落。多时人养不解飞,海山风黑何处归。”孔雀被人养在园林之中,虽锦衣玉食,却仍想着回归南方,如今身形憔悴,被人嫌弃,主人又买了一只新孔雀。而那只老孔雀,华丽已经褪去,不知能否回到家乡。后者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便足以让人沉浸到一段爱情悲剧之中。其实,孔雀性格凶猛,盗食农作物,并非人畜无害。但在异域光环的加持下,人们没办法不爱上这样一只美丽的生灵。
孔雀千里迢迢来到中土,如果将其看作是旅客,它们走过的路很长,见过的世面却很少。它们的命运早已注定:三两成行,守卫森严,路途漫长单调,来到一处皇家园林,被最有权势的人赏玩,直至死去。汉文帝初,陆贾出使南越,南越王“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汉武帝时,帝国经略西南夷,南来北往的道路愈发通畅,孔雀与象牙、犀角、鹦鹉等纷纷来到中原。三国时期,孔雀已经成为南方进献的常见物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三国吴孙晧时,孙谞任交趾太守,“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
▲【宋】崔白:《枇杷孔雀图》。图源:网络
帝国的扩张,不仅在于版图的扩大,更在于精神世界的膨胀。新征服地区的蛮夷土人,很难作为编户齐民直接提供赋税,却可以满足皇室“充备宝玩”的猎奇需求。人与孔雀的相遇,就像“文明”的眼睛看见了“野蛮”之地。与孔雀跋山涉水进入王都相反,还有一群人亲身来到“野蛮”之地,剥离想象,观察异域。他们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形形色色的“异物志”。东汉有一个学者名叫杨孚,岭南人,著有《异物志》。原书已佚,有部分内容为后人引用得以保留。杨孚眼中的孔雀是写实的:“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足有距,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这说明,人们很早就对孔雀有了充分的认知。唐人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的记录最为详细:“孔雀,交趾、雷、罗诸州甚多。生高山乔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减于鹤。细颈隆背,头裁三毛,长寸许。数十群飞,栖游冈陵,晨则鸣声相和,其声曰‘都护’。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长二三尺。夏则脱毛,至春复生。自背至尾,有圆文,五色金翠,相绕如钱。自爱其尾,山栖必先择置尾之地。雨则尾重不能高飞,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过,生断其尾,以为方物。若回顾,则金翠顿减矣。山人养其雏为媒。或探其卵,鸡伏出之,饲以猪肠、生菜之属。闻人拍手歌舞则舞。其性妒,见采服者必啄之。”这段文字详细介绍了孔雀的分布、形貌、习性、声音、性别、捕捉方法等,堪比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古人对于孔雀的认知也有荒诞之处。比如,唐人段公路引张华《博物志》云:“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雌鸣下风亦孕。”也就是说,孔雀不交合,相互唱歌就能怀孕。还有人认为,孔雀与蛇交配。唐笔记小说《纪闻》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诗人王轩养了一只孔雀,一日,奴仆告诉他:“蛇盘孔雀,且毒死矣。”王轩急忙派手下去救,手下不去,王轩发怒,那名手下则回答:“蛇与孔雀偶。”这种误解大概来自于孔雀叼住蛇玩弄,未及时吃下的场景,人们以讹传讹,便成了共识。但总体而言,人们已不再仅凭刻板印象去想象南方,而以经验的方式体会南方,这是中原王朝将边疆逐渐纳入自己统治的一个生动缩影。
▲【清】蒋廷锡:《孔雀图》。图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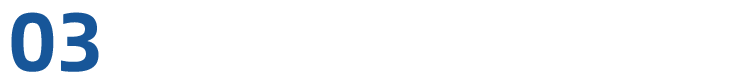
唐朝以后,邦国进献的孔雀日渐减少,州郡土贡的孔雀越来越多,这足以说明,帝国的疆域已经扩张到何种程度。尽管人们对孔雀的认识越来越翔实,但在宫廷之中,它的角色定位始终没变过——帝国动物园里的一颗明珠。帝国越强大,它的动物园就越大,里面的动物就越丰富。在古代,无数忧国忧民之士抱怨过皇家园林的规模,抗议皇帝的铺张浪费,然而大都无济于事。明朝弘治年间,光禄寺官员胡恭上奏道:“本寺供应琐屑,费出无经。乾明门猫十一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刺猬五个,日支猪肉十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虎豹一只,日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计之,共用猪肉、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绿豆粟谷等项四千四百八十余石。”这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但对很多皇帝来说,这笔钱必须得花。皇家园林里的生灵不仅仅是动物。它们是祥瑞,象征着天下太平;它们是贡品,代表着万国臣服。《宋书·符瑞志》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交州刺史垣闳献白孔雀”。孔雀如同一个使节,主动从远方而来,要为王朝增光添彩。哪怕“异物志”已经剥去孔雀身上神秘的色彩,只要到了进贡的环节,孔雀还得重新再穿上祥瑞的衣服。愈是天上难找、地上难觅,进献之物便愈是受到重视,愈可能出现在朝堂之上,进献者的功劳就愈大,帝王怀柔远人的名声自然就愈响亮。对于朝贡的邦国来说,进献异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因为中原王朝一般会进行回赐,馈赠之物相当可观。而且,来华的使节往往都带着一个商队,进入王都的市场,进行交易。正如《文献通考》所言,“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直慕义而来”。公元6至8世纪,中国南方的孔雀通过新罗,源源不断渡海去往日本。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行为自然是“献”与“贡”。当然,新罗有自己的小算盘。龙朔三年(663),唐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大败日本,作为联盟的新罗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也感受到唐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仅数年后,咸亨元年(670),唐朝新罗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七年,新罗最终请罪称臣。由此不难看出,新罗向日本赠送孔雀,便是希望化敌为友,强化力量以对抗唐朝。至于日本,一直渴望提高自己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打造一个小型的“天下秩序”。孔雀被带入日本之后,重复着它们在中国宫廷的命运:作为“珍稀异兽”进行展览,供百姓与贵族观看,宣示日本朝廷的神圣性。
▲【清】邹一桂:《孔雀牡丹图》。图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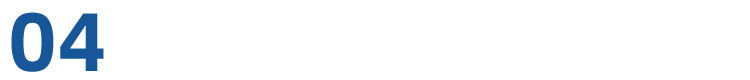
两宋以来,曾为蛮荒之地的南方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孔雀不再神异、稀奇。“异物志”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宋人范成大写的《桂海虞衡志·志禽》中记载有以孔雀为原料的菜肴,“孔雀……饲以猪肠及生菜,惟不食菘……又以孔雀为腊,皆以其易得故也”。元代贾铭撰写的养生著作《饮食须知》载:“孔雀肉,味咸性凉,微毒。食其肉者,自后服药必不效,为其解毒也。”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曰:“孔雀胆大,毒杀人。”孔雀的羽毛十分绚丽,受到人们喜爱,用处也最多。岭南、交趾一带的百姓常常采集孔雀的金翠尾羽制成孔雀扇。《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大朝会,则伞二翰一,陈之于廷。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尾扇,开元年初改为绣孔雀。”翟尾指的是野山鸡的尾羽,为了保证朝仪威严,开元盛世之下改成了孔雀羽。孔雀羽才是上上之选。《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贾母介绍了一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的氅衣:“这叫作‘雀金呢’,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后来,宝玉不慎让氅衣被炭火烧了指顶大的一个洞。晴雯提出,氅衣是孔雀金线所织,也拿孔雀金线用“界线法”织补,或许可以过关。这时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可见,社会上层对孔雀羽的喜爱。清代官服以孔雀翎为冠饰,又称为“花翎”。孔雀尾羽带有“目晕”,其实就是孔雀尾毛上的彩色圆斑,以多者为贵。一开始,清人不欲丧失民族个性,规定亲王、贝勒不得戴花翎,因为这是“臣僚之制”,宗室贵族岂能自降身份。后来,戴花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奖赏,宗室贵族也以戴花翎为荣。清后期,花翎更是成了清帝笼络臣子的工具,比如李鸿章戴三眼花翎,曾国藩、左宗棠戴二眼花翎。
▲【清】沈铨:《玉兰孔雀牡丹图》。图源:网络
历史的河流不断向前,翻天覆地的变迁已在不经意间发生。两宋以后,“文明”不再只是观察南方。越来越多的人涌进“瘴疠横行”的南方地区,将随处可见的草地、灌丛、竹薮改造为耕地,将山林里的乔木变成燃烧的柴火,将溪水流经之地变为人类的聚落。文明到来,野蛮让位。孔雀本身就是一个娇贵的物种,“生溪洞高山乔木之上……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适,盖巢于山林而下浴沙土”,而它们宜居的地方又不断被人类侵蚀。特别是到明清时期,人口膨胀,“野蛮”的领地越来越小,再加上华美的孔雀翎引来人类的大肆捕杀,孔雀的退却早已不可避免。南方逐渐不见孔雀的踪影,而进贡的孔雀只能来自遥远的东南亚了。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参考文献:
李兰芳:《孔雀考》,《形象史学》,2021年第4期
王子今:《龟兹孔雀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梁山:《孔雀与六到十二世纪的东亚外交世界》,《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
林晓光:《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