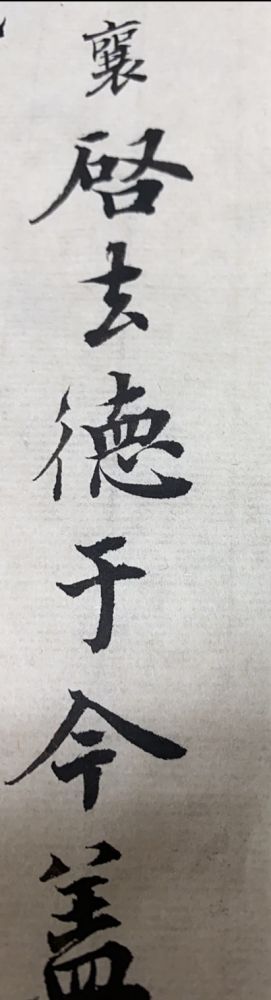2020年,在失业与疫情下生活 (完)
下雪了。一片一片铺天盖地而来,纷纷扬扬,旋转着,怀揣无限热情,奔大地而来。小兰丈夫看着窗外的雪,说:“明天你别起来了。我送孩子。”
小兰两手抱着手机看电视,两只脚搭在暖气上取暖,听到丈夫的话,抬起头说:“我也起来,给孩子们做早餐。”
早上小兰睁开眼睛,听到屋外丈夫扫雪的声音。扫雪是个力气活,她记得以前丈夫不在家,她把不到一岁的小宝放在围栏里,扔给他几个玩具,穿上鞋戴着帽子手套跑出去扫雪。心里想着孩子,扫雪的时候挥舞手中的大扫把,半刻不敢停留,回来身上直冒汗,孩子趴着围栏一直大声的哭,大宝坐在地上摆弄着一堆小汽车,看到妈妈回来了,停下指着弟弟说:“弟弟哭。”
小兰衣服都来不及脱伸手先抱孩子。那时候的小宝肉乎乎的像只大虫子,贴在她身上逐渐停止哭泣,抱着她的脑袋再也不撒手。
现在孩子大了,门口的雪也不需要小兰亲自扫。
丈夫带着一身晶莹的雪花进屋,坐在饭桌前喘着气说:“好大的雪。还在下。一会儿还得扫。”
“洒点盐?”
“没事。多扫几次。反正我在家。”
小兰看到丈夫头发上的雪片融化成水,在灯光下闪着光,像是白发。她心疼地说:“你怎么不叫我。孩子们早上乖吗?给他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丈夫一一回答,满脸欣慰地说大宝物理考试得了满分。小宝拿回来的考试成绩也全是优。
“我说什么来着,要对孩子们有信心。”小兰拍着手高兴地说。又问丈夫忙了一早晨,吃东西了没有。“你得注意身体,哪怕为了孩子们。孩子们大了,在这边没别的亲人,他们还需要我们。越长越好。”
“孩子们真的大了”小兰丈夫说:“昨天晚上看了一下以前的录像,那时候两个孩子好小。圆乎乎的脸,一脸稚气。”
“时光一去不复回。一晃十几年。”小兰也感叹。
小兰丈夫拿出来一包面包,递给小兰,要她多吃点再去上班。又说:“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这边公司业务走起来,你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不辛苦。上班挺好。”小兰打开面包袋子,拿出来一个咬一口说:“我倒觉得你失业也不是什么坏事,要不然你怎么会想起来自己创业,只要以后能赚一点钱,维持基本开销就好。哪怕比上班赚得少呢,好过在外面打工。看人脸色。”
“我也这样想。看人脸色倒无所谓。在家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多,挺好的。”
“对。以前赚钱多也存不下来。”小兰点头,低头吃着手里的面包说:“还错过了孩子们最宝贵的时光。不划算!不划算!”
丈夫点头。突然站起身凑在小兰脑袋上扒拉她的头发,小兰抬头想看丈夫在干嘛。他说:“别动。一根白头发。”说话间,小兰只觉得头皮轻微的疼了一下。丈夫将一根雪白的头发递给她。小兰接过去仔细端详,真是一根白发。
丈夫摸了摸她的头,嘴里唱着:时光一去不复还。
“你就安心创业。我们家里有一个人上班就行。”出门的时候小兰安慰丈夫。
坐在车里小兰想起来很多年前,丈夫读博士那会儿,教授曾派他去北边一个小村庄做实验。来回一千多公里。婆婆通过电话视频先对她说那么远,路上不安全,让你丈夫尽量少回家吧。
小兰说好。紧接着婆婆就跟丈夫说,她已经和小兰沟通达成了共识,认为他做实验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回家。
丈夫说小兰一个人带孩子,还要上学,太辛苦。
小兰凑到电脑前说,没事,咱家得有一个读书人,体力活让她来。
比那还要早几年的时候,那时他们还没孩子,也没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小兰刚出国,还在上语言班。班里有个男生来自东北,还有一个女生来自天津。两人同学不到两个月就同居了。一天上着课,老师布置了作业,自己跑出去喝咖啡,小兰很快写完了作业,前后左右找人聊天,东北男生扭头看着小兰,看了半天,说,小兰你可长得真俊。他身边的女友,那个天津姑娘惊讶的看了他一眼,扔下手里的笔,掐着他的耳朵低声教训说:“干嘛?你不上课,光调戏妇女了!”
东北男生一边哇哇喊疼,一边说:“俺们家有你一个读书人就行了。调戏妇女的事我来做。”
小兰觉得那句话很有趣。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还在用自己的生活贯彻着这种分工合作的观念。
不知道东北男生和天津女生是不是还在一起。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分手了。
小兰开着车,雪大路滑,一路上大家开车都小心翼翼,开得很慢。遇到红灯,一长串的车次第亮起来红色的尾灯,小兰踩着刹车,心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和老蒋在一起,现在的生活会怎样。
老蒋是丈夫的舍友。小兰和老蒋相识在华人教会。老蒋和老马一样,年纪比较大,国内有妻儿。小兰第一次看到他,他端着一杯热茶坐在桌子前看报,那神气仿佛是班主任等着开班会。老蒋是西北人,话不多,见人只是微微一笑,一张粗糙的脸上露出来两个小酒窝,倒也有几分憨态。
自从他认识了小兰,就总是来找小兰。有时候邀她散步,有时候邀她下棋,有时候请她吃饭。
小兰在他宿舍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他的舍友,这个人日后成了自己的丈夫。小兰的丈夫年轻的时候一头长发,个子很高,算得上帅气。
后来小兰丈夫说,有一天老蒋对着红霞漫天的天空看了足有半个小时,突然对他说:“我要把小兰那个人从我心里挖走。”
这是小兰丈夫第一次知道小兰这个人。
老蒋在离开德国之前来小兰和小兰丈夫家里道别。小兰带他去当地博物馆逛。老蒋问能不能牵着她的手。小兰没有回答,只是一路紧紧握着老蒋的手,很久也没分开。
老蒋后来离婚了。老蒋现在的妻子是小兰曾经的舍友小云。
老蒋来找小兰散步的时候,小兰不想去。小云举着手说,我去!和小云散步回来,老蒋无限委屈地悄悄对小兰说,他不是想和谁散步,他想和小兰去散步。
老蒋请小兰吃饺子。小兰说叫上小云吧。老蒋半天没出声,最后告诫小兰不要太相信小云。小兰不解,不停追问下,老蒋告诉小兰,那天散步的时候小云说小兰的高鼻子是整的。她还说小兰在出国前有一个干爹。
看着老蒋气愤的脸,小兰笑,说:“小云很可爱。她只是太喜欢你。”
“我不要她喜欢。”老蒋说。
老蒋什么时候和小云在一起的,小兰和小兰丈夫都不知道。
也许他们四个人永远不会再见。
小兰想,自己头发都开始花白了。
如果能再见,她会拥抱小云。也会拥抱老蒋。也许他们不再是老蒋和小云,而是小兰过去的时光,是曾经的小兰,留在了他们身体里。
那天小兰和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前几天小枫的妈妈请她吃饭。小枫把小兰介绍小帆给他认识的事情一一叙述给他母亲了。小枫和他的母亲很感激小兰的努力周旋。
“这事能成吗?”小兰问。
“他母亲这边也一直张罗给小枫相亲。她的意思是小帆比小枫大两个月,不是很满意。”
小兰挂了电话后,满是对小帆的歉意。
小帆听了小兰的复述,笑着不说话。
过完年小帆29岁。“这个年纪,被嫌弃也是正常吧。”
“那是国内老观念。”小兰有点心疼这个瘦弱的女子,大眼睛,皮肤很白,一个奔三的孤独灵魂。
小帆很讨厌这种怜悯的眼神。她记得学生时代打工,一次她没找到地方住,小兰让她去她家住,收拾出来一间房子,也不肯收她的房租。小帆打工回来帮着她带孩子,做家务。周末的早上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做蛋糕,摆在阳台上的桌子上,就着太阳吃。
那个暑假小兰丈夫在很远的一个地方的实验室,几乎没有回来过。小帆一次偶然听到他们夫妻俩通电话,言语中流露出对她处境的同情:没毕业,家里没有经济支持,全部都要靠自己。
小帆知道小兰没有恶意。但是她很不喜欢这种怜悯的措辞。也不喜欢这样被人议论着。
暑假工结束,返校离开小兰家那天早上,她背着自己的行李,不想惊醒睡梦中的小兰和孩子,小帆提着鞋光脚出门。她把房租用杯子压在桌子上,边上是她精心挑选给小兰的一副耳环。小兰送给她的那只绿皮小包,她带走了。
多年后,当小帆也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她才意识到当年的自己是多么自卑又敏感。
自从辞职后,小帆每天在家呆着。一步都不想出去。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卷到隔离的风波中。
卫生部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以为是老板换了号码来游说她。直到对方第三次打来她才接。
几天前她去看医生。同时间待诊的一个病人被确认新冠阳性。所有那个时间出现在诊所的人都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
小帆一点症状都没有。
她想到自己和小兰见过面,出于责任,她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兰。
小兰又告诉了丈夫。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许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兰说没事的。小帆也没有被要求做测试。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才隔离。
小兰丈夫点头。
第二天下班的路上,小兰去超市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到小帆家门口。
看到她家门口的景象,小兰心里一沉。
回去的路上,小兰对自己说,过去的就过去吧。都开始长白头发了,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过去的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提。”这是小兰丈夫曾经对她说的。
那天傍晚,她记得她穿的一双黑色漆皮靴子,那靴子直到去年鞋底裂了,她才不得不扔掉。她牵着小宝的手,大宝牵着Thomas 的手,四个人散步回来。进屋看见丈夫坐在客厅饭桌前,桌子上有半瓶杰克丹尼,半杯酒。
她说:“你回来了?”
“是的。我等你们一下午了。”
丈夫又起身对Thomas 说:“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Thomas 是小兰的邻居。是个中年单身汉。大宝上学后,有几次晚上开家长会,小兰请Thomas 帮忙照看孩子,自己去开会。
两个人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也有了在一起生活的打算。
小兰觉得丈夫不再关心她和孩子。她很疲惫,很想有一个能相互分担责任照顾孩子的家。
Thomas 对孩子很好。下班后常来陪大宝做作业,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小兰可以不受干扰的在厨房做饭,然后大家一起吃。
Thomas 担心地看着小兰。他不愿意离开。两个男人发生了冲突。Thomas 比小兰丈夫还要高出许多,那一刻小兰很担心丈夫吃亏,没想到被打倒的是Thomas. 小兰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见Thomas抱着胳膊倒下了,嘴里喊着去医院。
小兰将他送到医院,等了两个小时,才把右手打了石膏的Thomas 带回来。
自此后Thomas 似乎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和小兰说话,他给小兰写了一封信,说他会等她做一个决定。决定好了再来找他。
小兰对丈夫提出来离婚。丈夫不解地问为什么。
因为你不再爱我了。
以前发生的我永远不会再提。我还和以前一样爱你。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天下午,大宝同学的母亲Karin气哼哼地来找小兰,说大宝偷了她儿子许多star wars卡片。
Karin以前和小兰关系很好,她也有两个孩子,和小兰的孩子年纪相仿,她们经常一起带孩子在外面玩。Karin的丈夫是一个秃顶的钢琴家,那天他也在场。他站在他气势汹汹的妻子后面结结巴巴地说:“这个事不能太粗暴,得和孩子好好谈。我们也很抱歉,这也绝对不是你做母亲的错。”
小兰一开始不相信他们的话。当她打开大宝的书包,发现无数的卡片时,整个人瞬间崩溃,彻底失去了理智,转身扇了大宝几个耳光,命令他立刻把所有卡片还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孩子的行为并没有改善。小兰总是能从他书包里发现陌生的卡片。动物卡片,汽车卡片,有一次还发现了来历不明的钱。绝望之下她又动手打了孩子。
之后她给在外地工作的丈夫打电话,泣不成声,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后悔自己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对孩子极度的失望,丈夫连夜赶回来。
两个人一夜未眠,最后决定搬家,去丈夫工作的地方住,给孩子换个新环境。
搬家后,Karin 给小兰打过电话,小兰没有接。她无法面对。丈夫的确没有再提起过Thomas。
她不知道丈夫是不是也无法面对,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她。
直到现在也不确定。
对她,那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还有爱,她也感觉不到了。
如果没有爱,还是能相伴相扶。
头发已经开始白了。
白头到老,也许那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小兰给小帆采购那天,看到她家门口的雪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门口也放了她熟悉的饮料和食物。
回到家,小兰还是忍不住问丈夫是不是去过小帆家。
“是的。她也没有别人。不容易。”丈夫低声回答。
小兰看着丈夫,他也不再年轻,额头上有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不再明亮,头发也不再浓密。突然,她只感觉到丈夫的善良。
比起丈夫失去丈夫的爱,她更害怕孩子们误入歧途。害怕自己会伤害孩子。直到今天有时候想起来她给孩子的几巴掌,她会扇自己几巴掌,她想切身体会知道那有多疼。就好像给孩子吃中药,她要先试一口。
过去的就过去了。2020年实在是太糟糕了,就在今天,医疗保险公司给小兰丈夫打电话,说过去的半年里,作为独立创业人,他申请了政府补助,保险公司在计算保险金的时候忽略了这个事实,因此之前缴纳的保险金额不符合规定,要求他补交近一千欧。小兰丈夫很是郁闷,叹着气说:公司还没收入,一切都在萌芽阶段,生死未卜。支出却一分也不能少。
小兰安慰他:“不要着急。已经十二月了,2020年快过去了。生活总会好起来的。要对我们的明天有信心,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