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阳过之后容易累,今天休更一天,发个旧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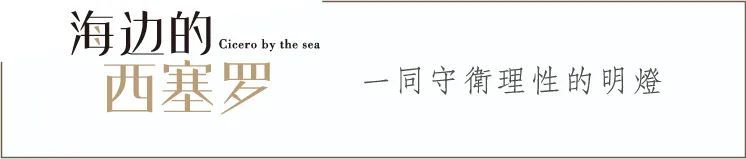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为什么李元芳、展昭、白玉堂,都有这个共同的“体制内职称”……
前两天,我在一篇稿子里,曾提过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我说,中国很多公案剧里,苦主伸冤的套路,其实都是一样的。一定是先有一个体制外的“侠”先帮苦主挡下黑恶势力的第一刀,而后再由官府的“青天”出马,用朝廷的权威加明察秋毫将冤情彻底洗雪。
你看《包青天》里的展昭和包公,《神探狄仁杰》里的李元芳和狄阁老,甚至《雍正王朝》里的侠王十三爷和冷面王雍正,都是这个“一官一侠”的配置。

但这话说了以后,马上就有读者跟我提意见,他说:你这话说得不对啊。展昭、李元芳这些人,他们看似好像是侠,但仔细一查,那也都是“官身”啊。
我想想还真是,你看展昭,在《三侠五义》里是皇上亲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还有个封号叫“御猫”。
你再看李元芳,在电视剧里是历任“千牛卫中郎将”、“检校千牛卫大将军”,也是一跟了狄仁杰,就马上升上正四品上的高官——注意,给他的官阶还是四品,职务又是侍卫。
如此说来,我那个公案剧中“一官一侠”的“配合打法”其实就不对了,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一官一官”:清官固然要是官,侠客最好也是官。展昭和包公,李元芳与狄仁杰,其实严格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体制内公务员”。
鲁迅先生所谓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了属于是。
而且有些事情,你还不好细琢磨,比如说为什么展昭、李元芳这样的大侠,封官都如出一辙的是“正四品”的官位呢?
这就需要了解一点清史才能看懂了——“侠义公案”小说成形于晚清,而在清雍正以后,密折制度得到了推广,雍正皇帝规定凡正四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向皇帝密折奏事的权利和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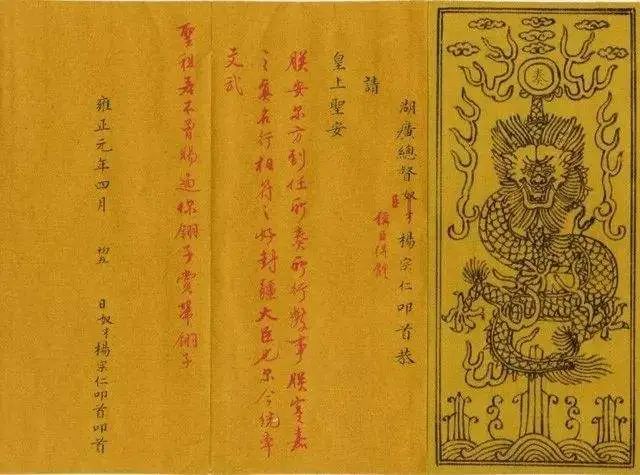
也就是说,正四品其实是一道门槛,过了这道门槛之后,你就算高官了,也是在皇帝那儿也是说的上话的人了。如果说中国古代官僚体系当中也讲究一点“皇帝面前,官官平等”,那么这个“平等”的起步点,就是四品,因为低于这个等级,你连直接跟皇帝打小报告的权利都没有 。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案剧里一定要强调侠客们受封之后都是不多不少“四品官”,其实就把意思打在了这里。
而且有些事儿想想其实蛮有意思的。
比如,虽然剧里唱“开封有个包青天”,但历史上的包拯,在管开封的时候的名头叫“权知开封府事”。“权”者,暂时也。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暂时代理首都市长职务”。
宋太宗以后宋代官僚体系当中,“开封府尹”这个职位就算给也只能给太子。真正干活的“权知开封府事”只是个“差遣”,所以“包青天”严格意义上说是标准的“临时工”。编制品阶是要另定的。
而真实的包拯虽然死后被追封正二品的“礼部尚书”,但在其“权知开封府事”的那段时间,包拯官职一直在正五品到从三品之间来回摆动的。
就是说,真实的包拯如果遇见了小说中的展昭,到底谁官大,谁该听谁的,还真不一定。

说到这里,侠义公案剧中,中国读者们对大侠的想象有多么“官方”也就不言自明了——宛如剧中的展昭、李元芳一样,一出场“路见不平一声吼”,扶危济困的时候,当然可以来自“江湖”,甚至可以是通缉犯。但随后,大侠们一定要被朝廷收编,不仅要有编制,而且官还不能小,最好一上来就是正四品,在皇帝那里挂的上号的那种。
似乎只有在成为这种“官侠”之后,善良的读书人们为侠客们操的那颗心,才能放下来——因为我们的英雄有编制了,安全了。

可问题是,为什么“侠义公案”剧里一定要有这种安排呢?为什么行侠仗义的大侠们一定要有一个官身呢?追诉起来,这其实中国武侠基因当中就一直带着的一个“胎记”。而如果你细读《水浒传》,会发现里面的好汉,一开始最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好出身”。你看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个出场的九纹龙史进,生性洒脱,行侠仗义,为了包庇被官府捉拿的朋友,不惜一把火烧了自己的田庄。可是如此洒脱的史进,在逃出生天之后,对自己的第一个未来人生规划是什么呢?《水浒》里说的很明白:“我若寻得师父(王进),也要在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这里出身,指的就是当官。也就是说史大郎即便犯了事,成了“江湖侠客”以后,想的还是将来要回到体制里去。不仅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宋江这些人,出场时也都提过高度相似的话,“讨个出身”、“寻个好出处”是他们不灭的梦想,水浒里如果有公务员考试,好汉们的参考热情比现如今迎接大学生肯定高多了。足见进体制,当官员,是这些好汉们的共同向往。是的八十回梁山座次排定之后,当宋江让铁叫子乐和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个后期纲领时,行者武松曾第一个跳出来,大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表面上看,这里好像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武松吐的一手好嘈,是天天想着重回体制的宋江背叛了“革命事业”。可是你稍微往回翻翻书,会发现《水浒传》全文,第一个提“诏安”这事儿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武松。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里,他跟宋江道别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当时是大受启发,赶紧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也就是说,最早提点宋江,让他想起即便是“杀人放火”以后还有“受诏安”这条回归体制之路的,恰恰是武松本人。所以武松重阳节跳出来抬杠时,宋江本来完全可以骂回去:“武松兄弟,我冷什么弟兄们的心?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康庄大道,不是咱俩当初一起想的么?咋了,这才隔了不到五十回,你就忘了?”但宋江高就高在,他没点破这一层,只是不再把武松当兄弟了——也许这就是当领导的艺术吧……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水浒传》这最叛逆的奇书当中,庙堂之上的体制对处江湖之远的侠客们来说,依然有着不可比拟的吸引力。是的,中国传统武侠故事里的江湖侠客们想要往体制内走,就跟物理世界里的水要往低处流一样,几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公理。从文学成就上讲,《水浒传》的文学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后来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但从文学发展史上说,晚清的《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又恰恰是前者的发展和总结。而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江湖豪侠们对于体制还仅仅是一种向往的话,《七侠五义》里的侠客对体制简直就是跪舔了——展昭因为救了包公而被赐封四品带刀侍卫、“御猫”,“锦毛鼠”白玉堂就不干了,认为他这个封号压了自己“五鼠”一头。非要跟展昭斗个胜负出来。这个想法如果放在正常逻辑里,其实就特别搞笑:你“锦毛鼠”的名号是江湖公认的,他“御猫”的封号不过是皇上给的,哪个更金贵不是不言自明么?——诺贝尔文学奖你都得了,你还在乎本地作协给不给你个作家身份么?可是白玉堂不这么想问题:展昭人家是“御猫”啊!朝廷认证过得……羡慕嫉妒恨。所以小说里的白玉堂他就真在乎这个。不仅在乎,还要“五鼠闹东京”。闹到最后的结果是自己也被包公注意到,表示愿意收编他。而白玉堂等五鼠面对包青天的诏安,表现是干净利落的“伏地认小”,管对方一个口一个“大人”,自己则卑称“小人”。这一把,连“诏安、诏安,诏甚鸟安”都没有人提了,五鼠们都十分愉快的被包公希数收归门下,成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那样的衙役。并未自己能“终得投靠、报效”感到无比幸福。多说一句,白玉堂被收编以后,得到的封号不多不少,也是“四品带刀侍卫”——足见这个职称对那个世界里的顶级江湖豪侠有多大吸引力了。于是,从《水浒传》开篇史进提出“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的远大理想,到《七侠五义》里白玉堂们的伏地认小。中国古典侠义小说里的侠客们,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走入江湖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梦想就是回归体制、重新被体制承认。而侠义小说写到最后,给的出路也是这个。所以在古典武侠小说中。江湖的、体制外的“侠”,只是暂时的、“终非长久之计”的,而庙堂的、体制内的“官”,才是永恒的,能“得半世安乐快活”的。于是,给包青天、狄阁老们鞍前马后、必要时当当捧哏的“四品带刀侍卫”,这就成了侠客们的终极人生规划。引言里我说“千古文人侠客梦”,这其实是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给自己研究武侠文学的专著所起的题目。我记得陈教授上课时曾经讲过一个段子:说他把这本书的初稿写好后,将其装在皮箱坐火车去广州,结果刚刚下车出站,突然便被飞车党给夺走了。陈教授当时就想,自己要是那武侠小说中的一位侠客多好!一嗓子喊去“哒,那蟊贼休走!”再一剑刺去……于是这本书的题目也就有了。是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不仅是文人,“侠客梦”也许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意向。中国文化中虽然一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格言。但不管闲事,也并不就是我们的民族本性。影响我们至深的儒家佛家思想,曾时刻教育我们要有胸怀天下、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着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脾性。应当说“爱管闲事”也许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只是被现实教育、被体制约束的不敢自己管了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公义受到损害、人间不平事发生,看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我们就会希望有一个侠客能“路见不平一声吼”。想让侠客们代替我们去仗义执言、去拔刀相助,帮一帮那蒙冤受苦的弱者,替她们挣断身上的锁链,治一治贪滑暴虐的恶徒,将他们绳之以法,甚至法外制裁。武侠小说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它是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纠偏与发泄。可是另一方面,被法家那无孔不入的驾驭术驯化的太好、管得太老实的我们,又知道侠客们的这种快意恩仇的法外制裁,终究是无法长久,不能被我们社会所包容的。所以我们就又生出了另一种幻想,希望体制内能有力量能出来查明冤案,还社会以朗朗乾坤。这就又产生了另一种幻想文学,也就是描写包公、狄公、海公们的“清官小说”、或者说“公案小说”。而到头来,人们发现体制外的武侠与体制内的清官,这两种(幻想中)的纠偏方式,最终还是要明主次、作取舍的。人们到底是更希望依靠体制外的侠客们行侠仗义,执行法外制裁。还是更希望体制内的清官们能抬出龙头铡,拨乱反正。这两者其实不能兼得。侠多了就一定会“乱”,官多了就一定会管。这两个解决方案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选择一个。而中国古代文人,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在结合现实思考后,最终作出的取舍,是让“侠客”服从甚至服侍“清官”,甚至让侠客自己被体制所收编,也成为“清官”。这个选择本身,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在自由与威权之间,还是更倾向于服从威权。我们也非常明白,有“侠以武犯禁”这个定性作为大背景,侠客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注定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们的命运宛如风中之烛一样,时刻面临着危险,迟早不是被收编,就是被剿灭。既然如此,那还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好,这样,侠客们至少就不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所以侠义与公案最终合流,成了“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的侠义公案小说。可是,当展昭、白玉堂们不再是江湖侠客,而成了“四品带刀侍卫”后,他们还能像当年“处江湖之远”时那般无牵无挂,自由随性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吗?这个问题,是侠义公案小说一直规避讨论、也无法讨论的。它是一个类似数学上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死结——当你追究极致的一统和稳定,把所有系统外的纠偏力都纳入到系统内,系统本身的计算冗误,就无法被清除了。所以对于这个悖论,“侠义公案小说”只能选择装作没看见。把希望寄托于包公们的无所不能。
最后说一句,侠义公案小说当中侠客最后一定会跟在大人后面,大人问一句“元芳,你怎么看。”他永远跟一句“大人真乃神人也”的俗套段落。总让我对比的联想起《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大侦探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探长雷斯垂德的关系。
同样是一民一官,一个体制外、一个体制内,福尔摩斯与雷斯垂德这对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对案情的讨论权上是平等的。福尔摩斯甚至可以用戏谑、嘲讽、看不上的语气去调侃雷斯垂德的判断。而雷斯垂德呢?面对这位总在嘲笑、调侃他办案不力的“诤友”,他并不会(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能)用其手中的职权给其小鞋穿。相反,他还乐颠颠的跑来给福尔摩斯如实的汇报案情的进展,听取他的建议与观点,最后,这对似敌实友的伙伴,总能一起将迷案揭开,让正义与法制彰显,让善恶各的所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福尔摩斯其实很像一个仗义的侠客,却没有走近体制;而雷斯垂德虽是恪尽职守的官员,却显然并不英明睿断。可是这已无关紧要了,在一个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每个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现代社会当中,那种“侠义公案”式的古典式断案组合,其实已经过时了。可是我想,只有当文人不必再需要侠胆,也能秉笔直书。当侠客们也不再必须追求“讨个出身”,也能行侠仗义的时候,一个现代社会更加美好的公平正义之梦,也许才能被真正实现。我从小就觉得这歌特“标题欺诈”——说好了要唱包公,结果从“江湖豪杰来相助”以后,全都走题到咏叹“七侠和五义流传在民间”上去了。不过看完本文,我相信你能理解它为啥这样唱了——想夸七侠五义,必须先夸包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