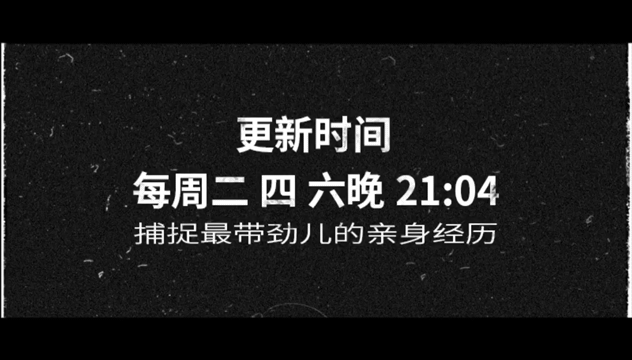我前几天翻到了一个当时打动很多人,现在快被遗忘的旧新闻: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直到得知了她背后的故事——这位五十岁的阿姨凌晨还在街上,是因为丈夫去世,为了养活两个残疾的儿子,不得不一天打三份工。当时牛奶洒了一地,有人问,她犯了什么错,她明明那么努力去生活。不久前,我从刑警陈文章那也听到个同样每天打三份工、为孩子拼命的妈妈。更揪心的是,这位妈妈突然消失在一次深夜拉黑车的路上。事发的城市里,到处流传着孩子找妈妈的视频:“叔叔阿姨麻烦你们,帮忙找找我妈妈。”
钱冬琴刚接了儿子的电话,嘱咐他从门口鞋垫底下拿钱去买饭,自己还要拉两个活,晚点回去。这是钱冬琴一天里的第三份工。每天清早,她在工厂的食堂帮厨,白天在城里运送共享单车,晚上就在国光超市附近用电三轮拉黑车。她是冲着后半夜有喝酒回家的醉鬼,两眼昏花,数不清钱,可以多收一点。醉汉的钱不是好挣的,冤大头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喝醉了酒只会更赖,轻则不给钱,重则撒泼打人。也就钱冬琴真敢跟人家闹仗,甚至蹬着三轮把人强拉到派出所要钱。他们背地里说这个女人“要钱不要命”,家里明明有男人,也没听说欠赌债啥的,一个女的贪这些钱,到底想干嘛?钱冬琴没管,仍然每夜穿梭在小城中,热情地招呼着行人。空着手,步子一步比一步沉,大半也很朴素,多半是那种乡下来城里办事的。现在晚了,回乡下的公交早停了,不坐三轮,他就得走回去。钱冬琴招呼男人坐车,男人摆了摆手,她立马跟上一句,坐嘛,给你便宜点。男人似乎听进去了,他停下脚步,上下打量钱冬琴一眼,上了车。赵庄在城东二十公里,跑一趟差不多40分钟,这可是个大单子,正好跑完回家。
钱冬琴失踪案,最开始进入我们视线的有两个人。
这个男人的态度非常奇怪,老婆失踪了,他一点都不着急,还是他那个13岁的儿子报的警。派出所警察联系他的时候,他态度很差地说他不管,“那臭娘们不知道跟谁跑了”,话里话外暗示这只是一起私奔。我打了个电话叫他来公安局,同时找人盯住了他,预防他逃跑。董明一路走走停停,先是去小卖店买了包烟,又到食品店买了点卤肉。跟梢的几次以为他是要跑路了,没想到他出来又继续往公安局走了。走进办公室后,董明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翘起了二郎腿。但董明显然更看不上钱冬琴。我一提起钱冬琴的事,他就皱起眉头:“就她那个样,她不杀别人就怪好!谁敢掴她一指头!”钱冬琴的妹妹说过,这夫妻俩在家,是钱冬琴收拾董明比较多。董明爱喝酒,又不照顾孩子,钱冬琴时不时要跟他干一架。而董明不占理又打不过,看钱冬琴就像看仇人一样。就在钱冬琴失踪的那个晚上,董明九点过回的家,十点多,钱冬琴儿子睡前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发现打不通,跑来找董明。董明没当回事,可他儿子是个有心的,又打了半宿电话,还求着董明出去找找钱冬琴。董明警告儿子再不睡觉小心挨揍,自己闷头大睡,第二天一早还照常上班。董明解释说,他和钱冬琴早就分房睡,根本不知道她哪天晚上回来不回来,也没有时间去害她。他说这是钱冬琴的情夫,钱冬琴敢跟他耍横,都是傍着这个大哥。这人真名钱本来,是城里跑黑三轮的一号人物,二十年前就管着道儿。俩人跑三轮时认识,因为正好同姓,钱冬琴就管他叫“四哥”。“她给四哥打电话一打就四五十分钟。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这么长时间的电话。”董明这一番话,我是半句都不信。又怂又坏,全是在甩锅。但他有一件事说对了,四哥钱本来,确实是我们的第二号嫌疑人。线人告诉我们,钱本来最近两天都没出来拉车,算算时间,正好是钱冬琴失踪之后。我们找到他老家,却发现他就在堂屋里坐着,哪也没去。一听说钱冬琴失踪,他看起来着急得要命,念念叨叨地说,那就是个直肠子,没有坏心眼的。我们查了这么半天,人人都说钱冬琴彪悍、霸道,这是唯一一个说钱冬琴好的,痴情得像演的一样。“钱冬琴男人早就不管她了,还净揍她。她要是真没了,你们得好好查查她老公,她老公整天惦记她的钱。”我顺着他点头,突然话锋一转,问,22号晚上最后一个电话是你打给她的,你们说了什么?钱本来说,22号晚上他在家睡觉,钱冬琴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没接着,才回拨的。电话也没说什么,就是钱冬琴跟他打听,拉一个客人从国光去赵庄要多少钱合适,“我说要三十就行,她说知道了,就挂了。”我顺手接过钱本来的手机,点开那条通话记录,指着时长问他:
钱本来脸色涨红,张了张口没说出话,又纠结了半天,终于告诉我说,就是闲聊天了。
“她一个妇女晚上拉车有点害怕,打电话找人说说话壮胆的。”我这才想起来,去赵庄那条路确实不好走,出城二十公里,那一片都是拆迁区,一部分房子砸了,剩余的大部分也是空置了,晚上恐怕连个亮都没有。于是,钱冬琴给她的“四哥”,一个萍水相逢、只是同姓氏的男人,一个同样孤独的老光棍,打了足足20分钟电话。紧接着,我就想起,那么22日晚上坐在钱冬琴后面的那个客人呢?虽然之前我们就怀疑过,黑车司机是最容易遇到抢劫杀人的人群。但钱冬琴大半夜开黑车,不知道乘客是谁,也没法查轨迹。现在,钱本来给出了最新的一条轨迹,20时19分,从国光超市去赵庄。20时32分,穿着红色上衣、开着红色电三轮的钱冬琴,经过了外环。我托了个同事去沿路找监控,自己在中控室继续找外环卡口的监控。如果这个男人没问题,最多40分钟,钱冬琴就会平安回到这个卡口。我抽着烟静静地看着,差不多两盒烟抽完,画面终于亮了一下,一辆三轮车经过。我倒回去又仔细看了一下,顶棚上的字,前挡风物品摆放和钱冬琴那个车一模一样,但驾驶员换成了一个戴着口罩穿着迷彩服的男子。凶手就是这个骑三轮车的男子,凶杀就发生在他们出城去赵庄的那段路上。我赶紧掏出电话问同事到哪了,同事说监控跟到20时50分了,车子拐进了一个废弃厂子,里面没监控,他正在里头搜。很多凶手都有作案后重返案发现场的习惯,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更多的是为了检查现场有没有遗留的痕迹。那片废弃厂房很可能就是案发现场,现在距离钱冬琴失踪不到48小时,凶手不是没可能回去,同事只有一个人!
不到30分钟,同事的车就开了回来。他一脸后怕地上来找我,我给他点了根烟,压惊。
21时30分,陌生男子开着三轮车进了外环。22时05分到次日凌晨1时05分,车子在城里逛了一圈,又回了赵庄。1时05分后,三轮车从赵庄出来,顺着沿河路开到了大桥附近。2时30分,三轮车回到了赵庄,走进一个死巷子,然后再也没有出来。22号那天,我在办一个伪造跳楼案。女子从三楼坠楼身亡,我们查监控时发现,有个男子拎着个锤子从单元楼里出来。我们追查男子的轨迹,发现他买了瓶农药回了老家,最后在他祖宅停放的棺材里扒出了他的尸体。当天处理完案件已经夜里12点多,我走沿河路回的家。那是我整个城市里最怵的地方。刑警这么多年,不知道在那条河里捞过多少尸体。抛尸、溺亡,所有城市里的“水”,都是故事最多的地方。他去沿河路,只是散心吗?还是说,我经过大桥的时候,那个迷彩服男子正在桥下,处理尸体?我跑下楼取出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把时间拨回到那个深夜。镜头里雷雨交加,除了被雨水拉长变形的闪烁灯光,只有无尽的黑暗。监控视频上的人很快落实下来,名叫赵福。但我们查不出他和钱冬琴、董明、四哥有任何关系。从我们按住赵福的时候开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问我们是谁,也不回答自己是谁。没有尸体,没有现场,一切技术手段都使不上劲,只有一个咬紧牙关的嫌疑人——这就像一个90年代才会有的案子。赵福把我们拖回了那个年代,那个警察没有技术武装,只能赤手空拳面对嫌疑人的年代。
整个刑警队里,真正称得上办过那种案子的,只有老预审孟三叔。
每次要弄一个人,孟三叔会花几百倍的精力去走访这个人身边的一切,然后把其中最失败的点挑出来,一遍一遍地踩。最开始,铁椅子上的赵福语气很平稳。说话很慢,声音很小,蔫遢遢的,好像没打算和警方做任何对抗,但又不回答任何问题。“你老婆哪去了?跟别人跑了?你说说你,一个老爷们,混得像样子吗?”“你家怎么回事?跟个垃圾堆一样,你这一天天的白活的吗?”“你不是两个小孩吗,你闺女多不容易,好不容易嫁人了,看都给你拖累成什么样子了,她还愿意见你吗?”我去过赵福家里,那个家比垃圾堆还脏,什么方便面、剩菜、馊衣服,从床上流到床下,从床下堆到床上,一走进去,那气味就给我干懵了,脑子里嗡嗡的啥也没有。这个“缺”,不是说需要,更是心结。单身汉要是心里认命,想着一个人的日子也得过,也不至于把房子糟蹋成这样子。赵福的屋子,就好像跟谁赌了气,一定要“她”帮忙收拾。赵福在村里有一桩轶事,四五年前,赵庄要搞拆迁,他为了多分拆迁款,和老婆离了婚。但拆迁赔完了,女人却不跟他复婚了,还飞速和别人结婚生了孩子,抛下了一儿一女。赵福肯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但再受骗,那也是四五年前的事儿,为什么这时候动手杀人?又为什么是钱冬琴?会让他杀人的事,也一定是他心理防线上最弱的一点,是逼他认罪的口子。三叔不间断地在赵福伤口上撒了几小时的盐,肉眼可见,赵福越来越蔫,几乎缩成了一团。孟三叔还在挖苦他:“赵福,你家的东西呢?怎就一个灯泡子还发亮的?”我当时看了半天才明白,这不是收支账,而是赵福在变卖家里的东西,账本记的是他卖的价格和原价中间的差值。赵福在这一年时间里,把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卖了,甚至包括抽油烟机,连厨房的餐桌都是砖头加瓷砖拼的。这件事似乎让赵福挺难堪的,他第一次开口打断了三叔:“俺卖自己的东西不犯法吧?”孟三叔一笑:“是不犯法,可你就是个傻屌,你谈那个女朋友什么名来?”
赵福最大的秘密,就藏在他的手机里。
刚缴下这个手机时,我没来得及看,在一边放了半个小时,再拿起来的时候,锁屏上赫然显示有一百多条未读消息,来自“老婆”。我查过赵福的户籍,知道他只有个离了婚的前妻,看到这个“老婆”,还觉得奇怪。我打开手机时,消息还在一条一条往上跳,各种各样的可爱表情包看得我眼花缭乱。点开聊天记录,半年以来,“缘分天空”和赵福每天都在聊天。赵福几乎干什么都要跟对方说,去赶集、去卖东西、去借钱,骑车五分钟回不了消息要嘱咐一句,路过自己爱吃的面馆给对方拍张照片。而对方也真能回:集上卖什么呀?骑车小心。你喜欢吃什么面?小的十几二十,大的几百上千。有时是对方车违章要交罚款,有时是吃早饭忘带钱,有时是母亲住了院,加起来一个多月能转一万多。这就是卖的钱冬琴的三轮车。钱冬琴骑着它,和四哥打着电话,走向了断头路。对方回了一个爱心的表情包,说自己后天就来,跟他见面,从此以后和他一块过日子。这百分之一万就是个杀猪盘。对面别说是不是“黄燕”,是不是女人都不好说。
看孟三叔终于把这件事捅破,我在一旁开始扮红脸,好声好气地说,赵福,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我说你这黄燕,是个假身份,真人是个男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抓他就是分分钟的事。其实“缘分天空”的登陆IP在广东,远在天边,等人抓回来,审讯时限早就到了。我们赌不起,只能先糊弄他。赵福情绪开始激动,想了半天找出一个理由反驳我,说“黄燕”给他发的语音都是女声。等到凌晨三点,人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我突然叫醒赵福,让他跟“黄燕”说两句。审讯室门口站着一个戴手铐的男人,一看到赵福,就瑟瑟发抖地求饶说我错了哥,我不该骗你。趁赵福还没来得及说话,我赶紧打了个手势,让同事把“黄燕”带走。赵福的眼睛还盯着空无一人的门口方向,三叔把他的头掰过来:“人都走了,别看了。这回信了吧?人就是骗你个憨子的。”他活下去的念头已经灭了,可是要让他认死罪,我们还得有饵。留在赵福家的现勘传来一个消息,赵福家里搜出了钱冬琴的手机,抢劫杀人无疑了。三叔拍了拍我,意思是剩下的他来审,让我赶紧去找证据。我怀疑钱冬琴现在已经被沉入了河底,因为要不是为了往水里扔,赵福干嘛半夜跑到沿河路来?但孟三叔看过那片河后只是摇头,说,你还是找找岸上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赵福一辈子面朝黄土,遇到这种事,也只会往土里埋。领导给我调来了五十多个特警队员,五十多个民兵,人手一根空心竹竿。河岸面积虽然大,但尸体如果埋在沙土里,那一夜的暴雨,加上这几天的高温,恐怕连沙子都浸出味儿了。只要拿空心竹竿往沙子里一插,闻一闻带出来的土,就知道底下有没有。而另一边的审讯室里,三叔好像突然丧失了对赵福的兴趣,玩起了手机。三叔把视频推到他眼前,说:“你望望,这个地方风景真好,有山有水。”三叔拍了拍刚送来的钱冬琴的手机,又指了一下手中的视频:“等着你的是什么后果你想过吗?”赵福脸色蜡黄,重重地斜靠在椅背上,几近哭腔地哀求:“你们叫我说什么啊——”我传过来了最后一个视频:所有警察已经围在了一个坑边上,坑刚挖了五六十公分深,露出一片红色的衣服。有监控、有尸体,要把这一切串起来,仍然差赵福的一句话。三叔轻声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想想你的孩子吧。”赵福呆呆地看着前方,突然像鬼上身一样,没头没尾地说:“可是,谁叫她骂我欸……”
赵福说,他并不想杀人,可是那个女司机实在是太凶悍了。

当时,那个女司机一路都在打电话,他觉得无聊,发现脚底下有个布包,就顺手翻了一下。没想到对方突然发火,把包夺了回去,还劈头盖脸地骂他,拿着个玥玛锁指着他说让他别找事。他说他只是被吓到了,所以下意识把锁抢了过来,勒了她一下。赵福嗫喏着说,当时他没反应过来,拿着包没撒手,两人扯了一下。赵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断断续续地说,是两本存折,每个五万块。他又没来由地补了一句,我答应黄燕,要给她买房子的。他看得那么清楚,怎么可能只是随手翻了一下?又怎么可能只是没反应过来所以不撒手?把钱冬琴勒晕后,他把对方拽到车后座,自己爬到前面,把车开进了废弃的厂房。当时,女司机已经在后面哼哼唧唧的有醒过来的样子,于是他在车上找出了一节刹车线,把女人捆住,又用剩下的刹车线勒在女人的脖子上。女人刚醒过来就开始破口大骂,骂他孬熊,说要找四哥弄死他。赵福没应声,勒了两下绳子,看对方说不出话了,才开口问:“密码多少?”女人拼命抓着刹车线挣扎,似乎要说话,赵福于是稍微放松一点。女人咳嗽了半天,抬起头看着他,说:“要么你今天勒死我,要么就放了我,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他需要钱,没有钱,就没法给黄燕一个家,甚至没法给黄燕路费让她来见自己。为什么这个女人连这种钱都要跟他抢?她要钱干什么?她会比自己更需要钱吗?赵福手上的绳子越勒越紧,钱冬琴开始蹬腿,挣扎,最后彻底不动了。但比起恐惧、痛苦,他当时想的竟然是,没有银行卡密码,那是不是只剩下这个三轮车可以卖了?
赵福把尸体拉回了家,放在院子里,顺便又进城买了四罐自喷漆回家。
凌晨一点多,他等儿子睡着,拉着尸体去了河边埋尸,随后回家用自喷漆把车改成了纯红色。钱还是不太够,赵福在家里搜摸了一圈,终于找出来女儿送给儿子上学用的电动车,反正儿子最近都在家上网课,他把小电动车带到村口,又卖了600块。1500加600,他终于凑够了2000,立马转给了黄燕。黄燕甜甜地说她后天就来。这两天里,不知道为什么,黄燕没再问他要钱,只是温柔地陪他聊天,什么都不要。23日晚上7点多,他还给黄燕发过去一条视频,他独自走在城郊的大街上,画面里是他的笑脸,和他背后的一片新小区。他说这地方就是他以前工作过的物资局,现在盖了新小区。“等你来了,我把老家房子卖了,咱在这卖个楼。以后咱俩一块好好过日子。”我后来发现,赵福的名字竟然在系统里出现过。大概半年前,他找公安报过警,事由就是电信诈骗。他跟派出所警察说,自己在快手上认识了一个ID叫“缘分天空”的女人,两人谈了恋爱,可是对方总是问他要钱。他琢磨着抢劫是不是不太对,所以跑来派出所问问警察。值班民警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电信诈骗。但骗的数额并不大,这类案子的主犯又大部分在境外,办下来成本太高了。他们跟赵福讲了一通道理,督促他把人删了,如果再有更大数额,再来报警,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没几天,“缘分天空”又从快手上给赵福发了消息,质问他为什么拉黑自己。“缘分天空”发过来一张身份证照片,姓名:黄燕,性别:女。她说自己只是想找个好男人过日子,“没想到你这样想我”。两人重新加上微信,高密度地聊天。每天醒来、睡去,全是“老婆”发来的消息。赵福再也没有缝隙去想这个人是不是骗子,家里的东西也一样一样被卖了出去。黄燕终于答应来找他,从此以后跟他在一起,可是他竟然没钱给老婆做路费。赵福进了看守所以后,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他说除非见到那个“陈警官”,否则什么都不会配合。看守所警察聊八卦似的跟我说,赵福在里边整天喊自己被骗了,被前妻骗,被老婆骗,又被警察骗,现在就要骗他的陈警官给他一个交代。同事劝我别放在心上,赵福多半是跟那些老油子在看守所里通过气,知道你找人假扮“黄燕”了,觉得不甘心而已。这对你又没啥影响,又不是上法庭做了假证。我是找人假扮了黄燕,可是把我和黄燕相提并论,未免太侮辱人了。赵福的手机在我手上,那个“老婆”仍然在不断地发消息过来。我想着套点话,回她两句,她立马就开始要钱,话里话外好像我对不起她似的。有时候我真想问问她知不知道,就因为她要的这些钱,一个年轻母亲枉死,一个男人即将押赴刑场,两个家庭,就这样毁了。早在看到“黄燕”的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2年前,我曾经败在一个这样的人手下,我曾经看着一个这样的“杀人凶手”,从我眼前离开。
2010年12月,我参加工作才一年多,还在刑警大队城区中队干着打杂的活。
那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睡午觉,一个妇女匆匆地敲开了我的门,硬给我塞了一个案子。
妇女来的时候态度扭扭捏捏,说自己被老公了骗了六十多万。再追问下去才知道,这哪是什么老公,是她认识的一个网恋对象。两个人谈了半年多,最近对方在创业,跟她说广东那边有个习俗开业要送发财树,八万一盆。这个女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下就送了八盆,总共64万。回过神来觉得不对,哪有这么贵的发财树?才找我们报警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相当低级的骗术,在当时可是最新的手段,我甚至不知道这是要定诈骗,还是得找市场监管局。看我没有要办的意思,一周后,这个妇女又找了我一回。这回她带着一本病历来的,本子上赫然写着——肝癌晚期。她说她不是傻,是因为她一年前就查出了肝癌晚期,医生说她最多只有两年,她不放心女儿,太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替她照顾孩子。癌症的大病险,保险公司赔了60万,她一分钱也没舍得花,一次化疗都没做过,只靠吃止疼药撑着,就想把所有钱留给女儿。但反过来想想,一个孤女带着60万,更让她放不下心来。半年前她在QQ上认识了这个男的,男人对她嘘寒问暖,让她又产生了一丝幻想。她试探性地把自己的病、家里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没想到这个男人加倍对她好了,一天好几个电话,叮嘱她吃药吃饭,后来甚至主动提出要跟她结婚。他说会把她女儿当自己女儿,将来就算她走了,他也会继续照顾女儿,把女儿接到广东,让她上最好的学校,将来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公说,他打算开个金融公司,为了女儿的未来多挣点钱。但广东人信风水,自己的爱人送的发财树才灵,送多少发财树,就是她对他感情有多深,以后公司能挣多少。女人想着自己反正是个将死之人,要紧的是女儿,是老公公司的未来。她不但把肝癌赔的60万打过去了,还垫进去自己手头最后的4万。但自从打完钱之后,“老公”对她就越来越冷淡,女人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这才找到我报案。她说不求全部追回来,只求看在她是个要死的人的份上,给她女儿一口饭吃,行不行?刚二十出头的我义愤填膺,找队长拍胸脯说一定要去一趟广州,见见那个骗子。骗别人救命钱,这不就是杀人吗?但其实,当年根本没有针对电信诈骗的法律,我做不了那个案子。
我第一次以警察的身份去了广东,最后又以警察的身份,灰溜溜地回来了。再后来,听同事说女人真的病故了,她的女儿无父无母还未成年,被送到了福利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广东,就算有案子要去那儿查材料,我也推给其他同事了。黄燕说话的方式,甚至黄燕的位置,都和当年那个男人一模一样。
黄燕的登陆地址在广州的一家写字楼里。当地警察带着我们简单问了问楼下保安,仅凭他们的日常情况,就估摸出来,这就是个电诈公司。同事很爽快地问我,是他们先端公司,还是我们先抓黄成?担心打草惊蛇,我们先追踪了黄成的信号,结果发现就在我们抵达广州的第二天,他正巧离开了这里,往西边走了。我们一路紧跟,黄成的信号先是到了南宁,接着又去了更西边的一个小镇,最后消失在一片大山里。我们再要往里追,当地警察劝住了我们,说再往里都是寨子,连公路都没有,汽车也进不去,进去几个警察,会被村民团团围住。2010年那一次,明明是冬天,但广州就像现在这么热。那时我们穿着过冬的衣服上的火车,一路走一路脱,到广东下车的时候,只剩下秋衣了。我至今都记得,我和同事两个人拖着装着冬衣的行李箱,像两个刚出江湖的打工仔,一下车就被一群黑中介围住。那一年的广州全是城中村,就像大山一样,藏污纳垢。当地警方带我们钻了好几个巷子,找到了女人“老公”胡生的那家“金融公司”。烧了64万的发财树,这家公司竟然就是个小破出租屋,房里就一台电脑。房东把胡生给我们叫了出来,那就是个个子不高、油头粉面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我俩的外地口音,也许是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这个胡生甚至不给我们一个眼神,只顾着给派出所民警散烟。我想给他上铐吓唬他,胡生笑眯眯地反问我,阿sir,我该坐哪里?当地警察也赶忙提醒我说,这档子事现在拿不出罪名,别给人落下口舌。甚至有人去给胡生松开了手铐,小心翼翼地请到办公室里。我想吓唬胡生说他这就是诈骗,结果他干脆不提发财树,就说他跟“老婆”情深似海,差一步就要登记结婚了。我只能直梗梗地说,人家都快死了,要是有点良心,就把钱还给人家吧。胡生哈哈大笑,说警官,有没有搞错,钱是我女朋友买发财树送给我的,为什么要退掉,不吉利,公司会黄的!我还要说什么,对方挥挥手说,我的律师马上就到,有什么事和我律师说吧。律师一进门,彬彬有礼地伸手问我要证件。看完证件后,只问了我两个问题:我看着桌子上的收据,明知道是假的,也没有办法反驳。胡生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笑嘻嘻地跟我说,欢迎警官再来广东玩,有什么需要可以打电话。我满肚子恶心,挥手打落他的烟,像小孩子一样放下一句狠话:“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后来,女人病死了,她的孩子进了福利院,后来,12年过去了。2022年,为了黄燕的2000块“路费”,赵福勒死了钱冬琴,我再一次来到这里。在山脚下蹲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终于看见一辆破旧的摩托从大山里窜出来。车头的人瘦瘦小小,正是黄成。摩托车上还放着几大袋东西,似乎是他的行李,甚至有一口巨大的铁锅。翘起的摩托车尾上缀着一个人,我大概认了认,是黄成的大哥。两兄弟一块把车停在小卖部门口,弟弟进去买东西,哥哥在外边看车。我冲进里屋,双手抱住黄成的膝弯,把他直接栽在地上,然后甩出警察证:这次,没有再出现趾高气扬的律师和伪造的发票,也没有赵福那样困难的审讯,铁手镯一戴,俩人就认了罪。黄燕是他们的亲妹妹,他俩借了妹妹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两人共用一个微信号,轮流扮演了那个“黄燕”。他们骗过好几十个人,赵福是其中最久的之一,虽然给得少,总抱怨没钱,但又总会给点。他们很清楚自己犯了罪,但并不是什么大罪,“就弄点钱花花,没犯什么大错”。这两兄弟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发出去的一条条消息是怎样在骨头缝里敲、敲、敲,把一个人、一个家敲散了架。我问他们骗的钱哪去了,黄成无所谓地说,都打牌输了。我想起刚到这个乡镇的时候,派出所值班室里躺着一地的男女老少,都用塑料打包袋捆着手,就在派出所地上呼呼大睡。我问民警这是咋回事,民警说都是抓的赌博的,半个月抓一次,一次抓一村子的人。这片村子,就是靠赌博运转起来的。当时我还以为他跟我说笑,直到后来我路过他们所里仓库,透过半开的门,我看见里面两米多高的牌九堆,都是从赌桌上没收来的。我终于可以让黄成伏法,可是那些沾着钱冬琴的血、沾着赵福的血的钱,又已经被另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拿走。钱冬琴案结案后,我们把尸检后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就在那里,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最后的谜底,钱冬琴为什么宁可死,都要挣那十万块钱,都不肯让出那十万块钱。钱冬琴的妹妹说,那是她留给儿子买房子的。董明不管儿子,只顾自己喝酒,她必须一个人为儿子的一辈子打算。说话的时候,她的儿子就抿着嘴站在一边,安静,出奇的安静。我突然想起来,最开始让这一桩失踪案被重案队注意到的,就是这个13岁的孩子。一整晚没有打通妈妈的电话,又被爸爸拒绝之后,这小孩翘了妈妈花大价钱给他报的补习班,一个人抱着手机,出门去报警。那个手机也是他妈妈给买的,小学期末考的奖励,在此之前,除了上网课就没怎么拿出来用过。这孩子成绩不错,也许是因为总莫名其妙挨爸爸的打,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见过妈妈拦在他身前,狠狠地打回去。爸爸想他回乡下学门手艺盖个房子,妈妈硬要给他争一个城里的学位,也许他还不知道哪条路更好,但他知道谁是爱他的。当时派出所被董明不在乎的态度迷惑了,以为这是个私奔,赶走了他。这小孩又自己跑到钱冬琴平时拉活的国光商场门口找人。他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和妈妈的合影,一个个举给那些司机们看,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妈妈。最后有个好心司机怕他出事,免费把他送到了他小姨家,他找小姨帮忙注册了一个快手,在上面发妈妈的寻人启事。“叔叔阿姨麻烦你们,帮忙找找我妈妈吧,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帮忙找找我妈妈吧。”那视频感动了很多人,这才让刑警队注意到钱冬琴的消失,在她遇害不到24小时,就开始介入。我听过太多版本的钱冬琴。一天打三份工的,敢讹醉鬼的,要钱不要命的,跟老公打架的,甚至是可怜无助的。就像聊天记录里,“黄燕”说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妹,说她只想找个好男人过日子,说她太爱赵强了,从没碰见过他这么好的人。只有这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他一直都很安静,13岁本来正是人嫌狗不理的年纪,可他总是很安静,教养好得奇怪。钱冬琴和丈夫打架,要让孩子在城里上学;钱冬琴每天起早贪黑,给他报了最好最贵的补习班;钱冬琴只有一辆很破的电三轮,而她儿子有一个比城里孩子还好的彩色书桌。
前段时间陈文章一直拖稿,我问他啥情况,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刑警,却被人诈骗了一万块钱。
行骗过程没什么技巧,对方打电话过来,陈文章确认是本人后,就转账了。
骗子仰仗的,仅仅是他们多年同学的信任。陈文章担心他真的遇到了难处。
陈文章很坦然,也不怕有人因此取笑他。
记录故事时,我原本担心钱冬琴和癌症妈妈的选择很难被理解——
毕竟我们经常听到“明明能活命却选择要钱”、“这么简单的骗局还逃不出来”。
但我后来又想,她俩一个拼命想给儿子更好的未来,另一个希望和喜欢的人度过余生,给自己的孩子找个托付。
这些普通又简单的愿望,明明很多人都有过。
只不过,这些善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被一个谎言毁掉了。
插图: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