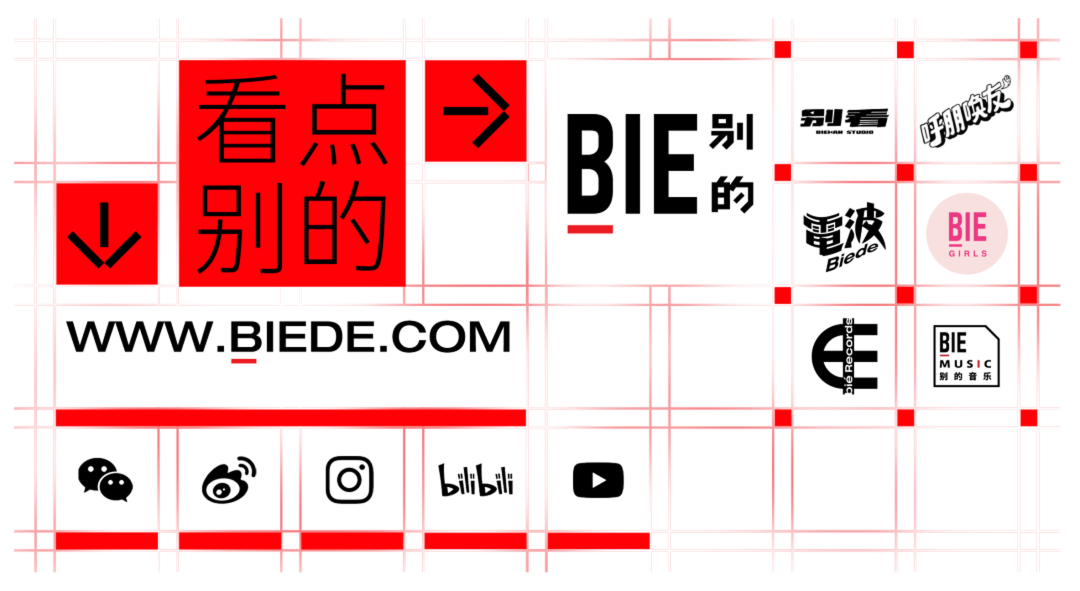我几乎每次去大理的素食馆吃饭,都会撞见一对母女。女儿叫羊羊,今年15岁。她染了一头红发,穿着自己喜欢的印花上衣、小短裙。羊羊很爱笑,经常笑到把牙龈都露了出来,眼睛眯成一道弯弯的月牙。她喜欢把每一个表情都放得很大,不太掩藏自己的情绪。她的母亲叫荆荆姐,很亲切的样子,第一次跟我聊天就滔滔不绝。说到激动时,她的脑袋还忍不住晃了起来,神情就像一个少女,完全看不出她已经 50 多岁了。她们是一对 “在家上学” 的母女。一开始,我把更多目光放在了女儿身上。在同龄人上学的日子里,她都在干什么呢?随着母亲的故事越来越完整,我发现她的人生也在随着女儿 “在家上学” 而发生了剧变。在这个故事里,女儿的故事是美妙的,她常常在不经意间妙语连珠。而母亲的故事更易被忽视,却是更有力量的,她们的成长是交织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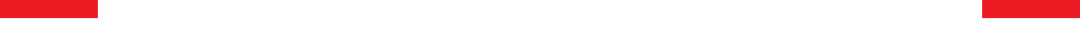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外貌上的区别很直观,那时的我不能染发,也穿不了小短裙。而且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孩,身上 “没什么刺”,对待陌生人的心态非常 open,会在恋爱时反思自己的亲密关系是否健康。而当时在一所重点高中的我,留着一头短发、一年四季顶着一身校服,还有青春期明显的发胖痕迹。我总是疲惫的、压抑的,至于亲密关系更是无从谈起。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我,身上是 “带刺” 的。我恨透了我的高中,恨到我拒绝生育,拒绝让一个新生命再去经历我的高中。也因此,当我知道原来还可以 “在家上学” 时,羊羊的一切对我而言充满了光环。羊羊的成长是靠玩过来的,她说,“我感觉我每天都在玩,只是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东西感兴趣”。一岁多开始,羊羊就痴迷于在家里的每一面墙涂涂画画,床单、衣服,包括自己的皮肤,随处皆可成为她的画板。到了夏天,妈妈会带着羊羊在海边度假。只要不下雨,每天一睁开眼,羊羊就会跑去家附近的沙滩。她喜欢搭各式各样的 “城堡”,用沙子堆、再倒点儿草、贝壳、木棍等等。几乎每年夏天,她就这么从早玩到晚,从夏玩到秋。在海滩玩沙子的羊羊
七岁后,她就跟着母亲各地旅居。她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山寨玩过大半年,每天村里孩子一放学,她就跟着他们漫山遍野跑,有时能跑两三里地。他们吃新长出来的树叶、摘各种野果子,采一大筐草药,“说是晒干了能卖钱,结果晒干却被人扔了”,羊羊说。羊羊还喜欢玩小动物,有时跟她聊着聊着天,她的目光会突然被栏杆上的老鼠吸引住,“你看,它跟我家仓鼠好像,呆在那里动耳朵,笑死了。它可能没看到我们,就跑这儿来了,可能又发现不对,又跑了。我跟你说,老鼠的视力特别差。”在她们现在住的民宿里,羊羊散养着四五只仓鼠。白天,羊羊拿小纸板为它们划了一整个电视机大小的房子。她有时一整天就呆在这里,为它们倒腾厕所、木屑,搞卫生之类。一到夜晚,仓鼠们就在房间内肆意穿梭。它们会啃笼子,啃床腿之类,“有时候它们会特别特别吵,这种时候基本就是饿了”,羊羊说话时会故意把语速加快、嘴型张大,像讲童话故事一样。羊羊用小纸板为仓鼠搭的房子
但童话故事里会有 “狼外婆”,羊羊的故事里也不例外。每次回外公外婆家,“他们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在家上学’ 以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捡破烂”。羊羊因此从小就焦虑以后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会不会被饿死?有段时间,羊羊每天一起床,就开始在书桌前画画。除了吃饭跟睡觉,她几乎一整天都在画画。她画画几乎不临摹,基本上想到哪儿就画到哪儿,她也只画两样东西 —— 要么是那种二次元的女孩,要么就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圆点、一些图形等。而让荆荆姐引以为傲的是,女儿的三幅画曾在一个画展上脱颖而出,被人用 700 块钱买走了。
羊羊正在准备去参加画展的画
羊羊就是这么玩着玩着长大的,母亲只规定她学习那些最基础的科目,剩余的都由她在玩乐中填补。看着小时候的女儿,荆荆姐会不由地感叹,她真是 “大自然的孩子”。到了七八岁,羊羊也有一些学习任务,比如识字写字、做数学练习题,阅读语文课本、还有各种神话、童话故事。此外,荆荆姐还会要求她写日记,“刚开始是口头说,慢慢地写一两句,反正每天都要写。”但羊羊每天顶多只学一个小时,母亲对她管得很松。她说,“那些课程,只要学完就成。有时候我妈发现我太长时间没学了,才会巴拉巴拉说我一顿。”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羊羊从没被要求学过。数学能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就够了。直到14岁,她才被要求阅读心理学、投资理财等的书籍。

羊羊与妈妈的书柜一角
大部分时间,羊羊仍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上 —— 玩游戏、看漫画、跳舞、游泳、研究穿搭等等上。她粗略地估算过,自己至少 “网恋” 过20次。羊羊通常对“网恋”对象的个人信息一概不知,两人甚至都不会视频通话,顶多就互发照片。关于第一个“网恋”对象,她唯一知道的是,他在上小学三年级。一次次恋爱和分手的过程中,羊羊也在对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行反思,体会孤独和去爱的滋味。这让她能够自主分辨出对方是不是在对她进行 PUA,也会主动反思自己对于恋爱对象的喜欢是否只是一种自我投射。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绝非 “早恋” 二字能一笔带过的。好在,她还可以跟母亲探讨这些话题 —— 比如她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是怎样的?她对喜欢的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她以后想组建怎样的家庭?包括对未来的迷茫等,她们母女俩聊天几乎没什么禁忌。羊羊也去一所体制内学校上过一个学期的课,那是一所乡村小学的五六年级。她觉得语文课是最无聊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篇作文把太阳描绘成红红的婴儿的脸。这个形容很奇怪,太阳就是太阳,干嘛非得描绘成别的东西?”
羊羊在教室里上课
“老师一直在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好像这些东西不能有一点儿自己的想法,全是别人的想法”,羊羊接着说。她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概括一段文章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她不断反问着。羊羊也不喜欢死板又爱制定规则的体育老师。有次体育老师在课上提问,“如果学校着火了,怎么做是正确的?” 羊羊故意在课堂上大声地说,“我会第一个冲出去逃跑,可能还要吼两嗓子。”这让她挨了批评。体育老师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排好队,然后井然有序地出去。但羊羊这么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顶撞老师,她对我解释说,“就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没必要去撞别人,但怎么可能井然有序呢?而且就那么大点的学校,(全校学生)也就一百多人,还要排好队出去?”“如果学校再大一点,才有可能会造成拥堵,而且解决方式也不是一句‘排队’那么简单,还是需要经过消防演习的”,羊羊补充。那堂课上到最后,体育老师提出,如果有谁不满可以离开,羊羊真就离开了。事后,她意识到这个班上好像除了自己,几乎没人敢提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而她的母亲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你可以跟体育老师对着干哟”,妈妈这样告诉她。 
动不动就蹿上树的羊羊
第一次参加学校考试,羊羊格外担心搞砸。她问:“妈,要考试了,我要是考零蛋怎么办?”结果听到妈妈说:“没关系呀,考零蛋就零蛋吧。”于是,她就壮着胆子去考了,结果语文居然考了 69 分,“我特别高兴,虽然考了全年级倒数第一,但全年级倒数第二也就比我高了一分,哈哈哈哈”。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羊羊简直像是 “从天而降” 的孩子。我忍不住想,如果荆荆姐当初做出没有让她 “在家上学” 的选择,她会变成什么样呢?也许荆荆姐自己就是那个投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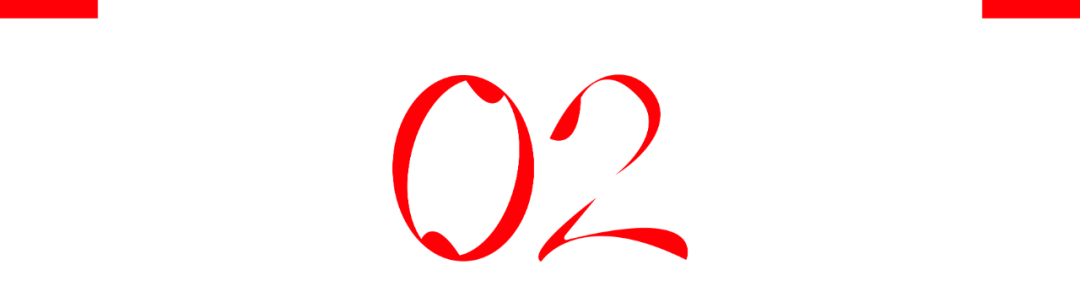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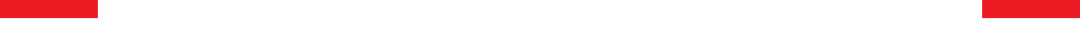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荆荆姐从小在一个极端严苛的教育环境成长起来。她的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是人民教师,父母的权威在家里是绝不容许挑战的。她从小成绩就拔尖,直到高中才迎来叛逆期。她向父母提出,想自己掌控自己的学习计划,“我就很希望整个上午只学语文,下午就学数学,我很享受掌握自己学习节奏与内容的快感”。不出意料,她的这番话惹恼了父母,他们严厉地质问她,“你比老师还能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这算什么?”,荆荆姐说,“反正我们家的教育就是否定与打压,一点儿缝隙都不留给我”。第一次沟通无效后,荆荆姐决定进一步反击,“我就摆烂,成绩大幅度下降,我就想用自己的失败来证明他们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这么逼我,看,成绩不好吧?”可家长与父母却把成绩下滑归因为,“你就是思春了呗?要不成绩下降这么快?”“我活了几十年,没有什么时候比那段时间更屈辱”,荆荆姐对此耿耿于怀。反抗的能量一直延续到上大学,她疯狂逃课,也交男朋友,“基本上只去开学的第一堂课,中间偶尔去几次”。当了期末考,她就突击一下,居然每次考试成绩还不错。荆荆姐当时不了解 “在家上学” 的概念,她只觉得能掌控自己的学习计划太美妙了。直到大学毕业,荆荆姐仍在反抗自己的父母。毕业后两年,她放弃了正式有编制的体制内工作,毅然决定南下打工。“我成年后最大的愿望是离开父母,我想要一份自由职业。我父亲不同意,可我就要去”,荆荆姐把离开父母的生活比作流浪,“流浪象征着自由,象征着我终于解放了,我终于有权利说‘不’、终于可以说话算数了。”她辞去了体制内工作后,仍找了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哪怕这不是她最想干的。工作中,她非常拼命,与丈夫一同当上企业高管。在九十年代,他们就能拿到上万块的月薪。两口子一起打拼,等到生小孩时,他们已在北京有不止一处的房产。直到孩子出生的空档,她才回想起那些久远的往事 —— 她想起自己高考填志愿时,是想填心理学或教育学的。但她妥协了,选择了热门、薪水高的计算机专业;她还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有多么无力,难道她的女儿要再经历一遍她的过往吗?在犹豫中,她一次次把带孩子的期限拉长 —— 要不带到一岁?再带到三岁?等到羊羊三岁时,荆荆姐正式决定让她 “在家上学”,不去上幼儿园了。而选择 “在家上学”,首先意味着她自己要成为 “全职妈妈”。很不幸,荆荆姐刚踏出第一步,就遭到了最亲近的家人的反对。“为什么我不能当全职妈妈呢?即便我不工作,我们家的经济也是能维持住的”,荆荆姐是考虑过现实问题的。但丈夫不赞同她突然放弃工作,这点上两人发生了不小的分歧。而荆荆姐的父母更是直言道:“在家上学,就是没文化”。从家庭内部得不到任何支持,那段时间,她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她说,“我感觉就像生活在冰窖里一样,被束缚住了,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周围随时出现的一个东西,都可能让自己立即崩溃”。她当时唯一想到的就是逃跑,就像当年逃离她的父母一样。于是,她带着女儿过上了一种漂泊的生活 —— 在家待半年,去其他地方生活半年。她无力为女儿提供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送她去上体制外学校,“在家上学” 就是她们最好的选择。最终,孩子放弃了体制内教育,荆荆姐也离开了 “体制内” 的婚姻。如果是学生时代的叛逆都是 “小打小闹” 的话,那这一次,荆荆姐真的成为主流社会的异类了,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的心情很复杂,“以前在婚姻这个体制内时,很向往到体制外去。虽说婚内也没什么心理支持,但好歹有个壳儿吧。现在真的出去了,连个壳儿也没有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一切都不确定。有一次,荆荆姐回父母家,她在家里宅了三个月都不出门。“我妈会很直接地跟我说,跟你一起出门,我就觉得丢脸吗,家人亲戚也会觉得,你一个四五十岁的人,没有工作,孩子又 ‘在家上学’、没有学历,婚姻上还不幸福,简直太失败了。”荆荆姐的父母断定,她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一个家族的异类。她只好把自己藏起来,但依然逃不过邻居的流言蜚语,“他们会跟我妈说,你女儿怎么天天宅在家里?你那个外孙女怎么也不上学?”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在思考要在哪个城市买房。她当时觉得一个物理上的家太重要了,就像是她们母女俩的一个保护壳。可结果是她三次买房,都遇到掏了钱却交不了房的情况,甚至屡屡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当荆荆姐失去对未来的掌控力时,她把目光放回重新组建家庭上。她交往过一个男友,双方已经到了见家长的地步,但两人的感情却戛然而止。荆荆姐反倒感觉松了一口气,她其实明白两人是不合适的。她说,“我当时就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能抓住一刻是一刻,哪怕我清楚我是违背了自己的心愿的。”这对母女关系,在这时,发生了微妙的对调。荆荆姐说,“我是受伤的孩子,而女儿被迫处在家庭主心骨的位置。这对女儿是很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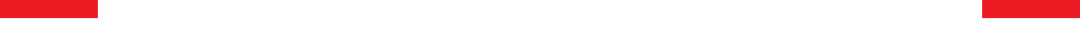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离婚后的几年里,荆荆姐甚至无暇自顾。母亲的状态也牵动着羊羊,她察觉出母亲的异样,就算自己玩手机玩一整天,她也不管,只会说一句轻飘飘的 ‘你不要玩了,我要出门了’。
于是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女儿也会一整天呆坐在书桌前,变得无心去海滩玩沙子。“我感到每天都感到特别痛苦,特别自责,好像我要替我妈表达点什么”,她说。羊羊说起一个故事,“我记得是讲有一个婴儿,出生后 15 天都没吃过母亲的一口奶。原来,是他出生之后,他的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他不吃奶,是想替妈妈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羊羊在那段时间,也能感受到她与母亲构成了一种 “生命共同体”。
羊羊与荆荆姐现在住的房子,羊羊说租两间房太贵了,就做了简易隔断
可在当时,羊羊的身边也没什么朋友能听她倾诉。她就开始在线上努力地找朋友,打游戏也好,加入新的 QQ 群也好。最终,这对 “生命共同体” 中的母亲率先走出了那种低迷的状态,当羊羊感到自己不再需要替她表达什么了之后,也就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荆荆姐常会感叹,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治愈自己的,“我这些年经历的所有不堪,她都看到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都在嘲笑我,只有女儿不会。她也不评判我,只是陪在我身边。”可这对 “生命共同体”,有时也会因为靠得太近而两败俱伤。当羊羊进入青春期、力量逐渐变强后,当两人爆发冲突时,荆荆姐形容自己不得不与女儿 “贴身肉搏”。“其实很多在学校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关系也多少有些问题的。只不过,他们很多时候不需要这么深入地去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还有外援,有学校或家庭可以作为缓冲”,她说。“一个小女孩,从崇拜自己的母亲,到想杀死自己的母亲,这个过程非常考验我”,荆荆姐会跟我反复说起这句话。刚开始与女儿交锋时,还未完全走出低迷状态的荆荆姐,很容易受到创伤。这种状况会触发她的应激反应,“我下意识就想夺门而逃,我真的没有力量待在她身边。”“我想的是,我安顿好自己就会回来的,我只是暂时性的离开。但一解释不好,就会给女儿带去伤害。女儿觉得把她送回亲生父亲身边,是在抛弃她。”荆荆姐解释。羊羊也跟我谈起了她与母亲的之间的 “伤口”。以前,听到母亲说 “不要你了”,她会想着去讨好母亲,比如 “请她吃好吃的,给她做饭,给她洗袜子等”。但她现在越来越不受威胁了,吵架时就会想赶紧经济独立,“完了完了,这个家待不下去了。”一开始聊起这个话题时,羊羊看起来还算轻松,但随着伤口撕得越深,她的声音逐渐变小,眼睛呆呆地盯着前方,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她哽咽着说,“每次一说到家庭,我就会陷入矛盾。跟我妈相处,我能明显感受到她对我的爱,但有时候她为什么要打击我呢?这些打击都是很根本的”。有一次,羊羊想多吃点零食,母亲可能觉得她吃太多了,就会说“你太贪婪了”。这时羊羊就会很受伤,不断想她的母亲为什么要用贪婪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还有一次,她们走过大理一中,羊羊一时兴起就说,“学校好漂亮,我也好想去那里上学。”结果母亲直接回她说,“你考不上的。”我过了一会儿才察觉她的异样,伸出手去拥抱她。她的头靠近我肩的那一刻,眼泪顺势而出。等我坐回去时,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泪人。我呆呆地看着她,不忍心再问下去。她接着说了下去,“我妈大部分时候不承认这种对我的打击,可能她小时候也在无意识地接受家庭对她的打击吧。但我需要我受到的伤害,被看见,被承认。”荆荆姐向我承认了她偶尔对女儿的打压,“我希望给孩子更大程度地自由,但发生冲突时,我很多时候会有我父母的影子。我有时候也想去压一压她,让她按我的来。那个时候,我好像突然理解了我的父母,就很需要自己的权威被满足的感觉。”看到女儿摆烂时,荆荆姐有些恍惚,“我甚至有时候在想,我女儿也像我当年那么摆烂,是不是想教育我?让我回过头来体会一下我父母当年对我的失望?”但好在,荆荆姐和羊羊还可以交流她们互相犯下的错误和不堪。”。羊羊也承认,“我妈整体还是很认可我的,我觉得她没有把自己那个成长环境全部转嫁给我,这已经很好了。”我给荆荆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怀疑过自己当年选择 “在家上学” 吗?她回答,“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 ‘在家上学’ 太美妙了。可当她逐渐对交友、探索内在世界感兴趣时,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觉得孩子不去学校是不是一种缺憾?之后,我就带她去学校体验了一个学期。最近两年,我也会无意识地跟同龄人攀比:哪个同学的小孩读博了?女儿的哪个表姐又去留学了?这都是我需要做的功课。”彬彬姐曾有一群 “在家上学” 的家长朋友,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家长朋友走的是精英教育路线,最后都会送孩子出国留学。另一部分家长则让小孩回归了体制内教育,她说,“基本就这两条路,像我们这种纯野路子的,很少”。我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羊羊,“如果你将来有了小孩,你会让她选择在家上学吗?”她的回答是 “不知道”:“可能还是会让她上学的,选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学校。至少在学校里,她可以获得一些支持吧?至少有朋友吧?很多 ‘在家上学’ 的小孩,朋友是很少的。不过,如果她无法适应体制内教育,那么她可以休学,也可以选择 ‘在家上学’。”除了自考大学外,荆荆姐还为15岁的女儿定下一个目标:如果她能在22岁之前赚到十万块,那么我就赞助她一百万,作为她人生的启动资金。我想了想,如果换个更草根的家庭,也许那个 “在家上学” 的孩子命运会与羊羊大不相同吧。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