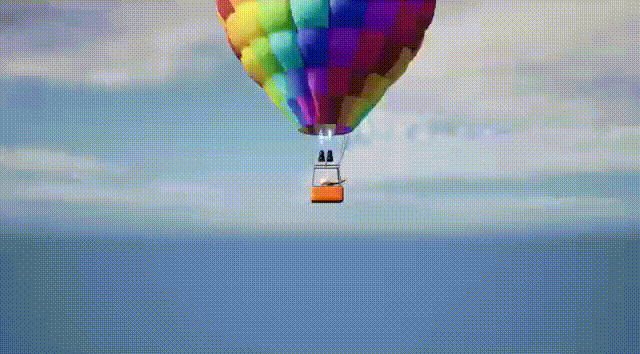

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下县的,它通过法令、制度、礼仪乃至思想观念等多重渠道,以弹性和灵活的方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与治理。
近年,“皇权不下县”之说影响日渐增大。一些论者强调地域差别,放大基层执行中央政令的迟滞性,乃至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抵触表现,从而推导出中国古代朝廷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相互脱节甚或截然对立的结论。中国古代,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指令时会因地制宜,但是,如果仅仅看到地方性和多样性,而忽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就不免陷入过度诠释,甚至用个性遮蔽共性,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性特点。
近30年来,较早明确提出“皇权不下县”的学者是温铁军,他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中说:“由于小农经济剩余太少,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是‘皇权不下县’。”此后“皇权不下县”的提法不胫而走,但细按原文,“皇权不下县”既非核心观点,也没有得到充分论证。事实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主要仍以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说”和萧公权的“乡村控制论”的分歧为背景。费孝通与萧公权的观点,都着眼于古代中央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效度。前者以乡土社会为分析对象,认为中央派遣的官员到县级政府而止,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务由地方乡绅主导和组织;后者则认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的权力真空并不意味着乡村自治,政府通过保甲等行政组织,对基层社会实施有效控制。两相比照,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说”可谓“皇权不下县”的理论模型,萧公权的“乡村控制论”与之针锋相对,强调政治权力对广土众民的严密掌控。持“皇权不下县”观点的学者往往援用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的“国家—社会”模式比附古代中国的政府和乡村,或参照近代公民自由权观念分析“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的农民。但是,随着讨论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皇权不下县”之说存在核心概念含混不清的问题。譬如“朝廷命官”不下县,能否等同于“皇权”不下县?“皇权”概念,是否又可以等同于“国权”?此外,国家在灾荒赈济、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为,反映的到底是“国家权力”还是“国家能力”?还有,一些学者盛称的县以下“乡村自治”,是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权”?事实上,上述种种概念分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费孝通等学者的本意在于建构一种认识和解释乡村社会的方法论视角,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对中国古代皇权是否下县作“一刀切”式的回答。误将社会学、政治学预设的理论框架,指实为历史判断,进而试图用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证实其判断,这种研究思路是有问题的。古人有言:“名者,实之宾也。”概念或理论的运用,要以解释客观实在的有效性为尺度,不能反过来为迎合主观认知颠倒事实,更不能利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制造视角偏差,从而曲为解说、标新立异。中国历史波澜壮阔,史籍浩如烟海,要找到几条看似与常识相悖的“新”史料并非难事。研究者尤应警惕以偏概全的视角陷阱,审慎把握历史大趋势下个别案例的诠释尺度,见“木”更要见“林”。试举一则明代史料为例。嘉靖三十四年(1555),给事中杨允绳论及国家政令执行困难问题时说:“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责之练乡兵则不集,命之团保甲则不严,委之以馈饷则不给,委之以哨探则不明。”单看这几句话,好像在说从督抚大员到县官的各级官员都不能有效指挥地方事宜(如“乡兵”、“保甲”之类),似乎证明明代中后期“皇权不下县”。但是,只要通观杨允绳全文就会发现,他立论的本意,是斥责地方官场苞苴公行以致政务废弛,并非专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何况杨允绳一人一时对某些地区统治失效的观感,不足以撑起对古代央地关系的宏观判断。
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是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表现。地方对朝廷的认同并不仅仅体现于官职的设置,更体现在权力运行的实态上。要整体把握中央政策下行于地方的多样面相,就必须既纵向梳理政策落地后被遵照执行的程度,又横向评估区域间的执行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全国整体行政格局的实际影响。在这种双重视角下,古代央地之间的权力运行呈现出“多样一体”的特点:中央统一号令是“一体”,各地方依据自身条件对中央政策的具体执行则是“多样”,二者看似矛盾,但“多样”与“一体”的互构关系,决定了二者不会彼此脱钩,也不会形成全然相悖的利益诉求,而是共同支撑着秦汉至明清中央集权国家的延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就是这种“多样一体”体制的典型产物。它出现于明代南直隶苏松地区,最初只是一种适应特殊情况的地方性办法,之后逐渐由湖州推广到浙江其他地区,乃至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等省份,至万历九年(1581)已在全国大部分府县推行。最终朝廷意识到此法效果良好,才将它确定为全国统一执行的定制。“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推行的一项税收及赋役制度。它将田赋、徭役、杂征合为一条,通常按鱼鳞图册(当时的土地登记册)所记田亩折算为银两征收。图为《江南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册》(清康熙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海峰 / 供图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面对这种现实,中枢决策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很容易遭遇地方落实上的困难,因此必须审慎地以前期地方试验为参照。“一条鞭法”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之前,虽然在地方上已由经验丰富的桂萼、海瑞、庞尚鹏等完成试验,但朝廷仍不急于划定强制执行的时间点。“一条鞭法”推行之初,张居正还心怀担忧地说:“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在后来的政策执行中,全国各地根据丁、田的差异,适时出台不同的征收标准和税率,有的地方根据田亩,有的地方根据税粮,有的地方则根据税银;改革速度也有快有慢,甚至出现一省之内不同地区完成改革的时间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情形。各地执行中央决策进度不一,似乎是中央统治力打了折扣,实际却使中央的一体决策与各地方多样状况有机结合,取得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效果。而这一点正是中央决策的目的所在,与中央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致。“多样”与“一体”并不矛盾,“多样”是对“一体”的巩固与支持,也是国家力量扎根基层的必要通道。
在“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影响下,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必须秉持“代天理民”的治国理念,以维持统治合法性。推行“德政”、“仁政”成为历代君臣的共同追求与普通百姓对官府的共同期待。“仁”、“德”等观念在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中奠基,又经过历代官修经史著作反复诠释,确定为处理国家政务的理想境界。“德”和“仁”的核心是人,在朝廷政策落地的各个环节上,人的因素尤其关键。从统治思想角度理解中国历史上各级政府执事者的思想与行动,可以纠正“皇权不下县”理论过度关注制度条文、忽视人的因素的误区,充实对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理解。从价值理念角度看,围绕儒家伦理,中国古代政治形成了崇尚善治的政治体系、德主刑辅的律令体系、固本宁邦的治国体系和学究天人的思想体系。以“仁”、“德”为核心观念的普遍性礼仪制度,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约束范围,与保障国家正常运行的刚性制度并行不悖。这些因素在地方官员承接中枢指令时,发挥着无形的道德规训力,促使他们维护朝廷权威、奉行朝旨,同时注意兼顾地方特殊性,保障当地民生福祉。如果只关注制度条文中是否有足够的“数目字”,忽视人的因素和德治追求对人的制约与引导,就无法捕捉到地方官员在政策执行上发挥的弹性作用,也可能忽视他们在维护地方利益上对朝廷政策的缓冲能力。明代后期,地方官员在灾荒治理、扶助民生、推动生产等领域与社会力量积极配合,代表国家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正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政治道德训诫使然。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将官德与实政结合起来的官箴书,给新任官员提供熟悉当地风俗的指南,帮助新任官员找到在当地落实仁政的着力点。正因为这支长期浸润于儒家道德教化的官僚大军同时承担着贯彻中央号令与管理地方的双重功能,晚明时期,在皇帝长期不理政、中枢党争不断的情况下,国家运转与社会稳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由此看来,仅凭“小农经济剩余太少”、行政资源过于单薄,就断言皇权缺少下县动力,完全是缺乏依据的。《文献通考·职役一》有言:“士大夫治其乡之事为职,以民供事于官为役。”这条史料反映了南宋以来乡里制度的转变:在国家官僚体系之外,地方士绅参与地方管理,同时还有一批熟悉风土人情和基层政治运作的当地人充任差役,多方协作,共同辅佐中央权力对当地的治理。显然,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下县的,它通过法令、制度、礼仪乃至思想观念等多重渠道,以弹性和灵活的方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与治理。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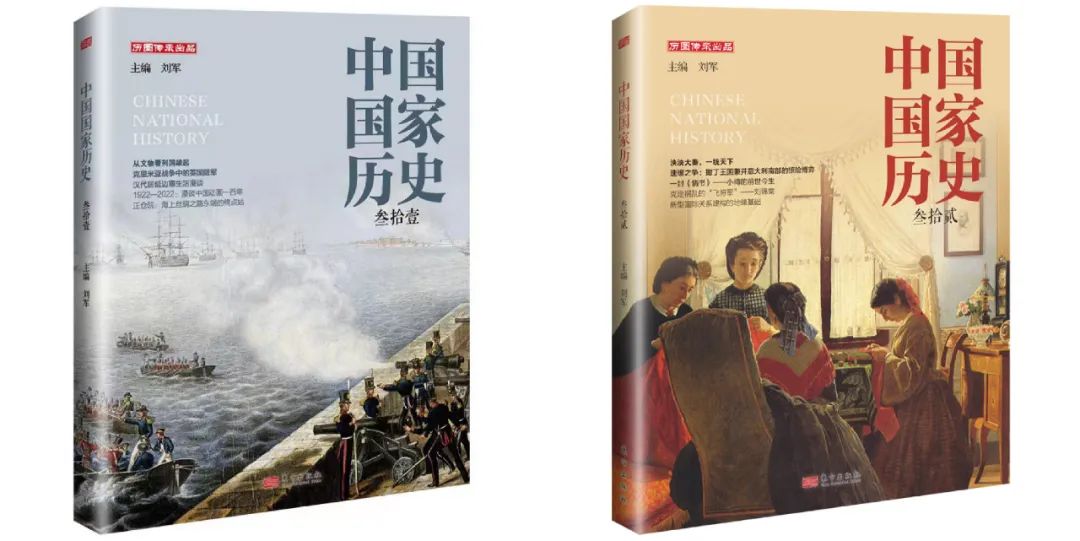
《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识别下方小程序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