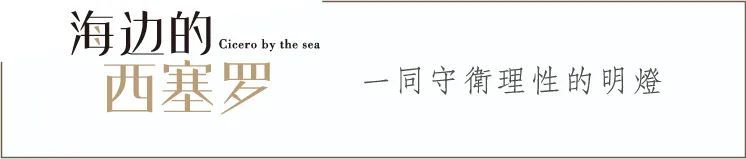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各位好,今天的文章《黑海舰队挨揍,拉夫罗夫改口,俄乌战争的“下半场”真正开始了》发在加图上了,喜欢的朋友还是点击下方图片移步去看:

俄乌战争关注了这么久,我想也快临近某些时间节点了,当然它来的或迟或早都无所谓,如这篇文章为您分析的,时间依然站在乌克兰那一边,现在急需变化的是俄罗斯。
马上就要中秋了,今年我自己也本来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不过现在看来可能时间需要推迟。倒也无妨,但愿也能事缓则圆吧……只不过,因为私事缠身,心境难宁,就没有太多时间留下来写稿子了,所以最近有些朋友怪我出稿率下降,是不是江郎才尽了……西塞罗这边,依然很抱歉没写一篇新稿子。发一篇几年前写的关于苏东坡关于中秋节的旧文以飨读者吧。提前祝您中秋快乐。

古典的中国,好的诗人有很多,但若说有哪一个诗人的气质最像一个现代人,我觉得莫过于苏轼。大部分中国古代的诗人,都是有鲜明特点的: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王维是诗佛、李贺是诗鬼、还有秦观喜欢逛青楼,元稹就会悼亡妻、李商隐写的东西看了注释你也不懂,但真他娘的好看;李煜丢了国家就化身祥林嫂,余生只写我发愁我发愁我发愁……而你读来读去,会感觉他们和你之间总是隔了那么一层,宛如一件古董,虽然能拭去浮尘,却总抹不掉那暗淡的哑光。唯独苏轼是个例外,读他的诗你总会感觉是在看一个才华横溢、却又内心戏特足的网红朋友在发朋友圈,情绪总是那样多变:悲伤的时候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中二的时候他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坦然的时候他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一转头,你又看见他在灌心灵鸡汤:“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前。”总之就是在各种情绪之间不断反复横跳,似乎是什么他都能写,给你一种你要猜出他下一首写啥算他输的感觉。我小时候字很丑,有一阵子沉迷于抄诗词字帖,有的时候抄着抄着觉得这诗谁写的啊,写的真tm好,但就是太跳脱,这是古人写的吗,然后抬头一看,往往上书的就是“宋·苏轼”的大名。所以,有古诗词学者在长篇累牍的较真“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样把车都开到读者脸上的黄色诗歌到底是不是苏轼写的——我觉得真不必,苏轼就是这么一个“特没谱”的人,没准人家一时兴起,真有戏为文,开个黄腔也说不定。而且苏轼的很多诗,会让你感觉他的情绪特别现代,完全没有很多诗人的那种古董感。你就说他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吧。“每逢佳节倍思亲”算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很多人都写过。但你思亲就思亲呗,能玩出什么花来?他在词前面专门来了一段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由就是他弟苏辙。苏轼相当于明确告诉他弟:我今年中秋节组了个饭局,喝的很嗨,填了一首好词啊!……然后捎带手怀念了一下你。其他古人的思亲诗词,一般落笔到最后都会很落寞,什么“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类的。因为中国古代构成社会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离乡在外,与父老兄弟骨肉分离,他其实是不完全的,所以古人怀乡思亲往往都会想的很认真,不把自己说的很悲伤抑郁不算完成任务那种。但唯独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你能感觉到这个个体是可以不依托家族、兄弟,独立与这个世界、与明月对话的,所以词中充满着那种他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心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故乡、亲人之于他,虽然也重要,但真的只是外物。所以即便中秋佳节,这种古代必须团圆的日子里,他也可以任达的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你也好,我也好,能够相隔千里,共赏这轮明月,就可以了。我们不必长相守。我们现代人其实就是这么面对社会,也面对家族的。作为个体,我们必须独立的面对很多问题,而对家人、亲友,我们的关系没有古人那么浓的炸不开,想要亲近,但也有疏离,更多时候只能在独自“欢饮达旦”之余,举头想一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苏轼的这首词,真的很符合现代人的心境,它成为中秋节你在朋友圈里最常见到的句子,就是这个道理——跨越一千年的时光,苏轼准确的写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群体心理。这样一个超脱于时代之人,是怎样练成的呢?我们必须聊聊他的人生。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的人生是开挂,有的人的人生却是笑话。而苏轼这个人就比较特别,他的人生前半段仿佛要开挂,后半段却似乎沦为一个黑色幽默。而所有这一切,他其实都无法左右,他的命运,主要不看个人努力,而是要考虑历史大势。苏轼是22岁时进入北宋官场的,跟今天应届大学生毕业一个年龄。前几天听说现在很多应届大学生的梦想是毕业十年内年薪一百万,但苏轼“毕业”后的现实,比这些人梦想的还好——他科举遇到的主考是欧阳修,欧阳老师对这个年轻人的文笔、见识大加赞赏。说他不仅文章他日一定独步天下,气度更有宰相之才。人在年轻的时候最难得的,就是能获得这种大咖的赏识。所以在欧阳修、梅尧臣这帮老前辈的提拔、宣传之下,苏轼不仅官场上平步青云,文名更是冠誉京华。每作新词,汴京城内都争相传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业有成加顶流网红,苏学士人生赢家赢麻了。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霉运就来了。由于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同志在某篇文章的某段注释里提了一句“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成为了我们初高中历史课本中都重点介绍的考点,形象无比伟光正。但如果如果你放在宋代的历史情境下去看这件事,这事就会变得很微妙。言九林先生在《秦制两千年》当中曾经精辟的总结说,中国历代帝制王朝在建立初期都会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大有为之君厉行改革,而这种改革的目的,往往就是加强朝廷的权力,将民间积攒多年的力量收割过来充作国用。北宋其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清静无为”到想要“大有为”的过程。正好还被苏轼赶上了 苏轼入仕的年代,是宋仁宗末期。这位仁宗皇帝被历史评价为“什么都不会,唯独就会做皇帝”,而他当“会做皇帝”的法门就在于垂拱而治。有个段子说,宋仁宗有天早上起来,跟近侍说:朕昨天晚上馋羊肉了啊,好想吃个烤全羊。近侍就奇怪,说陛下您富有四海啊,想吃个夜宵直接上饿了么点个外卖……啊不,吩咐我们去准备就好了么。仁宗皇帝就摇头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我是皇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一旦轻易连夜下个命令,说赶紧给我准备羊肉。给我制备食材的人一定觉得我特好这一口,今后天天晚上给我备下。天长日久,这是多大一笔开销啊?如今京中一个中产之家,一年才能吃几次羊肉啊。我不能这么浪费。是的,正是因为仁宗奉行这种轻易不开尊口,不使用皇权的态度。宋朝国力才在他的朝代达到了鼎盛,人民富足、文化气氛活跃,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晚会有人试图将潜在的民力转化为能被朝廷所用的国力。对宋代来说,这个时间发生在宋神宗继位之后,这位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皇帝急于证明自己和其父亲英宗这支由宗师入继大统的旁支的统治合法性。也自信宋朝经过这么多年国力的发展,有实力和北辽、西夏叫叫板了,所以想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皇上打瞌睡,一定会有臣子送枕头。于是王安石就站出来主持变法。王安石提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想搞“增量突破”,但实际上谁都知道,仁宗时代那种垂拱而治的无为作风一去不复返了,民力收割即将开始。在这个当口上,苏轼能有什么态度呢?他其实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欧阳修提拔他,说他是宰相的种子,其实就是为了给仁宗时代的“庆历名臣”储备后备军的。上升路径和观点决定了他必须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王安石的政策冒进。可是苏轼又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不喜欢像司马光一样旗帜鲜明的组成旧党与王安石对线。所以三闹两闹,苏轼成了夹在新旧两党之间十分尴尬的“温和保守派”,两头不落好。于是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来了个“自请外放”,主动要求到外地去做官。这个举动传达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我的主张不合时宜,皇上和王相公都不喜欢我,司马相公也觉得我不给力。那朝廷的事儿我不参合了总可以吧?对汹涌而来的时代之潮,我即不顺流也不逆流,抽身而出,躲总还躲得起吧?每读词的上半阙,我总疑心苏轼其实已经把自己不甘的抱负与纠结隐喻在了词中。你看词的开篇就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知道眼下的朝中,新党和旧党究竟都得如何了呢?随后他就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注意,这里用的是“归去”,苏轼想“归去”到他曾去过的那“琼楼玉宇”中,再展抱负,可又担心“高处不胜寒”……激烈的党争站队,实在已经让他寒了心。所以他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还是学学提拔自己的恩师欧阳修,远离了庙堂之高,去处江湖之远吧。人间安乐,不是挺好的吗?可能敏感的他这时已经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所预感,所以他在下阕中又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总觉得,这个“共婵娟”也许不仅仅是横向空间上对亲友的,更可能是纵向时间上对自己的——但愿将来我能活的长一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常常看看这轮明月吧。后来证明,苏轼在填这词时,嘴和开过光一样——他的忧虑都应验了。
如果把“整人”也算做我们历史上的某种国粹的话,那么“文字狱”应该算“粹中之粹”之一。仅仅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话、写了几首诗、填了几阙词,就要论罪下狱、甚至砍头族诛。帝国时代末期那些皇帝们的心理变态程度,简直也没谁了。但在明清才兴起的文字狱这玩意儿,在宋代却有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前奏”,那便是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这个很“不宋朝”的冤狱为什么会在宋代这个以善待士大夫闻名的朝代,并精准的落在了苏轼的头上的呢?元丰二年,被调去当湖州知州的苏轼按惯例写了一份谢表,其中说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你说这话算是苏轼在谢表里“夹带私货”发牢骚吗?其实算也不算。苏轼“不适时”这个事儿,是他当初外放的时候就跟朝廷达成默契的么。说说本也没啥。但表文发上去之后,却立马惹了祸。御史台说他“心怀怨怼,谤讪朝政”,朝中的昔日旧友们对他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处分很快就下来了:即刻索拿,押解到京城问罪!据说苏轼接到处分时,还穿着知州的朝服,堂堂一州知州被直接抓起来赴京,处境之狼狈,可想而知。那为什么此时的朝廷会突施雷霆之怒呢?其实说白了还是他太有名了。前文说过,欧阳修当年为了给苏轼铺路,联合一堆庆历老臣给他捧场,把他硬生生碰成了一代文坛霸主。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名太盛让苏轼隐隐然掌握了一种能够独立于朝廷的话语权。他的所有诗词、文章,都会得到传唱,即便他自己已经躺平,不想管新旧党争之事,也会被人拿来解读,读出与新法相抗的意思。而元丰二年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点,这一年,前期站在改革前台的王安石已经辞官,宋神宗本人站到了前台,亲自推动“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是所谓元丰新政。元丰新政让朝上所有还在犹豫的大臣们都看明白了。原来变法不是王相公的主意,而是皇上的意思。那就别犹豫了,赶紧表忠心呗。可是到了此时,朝中原有的旧党已经都罢官的罢官、贬黜的贬黜,没有靶子可以打了。找了一圈,大伙就看到苏轼这个早早出去躲清闲的家伙那儿三天两头叨逼叨,于是举报党们使了个眼色,一拥而上,就把这家伙打翻在地了——你有没有“谤讪朝政”?我管你有没有!时代需要你当这个旧党头子,甭废话,就你了!于是一直小心避祸的苏轼,还是被卷到了时代的旋涡当中。在他被下狱的一百多天里,几次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于是他写绝命诗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暗愚自亡身。”曾经何等豪迈的苏学士,居然这样最低声下气的写诗,读来真令人喟叹。但你说他是在跟时代摇尾乞怜求放过吧?好像又不是。这话跟他惹祸的那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实在太相似了看起来像求饶,真传出去似乎又是在“谤讪朝政”。所以说来说去 ,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变局中,苏学士的才名、他的影响力,就是他洗不脱的最大的罪。只要他的思想还是独立的,他就难以融进那时代的底色中。还好,宋神宗好歹没有后来的明清两朝皇帝那么不讲理。审到一定时候,还是亲自下旨,饶了苏轼一命吧。但对不起,影响力你不能有了,从此思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而且要经常挪窝,别闲下来。一直到他60多岁终于被放还之前,苏轼被越贬越远,从湖北到广东再到海南。他一直在流放的路上,行走着。说来很讽刺,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真的实现了他当年“千里共婵娟”的梦想——在每个流放地,虽然相隔万里,他都抬头赏着同一轮“婵娟”。到黄州,他去游赤壁,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到更远的惠州,他吃荔枝,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似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发现当地的美好之处,开心的记录下来,再像发朋友圈一样开心的把它写成诗。贬谪在中国也算是文人经常咏叹的题材,但苏轼在这一路上初五他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痛苦。虽然很少有人经历过如他一般漫长的贬谪。苏轼似乎把后半生当成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走到哪里,就安适在那里。对恋家思亲的古人最残忍的贬谪,对他失效了。原因在《前赤壁赋》里。在赤壁之下,还是望着那轮明月,他说:“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之。”是的,只要明月长相照耀,他就永远文思泉涌,而只要有思想为伴,他并不求什么外物。苏轼带着他的明月远行了,他从自己那个纷繁的时代中脱出了,一路走来,一直走到你我身边,在我们的吟诵中,与你我共赏着今日的明月。再没有什么可以摧折他,因为在明月下,他的身影是颀长、旷达而又独立的。
又是一个中秋,高挂在天边的这轮明月,曾经映照过苏轼,给不适时的他以无尽的才情与力量。而就像苏轼当年咏叹明月时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时代的河流依然汹涌的流淌着,我们不知道它会将我们这些个体推向什么样的方向。这种祝愿是空间上的:远万里之外的你与我共赏这轮明月。也是时间上的:愿一年、两年乃至无数年后的中秋,我们都能这样一起安然的谈古赏月。不管你我相隔多远,不管未来前路几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