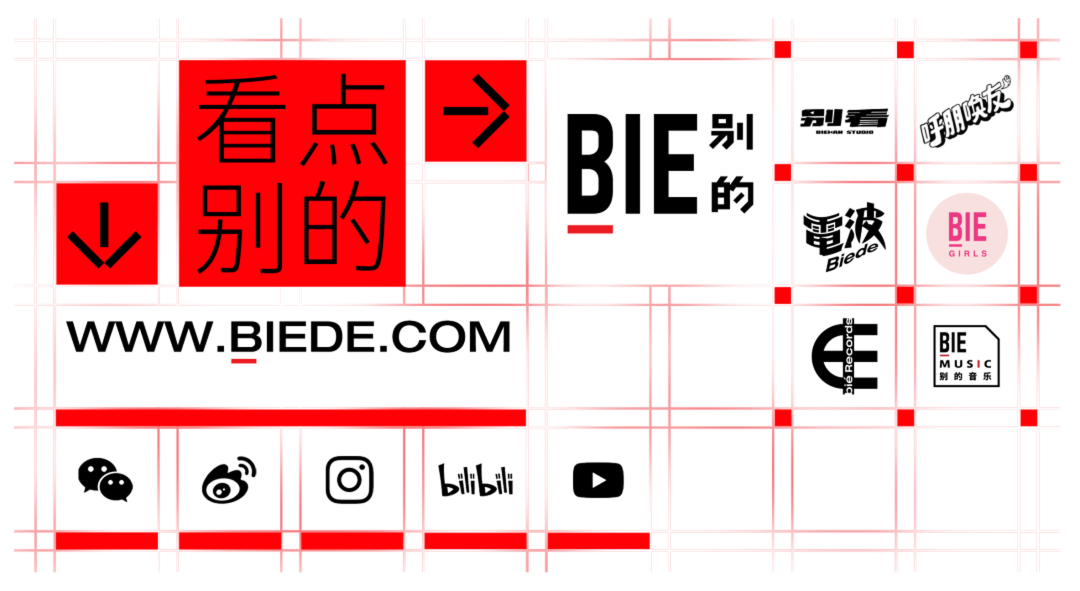今年第 11 号台风“轩岚诺”在前天登陆浙江省朱家尖岛。酝酿已久的暴风雨在蠢蠢欲动,有一群热爱冲浪的人却无比激动。他们拿着冲浪板,来到秘密浪点,就是为了在大自然的馈赠下,尽情享受一波台风浪。 时间回到六月底的某一天,上海与春天擦肩而过后,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自己的孤岛。而我,一如往常,在 15 分钟内,订好了离开上海的高铁票,收拾好行李,锁好家里门窗。小区楼下的核酸站工作人员见我拖着行李箱问去哪,我也假装听不见。我满脑子只想着:终于可以去冲浪了。我从来未像此刻般渴望大海。 直到海水变蓝
直到海水变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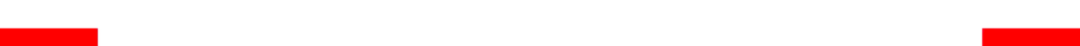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这是我离开海边最长的一段时间。一路高铁转拼车,由于当时各地的防疫政策,对来自上海的人并不友好,在高铁到站前的一分钟,我还在给防疫办打电话,确认自己下车后不会被隔离。几番周折,终于到了离上海最近的可以冲浪的地方——位于舟山朱家尖的 City Surfer 冲浪俱乐部。
这是我离开海边最长的一段时间。一路高铁转拼车,由于当时各地的防疫政策,对来自上海的人并不友好,在高铁到站前的一分钟,我还在给防疫办打电话,确认自己下车后不会被隔离。几番周折,终于到了离上海最近的可以冲浪的地方——位于舟山朱家尖的 City Surfer 冲浪俱乐部。六月底,到了朱家尖后,我拍下的第一张大海的照片
六月以来,City Surfer 的微信群里不断有人问“上海人可以来冲浪吗?”,同时陆陆续续有人排除万难顺利上岛。客服每天处理最多的,不是关于冲浪的问题,而是怎么让上海人顺利入境和入住的琐碎事。到了朱家尖,以为在被关了两个多月后,我会陷入 emo 的情绪,谁知还没缓过神来,便被叫去喝洗尘酒。一起喝酒的包括刚在舟山经历了 14 天隔离的上海朋友、刚被公司裁员拿了 N+1 的幸运儿、开不了店于是来度假散心的 club 主理人……劫后余生的我遇到了劫后余生的大家,没有太多相拥而笑或抱头痛哭的情节,说不出当下到底谁的遭遇更糟糕或者更好笑,但在海边,谁还想聊糟糕的事呢?海浪声就酒,人生的奇遇记都是极好的下酒菜。白天海里浪,晚上酒里浪,对冲浪人来说,都是水,没有什么是一道好浪或一杯好酒解决不了的
 住在城市里的海盗
住在城市里的海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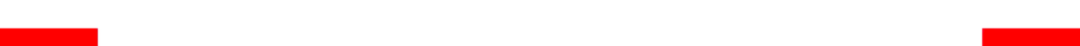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以前国内能玩水上运动的地方,少之又少。要么远,要么贵。在国内没有美人鱼,只有“水鱼(广东话: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疫情期间,由于无法出国,在我这条水鱼以为自己只有被宰的命运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海盗。在东南亚海边阅男无数的我,在会议室里,看到海盗的第一眼就知道,那头深浅不一的黄毛必定是长时间在海水里泡出来的。我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形象的人,会出现在钢筋水泥的上海,还给自己起了个这么中二的外号,心想他多半是《加勒比海盗》或者《海贼王》看多了。后来我了解到,海盗在巴厘岛当过几年岛民。因为在冲浪上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便成了朋友,同一帮也有海岛生活经历的“城市难民”,三天两头便聚在海盗上海的家里,吃饭喝酒抽水烟,试图短暂地回去自己的粉色泡泡里。每个喜欢大海的人,生活带来的疼痛感,会随着离开大海的时长慢慢叠加。2020 年 6 月,对城市生活的忍受已经到了临界值,海盗说想做一个冲浪俱乐部,让上海这些由于疫情没法出国冲浪的朋友,重新回到大海,弥补无法出国冲浪的缺失。海盗和朋友便开始沿着江浙沪的海岸线找呀找,找那个可以冲浪的地方。
以前国内能玩水上运动的地方,少之又少。要么远,要么贵。在国内没有美人鱼,只有“水鱼(广东话: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疫情期间,由于无法出国,在我这条水鱼以为自己只有被宰的命运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海盗。在东南亚海边阅男无数的我,在会议室里,看到海盗的第一眼就知道,那头深浅不一的黄毛必定是长时间在海水里泡出来的。我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形象的人,会出现在钢筋水泥的上海,还给自己起了个这么中二的外号,心想他多半是《加勒比海盗》或者《海贼王》看多了。后来我了解到,海盗在巴厘岛当过几年岛民。因为在冲浪上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便成了朋友,同一帮也有海岛生活经历的“城市难民”,三天两头便聚在海盗上海的家里,吃饭喝酒抽水烟,试图短暂地回去自己的粉色泡泡里。每个喜欢大海的人,生活带来的疼痛感,会随着离开大海的时长慢慢叠加。2020 年 6 月,对城市生活的忍受已经到了临界值,海盗说想做一个冲浪俱乐部,让上海这些由于疫情没法出国冲浪的朋友,重新回到大海,弥补无法出国冲浪的缺失。海盗和朋友便开始沿着江浙沪的海岸线找呀找,找那个可以冲浪的地方。 游击式寻浪
游击式寻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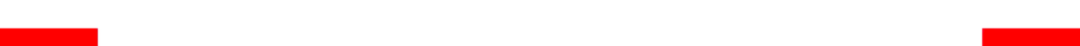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最开始,他们来到离上海约 100 公里的启东市,找到一个原本对公众开放的海滩,在那里,有理想的浪,他们还为之起名为“Chill-ifornia 启利福尼亚”。结果没去几次,便被人发现。启东每年溺水事故频发,海滩管理严格,不能进行水上运动,只要有人冲浪便会被举报。后来,海滩附近甚至被围上了铁丝网。在遭遇被赶、被拦,各种不友好的对待后,他们来到了舟山市的朱家尖,并顺利让冲浪运动在这里生根发芽,当地政府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City Surfer 城市浪人冲浪俱乐部”便慢慢有了真实的肉身。成立初期,City Surfer 只是个线上社群。海盗每周统计参与周末冲浪的人员数量,为他们订来往上海和朱家尖的车宿。当时所有的冲浪装备,包括十几块冲浪板,都存放在海盗位于上海徐汇区那个不到 50 平的家里,每周跟着冲浪的人来回搬运。由于俱乐部位于景区,不能搭建永久建筑,因此主体由便于拆卸的集装箱拼装而成。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人知道这个在海边的集装箱什么时候会被台风吹走。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家尖的周末慢慢多了一些带着冲浪板到海边的人。每个周日,冲浪的人就像午夜的灰姑娘,脱下的不是玻璃鞋,而是脚绳,到点就要回去城市上钟,在回家的路上可能还会遇上跨海大桥大塞车。
最开始,他们来到离上海约 100 公里的启东市,找到一个原本对公众开放的海滩,在那里,有理想的浪,他们还为之起名为“Chill-ifornia 启利福尼亚”。结果没去几次,便被人发现。启东每年溺水事故频发,海滩管理严格,不能进行水上运动,只要有人冲浪便会被举报。后来,海滩附近甚至被围上了铁丝网。在遭遇被赶、被拦,各种不友好的对待后,他们来到了舟山市的朱家尖,并顺利让冲浪运动在这里生根发芽,当地政府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City Surfer 城市浪人冲浪俱乐部”便慢慢有了真实的肉身。成立初期,City Surfer 只是个线上社群。海盗每周统计参与周末冲浪的人员数量,为他们订来往上海和朱家尖的车宿。当时所有的冲浪装备,包括十几块冲浪板,都存放在海盗位于上海徐汇区那个不到 50 平的家里,每周跟着冲浪的人来回搬运。由于俱乐部位于景区,不能搭建永久建筑,因此主体由便于拆卸的集装箱拼装而成。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人知道这个在海边的集装箱什么时候会被台风吹走。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家尖的周末慢慢多了一些带着冲浪板到海边的人。每个周日,冲浪的人就像午夜的灰姑娘,脱下的不是玻璃鞋,而是脚绳,到点就要回去城市上钟,在回家的路上可能还会遇上跨海大桥大塞车。 不仅仅是冲浪
不仅仅是冲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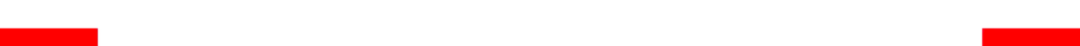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因为冲浪灰姑娘们的时间只有周末两天,所以冲浪技术到了下个周五,都会清零,哦不,归零。比起冲浪,大家的酒量似乎更厉害。然而在朱家尖有个不成文的共识:放过任何一个喝多了的人。当然,你喝多了的丑态可能会在两年后,依然会时不时被当成搞笑梗一遍遍提及。周一到周五在 city suffer 的人,到了周末便摇身一变成 city surfer。这个离上海最近的冲浪俱乐部,无论是成立初衷,还是发展过程,都几乎注定了是要带着这种使命,接住各种从上海转移过去的情绪和能量。而在我看来,2022 年的这个夏天,她从一个小联合国,变成了一个流浪者的中转站,有的人快要离开,有的人过来见见快要离开的朋友,似乎大家都知道自己要走,但只能对离别习以为常。朱家尖的海成了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A面和B面:A面在城市,B面在海里。我找了几位 City Surfer 的老朋友,听他们聊聊冲浪,聊聊他们的A、B面,和关于冲浪之上的一切。
因为冲浪灰姑娘们的时间只有周末两天,所以冲浪技术到了下个周五,都会清零,哦不,归零。比起冲浪,大家的酒量似乎更厉害。然而在朱家尖有个不成文的共识:放过任何一个喝多了的人。当然,你喝多了的丑态可能会在两年后,依然会时不时被当成搞笑梗一遍遍提及。周一到周五在 city suffer 的人,到了周末便摇身一变成 city surfer。这个离上海最近的冲浪俱乐部,无论是成立初衷,还是发展过程,都几乎注定了是要带着这种使命,接住各种从上海转移过去的情绪和能量。而在我看来,2022 年的这个夏天,她从一个小联合国,变成了一个流浪者的中转站,有的人快要离开,有的人过来见见快要离开的朋友,似乎大家都知道自己要走,但只能对离别习以为常。朱家尖的海成了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A面和B面:A面在城市,B面在海里。我找了几位 City Surfer 的老朋友,听他们聊聊冲浪,聊聊他们的A、B面,和关于冲浪之上的一切。A面:日企营业部经理

B面:浪龄 13 年

在 2019 年搬到上海之前,我在台湾生活了 6 年。经常下雨的台湾,能在户外玩的运动不多,有什么运动在雨天也能玩呢?噢,那就去冲浪吧。没有任何两道浪是一样的,冲浪就像赌钱:在海里看到一道不得了的浪朝你过来,你知道那可能是今天最好的浪。如果没抓到它,你永远会记得这种失败的心情。其他的运动,失败了还能重新来,但冲浪不可以。同样的,如果抓到了,成功感也会永远在你心里,但属于这道浪的那种兴奋,也仅仅只有一次。城市焦虑在日本是个严重的问题。生活一成不变,人们总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陷入一个“为什么我一直努力但结果却是这样”的黑洞。但如果把工作看作是一个赚钱的方式,周末不要加班,把时间留给自己,这样就可以跟周一到周五的自己和解了。对于我来说,周末去冲浪,就是努力工作的理由。但是,如果周一到周五都在冲浪,那周末冲浪就没那味儿了。好比啤酒是好喝的,但如果从早上八点开始喝,到后面就不想喝了,但在下班之后开一罐啤酒,就是生活最高的享受!A面:服装品牌平面设计师

B面:浪龄 16 年
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大约七年前搬到了上海。当时的中国非常野,在我眼里,一切都很新奇,甚至觉得在城市里迷路都很好玩。现在,身边的东西已经不再给我带来新鲜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适和更多关于生活的灵感。中国对于我来说,渐渐比西班牙更像是我的家,尽管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生活在这里越来越不方便。从小我就对冲浪很好奇,但直到 18 岁我才第一次接触冲浪。大学暑假那会儿我在西班牙北部打工,用我人生第一笔工资去买了 5 节冲浪课,太值了!在那以后,冲浪在我的生活里成了一种快乐。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一个外人,由于工作计划和生活上的限制,对冲浪的热情一度被中断。另一方面,在生活中,我更享受跟自己独处,保持与其他人的距离。这次疫情让我有机会去重新审视与身边人的关系。对我来说,冲浪就是生命拼图里的一块,去平衡我在石屎森林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在 City Surfer 俱乐部里,我享受跟大家在一起时的感觉,那些在海里开对方玩笑、为对方鼓劲的瞬间,哪怕做些傻乎乎的事,我都觉得很开心。A面:互联网广告人

B面:浪龄 6 年
从大学开始,我便离开了舟山,去到大城市读书和工作。小的时候,我总觉得舟山跟外界是脱离的,以前去上海还要坐过夜的游轮。我在去美国读书的第一年开始接触冲浪。跟很多人一样,一开始因为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关系,冲浪就是为了酷,现在想起来还挺无脑的(笑)。随着越来越深入这项运动,我跟大自然的连接越来越强烈,大自然的力量,会让我回归到一个更靠近原始的状态。那个瞬间,我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是身外之物。因为疫情的契机,去年选择了回国发展。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海盗,发现我们想法相近,于是一起把冲浪文化带到这座小岛,对我这个舟山人而言,就像完成了一个使命,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吧。我经历了纽约和上海两场疫情,在上海的时候,因为国内社交媒体的关系,信息和声音非常集中,那种紧张感和压迫感,让我对疫情有了不一样的感知,在纽约的时候,更多只是一种体验。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城市浪人的状态,城市和海边的边界,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明显。在城市我专心上班,在海边我专心冲浪。6 月的时候,我选择回来舟山,一有时间就冲浪。可能是因为害怕变老吧,想在冲浪上多花点时间。A面:互联网工程师

B面:浪龄 10 年
我最近实在是很难写上海的生活,5 月份回台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生活这么久都是空白的。08 年我在北京当交换生,从 13 年之后就一直在这边工作,在上海生活了七年,见证了这十年的辉煌,也碰上了互联网发展的好时候,体验了许多同龄人没有的经历。那个时候的人们,有一种“未来会更好”的信念,社会一直在变好,身边的同学还会讨论要去当背包客看看这世界,每个人有一种活力感。然而现在,像是一辆失速的列车,车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台车子要失控了,但是没有人有方法阻止它。08 年之后越来越开放的光景已经不复存在,我想是时候该离开。因为从事互联网行业,我在城市里就是每天都不想上班的状态,空闲的时候想要去冲浪或是研究食谱。我从 20 岁左右接触冲浪,断断续续十年左右,到后来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活动,基本上跟大妈去跳广场舞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海边生活就是又爽又废,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废!上海这座城市压力很大,海边会变成一个临时的精神避难所,很多人会到这里来短暂放松,之后再回城市里面继续工作(被压榨),就像是一个快要坏掉的机器需要进厂维修一样。A面: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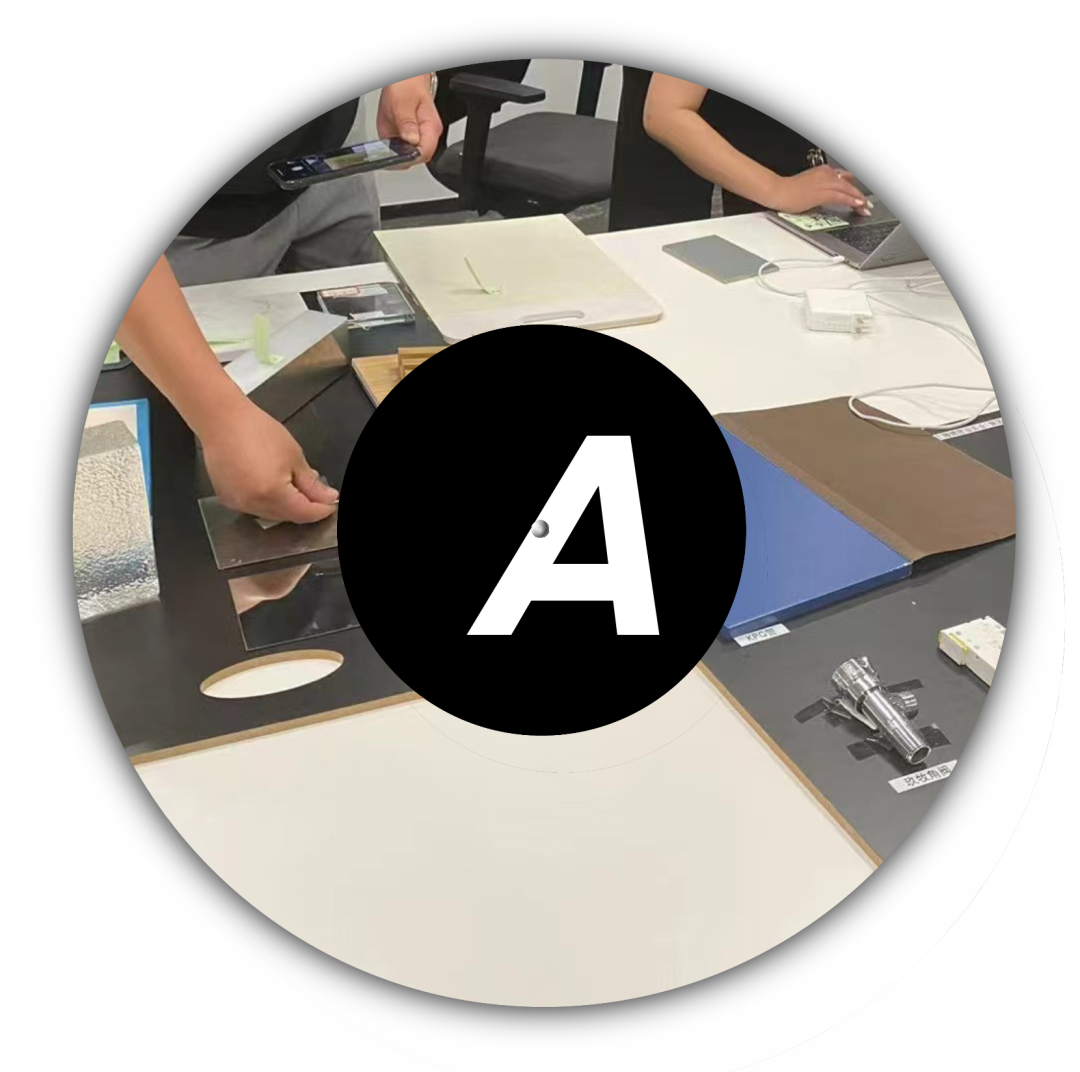
B面:浪龄 2 年
我是在上海读书,后来一直在这边工作的台湾人。从小在海边长大,海边会让我有家的感觉,能让我放松下来。我需要去到没有人的地方,回到大自然。去海边,算是一种留在我血液里的遗传。在城市里,我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卷的状态:打四份工,疯狂上六个月班,然后放六个月假,开着房车去外面走一圈。我还挺享受这种状态,觉得自己不认老。关于上海的改变,这么多年来,我在这里陪她一起成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讲不出来,或许离开十年,再回来,会更有感知。但对于我来说,有趣的内容一直都是人,大家做的事情是什么,在我看来其实没那么重要。不能堂食,那就来我家吃咯。但我的确越来越不喜欢上海了,以前我喜欢上海多于其他地方,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对多元性的接受度非常高,但现在感觉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了。去朱家尖冲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方便,是我现有条件里的最优解。那边的浪可能不是最好的,甚至明知没浪也要去,可能是因为知道去到了,就能够遇到那一群人吧。A面:斯坦福大学电影系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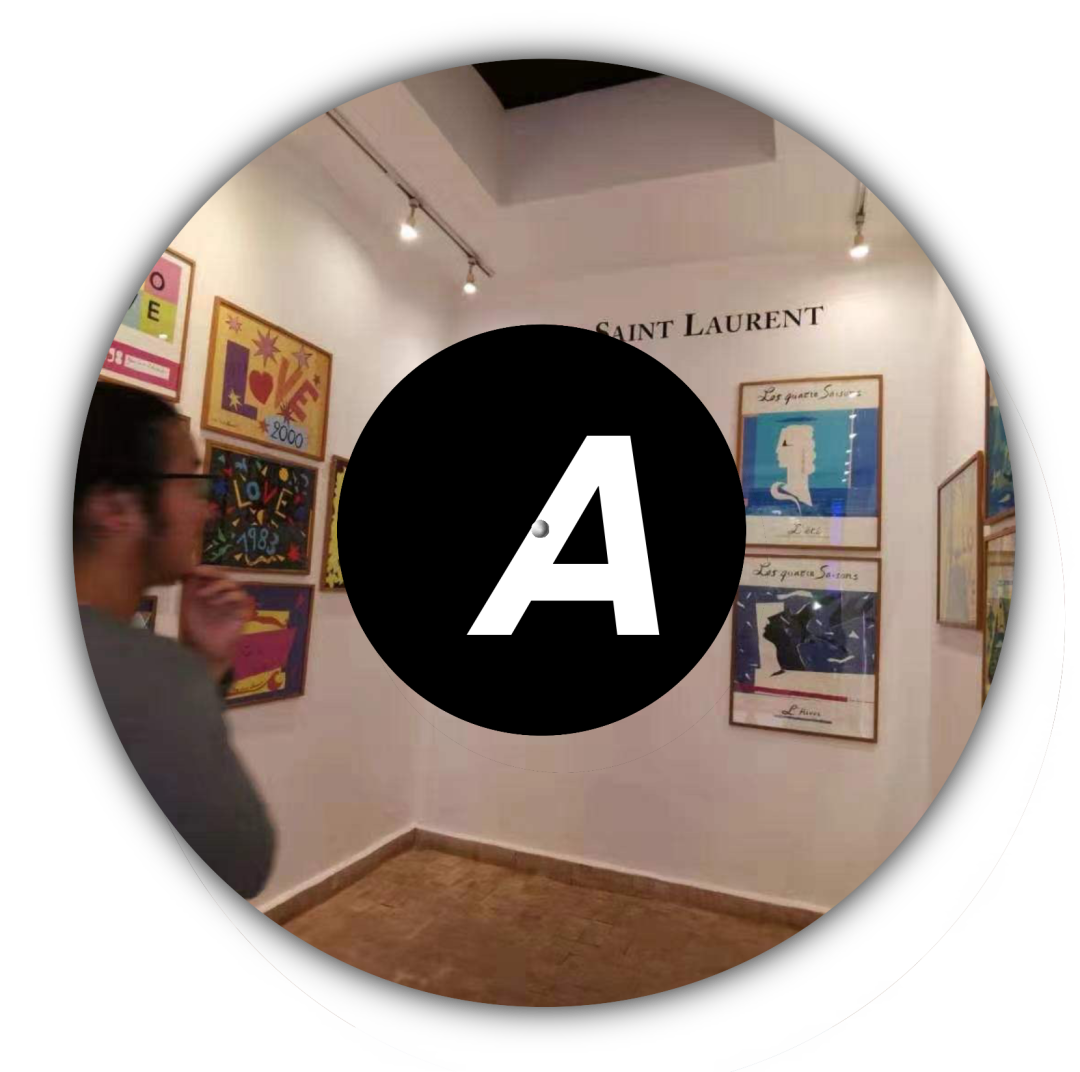
B面:浪龄 2 年
关于大学,我不喜欢的多过我喜欢的。大家学的东西很同质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学计算机和工程,人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少人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趋势。我是学电影的,这种小众的学科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在加州这个人人都想去硅谷做创业精英,就连车牌号码都带“AI”、“VC”字眼的环境,我就是个异类。反正我就是个很躺平的人,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学习环境里,挺痛苦的。说起来搞笑,我明明在加州读了四年书,中间还去了一次夏威夷,但都没有冲过浪。直到 2020 年回国,才在海南第一次学,那一刻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啊!我就应该去到海边的!”在冲浪的时候,我会进入一种极度专注的超体状态,就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所有烦恼可以全部忘掉,就只是我、冲浪板和大海而已。冲浪可能没有真的 fundamentally 改变我的什么东西,但让我意识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怎么说出来这么土啊,但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它让我看到了很多我之前认知里不存在的生活方式。A面:上海日式餐厅竹王 Takeo 和酒馆 Tokyo Night 老板、时尚总监

B面:浪龄 40 年
2007 年我来到中国生活,现在 55 岁,冲浪 40 年了。70 年代起,冲浪文化的浪潮开始席卷日本,每个年轻人都渴望拥有冲浪T恤,抱着冲浪板去海边。那个年代,冲浪就是等于受欢迎。很多城市人会在车上安装绑冲浪板用的车顶架,去显摆自己会冲浪这件事。所以“City Surfer”这个词,在当时是贬义的。日本海边的地方主义严重,城市人去海边,会被本地人瞧不起。中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当地冲浪俱乐部,跟着俱乐部里的前辈学习冲浪。俱乐部之间会进行比赛,选出该地区最好的冲浪选手,再进入全国大赛。全国大赛前三名冲浪手,能获得成为专业选手的培训资格,有机会成为职业冲浪运动员。我也跟着俱乐部参加过比赛,希望成为专业运动员,获得赞助。但后来意识到,冲浪是真的很需要天赋。年轻时,冲浪对我来说,是一项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摇滚乐一样,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一家之主,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非常大。以前在日本,一有空就去冲浪,哪怕只是周末两天。来中国之后,因为上海离哪儿的海都远,只能一个月去一次,囤积了一个月的压力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被释放出来。在这里,我遇到的每个冲浪的人都很友好,大家都是真心喜欢冲浪的。现在中国的冲浪场景,就像 70 年代的日本,有人觉得酷,有人想要美,有的人只想体验一下,但最后,真正热爱冲浪的人会被留下来的。 寻找可能的C面
寻找可能的C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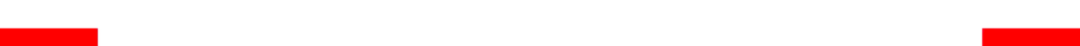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访问的最后,我问勤弥前辈,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现在中国的冲浪场景,你会选哪个词。他毫不犹豫地说:“素敵き(太好了),wonderful!”这个夏天我在朱家尖,试图通过对话,摸清并描述空气的形状。City Surfer 们的情感表达总是真诚而又笨拙的,“想冲浪”似乎是唯一的目的,这种璞玉般的情感,恰恰是这个俱乐部的气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总是来不及褪去从城市带来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正是这个原因,对彼此的生活都会多一份理解,无论这个周末你只是来冲个浪,还只是想卖醉。因为有大海,人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唯一的选择。当有了自主性的选择,哪怕不知道这个选择通向什么样的路,但有选择的人,必定是自由的。身处阶级和资本的系统里,是否要玩这个规则早已设定好的游戏,也是一个自主性的选择。不想玩游戏,或者已经玩腻了的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不一样的轨道,我们都在这个偏离的轨道上,在合理和安全的区间内,或远或近地去尝试,所以冲浪人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然而,天涯途上谁是客,冲浪人是留不住的。或许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足够幸运和自由,都可以去寻找不一样的生活,可能会离开,可能会继续走。但无论在哪,浪里的朋友都会祝福一切的到来和离别,并为你备上一杯酒。
访问的最后,我问勤弥前辈,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现在中国的冲浪场景,你会选哪个词。他毫不犹豫地说:“素敵き(太好了),wonderful!”这个夏天我在朱家尖,试图通过对话,摸清并描述空气的形状。City Surfer 们的情感表达总是真诚而又笨拙的,“想冲浪”似乎是唯一的目的,这种璞玉般的情感,恰恰是这个俱乐部的气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总是来不及褪去从城市带来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正是这个原因,对彼此的生活都会多一份理解,无论这个周末你只是来冲个浪,还只是想卖醉。因为有大海,人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唯一的选择。当有了自主性的选择,哪怕不知道这个选择通向什么样的路,但有选择的人,必定是自由的。身处阶级和资本的系统里,是否要玩这个规则早已设定好的游戏,也是一个自主性的选择。不想玩游戏,或者已经玩腻了的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不一样的轨道,我们都在这个偏离的轨道上,在合理和安全的区间内,或远或近地去尝试,所以冲浪人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然而,天涯途上谁是客,冲浪人是留不住的。或许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足够幸运和自由,都可以去寻找不一样的生活,可能会离开,可能会继续走。但无论在哪,浪里的朋友都会祝福一切的到来和离别,并为你备上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