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作者:大唐梁金吾
获取更多好看文章,请关注最爱历史
多年以后,当司马迁放下撰写《史记》之笔时,他大概仍会想起那个令他蒙羞的时刻。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九月,他被以“诬上”的罪名逮捕入狱。“诬上”等同于后世的欺君之罪,在汉朝应判腰斩。但此时,他所收集整理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仅仅撰写了一小部分,还未达到流芳百世的巨著规模。《太史公书》是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叮嘱他一定要完成的史书。对司马迁来说,撰写此书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有延续父亲遗愿的意义。眼下,面对生死关头,他只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所幸,汉朝对于死刑的执行界定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当时规定,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种是交钱赎罪,即“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而另一种则是承受“腐刑”,通过去势失去做男人的资格。司马迁彼时为太史令。汉朝官制规定,太史令为秩级六百石官员,每月禄米仅有70石。在汉朝,丰年时米价一般在30—50钱(五铢钱)/石。也就是说,司马迁不吃不喝,一年收入最多为42000钱,要一下子拿出50万钱罚金去赎命,难过登天。所以,被捕入狱后,司马迁没得选,只有承受“腐刑”才能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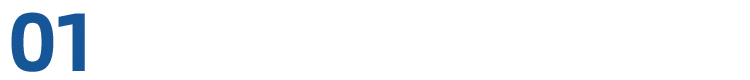
天汉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的苏武被扣押,汉武帝大怒,决定再征匈奴。此时,曾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均已谢世,大汉有兵无将。汉武帝只能沿用过去的思路,起用宠妾李夫人之兄、曾破大宛获良马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帅,以三万步骑协同作战的模式,进攻匈奴。考虑到李广之孙李陵曾任建章监和贴身侍卫,又有多年在敦煌、张掖屯兵练武的经验,且曾深入匈奴腹地勘察地形,汉武帝认为他更适合担任李广利大军的后方运粮官。所以,待朝廷点完将后,汉武帝又将李陵召回朝,要他为大军筹备出征粮饷。但是,李陵在入朝拜见汉武帝时,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给李广利当后勤部长。李陵的理由很直接,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祖上三代都是冲在最前线替汉朝打仗的先锋,如今,仅让他做个后方粮官,有辱李广子孙的家族使命。当然,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广利打仗向来平庸,难有胜仗,李陵若充当其运粮官,难出战绩,不利于振兴当时已趋没落的李广家族。
▲李广画像。
于是,李陵请求汉武帝另赐一队兵马给他。他愿意率着这支“别动队”,绕到匈奴人的后方,发起致命一击,以配合李广利在前方的攻势。李陵并未死心,他继续表示,自己愿意率领麾下那支在酒泉、张掖等地备战练武的5000人部队先行,为李广利大军占据先机。李陵手里的这支部队是清一色的“丹阳兵”,以步战善射闻名。汉武帝本来担心“以步御骑”容易招致败仗,可李陵却信誓旦旦地表态,自己有完胜的把握,希望汉武帝尽快授其兵权,直捣单于庭。这下,汉武帝大喜,遂令李陵率军先行出征,再命强弩都尉路博德领兵做李陵的后备。这个决定却遭到路博德的强烈反对。路博德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从前曾为伏波将军,灭过南越国,打仗是一把好手,老将怎么可能充当他人的配角?但他对汉武帝说出的理由是,李陵选择在九月秋收之际发兵,犯了兵家大忌,他不愿看到汉军将士为此而送命。无奈,汉武帝只能取消了路博德接应李陵的计划。不幸的是,李陵此次出塞,竟遭匈奴主力包围。他挥师搏击、杀敌数千,却仍难逃被包围的命运。在匈奴左、右贤王主力八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矢尽道穷”,只能将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广利身上。然而,就在李陵大军遭遇围困之际,他的手下管敢却率先投靠了匈奴人。管敢是李陵军中的斥堠(侦察兵),十分熟悉李陵军队的兵力部署。管敢向匈奴人泄露了李陵的底牌,导致李陵未能等到援军便已全军覆没。战后,李陵害怕被汉武帝问责,遂投降了匈奴。消息传来,汉武帝大发雷霆。而朝中大臣也多是见风使舵之辈,陛下盛怒,他们也有多狠骂多狠,唯独列席朝会的司马迁,一言不发。司马迁的反常,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便点名询问其看法。司马迁说,自己与李陵年纪相仿,又同朝为官,虽然平日里工作没什么交集,但“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针对李陵投降一事,司马迁坚持认为,李陵虽战败,但他的所作所为已公诸天下。他是个十分看重家族声誉及爱惜名节之人,他活着投降匈奴,应该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策,以待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司马迁绝对不会想到,正是自己这段为李陵辩白的发言,彻底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刘彻。图源:影视剧照
汉武帝误认为,司马迁对一个败军降将的“洗白”,旨在指责李广利、路博德等后方大军救援迟钝,由此引申,则是汉武帝用人失当,才导致本该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失败的恶果。一念及此,汉武帝也不给司马迁解释的机会,便给他定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下狱论死。问题来了,司马迁替李陵辩白是否站得住脚呢?也就是说,李陵的投降行为到底是真是假?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李陵先假投降,后迫于形势而真投降。但反过来想,李陵一开始或许就是真投降,只不过他的表现并不像其他投降者那样卑躬屈膝,反而是带着一种悲壮和无奈,恰恰是这种“悲情英雄”的铺垫造成了司马迁的误判。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从遭遇匈奴大军围困到完全战败投降,中间曾有过一段纠葛挣扎的过程。那时,面对匈奴大军的合围,李陵率军边打边撤,最后被匈奴兵断了后路,堵入一处峡谷之中。匈奴单于并不打算放过李陵,遂在峡谷两侧的峭壁上埋下伏兵,等李陵率军进入其提前布下的“口袋阵”后,再“乘隅下垒石”。经此一战,李陵的5000步卒死伤惨重。即便如此,李陵自始至终都坚持力战。直到双方战至黄昏时刻,看到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李陵这才身着便装只身出营,并制止手下跟随:“便衣独步山营,止左右:‘毋随我。’”
▲李陵画像。
按照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解读,李陵此时单独出营并非为了乞求投降,而是想凭借个人之力刺杀单于,以期改变战局。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与李陵作为军队统帅的身份背道而驰,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后面李陵去刺杀单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良久,(李)陵还,叹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 。”此时,摆在李陵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在军中自戕,另一条是回去接受汉武帝对战败者的处罚——斩刑。而斩刑这条路,他的祖父李广当年率军出征匈奴时,就已经替他尝试过了。史载,李广当年率军自雁门关出击匈奴,因遇匈奴单于主力围困,为匈奴兵生擒。后来李广诈死,偶然劫得匈奴良马,逃回汉朝。汉武帝见后,立即让廷尉府逮捕李广审讯问罪。廷尉府官员认为,“(李)广亡失多,为虏所生得,当斩”。最终,李广靠同事、亲朋及自己的家资,才得以交钱赎罪,贬为庶人。如今,历史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李陵的头上。他应当十分明白,失兵回汉朝,或许仍有机会苟活于世,但重振李氏家族的希望从此熄灭了。于是,据《汉书》记载,李陵刺杀单于失败后,曾有一名军吏劝解过他:“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军吏所说的“浞野侯”,正是曾流亡匈奴十年的汉将赵破奴。赵破奴与李陵类似,也曾率万骑部队深入匈奴腹地展开“斩首行动”,但出师不利,为匈奴左贤王所俘。直到李陵率军出征前夕,赵破奴才携家带口回到汉朝。朝廷对他的处置也比对待李广宽容,汉武帝没有怪罪赵破奴,反倒以礼相待。听完军吏的话,李陵立马制止手下的劝降意图:“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毫无疑问,如果司马迁知道此事,他必然会结合李陵之前的表现,进一步巩固其心中李陵拥有“国士之风”的看法。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让人失望。在随后的突围过程中,当李陵看到副将韩延年突围失败选择自杀殉国时,他却又宣称“无面目报陛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投降匈奴。前后反差,匪夷所思。据史书记载,李陵到了匈奴后,备受单于礼遇。当时,他的同僚好友、出使未果的苏武正被单于扣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牧羊以消磨意志。李陵得知此事后,一直“不敢(访)求(苏)武”,甚至被单于督促着前往北海劝降时,他也表现得异常拧巴。见到苏武后,李陵当即自剖心迹道:“(李)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李)陵?”——你苏武不愿意投降的心情和毅力,怎么可能超过我呢?又说,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达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还谈何忠君保节呢?见劝说苏武无用,李陵又说:“嗟乎,义士!(李)陵与卫律(此前威胁苏武投降匈奴的胡人)之罪上通于天。”并做势要与苏武诀别。
▲苏武画像。
如果不深入剖析李陵投降的影响,仅从他的行为和言辞入手观察,读史之人更多看到的只是他的忏悔与自责。司马迁与李陵同朝为官多年,即使没有任何交集,仅凭军报上的寥寥数语,也很难不受同情心的影响,对李陵在前线的惨状和投降后的痛苦产生深深的同情。而汉武帝却始终将信将疑。李陵投降后,天汉四年(前97),汉武帝又以公孙敖为因杅将军,让其率步骑4万配合李广利出征匈奴。这一次,公孙敖的运气没比李陵好多少。他带出去的4万部队,多数折损于匈奴主力之手。撤兵回朝后,公孙敖遭到了汉武帝的问责。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他只能将这一切的过错归咎于李陵,胡诌一语:“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公孙敖的话并无依据,且最后被证实替匈奴人练兵的,是另一名汉朝降将李绪,而非李陵。但那一刻,汉武帝显然已经完全泯灭了他对李陵的最后一丝信任。他将李陵留在汉朝的族人尽数杀光,替李陵求情的司马迁也受此牵连,获罪下狱,徘徊在生死边缘。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仗义执言受腐刑,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事件,然而,随着两人的故去,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东汉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司马)迁蚕室。”照此说法,在司马迁受腐刑一案中,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诱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过分指责和揭露景帝、武帝父子在位时的过错。不巧的是,该篇后来被汉武帝御览,愤怒的汉武帝当即令人删去。李陵投降匈奴后,司马迁替其求情,汉武帝便借故发火,将司马迁处了腐刑。往前追溯,卫宏的观点实际上源于西汉末年的宗室刘歆。▲《山海经》,刘歆曾为之作注解。图源:网络
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之子、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他在《西京杂记》中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可见,太史公一职是在汉武帝时确立的,此前录史之人皆是家传。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汉朝独一无二的太史公。在汉朝,太史公一职虽位在丞相之下,但国家发生的一切大事,底下的人呈报中央,都得先拿一份给太史公备案,而后再交予丞相处置。所以,太史公拿到的,都是朝廷的一手资料。而录史者,又向来要求使用春秋笔法,司马氏录史直言不讳,尽说景帝、武帝父子的龌龊事,汉武帝岂能容忍而不拿他开刀?刘歆认为,“李陵之祸”为汉武帝提供了处置司马迁的借口,同时也激起了司马迁日后的怨恨。这种怨恨,在他受刑之后再次爆发出来,从而导致其再下狱,最终身死狱中的结局。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在位期间,将太史公这个官职改为太史令,只是履行太史公此前负责的文书工作而已,而且不再任用司马氏子弟为史官。那么,刘歆、卫宏等人关于司马迁受腐刑一案的说法,是否可信呢?翻开《史记·孝景本纪》,在文章的末尾,司马迁发表议论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这段话的意思是,汉文帝在位期间原本已天下太平,但是到了汉景帝时代,他却错用晁错激化矛盾,酿成“七国之乱”。要不是后来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谋略,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子孙,诸侯王之祸估计很难平息。这难道不是朝廷在安危之际施用谋略的最好例证吗?
这么看来,在司马迁眼中,后世公认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汉文帝的功劳,而汉景帝的能力甚至都不如自己的儿子汉武帝。但话说回来,刘歆、卫宏等人主张的是司马迁贬低孝景、孝武这一对帝王父子,从现存史料分析,这种结论似难成立。不知目前流行的《孝景本纪》是否遭到删改,跟司马迁最初的版本已有不同?读罢班固的《汉书》,汉明帝刘庄得出一个观点:“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他认为,司马迁针砭时弊过于激烈,虽然可以留名于后世,但或多或少都贬损了当世的君王,实在没有半分忠臣义士的影子。王肃是汉魏之际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师从大儒宋忠。他认为,班氏父子在编撰《汉书》时就曾说过,司马迁写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如此才有“实录”之美名。既然录史需要秉笔直书,汉武帝看完之后,“怒而削之”,也是人之常情。
▲王肃之父、司徒王朗。图源:影视剧照
对此,《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之言称:“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班彪之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太史公书》应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且去司马迁不过百年,想来所言非虚,当时流传的《史记》已经缺失了十篇文字。但他们自始至终从未留下有关《史记》遗失的时间、篇目及原因。对于《史记》遗失的详情,《汉书》注家之一、三国时期学者张晏认为:“(司马)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这一意见,成为现代学界关于《史记》遗失篇目的公认观点。但由于司马迁生卒年仍有争议,《史记》失书与汉武帝是否有关,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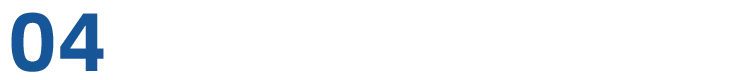
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受腐刑无关任何人,也不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是他想要以此抗争汉武帝晚年残暴的统治。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徐朔方认为,依照王国维对司马迁的生卒年考证,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时,年已47岁。司马迁膝下至少有一个女儿,其女后来嫁给了西汉丞相、安平侯杨敞。杨敞出身弘农杨氏,其祖上是赤泉侯杨喜。当年,项羽兵败垓下,就是这位杨喜与其他五名汉军将领在项羽自刎后分得其尸,扬名天下。
▲乌江自刎。图源:影视剧照
杨敞的正室、司马迁的女儿司马氏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强人”。昌邑王刘贺在汉昭帝驾崩后称帝,在位27天,据说做了不下一千件的荒唐事,惹得朝堂怨声载道,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开始密谋废立。杨敞是霍光的亲信,行动开始前,杨敞害怕得要死,回家便将废立之事向妻子和盘托出,结果司马氏告诉他:“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可见,司马氏在大事面前有多果断决绝。而司马迁受腐刑时,其女早已嫁作杨敞妻。司马迁一年工资虽不足五万,但遇到这种大事,女儿出于人之常情,又怎会对父亲见死不救呢?徐朔方指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司马迁觉得自己没错,拒绝花钱自赎;二是,司马迁看不惯汉武帝的行为,想通过此等赌气的行径,唤起汉武帝内心的自我审视。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汉武帝内心极其矛盾,一方面仍如年轻时那般豪迈雄阔,以追击匈奴、征伐大宛为己任,大力开拓汉帝国的疆土;另一方面也担忧“亡秦之迹”的再现。因为他早年立的太子刘据“仁恕温谨”,一旦即位,必然是个仁孝守成之君。所以,相较于“老太子”刘据,他更喜爱与自己性情相似的幼子刘弗陵。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祟下,汉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与太子刘据之间的关系。自从太子就宫后,他为刘据设立了博望苑,太子身边就“使通宾客,从其所好”,甚至还有不少他的反对派给太子出谋划策。显然,父子二人在皇权的争夺上愈演愈烈。

▲晚年的汉武帝。图源:影视剧照
众所周知,太子刘据是皇后卫子夫之子。其背后,卫、霍外戚集团势力自然不容忽视。可是,在外戚身份以外,卫青、霍去病等更是以征伐匈奴而闻名的大汉军事实权人物。对于一位以“皇权至上”为信条的大一统君主而言,政治权力的转移,对政治生命而言是致命的。换而言之,如果军方配合太子刘据介入皇权争夺,汉武帝的统治将面临提前结束的风险。很不凑巧,李陵身后的李氏一族也是大汉声名赫赫的军功世家。为了消除身边潜在的风险,汉武帝有理由故意不给李陵军队,让其自募人马出征匈奴,待其打不下去要撤兵时,再以道义及命令阻断他的退路,使之最终走上被迫投降的终点。只是他没想到,明明满朝文武已尽说李陵的不是,司马迁却还要出来当“刺头”,声称李陵有“国士之风”,逼迫他撤销治罪李陵的决定。这样,不治司马迁之罪,也就说不过去了。太始元年(前96),受尽腐刑与牢狱之苦的司马迁终于出狱。考虑到自己还要继续述说黄帝以来的历史,他只能忍着身心的苦楚及天下人的冷眼,重新找汉武帝要官。不知是否仍心存恼怒,汉武帝给了他一个略带羞辱但又俸禄优厚的官职——中书令。在汉朝,中书令是秩级“千石”的官员。但在司马迁之前,承秦所置,此官只用“宦者”。面对如此羞辱,司马迁只埋头苦撰《太史公书》的剩余篇目,直到太始四年(前93),其著基本完结。这时,埋藏在司马迁内心多年的愤懑,才终于找到一个宣泄口。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司马迁在赋中一叹“士生之不辰”,二感不甘于“没世无闻”,心态像极了曾以《离骚》寄托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的前辈屈原。
但在那个他认为“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年代里,他从未轻言放弃,哪怕死亡在前,哪怕极尽屈辱,他依旧选择了与手中的“史笔”共进退。也正是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终使《史记》获得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至高地位!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社,2017年
施之勉 :《太史公行年考辨疑》,《东方杂志》,1944年第16期
徐朔方:《考据与研究──从年谱的编写谈起》,《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韩兆琦:《司马迁自请宫刑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金璐璐:《汉武帝对司马迁<史记>影响考论》,《文艺评论》,2012年第2期
杨有礼:《秦汉俸禄制度探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刘淑颖:《汉代徙刑的嬗变与刑制改革》,《湖湘论坛》,201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