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游牧民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寻找理想栖息地。他们射箭、骑马、摔跤,迁徙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美学。比如,马背上的部落图腾、摔跤手的围领、蒙古包的穹顶、悠远的蒙古长调。在民族的行进中,这些文化元素也生出了不同的形状。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尝试回到各自生长的传统中,在民族、非遗、宗教中“寻根寻源”,追逐着自己的「水草」。我们关注到三位创作者,他们在自然、宗教、民族中不断回溯自己的身份,在舞蹈、音乐、艺术里洄游。与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试图了解,「他们一直寻找的水草,是什么?」 从内蒙古、从舞蹈、从身体出发,面向世界的“外景地”
从内蒙古、从舞蹈、从身体出发,面向世界的“外景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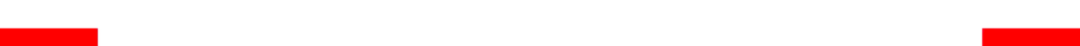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东妮尔,内蒙古出生,以编舞、当代表演、影像、软雕塑和科技等媒介材料创作艺术作品。她在纽约、北京和温哥华之间“游牧”工作,又始终以感知、实验和深耕,与“出发地”内蒙古的自然和传统文化元素始终联系着。
东妮尔,内蒙古出生,以编舞、当代表演、影像、软雕塑和科技等媒介材料创作艺术作品。她在纽约、北京和温哥华之间“游牧”工作,又始终以感知、实验和深耕,与“出发地”内蒙古的自然和传统文化元素始终联系着。
东妮尔和作品在水磨坊中心(The Watermill Center) 30周年展览“Stand”,纽约长岛,2022
Lindsay Morris摄影
在造空间策展的《一起游牧》中,东妮尔展出了影像作品《场域记录4:每一动都是仪式》。一个由羊毛制成的介于植物和生物间的巨大球体装置,在草原、群马和低语的牛群间,风给了它精微的舞动和生命。东妮尔推动球体,面向日月,一分一毫地在巴尔虎草原缓步行走。
《场域记录4: 每一动都是仪式》, 4K影像、彩色、有声,2021-2022
东妮尔在文工团的大院儿长大,邻居们,有编剧,将草原深处的生活编织成诗句。有作曲家,研究蒙古族音乐的曲调曲式。有布景师,绘制牧区场景的切面。有马头琴演奏者、长调歌者、录音师、舞者… … 在礼堂里,她看外国电影,也看妈妈演出和导演的节目;她熟悉剧场后台的结构、松香和霉菌味儿,以及还未干透的布景,这些布景中有内蒙古从东部到西部的植被——白桦林、草甸草原、荒漠草原、沙漠,也有物件和抽象的符号… … 她没有在牧区长大,但经由艺术,与蒙古人的生活和自然观发生连结。几乎每个假期,东妮尔都会跟着妈妈在内蒙古各地工作旅行。怪石头、鹿角帽子和羊毛、各种蘑菇,这些小物件会因为一次上路被带回来,成为她的收藏。在长期不断的往返路途中,她的身体和心神里沉淀了大量移动中的风景、地貌地质、生态生灵,和一些语言说不清,悬浮在空气中的气息和记忆。 《场域记录4: 每一动都是仪式》静帧, 4K影像、彩色、有声,2021-2022在19岁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前,东妮尔接受传统的舞蹈训练——芭蕾、中国民族民间舞等,其中蒙古族舞蹈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多年的学院派训练,一方面她在严格的要求下,练习、体会每一个动作的气韵,连接成词语,试图去完成得更接近那个被设定的理想范式。一方面她感到不满足,觉得身体虽然在舞动,却无法与当下的自己连接。学院体系里保留的传统蒙古族舞蹈是真实的吗?在这个体系中被定义的风格纯正性是唯一的吗?东妮尔想找到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在不满足和好奇心的驱动下,她在学校之外的时间自学和广泛吸收,从欧洲前卫戏剧(European avant-garde theatre),美国剧场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的作品,到卡尔维诺的小说,大乘佛教哲学,和北京各处发生的小型演出… … 最重要的,她开始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直觉。2011年,东妮尔开始了纽约的旅程。这期间,贾德逊舞蹈剧场(Judson Dance Theater)艺术家们的开创性工作和实验艺术的场景延伸出来的艺术作品对当时的她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编舞的扩展实践,到重新发现日常行动,到舞蹈作为一种媒介与视觉艺术的交叉等。这个过程中,它对多样性、差异性和共存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觉得与游牧精神不谋而合,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次试验。“人与移动的风景”是与“时空”、“仪式”等并行的,东妮尔的几个创作母题之一,围绕它,在不同的阶段,她以多样的方法做作品。有两个冬天,她完全生活在呼伦贝尔。牧人们穿着非常厚重的“皮大哈”,如猛兽般用木锨破雪放牧。白色草原上,人在劳动,呼出热的水汽。有时候分不清楚是人还是动物。2009年,东妮尔编排了《冬牧》,作为凝练巴尔虎蒙古人、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人生活的舞蹈诗剧《呼伦贝尔大雪原》的第二篇章。2016年,东妮尔创作了《云图》,舞动是在时空里缓慢延展的。来源于东妮尔自身身体化的感觉。躺在草原上的时候,看天上的云,云移动非常缓慢,但每一瞬间,都是变化,云的图像和人的心绪图像互相牵动。草原给了人时间的尺度,在无限延展的时间和空间里,人的烦恼已经不重要了。这是属于蒙古人的自然观。2017年《场域记录I-II》,她将高原地形细致的转化为一个总谱(score),引导即兴舞蹈和声场一同生成共振的场域,舞者们像风景中鲜活的又遵循着某种规律的生灵。
《场域记录4: 每一动都是仪式》静帧, 4K影像、彩色、有声,2021-2022在19岁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前,东妮尔接受传统的舞蹈训练——芭蕾、中国民族民间舞等,其中蒙古族舞蹈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多年的学院派训练,一方面她在严格的要求下,练习、体会每一个动作的气韵,连接成词语,试图去完成得更接近那个被设定的理想范式。一方面她感到不满足,觉得身体虽然在舞动,却无法与当下的自己连接。学院体系里保留的传统蒙古族舞蹈是真实的吗?在这个体系中被定义的风格纯正性是唯一的吗?东妮尔想找到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在不满足和好奇心的驱动下,她在学校之外的时间自学和广泛吸收,从欧洲前卫戏剧(European avant-garde theatre),美国剧场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的作品,到卡尔维诺的小说,大乘佛教哲学,和北京各处发生的小型演出… … 最重要的,她开始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直觉。2011年,东妮尔开始了纽约的旅程。这期间,贾德逊舞蹈剧场(Judson Dance Theater)艺术家们的开创性工作和实验艺术的场景延伸出来的艺术作品对当时的她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编舞的扩展实践,到重新发现日常行动,到舞蹈作为一种媒介与视觉艺术的交叉等。这个过程中,它对多样性、差异性和共存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觉得与游牧精神不谋而合,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次试验。“人与移动的风景”是与“时空”、“仪式”等并行的,东妮尔的几个创作母题之一,围绕它,在不同的阶段,她以多样的方法做作品。有两个冬天,她完全生活在呼伦贝尔。牧人们穿着非常厚重的“皮大哈”,如猛兽般用木锨破雪放牧。白色草原上,人在劳动,呼出热的水汽。有时候分不清楚是人还是动物。2009年,东妮尔编排了《冬牧》,作为凝练巴尔虎蒙古人、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人生活的舞蹈诗剧《呼伦贝尔大雪原》的第二篇章。2016年,东妮尔创作了《云图》,舞动是在时空里缓慢延展的。来源于东妮尔自身身体化的感觉。躺在草原上的时候,看天上的云,云移动非常缓慢,但每一瞬间,都是变化,云的图像和人的心绪图像互相牵动。草原给了人时间的尺度,在无限延展的时间和空间里,人的烦恼已经不重要了。这是属于蒙古人的自然观。2017年《场域记录I-II》,她将高原地形细致的转化为一个总谱(score),引导即兴舞蹈和声场一同生成共振的场域,舞者们像风景中鲜活的又遵循着某种规律的生灵。 《场域记录II》,贾德逊教堂运动研究(Movement Research at the Judson Church),纽约,2019
《场域记录II》,贾德逊教堂运动研究(Movement Research at the Judson Church),纽约,2019
2019年《场域记录3》之后的创作,她专注于身体的物质性(materiality)、身体与其他材料间的平等和互相转化,这使得她自然的拓展到不同的媒材,其中对有机材料的选择与她的文化根源紧密联系。东妮尔也曾对自己的身份感觉到困惑,觉得自己是“游客”:在北京,她是内蒙人。在纽约,她是中国人。回到内蒙,她不会讲蒙语,是外人。在非常近期,在历经了更多不同地域的生活和思考后,她开始肯定自己的视角:“我在移动中体验世界,和不同的世界材料发生新的连接。我的身体是我的家,当感知清晰时,生活在哪里不是最重要的。”“草原可以是一个内部的草原,躺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就像家乡的草原。” 东妮尔在新巴尔虎右旗,2021
东妮尔在新巴尔虎右旗,2021
东妮尔觉得,对“纯正性”的过分强调,可能是危险的。与游牧精神内核中的包容和突破也许已经相违背。蒙古族舞蹈、艺术和身份,都可以是开放、动态的。
 「天声」的音乐内核
「天声」的音乐内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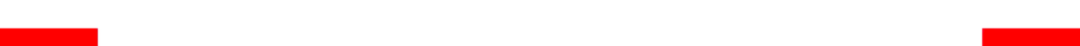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7月底的西宁,青盐艺术书展上,天声乐队临时做了一个专场演出。演奏专辑《盲》,现场演出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小剧场,成员身穿白色的衣服,带着白色的面具,缓慢地移动向一个中心。屏幕上放着结冰的青海湖,一个现代舞者在起舞。现场,两个人一起敲中国大鼓的动作又像是某个宗教仪式现场。摇滚乐、宗教、民族音乐。空间里,很多东西奇妙融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他们今年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演出。天声乐队发给我的最新简介中,青藏高原的后现代主义摇滚乐队和综合艺术团体。今年乐队原本有很多计划,坐标计划2022,十周年特别巡演,下一张专辑的筹备。计划在延期和取消中反复打转,最终搁置。天声是一个由观念统领的乐队,感官五部曲、坐标计划。你感觉他们会做一个长期的实验。吉他手张剑峰在中学时买了第一把吉他,后来去北京上学,玩一些很燥的摇滚乐。团队的几个成员也差不多,学吉他,在外上学,玩朋克、玩重金属。年轻人一块儿组乐队,主唱模仿摇滚明星的音色、唱腔。乐队模仿曲子的结构、配器。 回西宁后,张剑峰在体制内工作。几个朋友还是想做乐队,但是他们有些厌倦模仿了。西方摇滚乐诞生时的精神,和他们自己,与这个时代,都毫无关系。天声乐队,想寻找自己的内核。天声本来是飘渺、优美的意思,他们想着既然不唱歌了,就做器乐摇滚。后来他们做的音乐明显与优美毫无关系。去年,他们为《盲》拍了一部半自传式的实验电影。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诗人,终日写诗却浑浑噩噩。一天,窗口降临了一个先知,他顺着指引走出房间,走出城市,穿过郊野,到结冰的青海湖镜面上舞蹈,在下雪的仙米森林里打鼓、过夜,登到祁连山顶看日出。很多时候变化是混沌的,先知只是一个具象的符号。摇滚乐在很小的时候吸引他们,是一个释放和自由的启蒙。在西宁生活,偏僻、压抑,没什么音乐氛围,天声的成员来来去去,会乐器的基本都试过他们乐队。对张剑峰来说,做音乐是生活与时代压抑的出口。生长于青藏高原,生活在青藏高原,几个成员不同程度地受到藏传佛教的熏染。「感官五部曲」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佛教,成员虽然不尽信仰佛教,但是都有学佛。佛教中有「色香声味触法」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人类的感官——我们跟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感官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阶段是割裂与困惑。天声成立的第七年,他们才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惑》。堆了各种采样、古筝、蒙古族的马头琴、藏族的山歌与乐器、电子合成器的声音。把他们接触到的一切都往上堆,各种声音嘈杂、碰撞、断裂。张剑峰认为那时候是一种符号化的表面尝试,表达了他们自身断裂的处境。后来的《盲》中,他们不再直接用民族乐器、请民族乐手去表达民族性了。他们不再追求悦耳,用音乐本身的语言去再造一种语言。整张专辑借鉴了交响乐(管弦乐套曲)曲式,填充各种材料和音色较为好玩和实验。在《盲》的现场演出中,有音乐、电影、表演、装置,灯光,甚至气味。很多符号在现场和屏幕间穿梭,装置则会把观众投射到虚幻之中,乐手的表演穿越到遥远的山谷,电影中人物却似乎在舞台上鼓舞……所有这些视觉元素营造出一种「盲」的错乱感。盲的意思是,麻木,但是得知道自己的麻木。在天声自己的哲学里,德勒兹提出的「游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勒兹认为,「游牧」是一种多维度的生成,从内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天声不想去风格化自己的音乐,贴上后摇滚、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等标签。当人们觉得摇滚乐没意思,去做实验性的音乐。这些东西突然被命名为后摇滚,这个风格就有了程式,进了博物馆。天声乐队的「坐标计划」,是他们游牧的一个游戏。「坐标计划2018」在城市商业区、黄河岸边,废弃车间,昆仑山支脉青沙山间巡游,融合 了音乐、诗歌、舞蹈、装置。他们在群山深处、黄河岸边、城市空间里为流水、为民族仪式、为自然与神话而演奏。「坐标计划 2022」中,他们计划走出青海,去拉萨、西安和温州。计划没有成行。他们从音乐体例的模仿与单纯的情绪表达中出走,传统器乐的使用是他们的起点,而他们还将在音乐中游牧得更远。
7月底的西宁,青盐艺术书展上,天声乐队临时做了一个专场演出。演奏专辑《盲》,现场演出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小剧场,成员身穿白色的衣服,带着白色的面具,缓慢地移动向一个中心。屏幕上放着结冰的青海湖,一个现代舞者在起舞。现场,两个人一起敲中国大鼓的动作又像是某个宗教仪式现场。摇滚乐、宗教、民族音乐。空间里,很多东西奇妙融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他们今年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演出。天声乐队发给我的最新简介中,青藏高原的后现代主义摇滚乐队和综合艺术团体。今年乐队原本有很多计划,坐标计划2022,十周年特别巡演,下一张专辑的筹备。计划在延期和取消中反复打转,最终搁置。天声是一个由观念统领的乐队,感官五部曲、坐标计划。你感觉他们会做一个长期的实验。吉他手张剑峰在中学时买了第一把吉他,后来去北京上学,玩一些很燥的摇滚乐。团队的几个成员也差不多,学吉他,在外上学,玩朋克、玩重金属。年轻人一块儿组乐队,主唱模仿摇滚明星的音色、唱腔。乐队模仿曲子的结构、配器。 回西宁后,张剑峰在体制内工作。几个朋友还是想做乐队,但是他们有些厌倦模仿了。西方摇滚乐诞生时的精神,和他们自己,与这个时代,都毫无关系。天声乐队,想寻找自己的内核。天声本来是飘渺、优美的意思,他们想着既然不唱歌了,就做器乐摇滚。后来他们做的音乐明显与优美毫无关系。去年,他们为《盲》拍了一部半自传式的实验电影。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诗人,终日写诗却浑浑噩噩。一天,窗口降临了一个先知,他顺着指引走出房间,走出城市,穿过郊野,到结冰的青海湖镜面上舞蹈,在下雪的仙米森林里打鼓、过夜,登到祁连山顶看日出。很多时候变化是混沌的,先知只是一个具象的符号。摇滚乐在很小的时候吸引他们,是一个释放和自由的启蒙。在西宁生活,偏僻、压抑,没什么音乐氛围,天声的成员来来去去,会乐器的基本都试过他们乐队。对张剑峰来说,做音乐是生活与时代压抑的出口。生长于青藏高原,生活在青藏高原,几个成员不同程度地受到藏传佛教的熏染。「感官五部曲」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佛教,成员虽然不尽信仰佛教,但是都有学佛。佛教中有「色香声味触法」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人类的感官——我们跟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感官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阶段是割裂与困惑。天声成立的第七年,他们才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惑》。堆了各种采样、古筝、蒙古族的马头琴、藏族的山歌与乐器、电子合成器的声音。把他们接触到的一切都往上堆,各种声音嘈杂、碰撞、断裂。张剑峰认为那时候是一种符号化的表面尝试,表达了他们自身断裂的处境。后来的《盲》中,他们不再直接用民族乐器、请民族乐手去表达民族性了。他们不再追求悦耳,用音乐本身的语言去再造一种语言。整张专辑借鉴了交响乐(管弦乐套曲)曲式,填充各种材料和音色较为好玩和实验。在《盲》的现场演出中,有音乐、电影、表演、装置,灯光,甚至气味。很多符号在现场和屏幕间穿梭,装置则会把观众投射到虚幻之中,乐手的表演穿越到遥远的山谷,电影中人物却似乎在舞台上鼓舞……所有这些视觉元素营造出一种「盲」的错乱感。盲的意思是,麻木,但是得知道自己的麻木。在天声自己的哲学里,德勒兹提出的「游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勒兹认为,「游牧」是一种多维度的生成,从内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天声不想去风格化自己的音乐,贴上后摇滚、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等标签。当人们觉得摇滚乐没意思,去做实验性的音乐。这些东西突然被命名为后摇滚,这个风格就有了程式,进了博物馆。天声乐队的「坐标计划」,是他们游牧的一个游戏。「坐标计划2018」在城市商业区、黄河岸边,废弃车间,昆仑山支脉青沙山间巡游,融合 了音乐、诗歌、舞蹈、装置。他们在群山深处、黄河岸边、城市空间里为流水、为民族仪式、为自然与神话而演奏。「坐标计划 2022」中,他们计划走出青海,去拉萨、西安和温州。计划没有成行。他们从音乐体例的模仿与单纯的情绪表达中出走,传统器乐的使用是他们的起点,而他们还将在音乐中游牧得更远。 果子的生命材料
果子的生命材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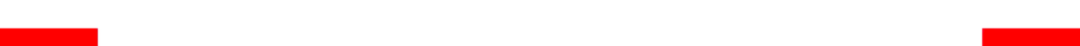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八月的内蒙古草原上,有一场热闹的婚礼。婚礼的主角,果子,穿着自己钩织的白色婚纱和头巾。一百多个朋友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大多是以「游牧」为生活方式的人,在与自然和在地传统的无限亲密中大胆创作的人,手作者、舞者、流动艺术表演者、音乐人,都是他们不同的身份。果子第一次过上游牧生活,是在大理。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短暂地尝试工作,都不开心,于是计划在旅行中度过间隔年。结果在大理停了下来。大理的冬天起风、下雨、阴冷。果子买了毛线,给自己勾了帽子、毛衣、围巾。朋友见了,就送她一个摆摊桌,一个竹编背篓,陪她去人民路摆摊。之后的一段时间,果子白天钩织,晚上摆摊,过规律的生活。2015年,大理还是摆摊的好时候。人民路存在很多暴富的「神话」,一些手艺人从摆摊起家,开了门店、开了民宿。果子是潮汕人,在六岁的时候就会钩织了。钩织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一些地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潮汕那边有外贸公司做钩织产品,在村里组织一些闲暇的妇女做手工钩织。果子的外婆、妈妈、阿姨在工作和家务之外,聚在一起,把毛线摆开来,在闲谈中,手中的毛线变为帽子、围巾、手套……这是她们补贴家用的方式。小果子在旁边看着,拿起钩针和毛线,传承下了这个手艺。在大理,果子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基本没有自己租过房子。有一个叫二十二的朋友,在离古城不远的凤阳邑租下了一个一百多年的老院子,房子是传统白族的石木结构,她收拾出了几间房间,接待「流浪汉」,果子是第一批住客。大家都比较穷,并且对消费主义推崇的良好生活没有太大兴趣。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原始的。床垫是去废弃院子里捡的。没有厕所,她们挖了个旱厕。隔几天去朋友家洗澡,后来有朋友送了她们一个移动式洗澡机。那时候大理还有一个地方叫「OM山洞」,条件比他们好很多,还有桑拿房。这两个地方一起,成为了国际流浪汉收容所。在这里住过的手艺人,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艺术组织,「瓦嘎帮」,意为「流浪者」。她们做捕梦网、植物染、粘土饰品、绕线曼达拉、macrame编绳、钩织。还有画家、音乐人、艺术家。和全世界那些群居的嬉皮士差不多,靠手艺为生,靠创作活着。做的作品大多围绕迷幻文化、部落、自然、宇宙、宗教、内心能量。受了朋友们的影响,果子从一开始钩织实用的物品,转向钩织一些装置,比如曼达拉。她把钩织当作一种修行的方式,一针一线、一呼一吸,和冥想一样,专注在一个点,进入、忘我。一次,果子从上午十点,钩织一块绿色的圆形挂毯,反应过来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地摊已经铺满了整个大厅,足足有两米多。很多时候,大自然也是灵感的来源。天空与海洋的蓝色,大地的棕色、生长出枝叶的绿色、点缀上繁花的彩色。她捡被修理掉的樱花枝、掉落的松果、好看的石头。去二手市场收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个鸟笼。对「瓦嘎帮」的成员来说,「游牧」才是一种永恒的生活状态。她们把大理当作一个大本营,自然和气候是她们追逐的水草,在七月份的雨季来临前离开,去西藏、新疆等地避暑。在冬天的时候去泰国、印度等地,在海滩享受整天的阳光。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果子会把钩织用的毛线都背在身上。八十几斤的身材,肩上的背包有四十斤。后来她学会精简行李,善用现代化的快递,毛线四散在朋友家和几个据点。被问及「会不会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时,果子说,只要在钩织,她就拥有自己的世界。2018 年,果子加入了「太行流动艺术团」,从大理搬到上海朱家角。依然是一种松散的群居生活,大家定时起床、在院子里练习。晚上一起看电影,有人会站起来继续练习,身体与水晶球、武幻、火等道具融为一体。果子结识了同样玩流动艺术的先生。出门时,他们流动到哪,表演到哪。赚点路费,继续上路。今年八月,在先生的老家,内蒙古的草原上,婚礼变成了一场音乐节。果子把这两年积攒下来的钩织作品,布置在草原的各处,场地同时也是一个钩织展。他们租了四十几个蒙古包,最大的蒙古包成为主舞台。在果子钩织的曼达拉下,户外还有一个DJ台。朋友们轮番上阵,鼓队、现场音乐、世界音乐、电子音乐……很多朋友想上台还排不上号。还有流动艺术,果子自己玩了会儿火舞。婚礼仪式在傍晚七点开始,背景是草原的日落。那天天气很好,太阳一点点落到地平线以下,留下金色的晚霞。晚上,烟花散了,大家松松散散地躺在草原上。有人送了果子一个天文望远镜作为新婚礼物,可以看月亮表面。还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这些年来,钩织和流动艺术是果子生命版图里最重要的部分,她来去于不同的风土与温度之间,游牧着的生活方式、在路上遇见的朋友们、属于自然的气息,时刻作用在果子的创作中。毛线、纹样、花色、火把,她在这样的生活中,自由地延续着这些材料的生命力。东妮尔的舞蹈语言、天声的音乐内核和果子的生命材料,传承于自然、民族、传统,又在行走中不断交织、生长,编织出新的生命活力。正如adidas Originals「骤」系列产品将西部游牧部落传统“马毯”上的编织元素巧妙呈现于鞋身之上,创作者在民族性与传统文化的滋养,天地与自然的灵感之间,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游牧文化、对传统元素、自我感受与观念进行新的阐释。adidas Originals 于近期发起项目「万物寻宗」,并推出该项目首季——「骤」系列产品,「骤」围绕西北地区风土人情展开,从传统游牧民的马毯、包包、服饰上传承部落图腾、编织纹样进行创新性的融合,构筑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游牧世界」。Superstar 是品牌的代表鞋款,此次运用了内蒙草原相扑选手的「围领」元素作为创作灵感,来自草原的力量,带你踏入民族与潮流融为一体的「游牧世界」。全系列由中国香港潮流艺术家邓卓越担任策划顾问,以“寻根寻源”为宗旨,力邀邀众多非遗艺术家、匠人参与共同演绎,将不同的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多个产品系列。adidas Originals「万物寻宗」 始终坚信不论如何变化,传统文化中的“根”和华夏民族的“宗” 是永远流淌在人们血液中的因子。年轻创作者对自然与传统的延续,成为寻找身份归属、创作、表达自我乃至存在的新方式。
八月的内蒙古草原上,有一场热闹的婚礼。婚礼的主角,果子,穿着自己钩织的白色婚纱和头巾。一百多个朋友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大多是以「游牧」为生活方式的人,在与自然和在地传统的无限亲密中大胆创作的人,手作者、舞者、流动艺术表演者、音乐人,都是他们不同的身份。果子第一次过上游牧生活,是在大理。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短暂地尝试工作,都不开心,于是计划在旅行中度过间隔年。结果在大理停了下来。大理的冬天起风、下雨、阴冷。果子买了毛线,给自己勾了帽子、毛衣、围巾。朋友见了,就送她一个摆摊桌,一个竹编背篓,陪她去人民路摆摊。之后的一段时间,果子白天钩织,晚上摆摊,过规律的生活。2015年,大理还是摆摊的好时候。人民路存在很多暴富的「神话」,一些手艺人从摆摊起家,开了门店、开了民宿。果子是潮汕人,在六岁的时候就会钩织了。钩织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一些地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潮汕那边有外贸公司做钩织产品,在村里组织一些闲暇的妇女做手工钩织。果子的外婆、妈妈、阿姨在工作和家务之外,聚在一起,把毛线摆开来,在闲谈中,手中的毛线变为帽子、围巾、手套……这是她们补贴家用的方式。小果子在旁边看着,拿起钩针和毛线,传承下了这个手艺。在大理,果子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基本没有自己租过房子。有一个叫二十二的朋友,在离古城不远的凤阳邑租下了一个一百多年的老院子,房子是传统白族的石木结构,她收拾出了几间房间,接待「流浪汉」,果子是第一批住客。大家都比较穷,并且对消费主义推崇的良好生活没有太大兴趣。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原始的。床垫是去废弃院子里捡的。没有厕所,她们挖了个旱厕。隔几天去朋友家洗澡,后来有朋友送了她们一个移动式洗澡机。那时候大理还有一个地方叫「OM山洞」,条件比他们好很多,还有桑拿房。这两个地方一起,成为了国际流浪汉收容所。在这里住过的手艺人,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艺术组织,「瓦嘎帮」,意为「流浪者」。她们做捕梦网、植物染、粘土饰品、绕线曼达拉、macrame编绳、钩织。还有画家、音乐人、艺术家。和全世界那些群居的嬉皮士差不多,靠手艺为生,靠创作活着。做的作品大多围绕迷幻文化、部落、自然、宇宙、宗教、内心能量。受了朋友们的影响,果子从一开始钩织实用的物品,转向钩织一些装置,比如曼达拉。她把钩织当作一种修行的方式,一针一线、一呼一吸,和冥想一样,专注在一个点,进入、忘我。一次,果子从上午十点,钩织一块绿色的圆形挂毯,反应过来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地摊已经铺满了整个大厅,足足有两米多。很多时候,大自然也是灵感的来源。天空与海洋的蓝色,大地的棕色、生长出枝叶的绿色、点缀上繁花的彩色。她捡被修理掉的樱花枝、掉落的松果、好看的石头。去二手市场收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个鸟笼。对「瓦嘎帮」的成员来说,「游牧」才是一种永恒的生活状态。她们把大理当作一个大本营,自然和气候是她们追逐的水草,在七月份的雨季来临前离开,去西藏、新疆等地避暑。在冬天的时候去泰国、印度等地,在海滩享受整天的阳光。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果子会把钩织用的毛线都背在身上。八十几斤的身材,肩上的背包有四十斤。后来她学会精简行李,善用现代化的快递,毛线四散在朋友家和几个据点。被问及「会不会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时,果子说,只要在钩织,她就拥有自己的世界。2018 年,果子加入了「太行流动艺术团」,从大理搬到上海朱家角。依然是一种松散的群居生活,大家定时起床、在院子里练习。晚上一起看电影,有人会站起来继续练习,身体与水晶球、武幻、火等道具融为一体。果子结识了同样玩流动艺术的先生。出门时,他们流动到哪,表演到哪。赚点路费,继续上路。今年八月,在先生的老家,内蒙古的草原上,婚礼变成了一场音乐节。果子把这两年积攒下来的钩织作品,布置在草原的各处,场地同时也是一个钩织展。他们租了四十几个蒙古包,最大的蒙古包成为主舞台。在果子钩织的曼达拉下,户外还有一个DJ台。朋友们轮番上阵,鼓队、现场音乐、世界音乐、电子音乐……很多朋友想上台还排不上号。还有流动艺术,果子自己玩了会儿火舞。婚礼仪式在傍晚七点开始,背景是草原的日落。那天天气很好,太阳一点点落到地平线以下,留下金色的晚霞。晚上,烟花散了,大家松松散散地躺在草原上。有人送了果子一个天文望远镜作为新婚礼物,可以看月亮表面。还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这些年来,钩织和流动艺术是果子生命版图里最重要的部分,她来去于不同的风土与温度之间,游牧着的生活方式、在路上遇见的朋友们、属于自然的气息,时刻作用在果子的创作中。毛线、纹样、花色、火把,她在这样的生活中,自由地延续着这些材料的生命力。东妮尔的舞蹈语言、天声的音乐内核和果子的生命材料,传承于自然、民族、传统,又在行走中不断交织、生长,编织出新的生命活力。正如adidas Originals「骤」系列产品将西部游牧部落传统“马毯”上的编织元素巧妙呈现于鞋身之上,创作者在民族性与传统文化的滋养,天地与自然的灵感之间,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游牧文化、对传统元素、自我感受与观念进行新的阐释。adidas Originals 于近期发起项目「万物寻宗」,并推出该项目首季——「骤」系列产品,「骤」围绕西北地区风土人情展开,从传统游牧民的马毯、包包、服饰上传承部落图腾、编织纹样进行创新性的融合,构筑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游牧世界」。Superstar 是品牌的代表鞋款,此次运用了内蒙草原相扑选手的「围领」元素作为创作灵感,来自草原的力量,带你踏入民族与潮流融为一体的「游牧世界」。全系列由中国香港潮流艺术家邓卓越担任策划顾问,以“寻根寻源”为宗旨,力邀邀众多非遗艺术家、匠人参与共同演绎,将不同的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多个产品系列。adidas Originals「万物寻宗」 始终坚信不论如何变化,传统文化中的“根”和华夏民族的“宗” 是永远流淌在人们血液中的因子。年轻创作者对自然与传统的延续,成为寻找身份归属、创作、表达自我乃至存在的新方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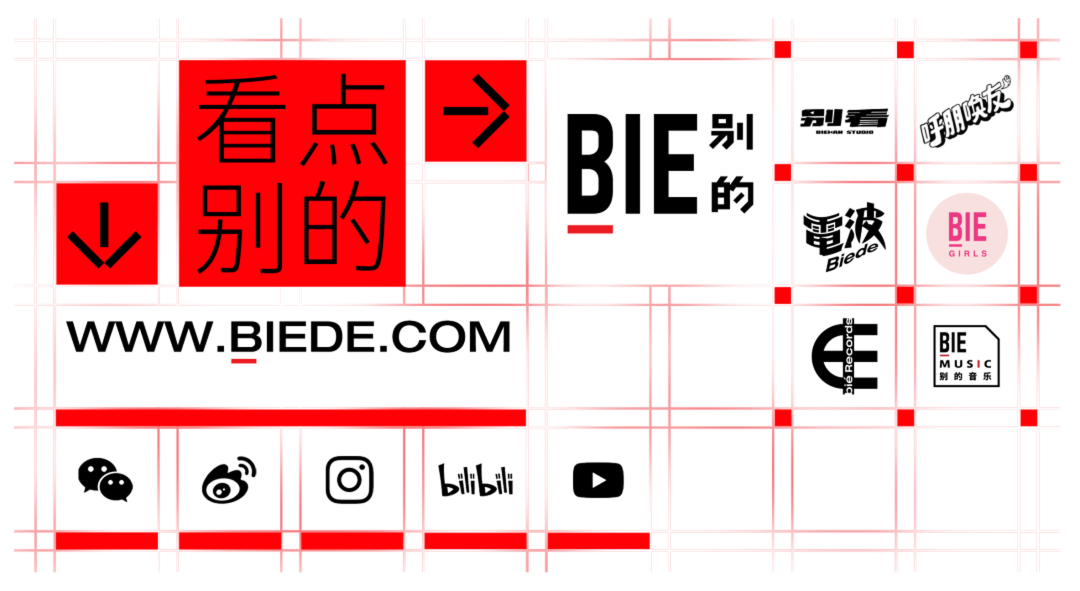
《场域记录II》,贾德逊教堂运动研究(Movement Research at the Judson Church),纽约,2019
东妮尔在新巴尔虎右旗,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