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阿绵
编辑|薇薇子
来源|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
封面来源|由阿绵提供
这是我在云南沙溪古镇定居的第三年。
被形态不同的村庄包围着的沙溪古镇,拥有无限贴近自然的地域环境。尽管这一两年,随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播出,古镇及周围一些村庄的商业化气息愈发地浓厚起来,但无论如何,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沙溪呈现在我眼中始终还是那个无论怎么样也看不腻的小镇。我与朋友于2022年在沙溪古镇周边一个相对更为安静的村庄里长租了一个20年的老院子,院子位于稻田边。23年初我们仍在修缮院子的大框架,而今年已经是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第二年了。 稻田边的小院我们修缮的房屋沿用了当地白族人的木质结构大框架,但又在当地房屋风格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本地的房子大都不喜欢开窗,屋里总是昏暗而阴凉,我们则在每一个空间的墙体都打出了一个个大窗户,为的是每天醒来睁开眼的第一个瞬间都能够见到一望无际的稻田。当然,还有怎么也不看够的云南的云。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到农村这个“旷野”不是没有理由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更加不“内卷”的工作环境,以及越来越多自由选择生活的可能性,让曾经一批又一批从农村挤向城市的趋势,在当下发生了调换——田园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向往。除此之外,这些年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地变得更加流行,身边的年轻人在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与争取这种空间与地理都更自由的工作方式。乡村,成为了更多人的首选。它比起城市里有着更低的生活成本,对如我一样从毕业后就没有上过班的人来说是一种优先选择。但是田园生活就全然如同诗歌一般美好吗?我想,倘若没有风险与代价,城市里的人们或许更早就将这些年网络上常提到的“裸辞”概念付诸行动了吧。
稻田边的小院我们修缮的房屋沿用了当地白族人的木质结构大框架,但又在当地房屋风格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本地的房子大都不喜欢开窗,屋里总是昏暗而阴凉,我们则在每一个空间的墙体都打出了一个个大窗户,为的是每天醒来睁开眼的第一个瞬间都能够见到一望无际的稻田。当然,还有怎么也不看够的云南的云。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到农村这个“旷野”不是没有理由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更加不“内卷”的工作环境,以及越来越多自由选择生活的可能性,让曾经一批又一批从农村挤向城市的趋势,在当下发生了调换——田园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向往。除此之外,这些年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地变得更加流行,身边的年轻人在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与争取这种空间与地理都更自由的工作方式。乡村,成为了更多人的首选。它比起城市里有着更低的生活成本,对如我一样从毕业后就没有上过班的人来说是一种优先选择。但是田园生活就全然如同诗歌一般美好吗?我想,倘若没有风险与代价,城市里的人们或许更早就将这些年网络上常提到的“裸辞”概念付诸行动了吧。
一人公司和田园生活背后的代价
焦虑这个词,伴随着我从南半球间隔年回国后的很多年。打工度假间隔年结束后,我在2019年底回国后的低谷期里开始再度拥有了又一年间隔,只是那一年的间隔,是伴随着我深深的焦虑的。那是刚毕业时的迷茫,对于不想要的似乎是清晰的,而对于自己想要的却又充满了迷茫。像是人走在一团雾里,对于未知的是不敢迈步的,因为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就可能会掉进一片深渊。这些年我不断排除着自己不想要走的路时,想要走的路也愈发清晰起来。同样,这条路走着走着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将我彻底的带到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上。但其实,我也很难在与他人述说的时候给自己贴上“数字游民”或是“自由职业者”的标签。因为“数字”更多时候意味着互联网上的工作,“游民”更多时候意味着旅居的生活状态,而“自由职业者”则更是在很多时候是能够自如地告诉别人“我到底是做什么”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从选择定居在沙溪古镇后,我除了每年会偶尔出门旅行一两趟,其余时间更多是在小院里生活。我的工作模式也变得多样,想社交的时候就去摆摊卖烧烤饮料;在沙溪不同季节生长不同果物的时候就去山里摘果子,例如到了青梅季,我们就跑去朋友家的后山采了几筐青梅拿回家做酒和青梅露,朋友圈随手发一发也会有一些人来买健康有机的在地特产;偶尔会带来到沙溪的客人们体验一些在地的体验项目;线上也会定期给一些客户做life coach教练对话以及交付一些轻咨询......如今的生活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标签集合的边缘切换的状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也算是生生地与焦虑共处了好些年。去年2月份刚结束完小院1.0改造的时候,焦虑几乎成为了我日常情绪的代言词。每天都是不断超出预算的材料费、工人的工钱,因为本地白族人工作的习惯是与城市里非常不同的,他们生活更像是古人的一种慢节奏,“修闲”也是白族人常会挂在嘴边的词,村里的嬢嬢们路过与我打招呼时也常吆喝着我去她们家“修闲”一下。“修闲”的涵义,想必也有一些停下脚步与身边人链接的意味。但对于正在改造的我们而言,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也同样意味着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初来沙溪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积蓄,而在改造期间,朋友所有的时间也都投入在了与工人共同改造中,直至现在,我们在完成了老院大框架的整改后所有剩余的改造都由她亲力亲为的完成。另一方面,改造需要的材料费仍旧如流水源源不断,我们在最紧巴巴时甚至是找朋友借钱来完成改造。那段时间,焦虑充斥了我的生活。生活的两点一线是出租屋和工地,偶尔会在下午出去散步喘口气。焦虑占据了大脑的时候,自然的美景都是无法顺遂入眼的。所谓身在心不在,大抵算是那个阶段的状态吧。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从选择定居在沙溪古镇后,我除了每年会偶尔出门旅行一两趟,其余时间更多是在小院里生活。我的工作模式也变得多样,想社交的时候就去摆摊卖烧烤饮料;在沙溪不同季节生长不同果物的时候就去山里摘果子,例如到了青梅季,我们就跑去朋友家的后山采了几筐青梅拿回家做酒和青梅露,朋友圈随手发一发也会有一些人来买健康有机的在地特产;偶尔会带来到沙溪的客人们体验一些在地的体验项目;线上也会定期给一些客户做life coach教练对话以及交付一些轻咨询......如今的生活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标签集合的边缘切换的状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也算是生生地与焦虑共处了好些年。去年2月份刚结束完小院1.0改造的时候,焦虑几乎成为了我日常情绪的代言词。每天都是不断超出预算的材料费、工人的工钱,因为本地白族人工作的习惯是与城市里非常不同的,他们生活更像是古人的一种慢节奏,“修闲”也是白族人常会挂在嘴边的词,村里的嬢嬢们路过与我打招呼时也常吆喝着我去她们家“修闲”一下。“修闲”的涵义,想必也有一些停下脚步与身边人链接的意味。但对于正在改造的我们而言,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也同样意味着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初来沙溪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积蓄,而在改造期间,朋友所有的时间也都投入在了与工人共同改造中,直至现在,我们在完成了老院大框架的整改后所有剩余的改造都由她亲力亲为的完成。另一方面,改造需要的材料费仍旧如流水源源不断,我们在最紧巴巴时甚至是找朋友借钱来完成改造。那段时间,焦虑充斥了我的生活。生活的两点一线是出租屋和工地,偶尔会在下午出去散步喘口气。焦虑占据了大脑的时候,自然的美景都是无法顺遂入眼的。所谓身在心不在,大抵算是那个阶段的状态吧。 改造出来的小院一角
改造出来的小院一角
改造老院子,听起来很酷,但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监工,第一次买材料,第一次画设计图纸。装修期间,我更多时候是负责后勤的工作,而朋友则现学现卖,每天都在工地看着工人干活,竟然也完全学会了建造房子的技能。现在,我们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由朋友独立完成的,我们都从没学过如何画设计图纸,很多时候都是做完了一天工再完全推翻返工的状态。不常在工地的我,更多时候便会去思索我们的支出与开销。但是对我而言,焦虑其实并不是简单因为要考虑装修经费而产生的。焦虑其实是我从毕业后几年以来常常相伴我左右的情绪状态。一旦进入到只是为自己打工的“一人公司”状态时,所有的一切都要由自己来承担,环境的波动更是对自己有了明显的影响。比如原本摆摊的地方后来摆的人多了城管就勒令禁止了,沙溪在地体验的活动也只在旺季可能会带来一些可观的收入,线上的工作则是需要耐心与自我状态的沉淀才能拥有不断招募客户的状态。如果不是投入在院子的改造中,也仍旧需要为付房租而考虑。因此,但凡选择这样的工作状态,它背后所要我们承担的代价与风险,其实远远高于帮公司打工。在公司随时可能会面临裁员,这些年更是会感知到大环境变动下每个个体的渺小,而在自己给自己打工的过程中,环境随时会将我正在做的事情喊cut,如果不是因为内心足够坚定走在这条迷雾里的路时,意志力也随时可能会崩塌。诗歌一般的田园生活,它是很美好,可是它的背后也是每个个体努力地在面对自己内在课题后的呈现。 我们动手改造后的工作坊
我们动手改造后的工作坊 回到自然里去,也回到自己内心里去
回到自然里去,也回到自己内心里去
我能够写下这篇文章,并且坦然地写下焦虑这个词的时候,多少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些年与焦虑的相处,也逐渐地能够从恐惧它,逃避它,再到如今越发能够与它和谐共处。我还逐渐发现,焦虑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能够给我带来行动的助推力。刚定居在沙溪最大的焦虑是金钱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状态无法支撑自己在这里生存下来,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焦虑,让我“逼着”自己去尝试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担心与恐惧也是常伴随着我的情绪状态。卖特产的时候会担心“是否客人真的会喜欢这样的味道?”,在城管喊停摆摊的时候会恐惧“那接下来能够带给我们经济来源的会是什么?”,夜深人静与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会恐惧“这样的生活如何长久?”最初我也会不自主的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想着那不如还是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吧。可是终究也没有真的投出那一份简历。其实对于从没上过班的我来说,如何制作一份会被公司认可的简历我都不知道。那就只能选择倒逼自己迈出曾经不敢迈出的一步又一步。 陪伴更多伙伴深度体验在地的日常
陪伴更多伙伴深度体验在地的日常
在最初尝试招募完全陌生的伙伴来到我们小院一同共住时,我是怀揣着很多的担心与忧虑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付费的方式来感受我们的生活呢?”“万一他们的体验感不好怎么办?”这些自我质疑的背后,我看到的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许多不认同与不笃定。在面临每个月都需要支付的房租压力下,从2022年的夏天开始,我在互联网上发起了第一次的共住招募。在招募之前,我们会邀请每位伙伴分享一份自我介绍,加之价格的筛选,从第一次来到小院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伙伴,再到如今我们接待了三十多位伙伴,我们几乎与每个曾经认为是远方的陌生人建立了非常深度的链接。或许是因为内在本就真诚的相信着人与人之间最初的距离就是如自然一般纯粹,所有的这些疑虑我也会直接地和来到小院的伙伴们分享,而以最初作为参与者身份的伙伴视角,他们总是能给到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我常常会用“家人”这样的词汇去表述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我一个人孤独地在自己的内在探索轨道上探索了太久,而当同频的人出现时,内心小宇宙的行星仿佛被一夜之间点亮了。每当我收到一些问题关于“纠结着是否尝试一种自己没试过的生活方式”时我都会邀请大家看一看,走出去后可能我们会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但是如果不改变的话,在舒适区的自己又是否真的舒适。 小院常会接待一些来此拜访的伙伴
小院常会接待一些来此拜访的伙伴
这些年来在沙溪生活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摆脱焦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如何与它共处。从一次次被动的接受谋生形式发生变动时,我也一次次被赋予了可以去创造新形式的机会,而对于想要来世界无限体验的自己来说,无疑也算是契合了自己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因此,对于自己在走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只管往前走,走着走着回头望去,发现迷雾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散开来。 2.0版本的小院
2.0版本的小院
现在是我们改造老院子的第二年,2.0的版本即将出现。从1.0水泥地面、堆满柴和杂物的小院,演变成了爬满了各种植物、有着自然气息的空间,一楼有与本地风俗结合的可以在冬季烤火的室外茶室、也有开放给预约制客人体验的面向稻田的手工工作坊、还有在花草簇拥下享用一顿户外晚宴的庭院。回望从院子开始改造的无限期待,再到过程中历经过的重重迷茫与焦虑,以及如今它与我的生命状态竟神奇重叠的平和感,我开始知晓,我们每个人的生长速度本就如同树苗一般,它缓缓地生长,过程中需要雨露也需要土壤,会经历暴风雨的冲刷和营养不良,但它仍旧会一点一点地长大。也不断地印证着这一点,回到自然里去,也回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去。 庭院里的晚餐
庭院里的晚餐
 发现其实人嘛,需要的真的不多
发现其实人嘛,需要的真的不多
随着在这里逐渐扎根,我发现自己的物欲需求不断减少。过去的自己在很多焦虑的时刻,会不自主的选择购物与进食来填补那份情绪积攒在内心的空洞,而当我真正地生活下来的时候,却反而发现其实人嘛,好像需要的真的不多。家门口自己种植的有机蔬果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生活所需,所需要的衣物更是大大减少,更喜欢的方式是偶尔买几件纯白的t恤,去山里摘一些好看的叶子回家做植物染。常常也会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在乡村里生活的日子,感觉钱都花不出去了。”一种更加极简的生活方式。我也看到了,被物质欲望裹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自己所需要的很多很多,但实则我们需要的并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多。
家门口种植的一片有机蔬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想要选择一种叫做“Fire”的提前退休计划,而同样也有很多人正在为了如何凑够养老的钱而困扰。但是在自己亲身体验后来看,提前退休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有时候不是我们需要多少东西来填补我们所认为的未来的空缺,而是我们的未来竟有如此多的可能性,而这个好好生活的当下,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创造着自己最想要的生活。今天的我,彻底适应了“无月薪思维”后,我开始学习的部分是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全然的相信自己与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也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其实不断离开的,绝不仅仅是这条社会主流的轨道,还是社会源源不断灌输给我的那份价值感的定义,即我们要去努力创造财富与成功的地位和事业。而选择离开那套框架体系后,我也正在重新学习去定义我内在认同的价值感,那是即便我选择不去追求所谓的成功,我存在并且创造我内在认同的美好,我也是一个极具价值感的人。做一个玩耍的孩童,孩子的世界没有什么阻碍
这些年,“松弛感”被越来越多的提及,但我们总归无法摆脱焦虑,尤其当我们内心的声音开始出现时,想要去追寻的力量与恐惧的力量会形成一股拉扯,我们在矛盾中焦虑地向前。但焦虑也可以将生活带去不同的方向,其中之一便是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有一些人在离开原有的轨道后会因为焦虑而促发自己更多地创造一些自己尚未尝试过的有趣的事情,这正是能够推动又一波生命力的东西。可能会有许多人在尝试了自由职业的生活后因为过度焦虑选择回到了稳定工作的生活状态中,他也体验了焦虑带来的再度选择。一位朋友Q,因为不想再在大厂里卷,她来到了云南旅居。在不断面临需要寻找崭新轨道里的工作机会时,她常常彻夜难眠。旅居生活几个月后,她还是选择离开了这里,回到了虽然有诸多压力、但能够提供给她足够安全感的一线城市。但她直言,在外尝试旅居的那段日子仍旧给了她很多勇气。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体验可以用“好的”或是“不好的”来定义,每一种体验,都是一种力量。当焦虑不断地出现,我们不断地看见时,创造的过程会变得越来越顺畅,越来越丝滑。最后,玩耍会成为一种赚钱的方式,生活也会变得愈发轻松与简单。在我当下的生活中,每当出现焦虑的情绪时,我会试着让自己去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当然也是因着沙溪这样宽松而美好的环境,让我似乎可以有各种各样选择的可能性,譬如,我会思考着利用小院这样美好的空间来邀请好友举办一次音乐会,借此也能够与更多好玩的朋友们链接;又或者,我们会设想一些既符合我们的理念,又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动来招募更多对我们的想法感兴趣的朋友来参加体验。如此一来,焦虑自然被轻松化解,而我在设计与举办不同活动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在玩耍的孩童。通过创造的过程,也能更快速地回到幼年时呼朋引伴的状态,孩子想要去分享好玩事情的念头是很简单很纯粹的,而成年人亦然。试着做一些转换,玩耍的过程即是创造的过程。沙溪新移民中,许多人也如我一样,经历过最初来到沙溪时的新鲜,再到逐渐感受躺平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份巨大的压力时,开始尝试发现自己身上有故事或是擅长的技能。基于沙溪这样一个比较小范围的在地社交环境,朋友们之间也会以“合作”的形式去输出自己能够带给他人的价值。譬如会在开民宿的朋友家里举办一些分享会,也会和其它的商铺进行合作,邀请更多的游客来体验自己的活动。同样基于沙溪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有一些朋友来到沙溪以后开始研究起了植物染,从自己去山里贴近自然的好奇心,再到自然里采摘各式各样美丽的植物创造衣物并且售卖,或是以体验的形式陪伴来到沙溪的客人们完成一份关于自然的礼物。我们常常笑言,“活在这个时代,活虽然不会活的多好,但是也不会饿死。”再回首时,大家对于迷茫感与焦虑的对话在慢慢地减少,如今在夜晚围着篝火会闲聊的,竟都是如何制作一份美味的菜谱,如何种出更有机的蔬果,以及什么时候再去采摘青梅这样的话题。我想,这是自然生长的魔力,也是不被人为定义后的时间概念,它本就如万物生长规律一般,缓慢平和。这是这三年我定居在沙溪古镇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门课,关于沉下心去看见,看见万物生长,看见世间规律,看见内心起伏,也看见稻田边看似平静如水的生活,实则内在历经万水千山的自己。

你有过“田园生活”的经历吗?你对于“裸辞”有怎样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36氪旗下年轻态公众号
👇🏻 真诚推荐你关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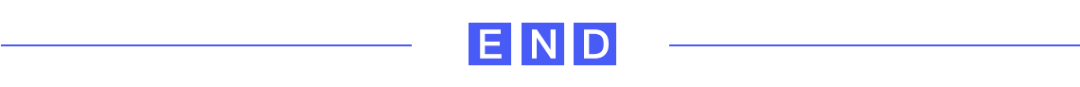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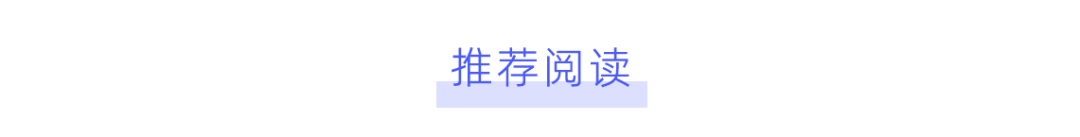

来个“分享、点赞、在看”👇
改造出来的小院一角
回到自然里去,也回到自己内心里去
陪伴更多伙伴深度体验在地的日常
小院常会接待一些来此拜访的伙伴
2.0版本的小院
庭院里的晚餐
发现其实人嘛,需要的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