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末尾,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为读者带来一部《通俗小说》,收入55个短篇。仁科似乎并不拘泥于小说的形式,他笔下的叙述者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以一种轻松、平和的姿态侃侃而谈,有时戏弄一下读者,也偶尔自嘲,讲到起劲的时候,还会爆粗口。
仁科,五条人乐队主唱兼手风琴手和吉他手、词曲创作者。出版社供图。张子豪 摄
然而,这些看似散乱的短篇却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主人公及其生活轨迹:他曾住在广州的城中村,为了生存,卖过盗版书,送过外卖,发过传单,虽然贫穷,依旧有趣,是个电影爱好者,也对吉他感兴趣。跟随他的视角,可以窥见拥挤、肮脏的城中村所暗藏的一些或荒诞或传奇或神秘的人事,而这些或许也只是他的胡思乱想。奇妙的想象、忧伤的梦境也会加入他并不可靠的回忆叙述中,时序错乱,人事逐渐模糊,这正是主人公的日常。

《通俗小说》,作者:仁科,版本:磨铁图书·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
仁科的小说语言简练、直白。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视角,走出出租屋,在城中村游荡,快餐店、烧烤档、破旅馆、发廊和士多店等一一映入眼帘。叙述者仿佛一架摄影机,不动声色地呈现他的生活与环境。可以注意到,小说的叙事经常是通过空间的转换、衔接展开,而小说不多的描写也主要关于空间和物品。这就使得小说语言偏视觉化,像电影般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具象化展开,一目了然。作者是如何将不同文本中的人事和场景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日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虽身处城市的不同角落,却可能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事件。在《地球仪》里,“我”在快餐店吃饭到一半,突然断电了。在《梦幻士多店》里,“我”闯入一个放着电视的空房间,想到电视机之所以没关,“也许跟刚才短暂的停电有关”。无论是《人性的弱点》里的阿兄和科仔,还是《明天太阳会从财富广场升起》里的“我”和小明,都听到士多店正在播放《明天你是否依然喜欢我》。不同小说里的人物通过共享同一事件、同一现象而关联起来。作者笔下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里相互串门,不同的人物也会出入同一个城市空间。作者将这些细节编织进不同的文本,由此把散落的人事和场景联系起来,构造出城中村的日常。有时叙述者还会在主人公的经历之外插入其他人的故事,如在《打兔子》中,即使面包店已消失在小东和小陈的视野里,叙述者依然讲述了面包店的故事。这种由主人公的视角辐射开来的叙述,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常常罗列一些物象,仿佛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都乏善可陈。在《人性的弱点》中,阿兄和科仔走在城中村,小说先是写:“城中村里一股霉味,阿兄和科仔穿过一元店、长话超市、成人用品店、私人诊所、麻辣烫、烧烤档、水果铺、糖水铺、蒙娜丽莎发廊、报刊亭士多店。”无论是城中村,或是家乡的县城景观,再到室内布置,作者用一系列的物象呈现客观环境。接下来,作者沿着阿兄和科仔的视角观察城中村。在同一段落的末尾,作者又写:“阿兄继续带着科仔穿过人群嘈杂的街道。每家店铺摆放的货品都溢了出来,占了半条街,使得原本窄小的街道更加窄小,一元店挨着糖水铺,士多店门口放着一个关东煮,成人用品店粘着私人诊所,麻辣烫隔壁是烧烤档,烧烤档过去是水果摊,过了报刊亭就是十元店。”作者再次介绍了城中村街道的布局,在重复中又有变化,而这一次是融入了过路人的视角。段落开头的叙述,仅呈现空间的物理存在,而街道的拥挤则是从过路人的体验而言。作者惯于用节制、简约的笔法勾勒人物的生活及其生活环境,使其显现为司空见惯。在工地罢工时,小东和小陈无聊到买兔子来“打猎”,现实的“沉重”就此卸下。但结尾处的两声枪响,又好似声音蒙太奇,暗示着某种不幸。对于底层生活,作者不渲染苦难,不表达同情,也不赋予意义,以“轻”的姿态介入其中。另外,作者还喜欢运用不同的视角、逻辑看生活,偶尔会经由主人公的梦境和“胡思乱想”制造一些童趣、浪漫和诗意。在某一刻,阳光从云层的裂缝射下,“我”看着阿珍,阿珍看着“我”,爱情正在发生;落魄的许昌龙在湖边洗脸,却望见对岸有人骑着一匹马走过。正像那条冰冻的巴浪鱼最后一次飞跃,“去到了别的巴浪鱼所到达不了的高度”,作者的想象力有时让日常别有趣味。卡尔维诺说“轻”需要一种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此时的“巴浪鱼”正是接近于轻的形象。然而,就像生活对爱情的嘲讽,文身师在刺繁体“爱”字时,故意少刺一撇;年轻的小伙子喝多了躺在路边,却被误判为杀人犯,出狱后已是地中海大叔,生活不是电影。整体而言,巴浪鱼只能享受一秒的自由,终究是“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化用五条人乐队的歌名,仁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半靠表演,一半真情流露”。此处所谓“表演”,指作者在创作时的一些匠心。仁科的写作,看似率真,几乎不假思索,但在一些细节处仍能捕捉到作者的“表演”。在《梦幻士多店》这篇略带神秘色彩的小说里,叙述者“我”打开士多店内隐藏的门把手,走进一个粉红色的世界。从士多店的陈设到隐秘房间的布置,以及“我”如何跟随一位少女走进她的出租屋,一路的所见所闻在作者笔下具体、细致地展开。如此具象化地呈现人物的所见所闻,给读者一种如同亲历般的真实感。然而,在小说的最后,我再次走进士多店,将门打开,隐秘房间内只剩“墙上一个金属的塑料钟”,小姐们和女明星的海报全都消失了。一切如梦似幻,仿佛“我”此前的经历只是个人的想象。那少了一包的泡椒凤爪,却像是烂柯人手中腐烂的斧柄。此时,这种具体到“泡椒凤爪、酒鬼花生、香辣鱼干”的叙述,其“别有用心”方才突显。有时作者会营造叙事的圈套。在《火影忍者和蜘蛛侠在街上派传单》中,蜘蛛侠告诉“我”,士多店那边来了一个大美女销售员。“我”因为老被蜘蛛侠骗,不太相信他的话。果不其然,士多店新来的售货员并不是大美女,但称得上是个小美女。此时,谎言已经落实,读者的戒心也随之放下,天真地进入了“我”的故事之中。直到小说最后,“我”才点明所谓“小美女”以及和“小美女”的对话也不过是我的构想,士多店坐了一个大妈。蜘蛛侠骗了“我”,而“我”也骗了读者。作者还擅长以看似多余的笔触去贴近生活。在《红城快车》这篇小说中,当回忆贝雕厂时,叙述者“我”提到,“没有招牌,没有LOGO,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至于县城里头的哪个酒吧,“我”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叫“蓝月亮”还是“超越”。这种对“没有”或是“遗忘”的强调,对情节的推进不起作用,看似很多余,但我们日常的记忆正是如此。在仁科的小说中,我们总是可以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场景。有时他通过戏仿电影情节,解构浪漫和传奇。《文身店的爱恨情仇》初看颇有王家卫的风格,但不可以乱来的爱情被乱来了。电影爱好者“我”在城中村的桑拿城,想象电影里的杀手一丝不挂地走进淋浴室。有时小说里的叙述者会跳出故事的通常逻辑:女友阿珍给“我”留下一张写满诅咒的字条,“我”却在意“她的书写逻辑混乱,还有错别字”;杀人犯走进沙县小吃要了一笼蒸饺和一碗拌面,吃完后付钱走人;因为一点无聊的口角,古惑仔一刀捅死了一名歌手。或许在仁科看来,这些反逻辑的“意料之外”,正是生活。正像演员打破“第四堵墙”, 叙述者偶尔也会告诉读者自己正在“表演”。在《老鼠和啤酒妹》《情书》和《鬼故事、八哥鸟、索菲娅,还有一条蛇》等篇目中,叙述者都在故意暴露小说的虚构性。这种元叙事策略并不新奇,但仁科似乎是以游戏的心态玩转“元叙事”,而非试图让小说通向某种意义。这些表演性的叙事策略,让仁科的小说多了一些趣味,尽显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和想象,与此同时,那些“真情流露”的部分更能触发读者的感知体验。在《烩面和蟑螂》这篇小说中,“我”和阿孙骑了很远,骑到晚上,就为了吃一碗他推荐的河南烩面。作者写道,当发现碗里有一只蟑螂,“如果是平时,我会让老板给我换一碗,或者退钱。但那天,我只是把那只蟑螂夹出来放一边,什么都没说。”这个微小的行为,不动声色地传达出我对阿孙的友谊。总体而言,这部小说集与其说是通俗,不如说是“轻”。不知是否受到卡尔维诺影响,仁科的小说,无论是在语言、结构、内容和情感上,都在消除重量。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对“轻”的探索,以“轻”的姿态观察现实,认识生活。或者以轻的方式面对生活之重,正是仁科的生活态度。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何明敏;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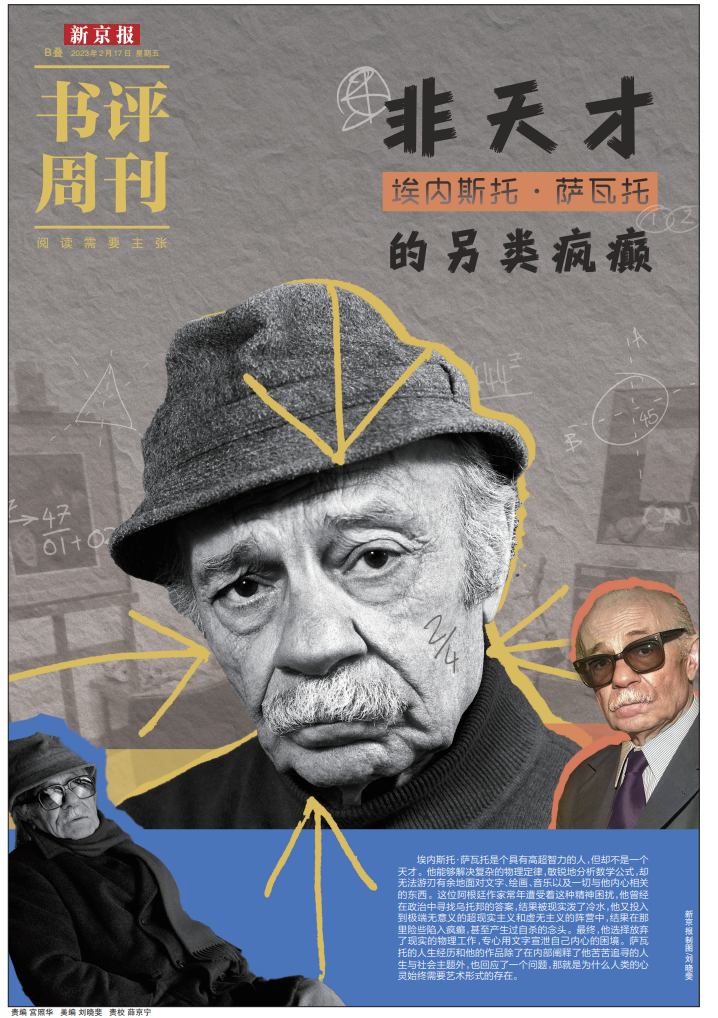 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17日专题
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17日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