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计兵(53岁,外卖员)
杨丽萍,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
自2020年初开始,深入外卖站点,
调研了全国100多位外卖员,
采访纪录超过一百万字,
并写成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中国现在有700万名外卖员,
两年的跟踪随访中,
杨丽萍看到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出身贫困的小夫妻,
靠送外卖,跑出了城市里的两套房;
坚韧隐忍的女外卖员,
为了给孩子攒医药费、上学钱,
跑单量超过站点里的200多位小哥;
热爱写诗的中年男人,送外卖积累创作素材,
他笔下的外卖员们诗意又浪漫:
“一个外卖小哥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条联系到杨丽萍,
责编:倪楚娇

接下这个选题是2020年的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的第五天。当时广州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我们家视野很空旷,往下看街道空空荡荡,人都封在家里,能够看到的就是穿着蓝色、黄色工装的外卖员。于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一直到2022年的二月份,我的书稿才全部完成,采访了浙江、广东、北京、湖北、江西等地的100多位外卖员。

路口等红灯的外卖员们 摄影:丝绒陨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摄影师,所以特意选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当外卖员,一边送餐,一边去大学听课,赚到钱了,就去买昂贵的摄影设备。
刘海燕
40岁左右,来自黑龙江
“520”那天,她送了一天的玫瑰花,但一点也不嫉妒收到玫瑰的人,她更喜欢老公送的礼物——一辆座椅宽大的新电动车。楚学宝
32岁,来自安徽蒙城
他一直记得一句电影的台词:“穷就是你的错。”小时候上学,他没有书包,拎的是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一直等到初二辍学了,都没盼来书包。所以他那么搏命,搏命到一天跑七八十单,累得连饭都吃不下,犯恶心,只能喝水。李伟
41岁,来自上海
他是上海土著,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前在事业单位上了六年班,后来选择离开。抱着要做管理岗的想法开始送外卖,两个半月就成了“明星骑手”,四个月成小队长,第二年当了站长,现在是上海城市经理。阿龙
33岁,来自江西南昌
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被判断是一级智力残疾,30岁才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送外卖。有人听说了他的故事,要给他捐钱,他都拒绝了:“要你们的(钱),那还要我干什么。”小于
31岁,来自河北衡水
他说,送了两个月外卖,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有一次客人地址写错了,他好心提醒,对方说:“你是不是想跟我要钱。”从那出来之后,他一个人在马路伢子边自我疗伤疗了好久。
胡超超
30岁,来自河南光山
河南人喜欢抱团,胡超超一个人做外卖,最后把全村的人都带过来了,让他们赶快来赚钱。他们不是亲戚就是发小,都住在一起。送外卖时互相帮衬,没事就聚在一起煮饭、聊天、打牌。匿名
来自杭州
他是一个拆二代,因为想要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就当起了外卖员,一到暴雨恶劣天气,其他外卖员都不想出去,他就会出来跑单。但当平台有补贴,大家都希望多跑的时候,他就会让给别人去跑。王建生
41岁,来自四川达县
左腿萎缩,从家乡出来后流浪了十几年,当过乞丐,捡过垃圾,最后在杭州成为外卖员。
在他眼里,商家和顾客愿意把餐食交给自己,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天冷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冲锋衣内胆脱下来,把餐盒包起来,怕它凉了。他说,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邹小容
47岁,来自重庆
儿子患了尿毒症,她跑了5年外卖,骑行13万公里,最终赚了30万,给儿子换了肾。

马路上随处可见飞驰的外卖员
赵盈盈
22岁,来自河南周口
妹妹患了白血病,她放弃了考研,当外卖员给妹妹赚医药费。她给妹妹讲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鼓励她要振作起来。王涛
34岁,来自湖北黄冈
一家四口住月租金500元的房子,给孩子报了4300元的英语培训班。黄远义
35岁,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
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一家人要在一起。老婆和女儿在老家留守,他每到腊月二十二准时回家过年。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他回老家待了三个月伺候月子。2021年,老婆和孩子执意来到杭州,黄远义就会早点下班,回家陪她们。李帮勇
42岁,来自云南昭通
单亲爸爸,出过事故,右手被绞进机器里残了。为了养活女儿,2018年当了骑手,送外卖的时候都要带着女儿。宋家三兄弟
来自安徽砀山
三兄弟同住2100元的宿舍,把钥匙放在门缝里,谁回家谁取。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开个饭店。
……
过去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外卖是一个简单机械的工作,门槛比较低,只是一个求生的手段。
但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其实寄托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我最早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最艰难的采访。因为外卖这行业和别的不一样,他的收入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人有时候挺烦的,没完没了地纠缠他们。我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跑单的高峰时期一般是上午的10:45到中午的13:45,晚上的5:00到7:30。我都会避开这个时间段,宁可多跑两趟,也不要让他们太辛苦。如果采访的时间长了,我也会支付他们一些“误工费”。

有时候我是守在大街上,或者蹲守在大商圈,跟等着接单的外卖员搭讪。或者在下雨天点份外卖,等外卖员送到了,趁他等电梯的间歇,随便跟他聊几句雨天送外卖的感受。也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愿意帮助你。外卖员说是每天在跟人打交道,但是没有人真的了解他们。他们把餐递过去,说“祝你用餐愉快”,对方接了,门“砰”地一声就关掉了。有的说“你挂在门口,不要打我的电话”,人都看不到。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出现,愿意倾听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也有这种需要。

▲
李帮勇,杨丽萍的采访对象。
每采访一位外卖员,我都想读得透一些,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有时候我会租辆电动车,从早晨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跟踪他们取餐送餐。只要能接触到他的家人、亲友和同事,我都是不遗余力地去采访。哪怕只是在电话中听他们讲一两句话,感受一下语气、语调都好。如果足够幸运,能够获取外卖员的信任,他们就会把家门向你打开。因为他们住得不是太好,家里也没有人打理,很多人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他们不愿意展示这一面。宋北京是为数不多邀请我去家里的。他们三兄弟都在杭州送外卖,住的是群租房里的一个房间。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缝里,这三兄弟谁回来谁拿。也不是从单元楼的大门进去的,是从阳台的门进去的。那个出租屋已经被隔得看不出原来几室几厅了,他们的房间最大,每个月租金2100元。房间里都是男人的味道,特别乱,地上乱七八糟放着外卖箱、电饭煲、啤酒箱,床头柜上堆满了保温杯、剃须刀、挂面,茶几上有没洗的碗筷和酒杯,到处都是杂物,坐都没地方坐。

▲
我正采访的时候,老大宋远行和老二宋远杰回来了。他们俩进门就开始做饭,两个人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特别好。哥俩特别有意思,个头差不多,都穿着饿了么的短袖T恤,一个后背上写着“知道网商银行了么,很多饿了么小店靠它开新店。”另一个是“困了么,上饿了么点咖啡下午茶。”像这些内容,我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是很得意的,全部来自于贴身的观察。如果他们不信任你,这种生活的场景你看不到。

▲
外卖员也是可以升职的,但是多数人其实没有升迁的想法,更在意赚了多少钱。勤快的外卖员,跑外卖收入可能一个月一万多,甚至达到两万。比如我采访的“牛人老曹”,他白天在写字楼做专星送,晚上跑饿了么,每个月至少赚1.5万,已经买了两套房,买咖啡的白领都不见得比他赚得多。
我很多采访都是选在星巴克,有的外卖员看到服务员递过来的小票,说这么贵。但是老曹就不一样,他是主动选择了星巴克,自己就把点单什么的搞定了。我特别喜欢他和我说的这句话:“有人问我,你送外卖不感觉丢人吗?我说我送外卖怎么了,我又没偷人家、抢人家、坑人家的,我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丢人?我现在送外卖,不说别的,我屁股下面两套房了。”我这一段文字全部整理自录音,没有一个字的修改,那种对自己处境的满意和得意,每次跟别人重复他这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扬眉吐气。

外卖员宋北京,身上带着送外卖的必需品:
口罩、墨镜、手机、充电宝、金嗓子喉宝
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别的梦想和爱好。比如在横店就有一些横漂,平时是群演,兼职送外卖。也有脱口秀演员兼职送外卖,把送外卖的经历编成段子。“外卖诗人”王计兵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他是开杂货店的,隔壁就是一个外卖的站点。他有天过去凑热闹说这个东西怎么弄,人家就帮他注册了一个。注册完他不小心一点,一个单就冒出来了,别人告诉他如果不跑就要罚钱,然后他就去跑了。
他一开始也没把这当正事儿,就是觉得整天守着杂货店有点无聊,出来跑跑挺开心的,还有钱赚。
同时王计兵是一个非常痴迷写作的人,原来写过小说,也写过诗,但没有发表。跑外卖的过程中,他相当于有了更多的生活体验。那些偏僻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人接,他就去跑,他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有助于自己写诗。有一天突然下暴雨,他正好手里没单,到桥下避雨,看到有一位饿了么小哥冒着雨骑行,他就写了一首诗:《阵雨突袭》 王计兵
一个外卖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马赛克
而雨水是徒劳的
蓝色的工装越湿
天空就越明亮
澄明的天空贴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贴在大地起伏的山脉上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和我并肩骑行
让我感觉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王计兵做外卖以后,他的诗才开始发表。现在他已经53岁了,还在送外卖,每天坚持干12个小时。
他有一句话也是非常打动我,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但做外卖就不一样,哪怕客人只把门开一条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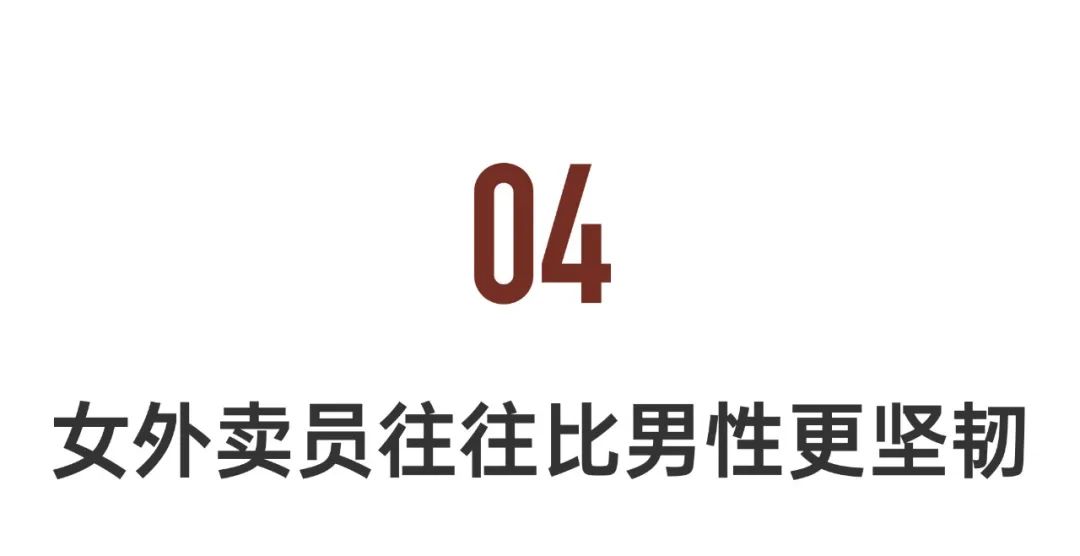
整个外卖群体里,女外卖员只占到10%左右,我对她们天然会有特别的关注。出来做外卖员的女性,很多家里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天津和山东的两位母亲,她们的孩子得了恶性肿瘤,为给孩子治病选择了做外卖。也有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我采访过一位女外卖员,丈夫出了车祸,原来是开鲜花店的,生意不景气,儿子中考报错志愿,进了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几万元。为了供孩子读书,她改做了外卖。还有人是看中了送外卖时间灵活。为了方便接送读小学的孩子,辞了职,利用小孩上学的时间去送外卖。

上海封控期间,一位正在送货的女外卖员
我印象很深的是深圳的一个外卖员刘海燕,她以前是养猪的,后来碰到猪瘟,猪全死了,欠了几十万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深圳赚钱。我采访她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来投奔她的小姑娘良菊。良菊是四川的一位瑜伽教练,疫情之后练瑜伽的人少了,她正好看到刘海燕的视频号,就想跟着她送外卖。刘海燕的站点里两三百个外卖员,加上良菊只有5个女性。站点没有女生宿舍,女外卖员只能自己租房子。她们也很照顾彼此,良菊在城中村里迷路了,打电话给刘海燕求助,刘海燕就赶过去接她,晚上还带她回自己家吃饭。如果遇到大型小区,有好几个门的,她会利用休息时间,把里边全跑一遍,然后制作一个小区地图出来,发在站点的群里,供大家使用。你会发现,这些女性外卖员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吃苦耐劳。刘海燕的业绩在整个站点都是前十的。我采访的有那么两三个女外卖员,她们的丈夫也在做外卖,都跑不过她们。她们很少抱怨,对外卖这个工作心存感恩,因为这份工作切实地解决了她们的困境,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处境。

我采访的外卖小哥中,除非是在做外卖前已经结婚了,如果想在送外卖的时候找个女朋友,成个家,非常不容易。
他们虽然收入不少,但是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我听说过一种说法:“两种人不能嫁,一是泥瓦匠,二是快递(外卖)小哥。”
疫情后,服务行业有20%的人流到外卖业做外卖了。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也会进入到外卖行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学历也逐渐走高,大学生整体占比接近二成。
外卖员李帮勇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感觉到外卖员明显变多,饭点的时候商场里都是在那等餐的。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单少了,提成也在减少。一箱啤酒扛到八九层楼,原来有补贴,现在也没了,配送范围从3.5公里扩大到4.5公里。李帮勇的月收入从五六千元降至四千多元,接下来也许会更少。

摄影:李颀拯
与此同时,外卖员整体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了,一代比一代强,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是超过我们这代人的。之前有一个调查,只有27%的外卖员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有小哥说:“送外卖让我变得越来越自卑。”外卖员的准入门槛不高,但不是谁都可以收入过万。我接触了很多“单王”,他们的智商或情商都是非常高的。同时这些人又非常善良,比如黄远义,放在平时分秒必争,但如果有人跟他问路,他都很耐心地停下来,指点清楚了,然后才往前走。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小孩从高空中落下来,外卖员伸出手把他接住;有人落水, 外卖员跳到河里把他救出来;煤气罐要爆炸了,外卖员冲上去……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路边休息的外卖小哥 摄影:丝绒陨
哪怕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群有担当的人。我了解到一个数字,疫情期间,一个外卖员的出行,可以让25个家庭不必冒风险走出家门。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赵彬看到空荡荡的城市,他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另一个外卖员王涛,他原来是一个施工队的头头,因为事故赔光了身家,只能来送外卖。自己都很惨了,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跑了800多单。不管城市接不接纳他们,他们对所在的城市都有很深的感情和责任感。所以这个群体,我越是深入采访他们,对他们越是尊重。不论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可以说是站着做人。也希望更多人理解他们,对他们多一份尊重,少一些不必要的差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