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书单“不要对年老的困境一无所知”(👈 点击阅读)的评论区,最前排的评论不是关于年老的担忧,而是运用相同的句式,呼喊“不要对年轻的困惑熟视无睹”。也许不止于困惑,如今的社会生活,抛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个实在的问题。失业率、加班时间、不平等一同增长,卷和躺之间,有什么看不见的门槛和把戏?现代性持续变异的过程中,我们怎样保持生存,也保持内心的完整?宏大叙事留下裂痕,精神政治步步紧逼,我们在哪里找到自己的空间和伙伴?以及,是要先“找找自己的原因”,还是找找社会的缝隙?今天我们分享 8 本直接或间接关于青年危机的研究、理论与纪实书籍。希望我们借由这些发现,能够更好地定位与理解身处的漩涡,至少不要过盲目顺从、任人宰割的生活。0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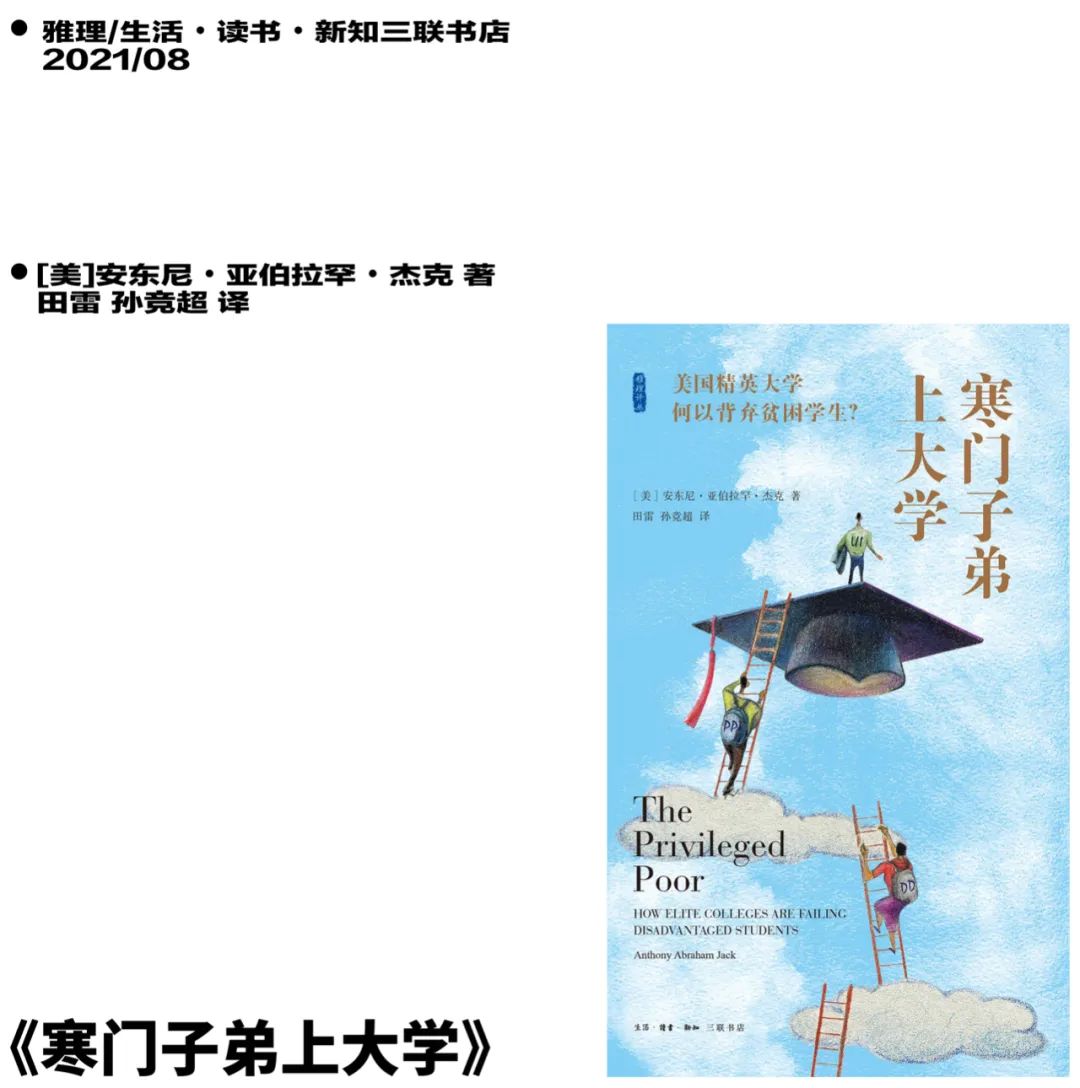
谁更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是精英的后代,还是出身寒门的学子?
人们乐于想象,一旦进入精英大学,学生的出身不再是阶级晋升的阻碍,反而是他们无畏竞争的动力。但作者在美国一所顶尖大学对数百名阶级、种族与机遇不同的本科生访谈后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冲出贫穷与暴力肆虐的街区,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由有钱人的习性主导的精英堡垒。一些隐性的课程,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令人无措的,甚至是羞耻的:寒门学子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习于与教授“拉关系”,认为自己“有资格”占用上位者的时间,或者表达对某个 B+ 成绩的不满——这些看似有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能力,往往比刻苦学习回报更多。
高等教育学常引用的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里这样概括我们面临的习性困境:“人们总是将被支配的那些品质与诸如顺从、谦逊、谨慎、拒绝荣誉、正直之类的德行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德行能够让人们接受更低的位置,而又不至于因为过度投入却收获甚微而愤恨不平。”
是你们自己固步自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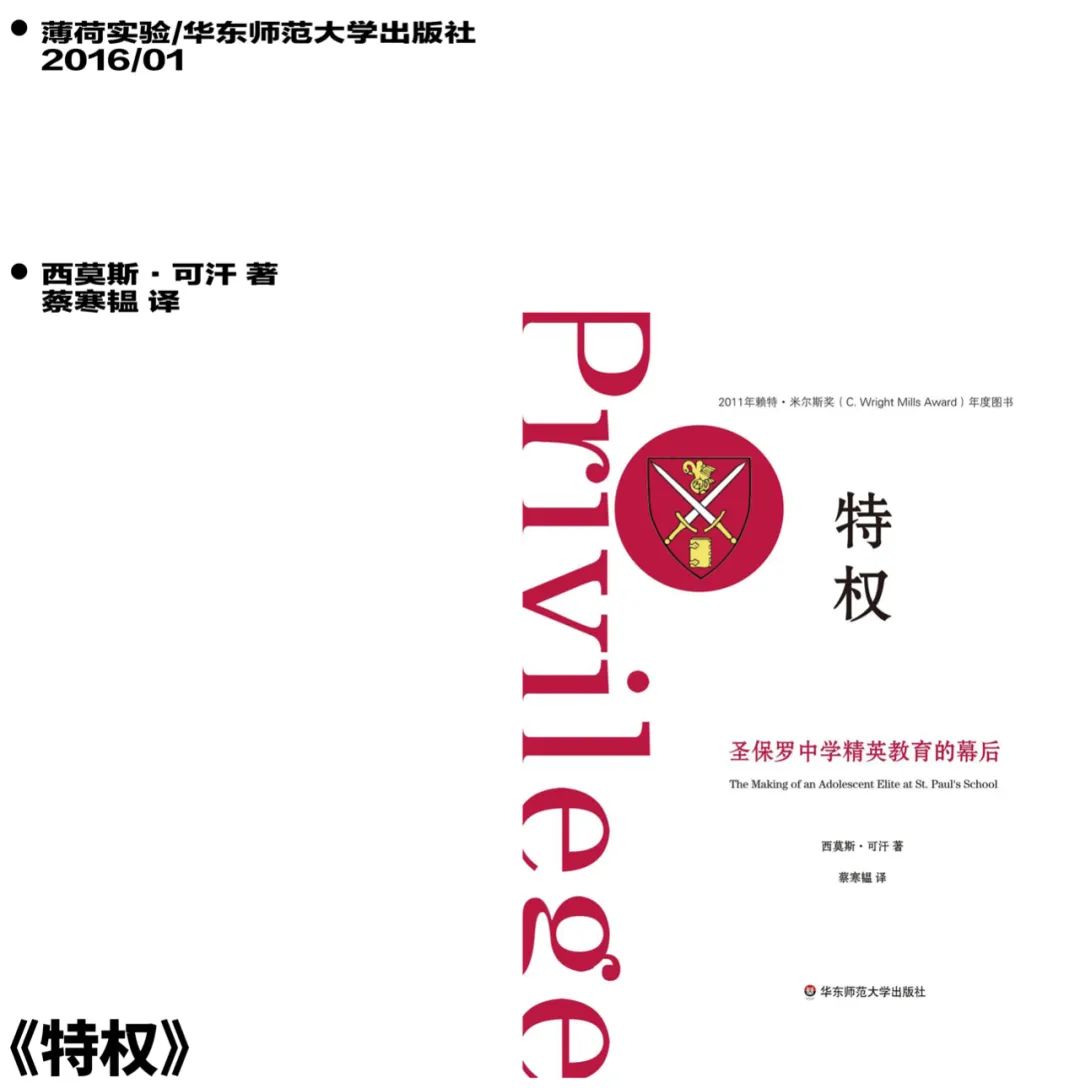
为什么我们仿佛有很多选择,但每一个选择都令人望而生畏?或者像《特权》的作者宏观地提问,为什么世界在变得开放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不平等?旧精英本来用于区分人群的文化,柏拉图、古典音乐、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在信息自由的时代已经成为开放获取的知识——甚至已经是“不酷”的知识了。作者发现,即便是在圣保罗这样的精英中学,高雅不再受到追捧,“淡定”才是新的特权标识。新精英拉小提琴,也听说唱音乐;买套头衫,也能舒适地出席正装晚宴。他们不再圈地文化,而是累积经验。这是特权合理化自身的新把戏:“你们固步自封,你们自己选择不利用这个新的开放世界的优势。”在这个开放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力等待着实现——这样拒绝普通的世界观并不止步于精英高中。一个个选择背后,开放的不仅是成为赢者的自由,还有“淡定”无能、成为淘汰者的不安。03
三十五岁退休的恐惧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蓬勃发展之后,生活品质普遍提升,经济下行才初露端倪。但是饱食者并不幸福。作者访问了三类人群,包括陷入贷款漩涡的人,与电脑打交道的人,和患上过食呕吐症的人。他发现,社会转型的代价,普遍发生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钱是最通用的货币,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人也视储蓄为单一的目标,因为“一个人从根本上赖以生存的最终手段——技术、技能、知识、判断能力,也许一夜之间就会被彻底推翻”。三十五岁退休的恐惧,早早地出现在书中人的口中(连数字都一样),因为“所有人都要不停吸收最新的信息和知识,掌握最新软件的技术,否则马上就会被时代淘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年轻人:一对曾经认为“应该呵护有先天疾病的生命”的情侣,工作后一致同意“要是我生出来一个那样的孩子,我才不要呢”。患上过食呕吐症的江津子,对作者反思起自己缺乏的“人类观”:“现在回过头来,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一心只想着出人头地,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我都没有学到这点……”年轻人的新名字,往往出现在经济下行的年代。在“全职儿女”与“三和大神”之前,还有一种生存模式,叫做“蚁族”。2009 年,《蚁族》让唐家岭村成为北京最出名的村庄之一。“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有基本一样的情况,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大学生本来是大城市产业膨胀的必需品,但大学扩招和全球经济危机一同改变了雇佣的供需关系。唐家岭村离大学都不远,交通方便,生活成本低廉。这些手握高文凭的劳动力于是暂时租住在村中的一方小屋里,一个月投四百份简历,期盼新工作的工资足以让他们离开这个暂住地。随着新的城市规划,唐家岭早已部分变为中关村森林公园,村民们将俯瞰公园的回迁房租给向中关村涌来的互联网新秀。退无可退的年轻人,都去了哪里?在回家考公、换地方打工和更为刺目的例子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安全网存在?05
人类在打工,机器在学习
这本书有个令人莞尔的副标题,“996 正在毁掉美国梦”。显然,美国与中国分享着同一个语境,即工作时间与不平等指标正在一同上升。作者追溯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工人运动与企业文化的变迁,提出了一个残忍的问题:为什么,作为一种文化,我们热爱工作,却讨厌工作者?对 AI 的恐惧,也反映出我们对自身工作的失控。其实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动化因为替代了肮脏又危险的工作,受到工人的欢迎。而今天的自动化,是在过度工作成为新道德、生产力提升消除了工作岗位、青年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下发生的。不会叠衣服,只会完成困难工作的 AI,正在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低薪工作:执行、审核、陪它学习。在书的最后,作者讲了一个他当码头工人时获得的启发,一种集体时间意识的伦理。别的码头工人教导他,放轻松,慢慢来,别当一个傻瓜。美国正在发生的 Quiet Quiting(安静离职,即只完成不多也不少的工作)与我们常说的“摸鱼”,是否又在类似的语境里,成为重新掌控自己时间的实践?06
其实,你在为了自己工作?

《过劳悲歌》:20 世纪中期,工厂的工人要求更多有回报和有意义的工作。但结果刚好相反,他们只得到了一种鼓吹意义的管理文化,这其实是实践中的一种新剥削方式。《精神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工人塑造成企业主。被他人剥削的工人阶级因此并非由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由新自由主义消除的。如今,每个人都是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就连阶级斗争都变成了与自我进行的内部斗争。07
宏大叙事稀缺症

什么样的人可以“否定”?在什么样的空间里,我们可以远离有毒的工作文化、进步主义的精神政治?《精神政治学》指出了两个方向:“游戏”和“痴言痴语”。如果我们将游戏者理解为摆脱效率的人,将痴言痴语者理解为不被灌输信息的人,也许可以理解各类游戏、游戏化的网络文学,各类“发疯文学”、发疯式的梗与黑话在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在这个意义上,二次元文化集合了“游戏”和“痴言痴语”的元素,成为《编码新世界》作者所言“二次元存在主义”的土壤:人们游牧在一个个游戏、动漫、网络文学与同人创作的平行世界里,一次次选择笃信某个世界的价值和仪式,即便了解没有什么是“唯一正确的”。“宏大叙事不是崩解了,而是从出生起就从未存在过;网络世界不是任何虚拟之物,而是他们确实生存于其中,表达观点、结交朋友的真实空间……对这一切,他们的前代人无法给出任何有益的经验指导。”08
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二手时间》不是一本直接关于青年问题的书,却是一本关于代际与遗忘的书。成长于九十年代的俄罗斯青年阿丽莎,在火车上与作者相遇。“我完全没有什么恐怖记忆……我只记得,那个世界是天真的,非常幼稚可笑。”她不理会母亲曾对新时代怀抱的理想,不相信因诗歌两眼放光的日子,对历史完全没有兴趣。“幸福?幸福是什么?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的孤独者都是成功人士,是幸福的人,而不是软弱者或失败者。”关于阿丽莎的章节叫做: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在二十世纪往后的大街上,作者听见许多类似的孤独之声:——爸爸,你怎么没有在九十年代发大财,那时候发财不是很容易吗?正如“宏大叙事不是崩解了,而是从出生起就从未存在过”,与历史的失联、与上一代经验的失联也造就了我们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如果不能像阿丽莎那样拥抱孤独,那么我们只能在这些遗忘、把戏、陷阱、精神政治之中,寻找自己否定性的存在主义。编辑: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