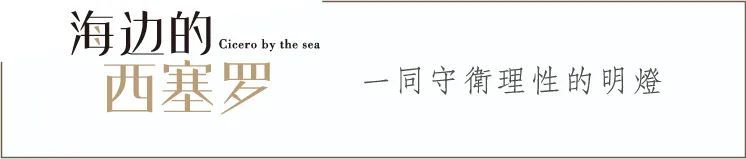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最近总有朋友让我聊聊南洋迷笛音乐节上发生的事情,行,今天就简单聊聊。
当地“不告而拿”的老乡们肯定觉得摇滚音乐节是个新鲜玩意。为什么要搞摇滚音乐节?说起来,摇滚音乐节这玩意儿,算是正宗的美国“公路文化”的产物。
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签了个法案,鼓励全美公路建设,美国随后迎来了他们的“大基建时代”,再加上美国汽车业战后大兴盛,由此就促成了美国非常特殊的“公路文化”——有钱有闲的美国城市青年们开上私家车、或者跨个摩托,也不为去什么目的地,就是为了去远方而去远方。
想理解那一代美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你可以看杰克·凯鲁亚克那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在路上》。他生动描绘了那个年头美国青年抛下“眼前的苟且”为流浪而流浪的那种“现代游牧民”生活。或者更通用的总结,也就是嬉皮士生活。而既然已经去远方了,那不妨就在终点附加一些“诗和意义”,于是摇滚音乐节这玩意儿也就应运而生。于是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摇滚音乐节一般都不开在大城市的中心区,而会选一些相对偏远的小城甚至小镇,比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明明就在纽约州,腕儿也足够,但就是非要找个荒僻小镇去开。原因就是那个——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就是想找个地方兜兜风,唱唱歌,在旷野上支个帐篷,这对他们来说才是远方。你看这些年的形势——前些年我国也经历了一大轮公路、铁路基础建设。最近两三年,乘着新能源的东风,中国汽车产业又迎来了一轮暴增,今年汽车出口量都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了。再加上疫情三年终于迎来了开放。再看今年年初,名不见经传的淄博突然一下子因为烧烤火了,年轻人突然时兴起“特种兵旅游”……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属于中国的“公路文化”可能也“在路上”了。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当下的中国一批大中城市年轻人,产生了“为了去远方而去远方”的冲动。一句话,当代中国,有一部分人生活品质确实到哪儿了,国家基建也允许,这东西自然会产生。这个时候,三四线小城抓住时机办个“摇滚音乐节”,弄不好就真能混成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这是机遇。可是当地领导的眼光跟上了,当地群众的意识却未必能跟上。你看南阳这次就是,音乐节还没开完,就传出了迷笛音乐节大量物品失窃,去过节的年轻人被当地乡亲偷的“只剩下内裤”的新闻。据说当地政府调派大量警力到现场维护秩序都没有用,因为有些老乡是呼亲唤友的组团去偷的,赌的就是一个法不责众。还有视频拍下现场某位乡亲大妈,公然就在宿营区翻人家的东西,被拍下来了还理直气壮,说这都是“你们不要的”。此情此景,当然引发全国舆论哗然,《潜伏》里的吴局长说“本来想露脸,结果把屁股漏出来了。”此言得之。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我看到有人又开始地域黑,说“河南人就是xxxx”……还有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评论的,什么“山海关南下了”之类的。但我们要对自己诚实,让我们抛弃地域黑,承认这种对外地人“不告而拿”的习俗,其实不为时或地所异,曾是一种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的“民俗”。一位武汉的大学生姑娘告别城市,回乡到某地创业,上千亩田地用来种南瓜。本来跟音乐节一样,也是个挺好的创意吧?先是附近一个村民偷偷在她的瓜田里偷摘了几个瓜,发现她种的有机南瓜口味不错,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村民,尤其是老人,纷纷都来了。发展到最后,居然有人开着三蹦子,直接到她家田里去运瓜。姑娘抓住了,他们理直气壮,说都“都拿,凭什么只抓我?”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跟这次南阳音乐节的事儿有点迷之相似?都一样的。再往前找,会发现这几年城里或在城市读书的年轻人到农村投资创业,遭遇类似的情况简直不要太常见。很多人就是这么被当地乡亲“捡”破产的。你问都2023年了,怎么还有人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人私有财产呢?其实你并没有想过,“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在咱中国是个新鲜玩意儿,在现代法制铺开前、皇权又不下县的几千年中,中国基层农村人们的财产观,遵循是另外一种逻辑,它叫“村社共识”。费孝通先生曾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谈到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写过一段无比深刻的话:“在这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村民们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说的简单些,也就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农村,一个人或家庭到底拥有多少财产,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它要取决于这个村社当中其他人的共同观点——左邻右舍、乡里乡亲,都认定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东西才是你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东西不是你的,那它就不是你的。比如你去看讲述拐卖的电影《盲山》,女大学生被拐进盲山以后,四处求告无门,村里的人眼睁睁的看着其“丈夫”对她的非法占有在大家眼前发生,却无动于衷,警察来了还合伙阻拦。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那个“丈夫”是他们村里的熟人,他用自己的村社关系,换得了其他村里人对他占有女大学生的同意,于是他就可以进行这种非法占有了。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古代很多农村有一个奇怪现象——当一户人家的田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要在族中培养一个或几个孩子出门考功名呢?这不是因为这户人家对学术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有多么向往。而是他们知道费孝通所说的那个基本事实——村民们是根据你与他的关系,来确定他对你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当然也包括财产标准,如果你家连个有功名在身的人都没有,甚至干脆男丁稀少,撑不起“门楣”,那么你连占有过多财产的资格都没有。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理解“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这样的观念为什么曾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还是那个问题,一个家族如果没有男丁,撑不起“门楣”,他就无力维系自身村社关系、而村社关系垮塌必然引发自己的财产边界垮塌。乡里乡亲们会大胆的越过边界,到你的权益范围来“捡”你的东西——就像那些下乡创业,却被当地农民们“捡”到破产的年轻人一样。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在这种基于村社关系分配产权边界的社会中,处于鄙视链最底端,财产权最不受保护的一群人,是谁呢?这样,很多人随意跨过边界,去“拿”和“捡”外地人的私有财产,就显得无比理所当然了——因为外地人跟他所处的村社里的任何人关系值都为零,没有关系就意味着你在这里财产权得不到尊重。实际上,在相对封闭的农业时代,产权模糊、必须基于关系维护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这种现象也不止中国才有,你看美国底层那些零元购的兄弟,他们的逻辑和行为机理也是一样的。而相比之下,像那些摇滚音乐节那样,年轻人开着车,倒个地方,支个帐篷把东西都放在里面,却默认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是只有一个高度成熟的现代社会才会发生的。你把人身自由迂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套现代规则说给一个前现代人听,他反而会奇怪——凭什么啊?你读书读迂了吧?
是的,要一个人,不是基于他与你之间的“关系”,和你的地位,而是基于普适的规则,去决定他对你的行为逻辑。那前提条件一定是这个人必须生活在一个现代、开放的社会当中,才能将这种规则意识视为生活所必须的水和空气。而这样的素质,显然,去音乐节上公开“拿”东西的老乡尚不具备。但你也得理解这些村民,他们生活在那个封闭世界当中,很可能这一辈子就没走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村庄,这个村庄对他们来说就是世界的全部。当村庄外所有的“异乡人”在他们看来都与他们没关系。既然“没关系”,那么怎么“捡”你的东西,也就都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打算和你打任何交道。所以,偏狭,永远在封闭与自固中产生。公德,只有一个需要广泛连接世界的人和社会才能具备。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在路上”,“去远方”。于是,我们又何必鄙夷、嘲笑那些“老乡”呢?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也经常见到这样的人么?他们对自己身边、国内的事物“谨慎”到简直胆怯,也不屑也无心向外望一眼。可是一说起超越这个边界之外的外国、外事,立马抛弃之前的道德标准,化身各种战狼喊打喊杀,甚至还有到别国去游玩,以放别人酒店的自来水以自况自己很爱国的……这帮人,你仔细审视一下他们的行为逻辑,跟那帮在音乐节上“捡”东西的老乡也没太大的区别。他们同样是一群目无普适规则、价值与秩序,只会根据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来制定对他人标准的“前现代人”。只不过,他们从没出过那个“村”,稍微大了那么一点而已。像《在路上》一样,开着车行到公路的尽头,看到一个心仪的地方,就支起帐篷住上,许久便览景色。你可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现代、也非常奢侈的梦想。
这不是车和路的问题,也不是远方有没有一个音乐节在等着你的问题。这关乎你沿途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们。想过这种生活,需要一个社会有更多真正的现代人去支撑。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