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载自:单读
上周六,巴以爆发多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空中、陆地和海上攻击,发射数千枚火箭弹,导致至少 200 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称其为“战争”,在加沙上空发动袭击作为反击,也导致 198 人或以上死亡,两个数字仍在上升。去年八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冲突持续三日。再上一次的交火发生在 2021 年 3 月,而继续往前追溯,暴力延绵不断。在今年出版的《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里,社会学家鲍曼谈及以色列建国的基础——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以暴力为底色,将“有人之地”看作“无人之地”的。而巴勒斯坦,“那里有着同样的不妥协、同样的不和解”。今天单读分享这段对谈,鲍曼从纳粹与现代性谈起,帮助我们理解巴以冲突中暴力的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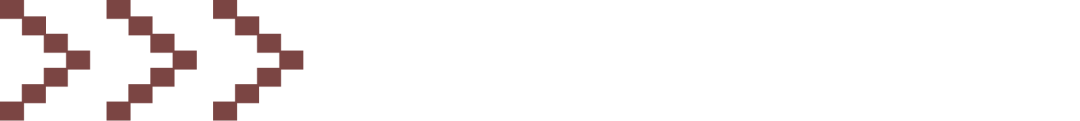
作者:[英] 齐格蒙·鲍曼、[瑞士] 彼得·哈夫纳
哈夫纳 在您的书《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您提出了这样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论题,即工业化地灭绝人类的想法是现代性的,而非德国民族主义特有的产物。那么,今天还会出现奥斯维辛吗?如果会,那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鲍曼 现代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它只是使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它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搞种族灭绝: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我们再也不用接受以前那种想法了——就像中世纪欧洲人相信的那样,就算不喜欢,我们也不能干涉上帝的创造。过去,人们是得忍受一些东西的。鲍曼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也是一个毁灭的时代。对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这些人被认为不可能适应人们想要的那个完美计划。毁灭就是“新”的本质,消灭一切不完美正是实现完美的条件。纳粹主义是这个现象最明显的例子。他们力图一劳永逸地根除人的境况中一切不受管制的、随机的或难以控制的元素。哈夫纳 是上帝之死开启了这扇门吗?虽然事实上,在更早的时代,比如说,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人们也会以上帝的名义相互杀戮。鲍曼 现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于我们自己的管理之下。现在,掌舵的是我们,不是自然,也不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既然他缺席或者说死了,那我们就要自己管理,再造一切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只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是以德国人为中心,重新安置所有人群——这是一项骇人的事业,炫目又傲慢。幸运的是,现在缺乏执行这个计划的一个要素:极权(total power,总体的权力)。只有纳粹德国才能执行这种计划。在不那么极权的国家,像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或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要素,现在的世界不存在。上帝保佑情况不会发生变化。哈夫纳 可人们对此的理解经常截然相反,认为它是一种对野蛮的回归,是对现代性、对现代文明核心原则的反叛,而非现代性的延续。鲍曼 那是一种误解。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是那些核心原则的极端的、无限激进的表现,而推进这些计划的人则做好了抛除一切顾虑的准备。他们只是在做其他人当时也想做,却不够坚定或无情到真去做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也在以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方式做那些事情。鲍曼 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人的互动自动化,我们还在追求这些东西。今天所有的技术,归根结底都在做这个。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被认为是进步。结果,我们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行动。而在直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哈夫纳 犹太人最早体会到现代人的境况——“纠结”。您也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过“纠结”的问题。鲍曼 犹太人最早暴露在纠结面前。他们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新世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他们是纠结的先驱。他们率先进入了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流动的现代性的特征。哈夫纳 您关于纠结概念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基于您在波兰所经历的反犹主义?在 1968 年 3 月的骚乱中,您失去了教职并离开波兰。鲍曼 我想,那段经历很有帮助。研究自己灵魂的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你永远只能回溯性地、带着后见之明和事后获得的知识来考察,别无他法。问题是,在我开始思考纠结的问题时,我是不是真的意识到我今天回顾时看到的那些动机。那是我当时思考的一部分吗?还是说,我只是在后来,在事后获得的知识的帮助下才想到的?我说不准。鲍曼 从逻辑上说,你假设它和我在波兰的经历有关是对的。和华沙所有同化了的犹太人一样,我也和“波兰性”有过一段戏剧性的恋情。我爱上了波兰的文化、波兰的语言、波兰的文学、波兰的一切,但我被剥夺了属于波兰的权利,因为我是一个异乡人。关于这个话题,我大学的一位老师,著名波兰哲学家塔德乌什·科塔尔宾斯基——他在业余时间也写抒情诗——说得很贴切。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关于这个主题的那首诗。那本诗集的名字是《快活的悲伤》(Cheerful Sadness)。鲍曼 科塔尔宾斯基是一位逻辑学家;他讨厌纠结。纠结让他不安,他反抗纠结。但他非常善于捕捉纠结。它给了他写作的灵感。那首诗写的是一个大地主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儿子。他不是投机分子,不是个野心家。他真想参与进去,想帮助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他问:“我做什么,你们才能接受我?”对方回答:“你得不是地主的儿子。”鲍曼 我不可能,也不想不是我所是的东西:忠于犹太传统,同时也忠于波兰传统。我把自己定义为波兰人,直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给我的书写评论的人总说我是波兰社会学家。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要被那样称呼,你得离开波兰。哈夫纳 现在,您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多年。波兰的食物呢?您还吃甜菜汤、猎人炖肉、苹果鸭吗?鲍曼 不常吃,因为得去波兰店买食材。不是哪里都买得到的。但当然了,我爱波兰菜。我尤其爱甜菜汤和波兰饺子——波兰版的意大利饺子。有个东西在波兰非常流行,但直到最近——来自波兰的移民潮开始之后——才能在英国搞到,那就是鲱鱼。这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但现在你能买到鲱鱼了。[鲍曼朝一个装牛角面包和其他糕点的碗做了个手势。]你还没尝这些法国美食呢!来,别客气。这可是专门为你烤的!鲍曼 你怎么不吃草莓?你一定要试试,它们美味极了!哈夫纳 您总是准备这么多食物,我都不知道从何吃起了!而且我觉得在专心谈话的时候很难想到吃东西,特别是考虑到话题之严肃。我们说到哪儿了?啊,对了,卡尔·马克思,也是犹太人。您是否也为人们对待您的方式感到失望呢?因为您曾认为,波兰社会主义可以终结族群标签和反犹主义。您觉得那会是一个平等至上的社会吗?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族群、种族或语言无关紧要?鲍曼 一些作者已经解释过为什么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犹太人较多。他们说,参加这些团体能使犹太人克服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心态。这些团体对潜在成员的族群出身不感兴趣,只关心忠诚和服从。族群归属无关紧要。在加入政党的那一刻,你就像蜕皮一样丢掉了你的族群出身。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看起来是这样。但不久之后,这变成了一种幻觉,某些共产主义逐渐发展为民族主义。但我的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吸引犹太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组织是唯一一个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平等的地方。他们不再代表低人一等的少数。哈夫纳 共产主义者也是纳粹最凶猛的敌人。就像希特勒在他 1939 年 1 月 30 日的国会演说中宣布的那样,纳粹计划“消灭欧洲的犹太种族”。鲍曼 对,这点很重要。只有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如一地反纳粹。我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很多人说唯一的选择,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只有这两个选项。西方民主国家对纳粹的态度非常松懈。它们把纳粹当伙伴,当政治游戏中平等的对手。犹太人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了。对他们来说,那是生死问题。可关心世界未来的非犹太人也得出了这个结论,即唯一真实的选择,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其他人只是沉默地见证灾难。哈夫纳 您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逐出波兰,失去了波兰公民身份。您去了以色列,但没在那里待多久。在熟悉犹太复国主义后,您发现它对您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为什么呢?鲍曼 的确,我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我为什么不想留在以色列呢?原因很简单。我去以色列是因为我被赶出了波兰。被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以色列,人们又要求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让它消失。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的自由主义日报《国土报》(Haaretz)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我的看法。标题大概是《为和平做准备是以色列的义务》("It Is Israel's Duty to Prepare for Peace")。我在这篇文章中做出了唯一一个事实证明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预言。在 1971 年,预言以色列社会,以色列人的精神,他们的意识、道德、伦理等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是需要一些见识和勇气的。西方还在庆祝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一个小国打败了几个强大的国家——大卫打败了歌利亚。我写道,不存在什么人道的占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和历史上的其他占领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不道德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被伤害的不只是被征服的人,占领者也受到了伤害。占领在道德上使他们受贬,并且长远来看还会削弱他们。我进一步预言了以色列人的心灵和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军事化。我说,军队将统治国民,而不是反过来由国民统治军队。事实的确如此,比我预言的还要过分。今天,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公民只知道战争。战争就是他们的自然习性。我怀疑,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想要和平,部分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怎样在和平时期——在不能通过扔炸弹、炸房子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应对社会生活中涌现的问题。人们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怎样使用其他方案——不涉及暴力的方案——来解决难题。暴力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它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色列已经走上了绝路。我甚至没法说我对长期前景感到乐观,哪怕在其他问题上,我一向乐观。因为我真的看不到出路。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要有出路,就得有人,有足够强大的一群人来实施一个计划。但在以色列,和平的势力被边缘化了,无足轻重。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也没人会听他们的。哈夫纳 就和平的意愿而言,巴勒斯坦人的情况也差不多。鲍曼 对,那里有着同样的不妥协、同样的不和解。巴勒斯坦人已经失望了太多次。他们已经看到承诺是怎样被打破的——多年来,以色列没有为开辟谈判空间而减少自己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开紧急会议,以色列政府就会宣布建立新的定居点,夺走巴勒斯坦的又一块领土。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没法乐观。我宁可不去想它。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为自己快死了、不会亲眼见证这场冲突很可能以悲剧收尾而高兴。你读过我的书《现代性与纠结》(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吗?哈夫纳 除其他问题,那本书也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鲍曼 那本书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有这样一句口号:“把无人之地给无地之人。”整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就建立在那句口号上。殖民地被认为是无人之地。殖民宗主国无视了那里已经有人了的事实。对他们来说,那些人是远离文明的野人,他们在原始环境中生活,在洞穴和森林里休憩。他们贫弱无力,可以被忽视,并且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也一样。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也许不是最后的——还有一些别的——但肯定是最令人惊叹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不过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变种而已。但我也能理解赫茨尔。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观念:我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我们将给这个野蛮人的国度带来文明。
摘自《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