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灯灯
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在28岁写下第一篇小说之前,叶昕昀从未想过自己可能具备小说家的天赋。人生的前25年,她过得循规蹈矩:一个来自云南边陲小镇的90后女孩,本科学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的国企上班,做行政工作,等待她的是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转折发生在工作第三年。国企的日子看似安稳,叶昕昀却深感无法适应。她决定辞职考研——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考研主要是为了逃避上班,找个三五年内能承接自己的地方。苦战两年,叶昕昀终于得以进入北师大读文学创作,成为作家余华的学生。余华对叶昕昀的初印象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因为她既不主动给导师发作品,微信群讨论某个文学话题时也不发言,每次只在讨论结束时说一句“谢谢老师”,还是跟在其他同学的“谢谢老师”后面。直到研究生快读完,叶昕昀才给余华发了三篇自己的小说,提出想报考他的博士生。余华读后很震撼,“这已经不是学生的习作,而是成熟作家的优秀作品”。他问叶昕昀有没有发表过小说,叶昕昀回答没有,余华说,“你是没有发表过小说的小说家”。前不久,我在北京见到了叶昕昀。如今,这个纤瘦的云南姑娘已经博士三年级了。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书里,她写身体残缺、命运纠缠的男女,写同时失去了自己孩子的母女,写互相仇恨而又无法分离的姐妹,笔法老辣,情节跌宕。读她的小说,常让我感觉像是南方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烤火,身上很冷,脸却微微发烫。我和叶昕昀聊了聊她的创作和生活,最终发现,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乎一个年轻人如何发掘了自己的文学天赋,更关乎一个内心持久动荡的人,如何找到了属于她的锚。以下根据叶昕昀的讲述整理。

从打工人到小说家
2014年,我大学毕业,回到云南曲靖,在离家不远的国企上班。我本科学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原本应该分到人力资源部,但后来被调到市场部下面的综合事务处,每天的工作是写会议纪要、做各种会务工作、走合同这些很琐碎的事情。没过多久,我发现我的性格融入不了国企的环境。我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每天却要接二十几个电话,所有工作必须和人沟通才能展开。入职时新员工培训,培训师让我们测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大家几乎都是E打头,只有我是INFP,引来了群嘲。我至今记得那种来自一群E人的压迫感。每天在办公室,同事们聊的话题都是孩子、老公、买房买车。我坐在他们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我感觉我的生活是停滞的,一想到往后10年、20年还是这个样子,我感到非常恐惧。上班才半年,我就不想干了。周围的人都劝我忍忍,说这么快辞职,不好找下一份工作。我想那就忍一忍吧,也许我刚进入社会,还没有适应。可我努力了三年,还是适应不了,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把生命浪费下去。我决定辞职考研。上班不适合我,我又不能干坐在家里,考研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强烈反对,我妈甚至气得要和我断绝关系。在她的世界里,国企已经是很好的归宿。虽然这些声音没有对我造成太多干扰,但第一年我还是选了不那么冒进的方式,白天上班,晚上回出租屋备考,上班间隙也在偷偷背单词。北师大文学院是众所周知地难考,我又是跨专业考研,难度更大。第一年我报的是当代文学方向,初试成绩出来,距离复试线还差6分,却刚好达到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复试线。这个成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第二年,我改报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那时我攒下了一笔存款,于是辞职背水一战,每天从早上八点闷头学到晚上五点,为了节省洗头的时间,用剪刀把头发剪到极短,大半年里体重一路飙升,报名确认时拍的照片堪称这辈子最丑。回到学校的每一天,我都几乎开心到想要落泪。研究生前两年,我全身心地享受着失而复得的校园生活:上课、写作业、去资料馆看电影、在图书馆读小说,偶尔有灵感的时候,写一些片段式的东西。在我们专业,老师上课时不会直接教给你写小说的技巧,但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我的阅读量,以及对文学的理解,都因此而有了很大的提升。到了研二下学期,毕业的压力开始逼近,我不得不再次考虑出路的问题。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有了创作成果,我很焦虑,不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我决定试一试,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一个个故事元素开始慢慢浮现在脑海中:云南特有的高原烈日,将一座小县城照得明晃晃的。县城里有一座寺庙,庙里有一间卖香烛和文书的厢房,房内有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她在等待一个独眼男人……这个故事便是后来的《孔雀》。因为想报考余华老师的博士生,我将《孔雀》和其他两篇小说发给了他。余华老师是我硕士期间的作家导师,我有他的微信,但从来没有给他发过自己的小说,害怕不成熟的作品对他来说是个负担。两天后他回复我,“你不用怀疑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你这方面已经成熟了”,“你是没有发过小说的小说家”。

一个小镇女孩的动荡童年
记忆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全县作文竞赛里拿了特等奖,得到了一本证书和老师们的夸赞。与此同时,一位同学在数学竞赛里拿了特等奖,获得的是县一中的保送名额。也许是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在我身处的环境里,有些才能并不能被转化成更为实际的需要。我的家乡在云南省曲靖市下辖的陆良县。那是一个贫穷且闭塞的地方。我上高中以前,县里治安很差,整个环境非常混乱,抢劫、拐卖、吸毒都算小事,杀人也时有发生。我有个关系亲近的表姐,是我二姑姑的女儿。她的丈夫以前在道上混,后来表姐夫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来家里把表姐和他们的女儿杀掉了。那时我才上初一,对一切还缺乏认知的年纪,去参加亲人的葬礼。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表姐的棺材被抬出来,上面盖着一层被血染透的棉被,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在紫黑色的血迹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浓烈的色彩。很多人说从我的小说里读到了一种动荡,我想这和我的童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孩子,每天活得担惊受怕,早上一醒来就感到恐惧,不知道这一天又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小学五六年级那段时间,我妈没有工作了,她原本在我们当地的丝厂工作,后来丝厂倒闭,她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就干脆在我们住的小区做门卫,夜里经常需要值班。虽然她值班的地方离家只有几百米,但每逢她值班,我晚上就睡不着,辗转反侧地想我妈会不会有危险,外面要是有人硬闯进来,她一个女人该如何应对。我爸爸是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算是动荡生活里的一点安慰。但这份安慰也很有限。我小时候总怀疑,爸爸家族的女性是不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否则为何都不能善终?我的大姑姑和她的女儿都患了乳腺癌,大姑姑的女儿乳腺癌晚期,几年前去世了。小姑姑今年10月也因为腹膜癌去世了。《最小的海》中有一篇名为《日日夜夜》的小说,女主角罗佳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有读者看完感叹我在医学方面的描述很精准,那是因为我亲眼见证过一个人从查出癌症到死亡的全过程。内外部环境的持久动荡,让我对安稳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很恋家,别的同学寒暑假都在实习和旅行,只有我一放假就回家和父母待在一起。毕业后进入国企,依旧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叶昕昀
然而,真正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安稳后,我却发现那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我适应不了。我从小就很难融入集体,是所有场合的局外人。在大人眼里,我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待着,成天“丧着个脸”,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孤僻小孩。可能有些人天生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没那么深。我从记事起就开始想象,未来我会以何种方式死掉。整个中学时代,我只读张爱玲的小说,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多遍。她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悲凉,以及她对爱情和人生那种悲剧性的判断,让我找到了深深的共鸣。长大后进入职场,我依然是被边缘化的角色。领导常用升职加薪来激励员工,但这些手段在我身上统统不奏效。于我而言,这些事情都没什么意思,它们无法激起我努力的兴趣。可当我看到别人都适应得那么好,工作两三年就开始结婚、买房、生孩子,走入既定的人生轨道,我还是会痛苦地想,为什么只有我适应不了这个世界?我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件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我努力了,然后我得到它了。得知被拟录取的时候,我哭着给爸妈打电话,那时候我想,命运终于眷顾了我一次。

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一件确定的事
申上余华老师的博士后,我又多了几年可以专心写小说的时间。我当时跟自己说,再给自己三年时间,看能不能写出来。从2021年春天开始,我进入了一种更规律的写作。我习惯在宿舍写,拉上床帘,戴上降噪耳机,很安静,又能听到一点舍友们讲话、走路的声音。这个环境让我非常有安全感,像是小动物躲进了自己温暖的洞穴。短则五六天,长则三个月,我沉浸在自己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里。有时候写着写着,人物会突然冒出连我都觉得很绝妙的对话,我一下子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是写小说最快乐的时候。每写完一篇小说,我都会发给余华老师看。余华老师给我的建议大多是方向性的,写得好的地方要放大,写得不够的地方要补充,要是写得太偏了,他会及时地把我拽回来。
叶昕昀和余华
有一次,余华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觉得我很擅长刻画畸形的人性。起初我不太认同,我说我这些人物怎么畸形了?我觉得他们都挺正常的。后来看到他给《最小的海》写的序才明白,他说的畸形不是表面的变态,而是深入到人性中,那些我们平时很难觉察到,或者羞于承认的情感。比如一个女性在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中所体会到的厌倦,一对亲姐妹对彼此的嫉恨,一个母亲对亲生女儿的冷漠。写作是一个自我暴露的过程。我写小说的动力,就是把我对生活的体会和思考,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那些曾经束缚着我的东西,一些隐秘的伤疤和痛苦,无所谓好与不好,它们只是一段中性的、客观的、恰巧存在于我的身体里的经历,需要用到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仅此而已。如果非要说我的母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精神成长吧。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会让我的内心更加平静,更加自洽。我很喜欢黑塞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个人不断地经历,不断地思考,最终领悟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过程。今年是我读博的第三年。说真的,读博的生活太快乐了,住宿舍,吃食堂,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看看书,写写东西。写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最起码我找到了一件我发自本心想做的事情。过去,上班、上学都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那都是我为了承担起我的社会角色,不得不做的。但是写作不一样,我确实想写,也喜欢写,并且能从中获得内心的充盈和平静。我不必继续当一颗螺丝钉,为了维持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运转存在,而是能从写作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中,找到属于我的世界。我的经历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它带有太多偶然性。我时常觉得,如果不是我突发奇想考研究生,我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如果不是刚好在那一年入学,我可能也没机会选余华老师做我的导师。老家街头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只不过我偶然间跳了出来,被命运的大手推到了这里。如果说在这段分享里,我有什么想说的,那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到了需要转变的时刻,并且你也做好了承担相应代价的准备,那就去做。如果没有,请先积蓄好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渴求命运对我们仁慈,但我们终归知道,自己能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点什么,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这个遍布着不确定的时代,过往动荡生活带来的不安和迷茫不会完全消弭,但每当我想到,我还有写作这件事可以做很久很久,内心便又会充满力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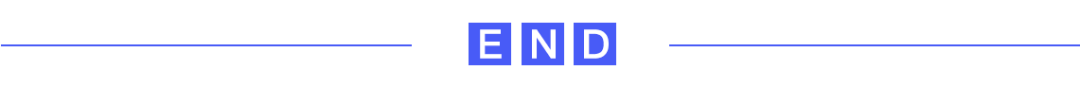
来个“分享、点赞、在看”👇
当我成为余华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