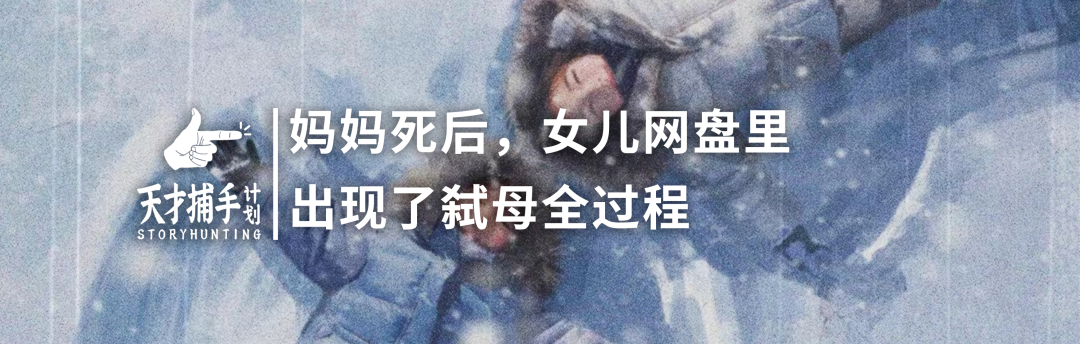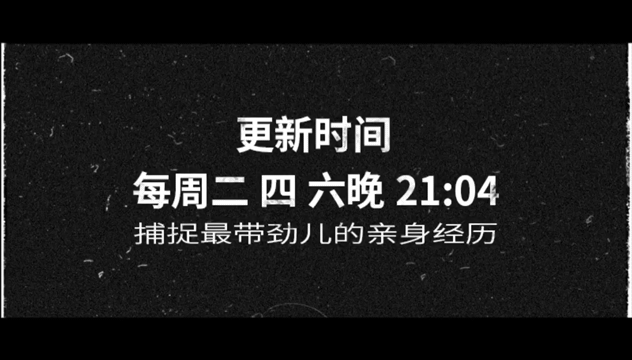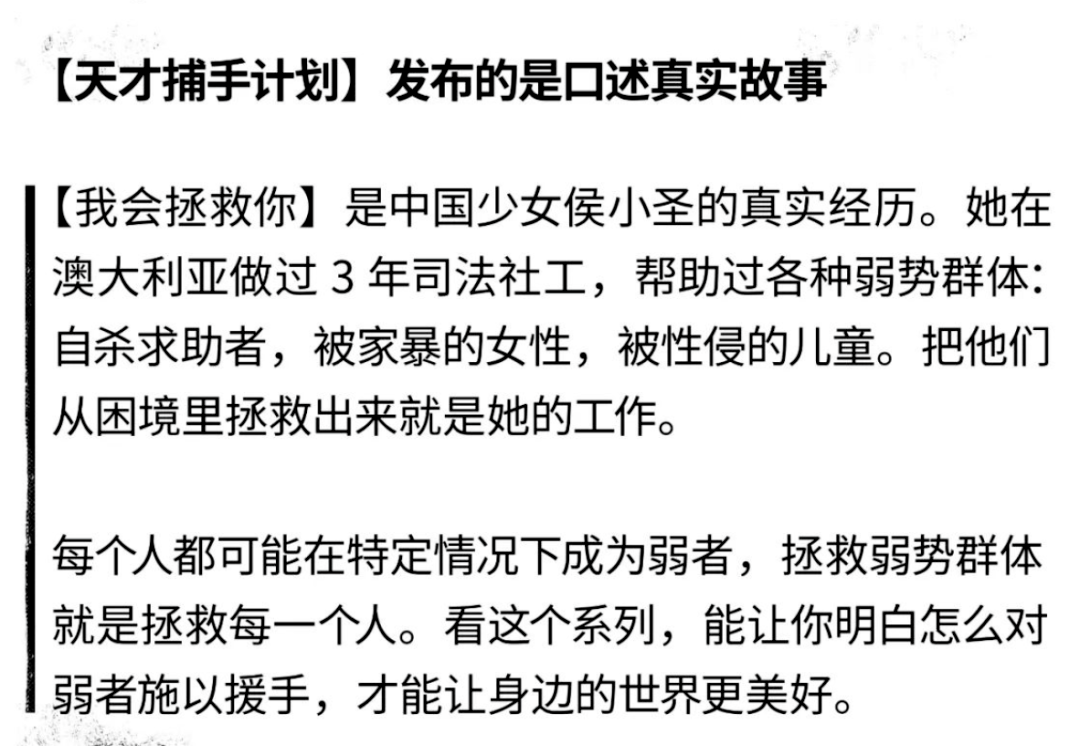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为什么我们总是告诫女生,不要在围观起哄中,答应别人的告白?
因为霍桑效应。
这是一种1933年就做过的实验研究,在一座工厂里,被视察的工人,会不自觉地提高生产效率。当时的科学家得出结论,当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时,就可能改变自己本身的行为。
也就是说,在围观起哄里,你可能会不自觉地应下不想答应的要求。
我的朋友侯小圣告诉我,被人围观,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
她曾经在澳洲当了3年司法社工,精通心理学和法学,本来不吃当众告白这一套。2018年有一次,她被一名白人男性告白。
身边大部分人都认为她会为了绿卡答应对方,而她明确拒绝了。
但在这之后,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成为社工的第一年,我曾经和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成为朋友。从外表来看,她完全是我的姐姐,身材瘦削高挑,但她有一双非常天真的眼睛,如果你和她说话,她会一直盯着你的嘴看,有一句话没看到就会追着要求你重说。因为一场病,贝卡的心智在10岁以后就没有长大。到我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已经28岁了。我的任务是给她做认知训练,每周三次,从最基本的抓握、折纸、穿珠子、指认身体器官开始,再到学单词,说、写完整的句子。通过这些训练,贝卡有希望继续“长大”,甚至可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帮公司整理资料,和人简单地打交道、交朋友。而贝卡也是我见过最争气的学生。比如写字母对她来说很难,因为是手部精细动作,但为了完成我布置的作业,她努力想过各种办法。有一次我打开她的本子,发现她用瓶盖画字母,一边再画上竖线。一页纸上全是巨大的“D”,又好笑,又让人觉得很可爱。她会拉着我看她画的画,上面两个小人坐在桌子边上,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笔,那是我,她把自己画得小小的。两个火柴人的手叠在一起,这是我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字母。贝卡的世界很小。她的母亲因分娩去世,父亲随后再婚,把她过继给了她的姑姑。姑姑对她不错,但也仅限于让她吃饱穿暖、安全长大。贝卡没法和人正常交流,有时我们学着学着,她会突然开始尖叫,伸出双手用力拍桌子。但每次发火后,她又会觉得不好意思,把头埋在胳膊里不肯起来。我会去哄她,她会扭扭捏捏地坐起来,然后道歉似的把自己手里的“宝贝”递给我玩,比如一串好不容易串好的珠子。短短半年的时间,贝卡已经能写出几十个单词,还学会了折小猫头,给它们画上眼睛和嘴。每次我来,她都会跑过来拉住我,给我看她又写了什么。但就在最近,贝卡突然有秘密了。她总是一个人趴在桌上写写画画,不听课,也不给我看。凑过去看,写的是“安德鲁和贝卡”,再下一页是“贝卡和安德鲁”,写了无数遍。她写的字母仍然巨大无比,每一笔都很用力,又歪歪斜斜的。有时候一整页放不下一个单词,就会重叠着写,乍看像一幅令人眩晕的抽象画。而她热恋的对象,是一个42岁的男人,智力和外表都是42岁。就在昨天,这个男人还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不知道贝卡有多爱我吧?我可以让她为我去死。”我心里明白,这场“爱情”的实质是,这个42岁的男人把贝卡变成了报复我、威胁我的工具。
半年前,我接下了给贝卡做训练的任务,每周要来找她三次。机构安排我顺道在她家的社区搞些活动,比如科普讲座、消防演练之类的。第一次走进社区活动中心,我就感觉似乎有人一直盯着我。我看回去,发现对方是个瘦瘦高高的白人男性,眼睛是蓝色的。布置场地时,我刚抱起一箱子材料,蓝眼睛的男人突然走过来说“我来吧”。他的上衣口袋上别着名牌,写着安德鲁,社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在接下来整场活动里,安德鲁一直站在我旁边帮忙,我中间走开了几次去给别的同事搭把手,不用半分钟就会发现他又出现在了附近。活动结束后安德鲁问我叫什么,我犹豫了一下,编了一个假名叫米琪。他掏出一个本子很认真地记了下来。从那天起,几乎每次我到社区办活动,这个安德鲁就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要帮我的忙。我给贝卡做训练,带着她在楼下运动,安德鲁会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手里拿着水,时不时来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问我喝不喝水,我说谢谢。他还跑来参与我们机构的活动。比如模拟社工咨询,他一定会来我的小组。我扮演咨询者,他扮演社工,我教他要怎么提问。在我看来,他是个有点麻烦的参与者。经常记不住词,还会问一大堆思路清奇的问题。有回模拟咨询结束,他跑来问我:“你不表扬我吗?”我说:“啊?”一开始我以为安德鲁只是过分外向,直到同事告诉我,他每次来参加活动都会问我在不在,如果今天我不在,他就会马上走。在这之前,我谈过两段恋爱,都是在大学里。我只会慢慢和人接触,从一起吃饭一起玩开始,成为朋友,再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人。我从来没和陌生人直接跨到恋爱,也不相信一见钟情,所以当时我更多的是困惑:这人为啥喜欢我?真正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有天我突然收到了安德鲁的邮件,他说自己正在社区里为我们机构募捐。他给我看他贴在活动室墙上的传单,还告诉我他已经带头捐了800刀(约3700元人民币)。问题是我们机构根本不接受私人捐款。机构的同事们还告诉我,安德鲁上一次来时,跟他们打听了我下班的时间。下一周的周二,我结束了跟贝卡的训练,发现安德鲁再一次恰好地出现在楼下。我把他带进社区活动室,迅速背出准备好的台词:“我对你没兴趣,也不会回应你,请你不要再来机构打听我的下班时间,这关系到我的个人隐私了。”安德鲁十分诚恳地道歉,说对不起,我只是真的很喜欢你。
安德鲁看着我的眼睛说,因为我看到你给贝卡做康复训练,觉得不仅你的工作有意义,你的能力也很强。我说在我之前,没人给贝卡做过训练吗?你从没见过社工?他说不一样的,前一个社工在的时候,贝卡总是很暴躁,他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看不起贝卡;而我来了之后,贝卡的精神和智力都有明显的进步,他知道我是真的尊重和想帮助贝卡,这很难得。他还有点受伤地强调,不是每个人展现出专业素养他就会喜欢上,“我喜欢你不仅仅因为你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更因为是你本人。”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如果男生说喜欢我贤妻良母,我一定会狠狠翻他白眼,但安德鲁正好喜欢“对”了我最希望被人喜欢的长处之一。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安德鲁。他比我大,我们社交圈子也不重叠,我对他没感觉,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接触过?我让他给我一点时间。我考虑了一礼拜,也找了自己的督导、朋友询问意见。他们大多都在机构里见过安德鲁一两次,对他的印象是很热心,也许有点笨,但人不坏。就连督导都跟我说,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一礼拜后,我再次找到安德鲁。这次,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先当朋友?”他用十分开心的语气对我说:“太好了,我还从来没搞过中国人呢!”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大概类似于端上来一碗面,结果第一口就吃到了苍蝇。我确认不是我听错,面前这位男士也没有表现出口误、觉得不对之后,当机立断地说:“不好意思,你那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我认为我们朋友也没得做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安德鲁脸上的表情只能用扭曲来形容:“你刚刚不是才答应我吗?你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吗?”安德鲁大步冲到我前面,我以为他要做什么,结果他只是非要抢在我前面出门。作为一个社工,我对这种威胁司空见惯,甚至没想起来跟机构报备。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安德鲁选择了从贝卡身上下手。
在和安德鲁谈话之后的第二周,我像往常一样,在周二上午抵达社区,敲开了贝卡家的门。但贝卡的姑姑告诉我,贝卡不在家。我很意外,以贝卡的心智水平,出门一般要有监护人跟随。姑姑在这,贝卡怎么会出去玩?我有点着急,问说什么朋友?我来了半年了,从来没听说过贝卡有朋友。姑姑突然厉声反问我:“难道她不能有自己的朋友吗?”说着她冷下脸,自顾自坐到一边,给自己煮茶喝去了。我被突然出现的冷遇弄得有点懵。一直以来,姑姑都对我很好,我骑车骑太多,有时候屁股疼,姑姑把三个软垫子缝在一起,给我做了一个专属的椅子和坐垫。她知道我们不能在案主家吃饭,就会准备很多小零食放在旁边,说是给贝卡吃的,贝卡一边上课一边往我嘴里塞,我不接受都不行。但今天,这种友善突然消失了,姑姑翘着二郎腿喝着茶,几乎把我当空气。我把下一次训练的时间提前到了隔天上午。走进贝卡的房间时,她正坐在桌前画画。她身边的椅子上搭着一件男式外套,她伸出右手抓着一只外套袖子。我们隔着桌子对视,她没有像之前那样热情地跑过来,就只是盯着我,表情甚至有点惊恐。那件外套我认得,是上次社区活动的时候安德鲁穿着的,甚至名牌还挂在上面。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脱下外套?我感到愤怒,甚至是惊恐。我很难不去想最坏的那种可能。贝卡眨着大眼睛看着我,那双天真的眼睛与她成熟的身体如此不搭。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哄着贝卡问,你和谁出去玩了?为什么会带这件衣服回家?贝卡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她和安德鲁出去了。天气冷,所以安德鲁让她把这件衣服带回家。但接着我又意识到,安德鲁让贝卡把衣服带回家,真的只是因为天气冷吗?为什么偏偏是一件带着名牌的衣服?我拍了衣服的照片,下课直接冲去社区中心找到安德鲁,问他要干什么。安德鲁用一副好整以暇的表情问我,这么激动,是不是吃醋了?我说你知道她智力有障碍吗?你的心智年龄比她大二十岁,这属于恋童;和智力障碍者发生性行为,这是性侵。他回答说,你不爱我,还不让我跟别人谈恋爱,是不是管太多了?我找到了比你更好的,你嫉妒吗?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东北话管这叫“黏牙”,就像一块黏糊糊的垃圾粘在嘴里,吐也吐不出去,清理也无从清理。自从安德鲁出现后,三次培训,总有两次我见不到贝卡,理由是安德鲁今天特别想见她,或者游乐园只有今天才开门,她不得不去。这种骗小孩的招数,也只有贝卡才会信。我跟踪了安德鲁,想知道他到底带贝卡出去干什么。第一次,安德鲁带着她在社区里散步,俩人挨得不近不远,安德鲁完全没有触碰贝卡。我跟在后面,没有听见他们说话。第二次,我发现安德鲁带着贝卡去了活动室,关上了门。我立马蹲在了窗户下面,脑子里已经闪过一串罪名,比如“在私密环境中对民事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肢体触碰”等等。结果他们谁也没碰谁,没坐一会,活动室里陆陆续续进来了别的人,最后竟然坐了二十多人,开始上编织课。安德鲁是组织人。贝卡坐在角落里自己一个人玩。安德鲁几乎看都没有看她,好像彼此只是陌生人。我根本看不出,他俩的相处中有什么可以被称为“爱”的东西。说实话,我也根本不相信一个42岁的男人和一个心智只有10岁的女孩,要怎么谈恋爱。我试着劝姑姑不要让贝卡跟安德鲁出去。说出他追我的那些事有些像污蔑别人,于是我给出的理由是,安德鲁会影响贝卡的训练。我很多次发现,安德鲁提前帮她拼好了我们教学用的拼图,甚至告诉她作业的答案,在上课时间带她出去玩。这对贝卡的影响很坏。智力障碍患者最缺乏的是“延迟满足”,学会延迟满足,才能学会情绪控制和如何学习。我花了半年建立这个机制,而破坏可能只需要一礼拜。贝卡现在已经对训练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我教她读简单的故事,读了两句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把书丢开,说啥也不愿意再学了。但姑姑坚持说,和安德鲁见面不会影响训练的,安德鲁对贝卡很好,他在社区十年了,知根知底,彼此熟悉。姑姑充满自信地给了我一个显然是刚刚听到的故事:其实安德鲁暗恋贝卡多年,之前没说是怕她们觉得他不真心。现在他想和她结婚。姑姑很赞叹地说,贝卡这样了他还喜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说我每周随访三次,一来就是六个月,我就不有情有义是吗?我从最基本的抓握、折纸、穿珠子、指认身体器官,教到现在贝卡可以学单词,说和写完整的句子;但这不如一个男人一周的殷勤。
我在网上搜索了安德鲁的一切账号,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打算干什么。安德鲁似乎不爱用社交媒体,他所有的账号都是空的。但我却得到了一个意外发现——我收到了一封自称是安德鲁前女友的人写来的邮件。邮件里有七八张截图,全都是各种活动上的我,角度怪异,不是侧面就是背面,只有几张清晰地出现了我的大部分脸。对方告诉我说,安德鲁的社交帐号近期发过这些照片,但他在我查到之前隐藏了。我加上了对方的联系方式,想找她确认证据。但女孩一上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前男友,感叹号不要钱地用:我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离这人远点!在她的叙述中,我惊悚地发现,这个安德鲁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恋型人格。在刚和女孩认识的时候,他疯狂追求对方,每天跑到公司接女方下班,出现在女孩生活的每个角落,就像最初对我那样。他在女孩面前扮演成一个有品位、懂珠宝的精英男人,女孩说,她当时完全把他当成偶像,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但在一起半年后,安德鲁就开始折磨对方。他出轨,甚至把出轨对象带回了家,告诉她们说,我真的同样爱你们两个,我无法做出抉择。女孩们崩溃时,安德鲁甚至反过来指责她们说,我上班已经很累了,你们还要闹。当两个女孩终于选出了一个继续留在他身边,安德鲁又好像玩腻了,最终通过借钱不还的方式,冷暴力分手。我设想了一下,如果这些套路用在贝卡身上,她会怎么样。一个10岁的小女孩,能接受最爱她的人突然变心吗?安德鲁会不会指责她,我不爱你都是因为你不懂事?安德鲁的招数,普通人都无法轻易识破,贝卡当然更不能。她的依恋肉眼可见地逐步升级。现在,她的画全部围绕着她和安德鲁展开,最常出现的是婚礼的场景,在画里,她给自己穿了一套白色婚纱,安德鲁站在她身边,头顶上用圆弧表示教堂。我和贝卡说起我们的计划,去读书、认字、学电脑,贝卡眨着大眼睛说,安德鲁说过,她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学习,只要和安德鲁结婚,他会保护她的。更奇怪的是,贝卡开始抵触我了。她总是故意坐得离我远远的,趁我不注意,把纸团成球丢我。甚至贝卡的姑姑,也总是在我们上课时坐在不远处,余光一直观察着我们。我觉得事情变得有些诡异了。在连续三次扑空后,我在一个周五突袭了贝卡家,拦住要关门的姑姑,把她推回屋里。她大声质问我干什么,我干脆问她,是不是觉得贝卡是负担,想把她脱手,巴不得她赶紧跟人结婚,自己就不用照顾了。姑姑面色涨红地反驳我说,别演了,你那点事我都知道。她斜着眼睛打量我,说你不就是被安德鲁甩了吗?你不想看到你的前男友喜欢别人。

我真想不到有人可以无耻到造谣我。我说我根本没和安德鲁谈过恋爱,我不喜欢他。我反应了一会,才明白她的意思是,我应该巴不得和安德鲁这么一个本土白人结婚,好拿澳洲绿卡。姑姑说,你会永远有工作吗?找一个澳大利亚人结婚不是更好的吗?我发现,我根本没法说服这个女人,我不非要通过跟谁一起生活才能留在什么地方,我也不需要谁来陪我才能生活。我根本无法证明,我不爱安德鲁,我不嫉妒贝卡,我只是想她好好的。贝卡的上一任社工告诉过我,贝卡的生父也就是姑姑的弟弟,认为姑姑“结不上婚”、“没有男的要”,所以把孩子过继给她,让她有个人陪。好似一语成谶,二十八年来,姑姑真的没有结婚。就连这个弟弟,也在再婚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们,也从未提过要看自己的孩子。二十八年的黄昏日暮,这个空空的房间里,只有这一对姑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找贝卡时迟到了,推门进去的时候听见贝卡在客厅里重复地说:“你会写puzzle这个单词吗?”姑姑一遍遍回答会,光是我推门到走进客厅这短短一段路,她就问了十多遍,姑姑也就回答了十多遍。那就是她们所有的交流。她渴望爱和陪伴,以至于哪怕是安德鲁对贝卡的“爱”,在她看来,也是如此宝贵。姑姑没有工作,社区给她介绍过民宿保洁的工作,她说因为腰伤无法坚持。她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养育贝卡得到的政府补贴,如果贝卡嫁出去,意味着她在五十多岁的年纪“失业”,甚至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我有好几周没有和姑姑说话。我想我得先证明自己对安德鲁根本没兴趣,才能解开这个结。
她的语气尴尬中带着生硬,她说贝卡最近有点怪,经常在楼下一个草坪上坐着晒太阳,平时都是几十分钟最多一小时,今天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她还是在楼下不愿意上来。我赶了过去。当时的场景确实十分诡异,贝卡一个人坐在草地上,保持着双膝并拢的姿势,手规矩地在放在身侧,整个人仰着头,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好像在看什么地方。我走过去叫她,她仿佛没听到,我朝她伸出一只手,她也完全不理会。我只能在她身边坐下,一边观察着她。仔细一看,发现周围一圈草皮好像有被压过的痕迹。贝卡坐的位置,是一个圈的正中心。最不自然的是,这个圆圈右上角有一圈石头,也被摆成圆形,好像一个大表盘跟一个小表盘。我想强行把贝卡拉起来,贝卡极力抗拒,她不断扭动身体,使劲踢我,大哭大叫,如果不是有邻居拦着,她甚至想咬我。半条街的邻居几乎都冒出来帮我按住贝卡,她姑姑也惊慌失措地跑出来,不断地问怎么了。我一边按住贝卡,一边向她求证,今天是贝卡自己下楼的吗?她说是,接着又补充说,贝卡这几天是有点奇怪,总是固定时间下楼,但就自己一个人,而且就在楼下坐着。我环视四周,确实没看见安德鲁。但我还是怀疑,这件事和安德鲁脱不开关系。贝卡被紧急送到附近的诊所,她姑姑跟着去了,我借用了附近邻居家门口的监控,想看看安德鲁有没有和贝卡接触。结果根本没有把监控往回倒多久,我就看见了那个身影。就在我试图拉起贝卡的时候、就在贝卡坐在草地上的时候,安德鲁就站在贝卡对面、我背后的灌木里。监控拍不到他的正脸,只看到灌木几乎遮住了他整个人,只露出了半张脸,对着我们的方向。
我浑身汗毛倒竖。这个行为非常明显,“服从性测试”,一定是他规定了要贝卡在楼下坐着,一旦贝卡通过了这个测试,下一步,他会要求她做什么呢?我把监控截图拍下来打印,冲到社区活动中心,把照片扔在了安德鲁面前。旁边有人进进出出,安德鲁不太自然地把这张纸推到一边:“我不能看自己的未婚妻?你吃醋了?”我警告他不要伤害贝卡,他阴恻恻地说,我没有伤害她,是你,她得坐在那里两个小时,是你害她动了,现在她只能从头开始了。他说你不用吓唬我,我有法律常识的,我知道这些事你没有办法让我坐牢。我不会跟她发生性关系,我还很喜欢他,我会娶她,我会一辈子跟她在一起。那天,安德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能把她训练到15岁,但你能把她训练到20岁、30岁吗?你不能。所以,你只是在帮我,把一个会闹脾气的妻子,训练成一个更懂事的妻子。我该谢谢你。”
贝卡今天也不在,我难以置信,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姑姑还能放任贝卡出门。我在监控截图上画了一条线,连接起安德鲁和贝卡,说你觉得这像是什么?我强调,这是一种监视,不仅是监视,还有训练,他需要贝卡听话,他说不能起来就是不能起来,你还认为这是一种爱吗?姑姑把这张纸推远,接着厉声反问我:“你从哪拿到的监控?”姑姑是贝卡最后的防线,如果她坚决要站在安德鲁那边,我真的无计可施。我想起最开始安德鲁那句“你一定会后悔”,我终于意识到,这才是他的报复。他知道我以我的工作为豪,所以他要通过伤害贝卡来伤害我。他真正要控制的是我。但我紧接着想到,是不是我不管就好了?如果我不配合,安德鲁会不会停止这场游戏,停止伤害贝卡?我撤回关注后,安德鲁真的着急了,他开始时不时把电话打到我们机构,找我聊些有的没的,比如你知不知道贝卡有多爱我,又比如你也太失败了竟然没谈过恋爱。那天,我正在上班,又接到这么个电话,我礼貌了五分钟,说没事我挂了。安德鲁立刻说有事儿啊,他问:“你昨天去给贝卡做训练,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不说话。我开始哀求:“求求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安德鲁慢条斯理地说:“最近贝卡太爱我了,我有点厌烦了,我想跟她分手。”他不搭理我,继续说:“你说,她那么爱我,爱到可以为我去死,如果这时候我对她说,‘我反悔了,你那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我认为我们朋友也没得做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你猜,她会怎么做?”那是我对他说过的话。他希望我觉得贝卡遭遇的一切,是因为我拒绝了他。我大口深呼吸。他又开始叨叨那些词,贝卡真的太爱我了,天底下女人有的是,你以为我找不到更好的吗,你别太得意了。我不敢挂断电话,不敢激怒他,心里想过了一百种可能与一百零一个方案。在絮叨了好几分钟后,安德鲁大度地留下了一句话:“我今天工作太忙了,还没想好,也许我下班就会去找她分手,你去找找看吧,看你能不能守在她身边。”
我联系了贝卡社区的另一个负责人,他们去了贝卡家,告诉我没发现什么异常。我想可能这只是安德鲁的新游戏,打算处理完手上的工作再去看一眼,但还没出门就接到了姑姑的电话:贝卡失踪了。我赶到了社区,和姑姑一起地毯式搜索,草坪,房子栅栏,我们之前运动时候走过的小路,我们一路喊着贝卡的名字,没有听到任何回应。贝卡的姑姑越来越紧张,她突然告诉我,就在不久前,安德鲁给她家打过一通电话,她问我那通电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说她家的电话有录音,可以给我。我立刻要回去听录音,刚走近贝卡家,就看见有零零星星几个邻居聚在那,看着她家窗口。三层小楼的楼顶,一个纤细的身影正挂在窗台上,半边身子已经伸出了窗台。我冲进贝卡房间的瞬间,她回头看着我,上半身小幅度地摇晃了一下,我以为她要跳下去了,往前一扑,脚趾头被椅子撞到,疼得眼冒金星蹲在地上。我埋着头,听见贝卡带着哭腔大声质问我:“为什么?”在她支离破碎的指责里,我大概明白过来,安德鲁告诉她,我和他分手后一直怀恨在心,我是社工,我很有权力,我会为了拆散他们把他送进监狱。她声音太大了,楼下所有人都仰着脸好奇地听着。我此刻看起来一定像滥用职权跟案主抢男人把她逼上死路的坏女人,这种八卦没准能在街区里流传一辈子。但我顾不上那么多。此时此刻,唯一能吸引她只有安德鲁以及跟安德鲁相关的一切,我再不情愿,也得利用这一点。我一边往前挪,一边对贝卡说,我跟安德鲁是在一起过,他和我说了很多秘密,包括对女朋友的要求,我给你讲讲好吗?你想听吗?我记得,在我还给她上课的时候,她常常会盯着我的嘴,“看着”我说话。如果哪一句没有“看懂”,就会追着要求我重说。我继续劝她,你不想知道安德鲁最喜欢的打扮是什么样的吗?我掏出手机把屏幕伸向她:“他说他特别喜欢看女朋友穿这种衣服——”为了看我的屏幕,贝卡开始转身,我把手机往回撤,她看不清,下意识地把腿收回了窗台,就在那一瞬间,我一把勾住她的肩膀,把她狠狠拽进了房间里,另一只手砰地关上窗户,锁死。我把贝卡按在地上,大声喊她的名字,让她抬头看着我,我说我培训了你7个月,你现在至少有13岁的智商了,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伤害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让你用死证明爱他,不能证明你们相爱,只能证明他想让你死。但这不意味着没有人爱你,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你去死!”
在那段录音里,我听到安德鲁用一种走投无路的语气对贝卡说,你知道吗,米琪威胁我,说她不原谅我,她要我永远坐牢。贝卡哭得伤心欲绝,而他一直叹气,花了一分多钟营造了一种极端绝望的氛围。接着他说,贝卡,我不想离开你,我想和你结婚,和你永远在一起,我们逃跑好不好?他要贝卡先跳楼,告诉她跳楼毫无痛苦,而自己会在人群里看着她,见证她死去,他再去跳楼,他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安德鲁入狱那天,我的心态是大仇得报,一早赶到监狱等他。隔着两个狱警,他跟我对上了目光,突然眼睛一眯,无限深情地说,米琪,你知道吗,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你等我,我出来会再追你的,我不会放弃的。按照规定,我把贝卡的案子转交给了同事,我没有再见过她们姑侄俩。听同事说,贝卡一开始配合度极差,认知水平比我带的时候有退步。他们带她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针对情绪问题、失恋后的修复,接着又从头开始训练。我不知道还要多久,贝卡能重新抵达我给她计划的那个未来:在家里接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社区的人打打交道,认识一些朋友。我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爱”上某个人。我好像只知道,我自己搬得动箱子,不缺安德鲁在那“帮助”;我知道我挺厉害的,吸引别人也很正常,但无论吸引来什么样的人,那不是我的错。我还知道,爱不是占有,爱不是崇拜,不是嫉妒,最重要的是,爱不是证明我价值的唯一路径。我抱持着自己所知道的这些去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侯小圣说,这个案子里的安德鲁,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NPD)。这种人行为的根基是自恋,他们对他人的痛苦没有同理心,表现出爱,只是为了“吸血”。
她还给出了一些辨别NPD的简易方法:
1.对方是否在极短时间里表现出对你的疯狂迷恋,表现得像是完美情人?
2.对方是否习惯性撒谎,尤其是扩大事实?
3.对方是否会在你拒绝ta要求时,表现出极端倾向?
4.对方是否总是吹捧自己、矮化你,甚至对你进行攻击,同时又说爱你?
5.对方是否极其恐惧独处,需要你或其他人的陪伴?
侯小圣建议,如果你本身就有讨好型/焦虑型/回避型人格,那么一定要物理上远离,保护自己。
如果不得不接触,最好要设立明确的边界。比如告诉对方:如果你再无端指责我,我就拉黑你。
“只要你保持边界稳定,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插图:大五花
本篇11060字
阅读时长约28分钟
如果你想阅读【侯小圣】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