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杨荔钠导演似乎已经留了很久的寸头。她面对镜头有些微紧张,但眼底闪着一种光亮。她时常想确认我能否体会那份似乎不属于我年龄的心情,笑着问我,“你能明白吗?”《妈妈!》是她第一部上院线的电影,距离她的纪录片处女作《老头》已经过去了25年。“25岁的时候我挺狂的,什么都不怕。”再次回到“老去”和“离别”的主题时,她回忆起了拍摄《老头》时给她留下的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似乎是命运种下的一颗种子,在《妈妈!》中,她有了一些自己的答案。在后来的25年里,杨荔钠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女儿过着自己相对简单纯粹的生活。《妈妈!》面向院线观众,杨荔钠也有一些自己的担忧,她笑着说:“我这样回答,是不是像给自己做辩护?”观众问得最多的,关于文淇的角色设置,关于电影台词的风格等问题,其实她早已做过完备的考虑。而在这次的采访中,当她谈及往事、到她的“女性三部曲”、再到她的创作方法时,她眼中的光亮,也逐渐变得有迹可循。从《老头》到《妈妈!》,思考老去
POST WAVE FILM
后浪电影:这部电影探讨了阿尔兹海默症和母女关系这样两个非常核心的主题。您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呢?杨荔钠:《春潮》之后,我就开始设想这部影片了,因为《春梦》之前“女性三部曲”讲的都是青年,《春潮》也是人到中年。到了《妈妈!》这一部,我想应该做一部老年女性题材的电影。
从《老头》开始我就关注老年群体,女性、孩子,一直都是我很关注的主题。
至于阿尔兹海默症,它是目前非常严峻、非常考验人的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有限,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其实已经中后期了。初期的时候,家里人都会觉得那是自然老去的样子。觉得记忆消失是很正常的,但事实上其实不能轻易地去判断它,它会有背后很深层的原因。所以我想这部电影的诞生,它具有现实意义,也有普世意义。后浪电影:您提到了您的《老头》,它谈论了衰老和离别这样的主题,这部纪录片对于您个人、包括对于您现在这部剧情片的创作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呢?杨荔钠:关于我怎么看待生死这件事,其实是有影响的。甚至我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想明白这事。所以我也很想用我擅长的电影语言继续跟观众对话。每个观众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值得被探讨,因为我们国家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进程里面,最重要的是青年角色的担当,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我们能为老人们做些什么?后浪电影:那您自己现在对于生死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杨荔钠:我认为生死是一种必然现象,就像我们身边看到的花鸟鱼虫或者我们养的小宠物,它们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可以悄悄地来,也可以悄悄地走。不去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干扰。老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面对死亡,但我觉得人生之所以这么久,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准备的时间去面对死亡。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不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时光其实特别残忍。大家都认为它好的时候,你自己不觉得。然后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半了。后浪电影:有没有具体发生什么事让你对死亡产生了新的看法?杨荔钠:我拍《老头》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在我镜头前倒下,那一刻我是慌张的,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我真的有被刺激到。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死亡焦虑,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在我的生命进程当中伴随了我很多年。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觉,在想我明天会不会醒不来。然后就会写很多封遗书,很drama。那种恐惧,只有自己知道,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后来当我到 40 岁、 50 岁的时候,我好像慢慢就不怕了。如果肉身都变成一颗星、或一粒尘埃,变得不再受时空控制时候,他们(亲人)的灵魂是不是随时都在你身边保护着你?我认为这些都是美妙的,也都是我对死亡的“妥协”和认知的变化。作为母亲,或是作为女儿的杨荔钠
POST WAVE FILM
后浪电影:像《妈妈!》这部电影,它会不会其中有一部分关于您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或者您和女儿的关系?不一定每一部电影都要保持一致(的风格),我试图去打破我自己的边界。
我也不介意别人说你的电影怎么没那么统一。这个电影的统一性,比如说它都是女性视角,也都是讲述女性的命运。
后浪电影:那您和自己女儿的母女关系,和您过往拍摄的母女关系,是否会有一些相似呢?有的时候我拿采访提纲给她看,我说过来看看,看看这些题怎么答。她愿意帮我的时候可以帮我,她不愿意的时候就不管,我急死了她也不管我。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听到她叫我,她叫妈妈,妈妈。我其实都听见了,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想听她叫妈妈。很好听。我们俩也会撕扯对方的头发,然后说别这样,这个太疼了,千万别扯。《妈妈!》里到最后妈妈保护女儿的方式也是我向往的一种母女关系。今年我女儿 18 岁,她马上要去读大学了,我作为母亲的角色已经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是我要照顾好我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我已经很忽视他们了,好在生命给我们一个年龄上的交错期,让人没有那么恐慌,同时要照顾两代人。不像我女儿在我面可以肆无忌惮,我作为女儿在有家规,有传统,有矛盾的时候我会让路,躲闪,再做沟通。《妈妈!》和观众,一次忐忑而期待的见面
POST WAVE FILM
后浪电影:当时在设计《妈妈!》两个主角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杨荔钠:这些年聚焦女性知识分子的题材是少见的,我认为她们应该被看到。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我是充满敬意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师传授知识,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其实是不想忽略他们的。尤其是更年长的一代,像母亲那个角色,从民国走到今天,经过了当代中国的变迁,热血青春都贡献给了社会和家庭。但是他们的晚年生活也有困难,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处理的?我想知道。后浪电影:因为要上院线和观众见面,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角色和观众有一定的距离感?杨荔钠:我这两天是有点焦虑,因为电影走向市场也是一场考核,但不是因为角色,一路路演和影展走下来,观众是喜欢母女角色也喜欢吴老师和奚老师,她们赢早已得观众的尊重和掌声。但市场好像是另一回事,我们的电影只有好演员,偏作者性的一部影片,不知放到市场上会怎样,这个我没有预判。杨荔钠:每一场都很深刻,无论是疾病开始前母亲像孩子一样求关注,吓的女儿从屋子里跑出来俩人互相打脸,还是女儿发病后的过程,每次她每次见到父亲,在雨中她等待父亲,在儿时的家里和父亲跳舞,一家人在山洞里团聚说我爱你。包括冯济真和周夏相遇到周夏带着自己的女儿回来再离开,母女疲倦的坐在家里沉睡任时光滑走,岁月流转。两位老师精湛演技幻化成角色本身,电影虽然结束很久了,但一想到她们我还会下意识去想哪位是我熟悉的奚老师和吴老师,而不是蒋玉芝和冯济真。后浪电影:除了二位演员老师之外,还有一个角色是文淇演的。您在设计文淇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设想的?很多观众对文淇这个角色有质疑,但路演调研时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反而觉得很正常。说到这个,我想起有一次我拍纪录片,在东北,一个特别冷的冬天。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往一个寺庙走,那个寺庙特别偏僻特别远。我在倒车镜里边,看到一个农村妇女穿得特别少,那会儿应该是穿羽绒服的时候,她穿了个特别薄的衣服,脚上穿着拖鞋,特别慌张地往前跑。当时也是我一个人开着车,我就把车门给她打开,我说你要去哪?那会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已经变得很疏离,人不太愿意去相信陌生人。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还是不理我,还是往前走。然后我就跟着她,我至少跟了她有三分钟,她才上车。这个过程当中,她在想要不要跟我上车。最后她还是选择信任我。我带了她半个多小时,全程我们没有说什么。就像电影里的女儿,她面对文淇,也没有说什么。我相信文淇在她每一次的目光注视里都能看到那种深深的信任。那种信任是我知道你现在犯错,在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依然相信你会好。这也冯济真老师这个角色,觉得自己作为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她们也是有一种相互救赎的关系。文淇在公交车上那场戏,冯老师把脸转了过去,这也是一种保护。所以最后周夏(文淇饰演),带着自己的女儿回来的时候,她能让我们看到一种代际女性的延续,她也是母女两个人疲惫不堪的时候,照进她们生活的阳光。那个时候冯老师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但是她不害怕,允许周夏给她擦口红,允许她在家打扫卫生,然后晚上跟她们睡在一起。周夏来去匆匆像风一样,她和冯济真不一样,她犯错有机会纠正,冯济真没有。我一直都在强调我们的人际关系看上去是越来越开放的,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封闭和躲闪,甚至是伤害和侵害。也许我们作为人不需要是朋友,是血缘,才能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建立在被索取的、被需要的价值上。后浪电影:这部影片它其中很多台词是有些诗意的,然后也有一部分台词带有一些舞台剧的质感,您是如何考虑的呢?杨荔钠:电影中,母亲出生民国,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女儿在这种家庭长大,后来又成了大学老师,所以我考虑到她们的身份和成长环境。我之前去做一些大学老师的采访,我觉得他们说话是有文气的,甚至有文学性的。交流起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也没有觉得有多违和。如果在电影拍摄当中,我稍微觉得有违和,或者是让奚老师和吴老师感觉有不舒服的,我也会调整。记忆中我们没有对台词部分有太多讨论。我当时也看了很多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书,这些病人发病之后说话甚至有哲学家的意味,带有哲理性的。后浪电影:因为您提到关注阿尔兹海默症,也做了很多调研,可以展开讲讲具体是如何去做这些调研的吗?杨荔钠:我去过养老院,住在北京非常多高知的养老院,他们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文学家,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些老人会有帕金森,认知障碍疾病的一种,就跟阿尔兹海默病一样。我感觉特别难过,现实当中的阿尔兹海默病人可能比电影还残酷。所以我觉得我们电影不能比这个现实更残酷,我认为那个尺度也是我们作者要把握的尺度。我看到这些学者们会特别难过,他们一生都在做和文字有关的工作。老了之后他们的手在颤抖,因为他们的记忆被拿走了,然后他们就坐在那在发愣,在生气。我们逃脱不了岁月的把控。在这样短暂又漫长的一生里面。但爱是永恒的。爱是唯一能解救和救赎人和人关系的渠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放肆,我也抵抗。我不太确定爱是什么,包括爱情。但是人到中年,这些好像就慢慢地打开了,不去看都不行。《妈妈!》说你怎样我都爱你,唯有爱才是所有的恐惧、焦虑、犹豫、和伤感的解药。从纪录片走向剧情片,女性三部曲的诞生
POST WAVE FILM
后浪电影:您的女性三部曲中,有您有意识地,想要抓住的共性表达吗?杨荔钠:我觉得《春梦》《春潮》和《妈妈!》都是梦境和现实的交织,哪一个是真实的?生和死哪一个是永恒的?这些其实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或者是我在现实生活里一直在想的事情。
后浪电影:您的三部剧情片,也被很多人称为叫女性三部曲,这个构思是从第一部开始就有的吗?杨荔钠:我用十年时间完成女性三部曲,她们之间有计划和排序。女性的故事我用尽一生都讲不完。在我看来,女性是情感动物,是可以牺牲自我去救助他人的这么一个生命体。但我不鼓励自我牺牲。都要好好爱自己。
女人作为个体,本身就是完整的,没有丈夫、孩子、家庭,女人自己也是完整的。所以一个女人经过的所有人生阶段,她们在社会里承担的所有角色,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被介绍的。
后浪电影:创作过程中有影响到您或者您个人特别喜爱的作品吗?杨荔钠:女性导演我喜欢简·坎皮恩,男导演比如说布努埃尔,我每次要开拍电影,我都会看他的书,但是他的电影我学不来,因为他太特别了。但我从他的文字当中,我就感觉特别亲近他。还有成濑巳喜男的(电影),我都很喜欢。 后浪电影:您之前提到,您在拍完一部剧情片之后会去拍一些纪录片。您说这个过程会很治愈,我特别好奇,这种治愈具体是怎么样完成的呢?杨荔钠:纪录片就是回到一种创作的单纯性和自由度上。
剧情片是集体作业,完成《妈妈!》这个影片,我特别感谢剧组主创和所有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非常职业的电影工作者,保证这部影片的呈现和诞生。
包括监制制片人尹露,摄影指导余静萍,美术指导翟涛,造型指导吴里璐,音乐沈必昂,声音指导王晓莎,剪辑指导朱琳,选角导演周正飞等等。
后浪电影:您最早是创作纪录片的,后来又有剧情片的创作,创作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片子,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或者理念?我们早期做独立纪录片,一台机器走天下,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做,那会儿还都在用DV。现在机器也是自由便携的,但这不等于创作的自由。我觉得恰恰现在难度是增加的,要拍摄的内容是什么,用怎样的方法讲故事很重要。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罢,作品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一直要考虑的,它也不是轻松的事。当然,剧情片的难度还在于要考虑团队资金的合作。现在像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拍纪录片其实是更自由更强劲了。但同时是不是设备便捷了,拍片就更容易了,我看大家获得资金也因为竞争力大而变难了。但事实上,很多年,我都是有饭吃的钱就可以拍纪录片,我并不认为我要拿一个很完整的资金才能开始。通常年轻人问我怎么拍片子,我会说带着现有的条件去做,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写,及时很重要,时机不可以被耽误。后浪电影:您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平时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样的?杨荔钠:平时我不是那种特别有计划性的,因为我之前计划都被养育小孩的过程打乱了。《春潮》的剧本,包括《妈妈!》的剧本,我都是在陪伴她上学的路上写的。
还有接下来的几个剧本,我都是特别随性的,都是见缝插针做出来的。我也不是那种计划型,即便有计划也会被我自己打乱。
比如那天在路演,台上的观众在问我问题,我脑子里面就嘣嘣飞下一个剧本的剧情还有台词,然后我就很快又把自己拉回到现场。杨荔钠:单从创作的角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 25 岁拍完《老头》。当时有的人就说我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还是个女演员,说我是灵光闪现不会持久。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我觉得所有的年轻创作者,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都不要怕,不要在意别人的评判。
因为这个评判有的时候可能就来自你最喜欢、最信任的人,当你们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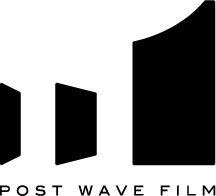
帮过张艺谋,救过李安,华语电影界最牛的幕后大佬是谁?详 细 课 程 介 绍 | 专 业 干 货 分 享
关 注 【 后 浪 电 影 学 堂 】 公 众 号 影 视 课 程 大 礼 包 免 ! 费 ! 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