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泽的《桑塔格传》对桑塔格的家人、朋友、助理做了地毯式采访,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
苏珊·桑塔格生前对别人为她写传记这件事深恶痛绝。撇开希望保护个人隐私这一点不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桑塔格的态度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传记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卑弱的文体。除了《约翰生传》这样极少数的例外,总体而言,传记是一种缺乏原创性的东西。传记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材料,让人了解,供人思考。它有用,却并非不可或缺。我们读过优秀的传记,但“伟大的传记”?似乎只能属于矛盾修辞。作为评论家,桑塔格从未写过关于传记的评论,这应该能说明一点问题。与桑塔格的意愿相悖,在她去世前四年,其传记就由她几乎不相识的职业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夫妇完成出版,这就是《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桑塔格去世后,罗利森对该书进行增补修订,中译本改题《苏珊·桑塔格全传》。此后出现的四部传记分别为英国人杰罗姆·博伊德·蒙塞尔写的《苏珊·桑塔格传》(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德国人丹尼尔·施赖伯写的《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以及今年译介出版的法国人贝阿特丽丝·穆斯利写的《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一版)和美国人本杰明·莫泽写的《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苏珊 · 桑塔格(摄于1989年1月20日)
莫泽的传记最晚出、部头最大(英文版及中译本均超过800页),且由桑塔格之子授权,因此,理所当然会得到我们的重视。不过,关于桑塔格传记的一个难题就是它们其实各有特点,难以相互替代。如果有读者因喜欢桑塔格的著作而对她的人生发生兴趣,我会首先推荐她/他去读罗利森夫妇的《苏珊·桑塔格全传》。这本书是以局外人的超然写就的,叙事详明,而无最近两部传记的冗长之病。如果读者只想获得扼要的了解,那读蒙塞尔的《苏珊·桑塔格传》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篇幅最短,所附照片却有好几幅既生动又为其他传记所无。施赖伯的那部也许是最平板的,无甚足取。穆斯利的,正文600多页,篇幅足够大,作者对桑塔格作品发表后的相关评价格外重视,所收集的材料是有价值的。莫泽的《桑塔格传》优点明显:作者对桑塔格的家人、朋友、助理做了地毯式采访,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比此前桑塔格儿子、儿子前女友的回忆录及桑塔格自己的日记暴露出的要多得多。《苏珊·桑塔格全传》里曾提到,有些桑塔格的情人的“姓名和生活有待于她授权的传记作者去考证分析”,比如有个“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C”,我们以前不知道是谁,现在莫泽已经揭示,她是安娜·卡洛塔·德尔·佩佐。卡洛塔(Carlotta)是那不勒斯的贵族,不爱读书,不事生产,1969年到1970年,桑塔格爱她爱到受虐狂的程度。桑塔格的朋友唐·莱文说:“苏珊其实只拜倒在两个人的脚下。如果她走进一个房间,看到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汉娜·阿伦特或卡洛塔,她立马就会坐在地板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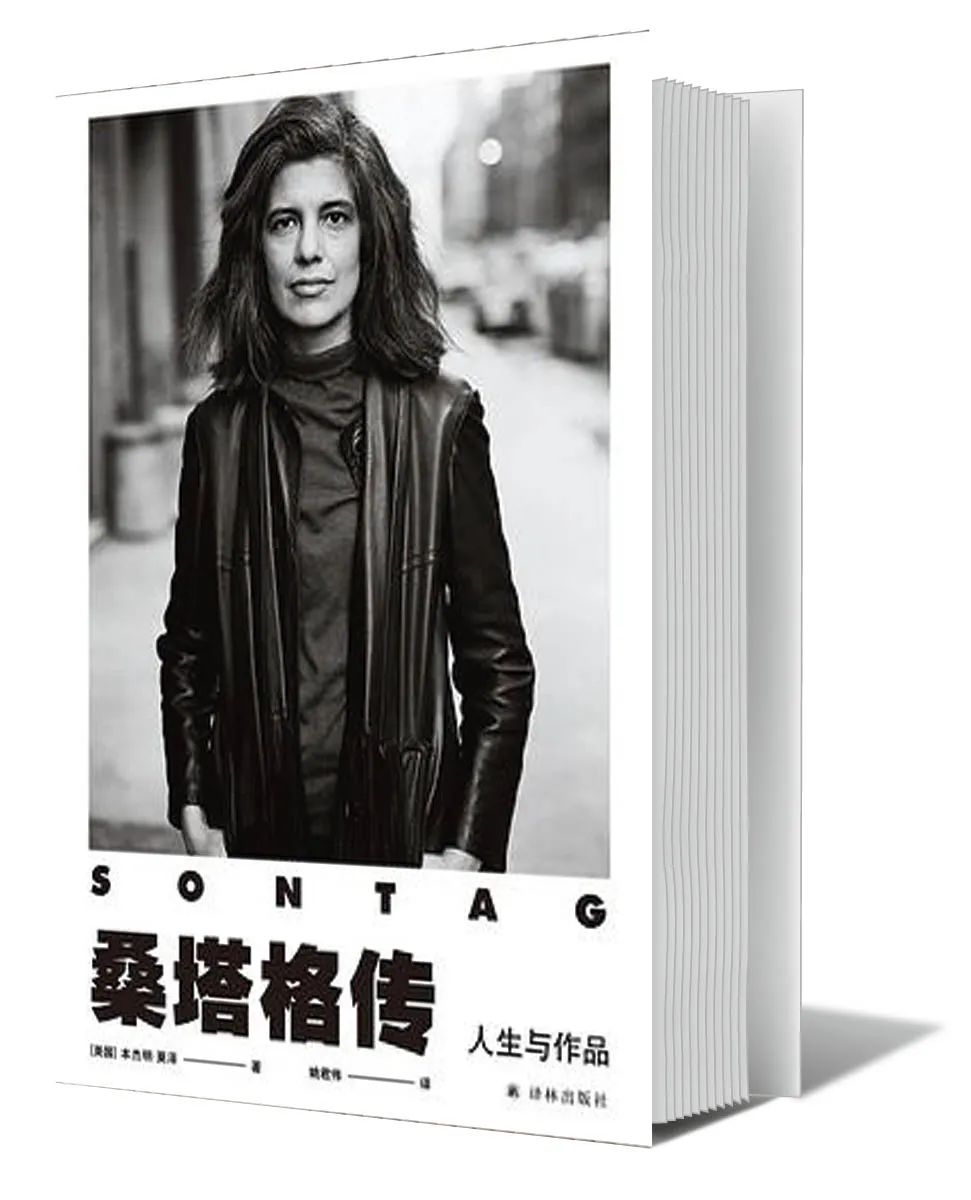
然而,在桑塔格的亲密关系中,她扮演过的角色可不止受虐狂这一种。20世纪80年代末,桑塔格跟著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交好之后,她的角色似乎就反转为虐待狂了。桑塔格的儿子称:“她俩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对情侣。”桑塔格颐指气使,甚至会当众贬低、侮辱、谩骂莱博维茨,“骂起来像开一挺小型机枪一样”。而莱博维茨则在这段关系中扮演一味隐忍的崇拜者角色,尽量做到无微不至,她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照顾一个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人物。”莱博维茨慷慨的程度,像桑塔格粗鲁的程度一样,让人震惊。富有的她为桑塔格大把大把地花钱,她们的会计师估计,“在她俩交往期间,安妮至少给了苏珊800万美元”。
不用说,奢侈的、任情肆欲的生活,是有腐蚀性的。莫泽的《桑塔格传》第三十二章的标题“劫持人质”,是个很形象的隐喻。作为世俗存在的桑塔格,被奢华生活和肉体享受所劫持,成了人质。用桑塔格自己在小说《火山情人》里写下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她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她知道自己在上升。”是的,她上升到上流社会中去,上升到丧失现实感的地方去。
我们说莫泽的传记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还是很含蓄的,假使直白一点,说是在探究桑塔格的性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也未为不可。我没细数,传记中涉及的有名有姓的、与桑塔格有过性关系的人,约在20位左右。其中最值得玩味的一位,也许是肯尼迪总统身边的年轻工作人员理查德·古德温。桑塔格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我睡过的最丑的人是床上功夫最好的人。”(第307页)但当她从古德温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肉体愉悦后,桑塔格想的居然是:“哦,该死,现在我真和旁人毫无区别了。”这里的“旁人”,指的是一般的异性恋者。为什么跟旁人一样这件事,在桑塔格看来,会是“该死”的?把这一点想明白,或许也就掌握了打开桑塔格精神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莫泽的《桑塔格传》在传主性生活方面的出色挖掘,是无可置疑的。在此之外,它则跟另外四部传记共享一个特征,那就是在思想诠释、精神阐发方面的贫弱。自然,这是毫不奇怪的:五部书的作者中没有一位是有思想的人,他们是材料的收集者,是事实的报道者。莫泽偶或有一两句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度,已属难得。我们对这类传记作家还能有什么期待呢?他们对桑塔格一生的真正贡献所在——她的评论——不可能有深入、精微的体会,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把作为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的桑塔格真正写好。
由于他们没有思想,也就不会去关心思想,所以哪怕仅仅在思想事实的层面,也有许多信息被这些传记作家忽略或漠视了。比如,假使你对桑塔格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早期交往感兴趣,那你即使翻遍这五部传记,恐怕也找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时,你就得去看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的《在法语中做梦:杰奎琳·鲍维尔·肯尼迪、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的巴黎岁月》(Dreaming in French,2012),才会知道德里达在信中对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多有鼓励。你还要再读米娜·米特拉诺(Mena Mitrano)的《在渴望的档案中:苏珊·桑塔格的批评现代主义》(In the Archive of Longing,2016),才会看到德里达信件的照片,他认为桑塔格的第一部论文集《反对阐释》跟他自己刚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应和的关系,而那些文章就是德里达后来的名著《论文字学》的雏形。
其实我无意苛责传记作家们,而只是想指出,作为读者的你,应该明白你手上捧着的这厚重的读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你不能指望从里面获得思想的启迪和刺激,如果你想得到那个,你更应该去读桑塔格,读《反对阐释》,读《激进意志的样式》,而不是桑塔格的传记。桑塔格晚年曾对自己做过一个有名的,同时也是发人深省的区分。她说,有一个“我”,有一个“她”,“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使“她”成为可能的那个人,而“她”则是写作者。桑塔格写道:“我不过是我,陪伴着管束着照料着那个她,好让她写出东西来。”(《重点所在》)假如我们借助这一区分,也许可以如此评价莫泽的《桑塔格传》:他活灵活现地呈现了桑塔格的那个“我”,却没能刻画出桑塔格的那个“她”。桑塔格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似乎表达了那么一层意思:她已经渐渐将“我”和“她”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但,哦,不!她远远没能。那个写作的“她”,那个思想的“她”,仍像一个幽灵,在外漂泊,未被擒获。莫泽说:“桑塔格真正的重要性越来越在于她所代表的东西。”这话当然没错,问题只在于,到底什么是她所代表的东西呢?在我看来,她所代表的,就是她自己笔下的那个“新感受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新感受力”应该永远是灵活的、机敏的、警惕的。正如桑塔格自己在评价卢卡奇时所说的:“当然,每一个批评家都有权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某些判断失误却表明整个感受力的急剧衰落。”当桑塔格自己的感受力急剧衰落后,她也就违反、背叛了自己所代表的那个东西。后来的思想者的任务就变成,不仅要像桑塔格提示的那样,把她分为“我”和“她”,还要进一步把“她”再分为“能代表她的她”和“不能代表她的她”。而这种思想的无穷尽的辨析和追索,是桑塔格曾教给我们的东西。(本文选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44期)
排版:雨筠 / 审核:然宁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