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每年的4月26日是“全国疟疾日”。疟疾是一种传染病,通过蚊虫叮咬传播。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世卫组织颁发“无疟疾认证国家”。从上世纪40年代的3000万到“0”的突破,我们用了70多年。中国建立的“疟疾监测体系”能够有效控制疟疾的传播,在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方法,被中国医护工作者带去了世界各地,用于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张军是中国医科大学1980级校友,毕业后在卫生部工作了七年。1993年,他辞了职,加入无国界卫生组织“HPA”(健康扶贫行动),成为该组织第一个成员。从最基础的改善生育方式开始,到帮助缅北当地建设卫生体系,漫长的28年几乎占据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我的团队属于无国界卫生组织——“HPA”(健康扶贫行动),1994年项目组成立,我是第一个成员。那时候去缅北百姓家里走访,都是找谁说话,谁穿衣服出来,其他人留在屋里。因为要自己纺布,衣服不够,所以谁出门谁才有衣服穿。我们为缅北克钦邦(缅甸北部的自治邦)、掸邦(缅甸联邦成员国)等地的3000多个村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服务范围覆盖了90%的中缅边境区域。28年来,我们机构在缅北发展了160多个全职员工,2000多个志愿者。我是60后,在我们这一代人眼中,整个世界以光速发展,那些始终如一的地方,便让人觉得落后了。提到缅北,大家率先想到的是“金三角”、“贩毒”和“诈骗”,鲜少有人看见这里的百姓在长达60年的战争中正在经历的饥饿与疾病。以前粮食不够吃,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洗澡和喝水都是在附近的河里。孩子们很瘦,肚子凸出来,典型的营养不良。呕吐、腹泻足以要一个孩子的命。过去没有医院,甚至连懂医的人都没有,女人怀胎十月,生下孩子的时候脐带是用竹片或者烂剪刀割断的。因为陈旧的风俗习惯,她们的产房通常设置在牛棚、猪圈,避免弄脏自己的家。然而所谓的家,也就是几根竹棍插进地面,钉上竹板,用竹篱围成墙,屋顶铺油布和茅草,上面住人,下面养牲口。不养牲口则直接把土压实,把竹篱墙扎进地里。下过雨后,家里潮湿,地面冒出许多小蘑菇。这几十年,居住条件一直是这样。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缅北体现出的贫瘠和原始,吸引了国际上很多非营利组织(NGO)的关注,粮食、支教、医疗等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涌来。机构在这里的时间普遍不长,短平快的做一个项目,项目结束就走。医疗最常见的做法是高薪聘请一个医生,开诊所,收治病人,能给老百姓解决很大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也意识到:一旦项目停止,医生走了,当地又会回到原点。此外,这样的方式本身也有限制。很多原始村寨的路是土路为主,边境百姓的交通工具以驴马、骡子、大象、摩托为主。如果医生只在一个点上设立诊所,有急症的话百姓来不及看医生,医生也不可能前往深山老林到处找病人。在缅甸,医生、律师属于精英,非常稀少,更不可能每个点都安排医生。1994年,项目刚成立的时候,我常感迷茫,担心第二年这个项目就结束了。从发展的角度讲,最好是能把当地的能力培养起来,把能做事的人留在这里。所以每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我们都问:“村寨里有没有读过书的人?能不能把他们叫过来,我们发补助,让他们协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哪怕是只读过一年书的人,我们都让他来帮忙;哪怕是教他填填表、登个记。但更多时候胸口充斥着无力感,因为很难找到读过书的村民。之后我们和缅北地方政府商量:能不能从整个地区抽二三十个年轻人,我们去外头找大医生给他们培训两年,讲各科的课和医疗知识。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则请缅甸的医生过来,按照缅甸中央政府的标准进行培训。缅北和缅甸的民族隔阂很深,彼此的军事、政治、法律都是独立的,国际上关于疾病、人口数量的统计等以缅甸为准,缅北不把数据同步给缅甸,国际社会就没办法获知缅北的情况。通过培训,缅甸的政府承认了受培训者具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能力,而缅北也间接接受了缅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先是实现了数据同步,而后缅甸开卫生工作会议的时候,也会向民族地方武装的卫生局发出邀请,而民族地方武装的局长也会到首都内比都参会。如今,具备基础医学知识的志愿者分布在各个区域,像“赤脚医生”一样,第一时间发现需要医疗救助的百姓,用最简单的医疗技术和器械设备进行基础的救治。从西藏怒江到云南省勐腊县,中缅边境线长达2186公里。边境线上很多地方没有天然屏障,有的地方就是一条沟。新冠疫情之前,两边百姓拿边境通行证可以自由进出。百姓互称“胞波”,关系很好,中国百姓在这边砍甘蔗,缅甸老百姓带着工具过来帮着砍。因为距离近,中国边境的百姓受缅北传染病的威胁较大。时钟往前拨动20年,缅北孩子的死亡率高达50%,其中60%-70%的死亡儿童是因为疟疾,现在缅北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几乎找不到没得过疟疾的人。疟疾的感染是蚊虫叮咬传播疟原虫导致的。蚊子不分国界,中国有句话说:“中国疟疾看云南,云南疟疾看边境,边境疟疾看缅北。”防治疟疾是HPA的重点项目,也是让我颇有成就感的事,有一种我们在缅北为国家保驾护航的自豪感。疟疾疫苗是2021年才研发成功的,在此之前最有效且可实施的预防方法是教村民使用药浸蚊帐—— 一种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接触到蚊帐的蚊子会被药晕或者杀死。听起来是给百姓发几个蚊帐的小事, 实际上费了一番功夫。在缅北的语言体系中,没有“疟疾”这个词,他们管“疟疾”叫“水病”。缅北的百姓在河里洗澡,上岸后被蚊虫叮咬出现高烧、发冷、全身打颤的症状,百姓一直认为病根是在水里。每年五六月份缅北进入雨季,蚊虫增多,上厕所的时候都拿着东西扇蚊子。我们要在雨季之前让百姓用上蚊帐。想让百姓用蚊帐,要先解释清楚,“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因为河边的蚊子多,所以大家误以为是水引起了疟疾。团队里的年轻人还自制了科普海报,把蚊子画得惟妙惟肖。第一次推广的时候,百姓把海报贴在了墙上,蚊帐却放在一边。我们的同事问:“为什么不用蚊帐?”百姓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么大的蚊子,用不上蚊帐。”这个答案让我们感觉好笑又无奈。后来画宣传画这件事我们就交给百姓自己。他们画出来的蚊子看着像苍蝇,但奇怪的是,当地人一看,马上能认出来是蚊子。2011年,缅甸公布的数据显示,疟疾病例约为40万,同年中国云南的输入性疟疾是5000例。到了2019年,缅甸的疟疾病例是4万多一点,云南的疟疾病例包括输入性疟疾病例降低到了188例。2021年,中国还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了“无疟疾国家”的称号。2021年2月,缅甸军政府上台,工人罢工,已经送到缅甸仰光的物资无法清关,佤邦的项目经理张光云曾尝试协调物资运输,结果却连负责人都没找到。我们的蚊帐最终没能在雨季前发给百姓。去年疟疾疫情也有起伏,但由于新冠疫情采取了风险管控,各地的流动比较小,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传染。缅北出现疫情是在2020年下半年,那时候缅北核酸实验室刚建立。中国医疗队给了缅北很多指导和支持。张光云和医疗队的同事把城区街道和各单位采集核酸样本装进专用的冷藏箱,再送到国门口岸,交由相邻边境县的卫健委防控人员取走样本在国内检验。检测结果出来后,张光云和医疗队还要把数据录进电脑。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凌晨。
2021年2月军政府上台后,医生也罢工。缅北的医疗系统瘫痪了,克钦邦第一特区的老田和他的医疗队接手了一个我国在缅援建的方舱医院。每天有两个护士和一个医生在方舱医院中照顾病人,为感染新冠的百姓提供免费治疗。最忙的时候,他们收治了50多个病人,前后有300多人出院,没有死亡病例。在缅北,更需要我们的是500多个原始村落里没有水电、没有医生的边境百姓。他们需要流动医疗队的同事带去物资,比如疟疾检测卡和治疗疟疾的药,常用的还有腹泻药、感冒药、退烧药、治疗皮肤病的药,给孕妇的叶酸、给孩子补充微量元素的营养包,还有孕妇生产需要的干净的产包。即便在疫情期间,老田也尽可能带医疗队每个月去一次村寨,做流动医疗,一般去15天。但是边远的寨子只能两个月去一次。每次出去,司机会带上全套的修车工具,不是车不好,而是山路崎岖,每次去一趟车都会坏。铁锹、锄头、铲子也要一并装上车,碰到塌方,所有人一起下车修路。一些车开不到的地方,雇骡子或者大象拉东西,再不济走过去,有时候还要蹚水过河。下乡的十几天,老田和同事住在村长家或者教堂里。克钦邦信基督教,教堂是村寨里最好的建筑——用砖头砌的墙,顶好的条件。但是克钦邦靠近西藏,平均海拔有3000米,冬天在教堂里睡觉,冻得直哆嗦,即便钻进睡袋再盖上被子也冷。村民很暖心,管吃管住。吃的东西、盖的被子很干净,他们把心意都放在里边。朴实、单纯,这是我和同事们对缅北百姓的印象,小孩子笑一笑,我们的心就软了。2021年10月份,有5个同事下乡回来之后,核酸结果呈阳性,其中两个同事比较严重,发烧38℃、全身酸疼,治疗了20多天才转阴性。另外两个同事没发烧,但失去了嗅觉;还有一个同事无症状,在第十三四天的时候恢复阴性。恢复之后,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开玩笑说:“感觉像是得了一场重感冒,但没有重感冒难受。”回想起老田刚来缅北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上厕所抱树的画面。村寨里上厕所都是跑进大山里,因为海拔高,蹲下的时候我们要抱着前面的树,不然感觉要滚下去。画面非常滑稽。现在,家家户户有一个干净的厕所,得益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改水改厕项目,也是我们HPA执行的项目之一。在两家百姓中间挖一个化粪池,然后采购一个塑料桶、一块铁皮,做一个简易的厕所,还可以冲水,每两家共用一个。2022年2月,缅甸暴发了第四波疫情,在死亡病例中90%——95%的人没有接种过疫苗。中国为缅甸援助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疫苗,而我们的使命是协助政府把中国援助的疫苗打在百姓的身上。疫情再加上缅甸政治原因,2020年之后物资运输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每次打疫苗,去乡下都需要协调几个冲突方和驻守关卡。还好在这里二十几年,各方的人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不为难我们,还主动帮忙。想要把疫苗从纸上和冷库落实到边境百姓身上,疫苗物资和交通运输并非最关键的因素,储存疫苗的条件更重要。按照医学标准,各类疫苗的储存对温度有不同的要求,低温冷库储存温度需要-20℃,普通冷库储存温度是2-8℃。运输过程要做到苗不离冰,否则疫苗的效价会降低,超过8℃疫苗就失效。我们在缅北给百姓接种疫苗的历史已经有十几年,包括11种儿童免疫疾病疫苗、妇女的破伤风疫苗,最近几年还有女童的HPV疫苗。边境的原始村寨不通电,为了保证疫苗能够在低温条件下运输,下乡的时候,我们把疫苗装在一个长20厘米、高35厘米的冷藏包里。一个冷藏包大概可以装60支疫苗,再放上冰袋。在10-12小时内,疫苗不会因温度过高失效。但如果去的是偏远一些的村寨可能在当地过夜,这就需要单独拿一个冷藏包,装上冻好的冰块,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换冰。打疫苗的时间很紧张,如果24小时内打不完,又没有冰块了,就必须要放到冷链点储存,否则疫苗也会失效。为了解决疫苗储存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我们项目组采购了很多太阳能冰箱,安置在去各个村沿途的路上。提前在冰箱里冻上冰块,路过的时候可以换。如果没有按计划打完疫苗,也可以先送到冷藏点冷藏。我记得有一个村寨特别偏远,车开不进去,还是武装部队派直升机把冰箱运进去的。2015年的时候,我们基本完成了缅北地区冷链系统的建设,能够支持现在新冠疫苗的接种。除了时效,让没有医疗基础知识的百姓接受疫苗,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2015年8月,项目副经理老孟和团队去一个寨子打疫苗,那是一个之前从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村寨。去之前老孟以为政府人员已经和百姓沟通清楚要给孩子接种疫苗的事情了,进村才发现和百姓破除沟通层面的隔阂有多困难。这个村寨的路是土路,不能骑摩托,村长还派人帮忙拿疫苗,走了40多分钟。到村寨他们发现,村长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了。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滋生了流言,村里流传着拿孩子做实验的说法,甚至说如果女孩打了针就不能生孩子了。百姓的态度和村长一样,很抗拒。第二次去的时候,老孟带上了区卫生所的人,跟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打疫苗。但是专业名词百姓又理解不了,这一次也没有打成。第三次去,派了一个做妇女工作的人同行。当时寨子里麻疹的传染率和致死率很高,他们跟百姓解释说,打针可以降低孩子的死亡率。现场的另一个同事撸起袖子给百姓看自己胳膊上打疫苗留下的疤痕。村民们半信半疑的让孩子们接种了疫苗。 ■ 疫苗接种这次打完疫苗,我们团队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9点钟。刚坐下,就接到了村民打来的电话,说有孩子发烧。其实,打疫苗之后发烧是正常现象。但是晚上11点,老孟还是带人回到村寨,帮孩子退烧,让村民们放下心。看见我们没有打完针就不管孩子,百姓才彻底打消顾虑。一来二去,百姓和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有时候没及时去,百姓还来问,为什么没去打疫苗。我们接触到的缅北百姓其实很单纯,也很善良,在缅北28年,办公室没有丢过任何东西。但是由于缅北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在靠近中缅边境线的城镇里,手机能接收的微弱信号都来自中国。最近两年很多外地人来到缅北做电信诈骗,我们的手机号每年要去公安系统做备案,否则跟国内联系频繁一点,就可能被封号。张光云的手机和微信都被封过。诈骗团伙在缅北发展起来之后,当地的赌博产业也繁荣起来,一个产业的诞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工作机会。以我们给志愿者的补贴为例,每个志愿者每个月能拿到大约200元人民币,有一些地区每个月则只有补贴35斤大米。但是在赌场打工,一个月可以赚1000元工资。老孟那里培训过的两个志愿者,最后选择去了赌场。生存的本能在某些时刻会影响人的选择,因为理解,我们甚至没有愤怒和谴责。现在团队全职的工作人员有70%是缅北的本地人,另外30%来自中国。缅甸高等教育学校会教授英文,工作的时候,大家用英语沟通。有这么多缅北人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果有一天项目结束了,我们回到中国,缅北的同事还可以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在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地区,让百姓拥有最基本的、活下去的权利。
■ 疫苗接种这次打完疫苗,我们团队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9点钟。刚坐下,就接到了村民打来的电话,说有孩子发烧。其实,打疫苗之后发烧是正常现象。但是晚上11点,老孟还是带人回到村寨,帮孩子退烧,让村民们放下心。看见我们没有打完针就不管孩子,百姓才彻底打消顾虑。一来二去,百姓和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有时候没及时去,百姓还来问,为什么没去打疫苗。我们接触到的缅北百姓其实很单纯,也很善良,在缅北28年,办公室没有丢过任何东西。但是由于缅北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在靠近中缅边境线的城镇里,手机能接收的微弱信号都来自中国。最近两年很多外地人来到缅北做电信诈骗,我们的手机号每年要去公安系统做备案,否则跟国内联系频繁一点,就可能被封号。张光云的手机和微信都被封过。诈骗团伙在缅北发展起来之后,当地的赌博产业也繁荣起来,一个产业的诞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工作机会。以我们给志愿者的补贴为例,每个志愿者每个月能拿到大约200元人民币,有一些地区每个月则只有补贴35斤大米。但是在赌场打工,一个月可以赚1000元工资。老孟那里培训过的两个志愿者,最后选择去了赌场。生存的本能在某些时刻会影响人的选择,因为理解,我们甚至没有愤怒和谴责。现在团队全职的工作人员有70%是缅北的本地人,另外30%来自中国。缅甸高等教育学校会教授英文,工作的时候,大家用英语沟通。有这么多缅北人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果有一天项目结束了,我们回到中国,缅北的同事还可以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在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地区,让百姓拥有最基本的、活下去的权利。
- 点击上图购买「在人间」新书《人间记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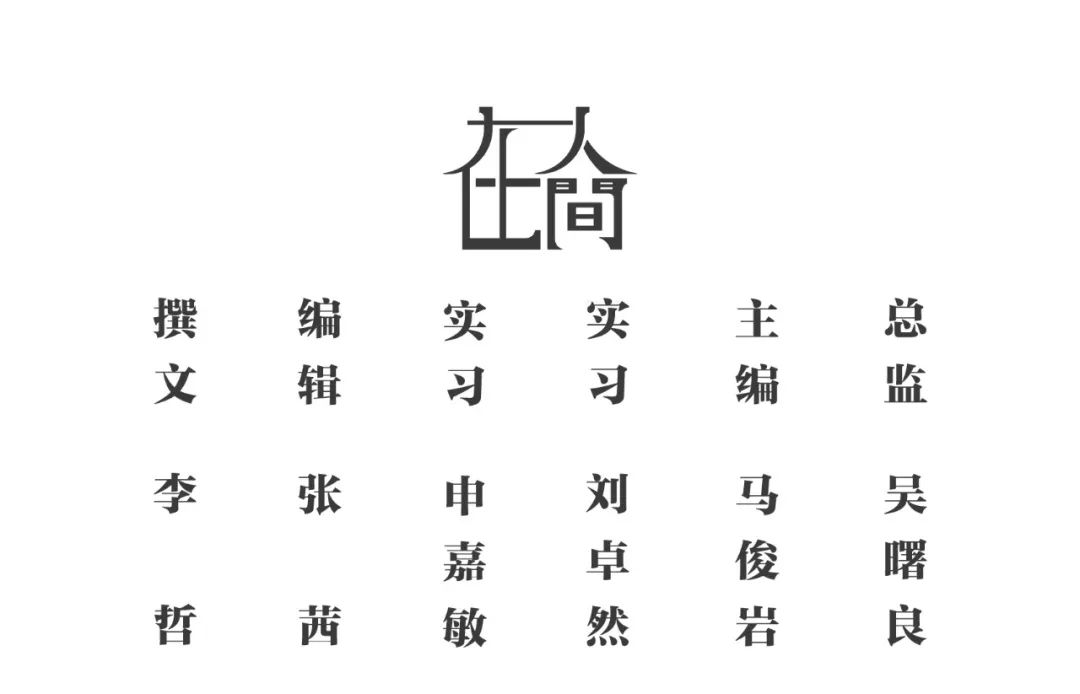
凡注明“在人间Living”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或在人间living栏目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任何方式使用;已经由本栏目、本网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在人间Living”或“来源: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违反上述声明的,本栏目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