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后不久,我到一家叫「摆渡人」的殡葬服务公司做「观察员」,起初是想弄明白这群能见度不高的职人平时如何上班。观察上岗的第一天,我在闲置办公桌上赫然发现 27 只排排坐的小橡皮鸭。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她们上班也喝手打柠檬茶。观察员生涯的最后一个结论则诞生于太平间。在最后一天到来前,和我沟通最多的小沈说,你不是一直想去医院太平间看看吗?我们明天一起去吧。她又说,正好最近几天在搞软装。在也许是国内独一份拥有软装的太平间对面,值班室的一线大哥分享 wifi 密码,并贴心解释,这里是地下一层,信号是一格没有的。小沈给我科普角落里那个像雪糕柜的箱子,说里面装的是医疗残肢,断手啦,断腿啦,并热心提议,你想看看吗?我边说「不了不了」边使用反向探戈舞步滑出。站在门外,我发现:太平间里有股冰柜味儿。在橡皮小鸭子和室内软装之间,还有一些。这里没有写什么能够满足猎奇心的故事,没有鬼,没有都市传说。仅仅是一些对殡葬的观察,和对死亡的小思考。顺便,还有和能接触到的所有岗位工作人员的聊天。走上那家「豆腐饭」饭店台阶,有人告诉我,按照习俗,从殡仪馆出来的人要跨个火盆。在我身前的玻璃地砖下,一团饱和度很高的红光在演绎一种介于跑马灯和喷泉彩灯的视效。推行现代无烟环保后,火盆进化成了电子火盆。小沈说,跨吧,体现一个参与感。
 他们死了
他们死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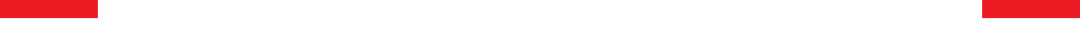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早上八点,太阳斜照老沪闵路的一侧,背阴那侧依然凉。我到早了。后来才晓得,市郊的老殡仪馆从来没有整点开始的追悼会。这一来就让我体验到一线殡葬人的必修课:等待。侯师傅穿西装,背着黑包,在太阳底下抽烟。虽然只见过两面,他还是认出脸,冲我点点头。周围推花篮的小车逐渐变多,八点半,门卫室有了动静。丧属陆续步入,穿过左侧办事楼,迈向右边弧形排列的告别厅,馆内不知谁养的花狗在众人间穿巡。有人给逝者至亲分发白绸系在腰上,丝絮因为静电粘满深色大衣。一定有人发现了,但也没人出声去拍打。
早上八点,太阳斜照老沪闵路的一侧,背阴那侧依然凉。我到早了。后来才晓得,市郊的老殡仪馆从来没有整点开始的追悼会。这一来就让我体验到一线殡葬人的必修课:等待。侯师傅穿西装,背着黑包,在太阳底下抽烟。虽然只见过两面,他还是认出脸,冲我点点头。周围推花篮的小车逐渐变多,八点半,门卫室有了动静。丧属陆续步入,穿过左侧办事楼,迈向右边弧形排列的告别厅,馆内不知谁养的花狗在众人间穿巡。有人给逝者至亲分发白绸系在腰上,丝絮因为静电粘满深色大衣。一定有人发现了,但也没人出声去拍打。 告别厅前等待的侯师傅
告别厅前等待的侯师傅 尚未准备到位的告别厅内景
尚未准备到位的告别厅内景
仪式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葬礼进行曲中,我看到平生所见的第一具遗体。那是位银发的奶奶,躺在棺木中显得很瘦小,下巴内缩,和遗像上那张圆润的笑脸并不太像。照片里她戴着珍珠项链,黑发蓬松。疫情开始后,为了杜绝密闭空间内的潜在传播,告别厅不再允许关门。不同厅室内的哀乐与哭喊交融,门外偶有闲谈,不远处还有一队吹拉弹唱。奶奶平静地躺在亲人们中间,司仪小陈在一旁引导,侯师傅在给她铺棺。按日剧里的叫法,侯师傅是「入殓师」,在摆渡人,这个岗位叫「生命礼仪师」。入殓完成时,逝者棺木里会有 19 件不同物品以备其「上路」后的花销。寿衣、寿鞋不必说,还有梳子、金银元宝、各类符纸,一层一层平铺。最后,他摘下花篮里的寿菊与白蔷薇,将花瓣铺满逝者四周。我蹲着帮忙拆塑封纸,默默感叹这个看似莽汉的人手咋这么巧。一直沉默的侯师傅忽然用后脑勺低声叮嘱了一句,「落在地上的不要捡。」事后站在门口,我被科普了一阵小鬼买路钱的知识点,这次出声感叹,侯师傅真厉害,不回头就知道身后有个菜鸡,心还很细呢!铁汉侯师傅抽着烟,憨厚一笑,然后冲正用那声优一样磁性的嗓音,向我们描述殡仪馆前辈如何恶作剧恐吓后辈的小陈说,你带她们去看看等会儿的故人沐浴吧。 殡仪馆的故人沐浴入口隐蔽
殡仪馆的故人沐浴入口隐蔽
所谓「故人沐浴」是近些年才在国内得以推行的一项服务,用现代 SPA 的概念对遗体进行细致护理,时长 30 至 90 分钟不等,家属可在一旁观礼。由于逝者无法自主移动躯体,护理师往往需要长时间搂抱或贴面完成遗体翻身等动作。早期在进行专业培训与推广时,曾在业内引起极大讨论。侯师傅说的「等会儿」是一个半小时后,这回,一起坐在玉兰树下抽烟等待的人换成小陈。中午的太阳把椅子烤暖和了些,小路上不时经过手执黑伞与布袋的人。「遗像与骨灰尽量都不要见光,」小陈解释说,「所以负责些的殡葬人员会提前帮家属备好遮光物。」年后殡仪馆陆续恢复正常运转,迎来一批领取骨灰与补订丧葬仪典的高峰。承接丧席的饭店从早到晚人声嘈杂,以小时为单位翻台 —— 这是追悼会后的另一惯例:出席人员在仪式结束后来到这儿,喝杯红糖水,入座吃这最后一顿以逝者名义发起的餐宴。与告别厅不同,故人沐浴区有粉色墙体和米黄色装饰,播着轻音乐。两位工作人员推着服务车开始擦洗。首先是剪指甲,从盖住遗体的毛巾下慢慢抽出一只手臂,指甲剪落下的响儿在无人出声的小房间里很清脆。逝者是位七十出头的爷爷,面色说不上灰败,身形枯瘦。一个人给他按摩四肢和涂抹沐浴露,另一个给他洗头、洁面,再贴上面膜。戴森吹风机轰轰响起时,逝者女儿开始抹眼泪。结束全身清洁,盖上干毛巾,化妆师上前做最后的遗体美容。女儿全程望着平躺在面前的父亲,末了提了个简单要求,「我爸爸的唇色还可以再深些,但不要太红。」观礼结束,遗体要推回存放处等待大殓,走出房间前,她上前握着刚剪好、磨完指甲的手说,爸爸侬好生休息,明天再来看侬。我后来试图回想那一天,在披花瓣的老奶奶和敷面膜的老爷爷面前的几十分钟里,我在想些什么。发现当时罕见地什么都没想。望向一个不再起伏的身体,就像望着一个「零」。作为一个存在时间和人类族群的存在等长的行业,殡葬礼俗大多古老且绵延。「守灵」的英文是「 wake 」,说起来,现今的仪式在过去大多有其实际用处,停灵与出殡时的喧闹是为「唤醒」过去医疗条件不佳下的假性死亡,在所有唤醒的努力过后,死的现实被确认。「一具不再运转的躯体,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人不复存在的证据。」那天的一切仪式对我来说都指向模糊,唯有两个瞬间。盖棺敲钉时,梆梆梆,一声比一声带来下坠的凉意;沐浴洗脸时,花洒淋过仰躺的脸,条件反射,鼻腔涌出溺水感。那两个时刻,我忽然有了实感。她不会感到幽闭,他不会遭到呛咳。他们死了。 造物钟爱对称
造物钟爱对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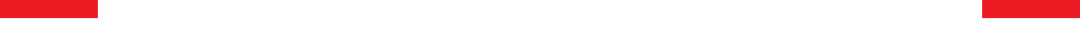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小时候过年,我家一直有个「神秘的仪式」。那会儿住一楼,奶奶会在饭菜全部摆上桌后,打开屋门、前院单元门、后院花园门,用金钟罩锁住我们几个馋嘴小孩,然后宣布:让祖宗先吃。过个三五分钟,她和爷爷对空气打个招呼,依次关上门,然后再宣布:坐下,吃吧。有次我忍不住向我妈提问,祖宗吃饭这么急,鸡汤不会烫嘴吗?被我妈一筷子敲脑袋上。疼痛让我模糊地明白,祖宗自有他/她吃饭的一套方法,同样这只鸡腿,我吃,祖宗也吃,我们属于是花开并蒂,各表一枝。直到最近某次,小沈与她同事小卷聊天,话题始于「烧冬衣」,说是曾经服务的一位海葬逝者,某天托梦给子女,说自己冷。子女转天便找到她们,安排烧了些厚衣服。「在海里是会容易冷的。」小沈说。「你说地府也有快递小哥吗?不然我们烧的东西要咋交到家里人手里呢?」小卷问。「你傻啊,」小沈回,「烧东西和祭祀时都要写姓名,讲究的还要生辰八字,不然收不到。」她想了想又补充,「不过地府当然也是有公差的。」我由此想到一个要紧的问题,我可从来没见爷爷奶奶出示过祖宗的姓名八字,真按这个说法,那些年里和我共享阴阳鸡腿的到底是谁呢?《殡葬人手记》这样介绍这个职业:「(殡葬服务)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会有人死去的现实。」天主教徒相信灵魂得救升入天堂,天堂服务区和人世并不打通,那里当然也不需要冬衣。而我们接纳了一个「阴间」,造物钟爱对称,世俗生活的一切在那里皆有对应。在镜子两面,我们各过各的,逢年过节串个门送个礼,「事死如事生」。
小时候过年,我家一直有个「神秘的仪式」。那会儿住一楼,奶奶会在饭菜全部摆上桌后,打开屋门、前院单元门、后院花园门,用金钟罩锁住我们几个馋嘴小孩,然后宣布:让祖宗先吃。过个三五分钟,她和爷爷对空气打个招呼,依次关上门,然后再宣布:坐下,吃吧。有次我忍不住向我妈提问,祖宗吃饭这么急,鸡汤不会烫嘴吗?被我妈一筷子敲脑袋上。疼痛让我模糊地明白,祖宗自有他/她吃饭的一套方法,同样这只鸡腿,我吃,祖宗也吃,我们属于是花开并蒂,各表一枝。直到最近某次,小沈与她同事小卷聊天,话题始于「烧冬衣」,说是曾经服务的一位海葬逝者,某天托梦给子女,说自己冷。子女转天便找到她们,安排烧了些厚衣服。「在海里是会容易冷的。」小沈说。「你说地府也有快递小哥吗?不然我们烧的东西要咋交到家里人手里呢?」小卷问。「你傻啊,」小沈回,「烧东西和祭祀时都要写姓名,讲究的还要生辰八字,不然收不到。」她想了想又补充,「不过地府当然也是有公差的。」我由此想到一个要紧的问题,我可从来没见爷爷奶奶出示过祖宗的姓名八字,真按这个说法,那些年里和我共享阴阳鸡腿的到底是谁呢?《殡葬人手记》这样介绍这个职业:「(殡葬服务)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会有人死去的现实。」天主教徒相信灵魂得救升入天堂,天堂服务区和人世并不打通,那里当然也不需要冬衣。而我们接纳了一个「阴间」,造物钟爱对称,世俗生活的一切在那里皆有对应。在镜子两面,我们各过各的,逢年过节串个门送个礼,「事死如事生」。 这个贡品叫「花馍馒头」,是摆渡人供饭必备久卧病榻的家人故去后,「供饭」仪式变得重要。病中人多有忌口,吃饭不香,怀着不让家人「饿着肚子上路」的愿望,不少家属会在「做七」时备下亡者生前爱吃的菜肴、茶、酒,在礼仪师引导下完成供奉。有次经过供饭的佛龛,看到桌上摆满熏鱼、红肠、糟虾和条头糕,旁边还有瓶「阿拉老酒」,我默默想,要是我家祖宗怕是不会吃的,他老人家会说,没加豆瓣酱的东西老子统统不要吃!那天回到家,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她们问我最近有什么新发现。我吃了几颗花生米,很忧伤地说,我听说,地府里也是要考编的。「稀巴烂!那死了还有什么意思!」考研失败的朋友把杯子摔得嘭嘭响。死有什么意思,我也时常想。我不同意「死者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准确来说,活着的人更需要。这需要并非不正当。任何一位丧子的父母,都会厌恶前来安慰的人说出那句「孩子已经走了,那里不过是一具躯壳」。小沈回忆过多年前在老的「殡葬一条龙」处所受的折辱,那位经手人将一包锡纸随手倒进棺木,元宝直接砸在了故去姑姑的脸上。经历死亡的家庭看重「由活着的人(自己)宣告死者之死」的权利,就像新生儿的满月宴,新婚的喜宴,到场的会是一群「需要认识 ta 」的人。在「死亡的发生」和「死亡的意义」之间的那段路,有人选择以仪式填补,人们由此赋予一段人生以说法。摆渡人有过一场特殊的追思会,作为主角的老人在年轻时主动冲进事故现场救险,全身遭受大面积化学烧伤,此后一生都在反复经历手术与复健,长期行动不便。照片上他笑得很豁达。老人生前爱收集旧物件,喜欢旅行,受伤后,喜欢成了遗憾。策划师小李与团队一起,在大厅挂起世界地图,摆上做旧的家具,台灯,还有老人搬去新住所那天的《新民晚报》,台篮让花艺师设计摆成船形,布好彩灯,特意避开环节中所有的明火元素。最后,小李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部移动投影仪,将 40 多岁意气风发的主角投在了那幅巨大的地图上。追思会来的多是家人,老人生前的工友、子女、侄甥、孙辈用各自的方式分享关于他的过去。发言人提到某个时间点,人们探头低声确认;提到某件大事,人们同时泛泪叹气。像天底下所有聚会一样,也有走神刷短视频的人,有席间就酒不离口神态涣散的人。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在场所有人共享新的记忆:世界从此少了一个勇敢的亲人。你能看到基因在这个屋里留下的痕迹,他们带着像小叔的鼻梁,像小舅的宽额头,像爸爸的眼睛,像外公笑起来的嘴角,互相告别,离开这里,散进原本生活里。
这个贡品叫「花馍馒头」,是摆渡人供饭必备久卧病榻的家人故去后,「供饭」仪式变得重要。病中人多有忌口,吃饭不香,怀着不让家人「饿着肚子上路」的愿望,不少家属会在「做七」时备下亡者生前爱吃的菜肴、茶、酒,在礼仪师引导下完成供奉。有次经过供饭的佛龛,看到桌上摆满熏鱼、红肠、糟虾和条头糕,旁边还有瓶「阿拉老酒」,我默默想,要是我家祖宗怕是不会吃的,他老人家会说,没加豆瓣酱的东西老子统统不要吃!那天回到家,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她们问我最近有什么新发现。我吃了几颗花生米,很忧伤地说,我听说,地府里也是要考编的。「稀巴烂!那死了还有什么意思!」考研失败的朋友把杯子摔得嘭嘭响。死有什么意思,我也时常想。我不同意「死者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准确来说,活着的人更需要。这需要并非不正当。任何一位丧子的父母,都会厌恶前来安慰的人说出那句「孩子已经走了,那里不过是一具躯壳」。小沈回忆过多年前在老的「殡葬一条龙」处所受的折辱,那位经手人将一包锡纸随手倒进棺木,元宝直接砸在了故去姑姑的脸上。经历死亡的家庭看重「由活着的人(自己)宣告死者之死」的权利,就像新生儿的满月宴,新婚的喜宴,到场的会是一群「需要认识 ta 」的人。在「死亡的发生」和「死亡的意义」之间的那段路,有人选择以仪式填补,人们由此赋予一段人生以说法。摆渡人有过一场特殊的追思会,作为主角的老人在年轻时主动冲进事故现场救险,全身遭受大面积化学烧伤,此后一生都在反复经历手术与复健,长期行动不便。照片上他笑得很豁达。老人生前爱收集旧物件,喜欢旅行,受伤后,喜欢成了遗憾。策划师小李与团队一起,在大厅挂起世界地图,摆上做旧的家具,台灯,还有老人搬去新住所那天的《新民晚报》,台篮让花艺师设计摆成船形,布好彩灯,特意避开环节中所有的明火元素。最后,小李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部移动投影仪,将 40 多岁意气风发的主角投在了那幅巨大的地图上。追思会来的多是家人,老人生前的工友、子女、侄甥、孙辈用各自的方式分享关于他的过去。发言人提到某个时间点,人们探头低声确认;提到某件大事,人们同时泛泪叹气。像天底下所有聚会一样,也有走神刷短视频的人,有席间就酒不离口神态涣散的人。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在场所有人共享新的记忆:世界从此少了一个勇敢的亲人。你能看到基因在这个屋里留下的痕迹,他们带着像小叔的鼻梁,像小舅的宽额头,像爸爸的眼睛,像外公笑起来的嘴角,互相告别,离开这里,散进原本生活里。 追思会的签到台,签名簿会后将烧给逝者,到场每人会佩戴一朵小白花
追思会的签到台,签名簿会后将烧给逝者,到场每人会佩戴一朵小白花
故人沐浴时有段开场白,「沐浴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告别这个世界做的最后一件事。」生死首尾相衔,你瞧,造物果然钟爱对称。我奶奶至今还在坚持神秘的仪式,只是我家现在不住一楼了。许多次我想要开口提醒,假如真的有死后世界,按道理,鬼魂没法乘电梯。看了眼我妈手里的筷子,忍住了。 人就这样
人就这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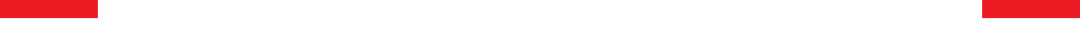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所有的死亡都带来缺失,抬出「圆满」来显得勉强。丧葬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乐观最积极的一门语言,陵园都叫「松鹤堂」「福寿园」,讣告用词也充满告慰,年老者用「仙逝」,中年会用「享年」,年轻的用「得年」。但无论如何,临死之际,大多数情况下,人是活不够的。
所有的死亡都带来缺失,抬出「圆满」来显得勉强。丧葬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乐观最积极的一门语言,陵园都叫「松鹤堂」「福寿园」,讣告用词也充满告慰,年老者用「仙逝」,中年会用「享年」,年轻的用「得年」。但无论如何,临死之际,大多数情况下,人是活不够的。 尚在布置的太平间门口
尚在布置的太平间门口
我在生活中见过两个活得极不耐烦的人,如果算上没见过的,那么还有戈达尔。这两位一个是每天坐着轮椅在小花园抽香烟的百岁老阿姨,还有一个和我同龄,老爱念叨,唉,做人没劲。白事管家蒋老师同我聊到墓地,作为购买者与使用者角色分离的不动产,人们对它的购置需求大致差不太多。没有小孩的家庭看重朝向、方位、有无遮挡物;有小孩的家庭则诉求更多些,墓碑上多刻葡萄、松鼠,寓意多子多福,希望长辈故去后,能对子孙多多庇佑。我没忍住插了句嘴:人也太累了,死了不能休息,还得忙着去给后代加 buff 。一位接完家人骨灰的年轻人在办公室里支吾,他说母亲也还在病中,实在无力同时顾及给父亲落葬,骨灰可以暂时寄存吗?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自如负担突如其来的墓地费用,工作人员安慰并提出了解决建议,彼此熟练而默契。无形中,从事殡葬服务的人帮每个家庭担了一些东西,像某位守在不远处的第三责任人。在当事人因打击而失去正常步伐时,她们的在场提供了支柱。「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那份「不休」便是死者撒手后,由他的周围人和摆渡人所共同承担的。小李印象最深的服务是「一次永无达成的和解」,因为孩子无法原谅母亲的养育方式而关系破裂,在弥留之际,母亲对赶来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辈子对你的教育是没问题的。」没有人知道这句遗言究竟是肯定了眼前长大成人的孩子,还是肯定了自己。蒋老师记得一位在疫情时去世的外地年轻人,孩子的父亲和舅舅匆匆赶来处理后事,他们只有一天时间,为了不让在家留守的孩子母亲起疑,火化后骨灰被当即抛洒进江中。他们说,不这样做的话,这位母亲一定会立刻跟着孩子去的。为了让人活下去,人的死被蹩脚地遮盖。更不必说在豆腐饭席上因为遗产而大打出手的人,在太平间里冷冻了十几年而被家人拒绝认领的人,还有那些过早离世的孩子。总有一定比例的家庭放弃领取小孩的骨灰。在巨大创伤面前,人们为了继续走下去,做出艰难的选择。老人的离世指向历史与记忆,孩子的离世却总在提醒失去的未来和梦想。协助处理家庭纠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位老人迟迟无法落葬,因为舅舅藏起领灰证拒绝配合,外孙女作为对接人只能干着急。蒋老师分享时轻描淡写,「你要有一个基本判断,一个孩子不会真的不想要自己老妈的骨灰。」剩下的就是劝解,让对峙双方愿意互相说出,真正的疙瘩在哪儿。哲学家齐奥朗相信「体验就是表达,死亡的唯一形式就是对它的体验」,除此之外的范畴都不算是死亡,顶多算是相关。凌晨两点,朋友又来对我念叨,「做人没意思」。我终于没忍住,现学现用,「做人本来就是没意思的。」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觉得没意思,说明你做人做上道了。」我问小李和蒋老师,从业这些时间,有没有一件依然放不下的事情。蒋老师说,有一次去医院接一个刚去世不久的逝者。那个人蜷在病床上,全身死灰,痛苦得已经不成人形。她被吓住了,那就是死,是赤裸裸的死。小李说,前几天办追思会的那道投影,我调整了好多次,最后老人的脚还是没能完全落地。下次,我要让他站在地上。 追思会那天,阳光投在座椅上
追思会那天,阳光投在座椅上
*注:正文斜体内容引用自托马斯·林奇《殡葬人手记》
文中小沈、侯师傅、小陈、小卷、小李、蒋老师为化名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尚未准备到位的告别厅内景
殡仪馆的故人沐浴入口隐蔽
追思会的签到台,签名簿会后将烧给逝者,到场每人会佩戴一朵小白花
尚在布置的太平间门口
追思会那天,阳光投在座椅上
尚未准备到位的告别厅内景
殡仪馆的故人沐浴入口隐蔽
追思会的签到台,签名簿会后将烧给逝者,到场每人会佩戴一朵小白花
尚在布置的太平间门口
追思会那天,阳光投在座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