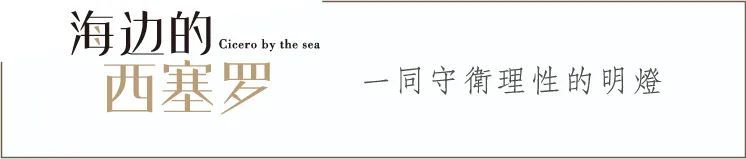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各位好,今天是七夕,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请假休更一天,祝大家节日快乐。发篇旧稿子吧。
引入正文之前,我想先多说两句,我在大学的时候选过一些很奇葩的课,因而接触了一些可能今天英文世界都不再版的书。意外得知了十九世纪“进化论”刚刚出现时,英国社会依照“科学”搞性别歧视的风气。
是的,如这篇文章所提到的:19世纪的很多进化论研究者们,放在今天都是典型的直男癌。
达尔文和赫胥黎都认为女性在生理上要弱于男性,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则更进一步的认为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庸。他觉得女性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给“高质量男性”充当生育机器。
而这观点是被当时的英国新兴工厂主们乐于接受的,因为这一方面这帮人就自认为是高质量男性,进化论这样说方便他们摆脱传统宗教婚姻的束缚外出找小三。另一方面此种论调,也给他们开设工厂时以极低的价格的雇佣女工,不给其与男性对等的劳保待遇,甚至对女工进行性敲诈,提供了“理论支持”。
于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指导”下,19世纪的英国女工处境是极端悲惨的,她们不仅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妇女一样需要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还要去工厂做工,并时常接受工厂主与监工们的五花八门的性讹诈——敢不接受我潜规则,我就解雇你!
所以恩格斯就曾经说:“我曾经在爱彻斯特一家精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布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能称为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形很难看。”

所以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的珂赛特,真的只是更悲惨现实的冰山一角。
对这些理论,虽然我知道它是纯粹的学术推演,但我依然觉得他们是“邪恶”的。这也促使我改变了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之前我只知道19世纪末的女权运动,一度非常激进的,有些行为堪称“性别恐怖主义”。今天欧美女权运动那些口号和行为,相比之下都是弟弟,但了解了更多内情后,我发现这种运动原来情有可原的——它不过是对同一个世纪那种过于强烈而变态、且自称有“科学依据”的男权压迫的一种反制。
我无法想象一个现代男人如果变性穿越回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英国,能采取什么比当时的女权主义更温和的行动。
至少在19世纪,女权主义是被动激发的,我们要感谢女性,发起的是一场运动而不是起义,因为那一次,真的,是“男方先动的手”。
同时,这种学习,也提示我产生了新一层思考——人类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
你看,十九世纪的进化论信徒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含贬义),他们通过自认为非常精明的“科学观察”和“理性推演”,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比道德更“科学”的结论,可以“科学的”歧视、、压迫女性。
可是这种“科学”是错误的,看完下面这篇文章你会了解,19世纪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性别的“科学的偏见”,其实并不科学,它只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全面——这种认知不全面在人类的科学史上曾经频繁发生,且会永远发生下去。科学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掌握对某件事的最终真理。
所以无论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或者任何人对其他人,我们都不要基于自己觉得对的什么理念采取什么“断然行动”。保持谦卑,保持谨慎,尊重他人,尊重道德,以及最重要的,像宗教曾教育我们的那样,彼此相爱。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最终真理,那就是它了吧。
这篇文章我写到最后,最大的感触是:科学的论证、理性的推断,推演了半天,其实只是证明了一个道德的教化和宗教的教诲已经预先告诉你事情,在科学和理性的尽头,道德和宗教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当然这不是说科学和理性就是不对的,而是说,如果你依照自己的科学和理性得出了一个与道德直觉完全相悖的结论,那请别妄下断论,你最好再想想——因为八成是你自己想错了。
七夕节,不管把它说成是“中国情人节”是否涉嫌过度解读,我都希望大家能在这一天彼此相爱。
七夕快乐!
人类为什么要分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事儿在当下谈,其实是挺引战的。如果你经常逛微博、知乎或推特,你会发现如今的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主义者彼此已经何等水火不容了。记得新冠肺炎刚开始全球大流行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公布一个调查报告,称在其调查的206,128名患者中,男性接受重症监护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死亡率可能性高出60%。所以该机构呼吁给男性新冠肺炎感染者以更多的重视。这个调查本来也没啥,但很多极端女权主义者立刻“给予男性患者更多重视”的结论不爽。澳大利亚一位39岁的极端女权主义作家克莱门汀·福特更在推特上直接称:“即便这是事实吧,也不错啊……看来新冠病毒杀死男性的速度还不够快”。这位福特小姐,算是个最典型的极端女权——叫嚣要“将男人控制到有限数量”那种。够令人吃惊的了吧,但福特这样的极端女权主义者在当今的欧美其实颇有市场,这些人将女权的目标从颠覆旧有的男权社会提高到了“消灭男人”的程度。甚至认为,等到技术能够让人类实现孤雌生殖了,男性作为一种“有缺陷的性别”就可以从历史中退场了。
100多年前,当世界妇女联合会将3月8日定为妇女节时,她们心中所想的“女权”是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投票权、受教育权和与男子同工同酬等权益。像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女权先驱,绝不会想到,百年会有人打着“女权”得旗号提出这种“性别灭绝主义”的主张。当然,我们得说清楚,与这种极个别极端女权“思想家”口嗨嘴炮相对应的,是极端男权仍在世界上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更普遍、更深刻的歧视:时至今日,在很多地区、甚至民族、宗教的文化当中,依然将女性视为可以奴役、甚至不被当人看的对象。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女儿被视为可被原生家庭榨干的一件“商品”、甚至是对女性的歧视、骚扰甚至性侵……可以说,这一百年来,对女权主义的越发“极端化”,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顽固而深刻的男权,是起到了刺激的作用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一战后协约国一方严厉制裁德国,结果反而激发了更为激进的纳粹党的上台。但既然两性之间的矛盾如此深刻,择偶、交配、繁育的过程如此麻烦,人类为什么还会选择两性繁育这种看起来十分低效的方式进行繁衍呢?试想一下,如果人类能够像细菌一样搞无性生殖,那似乎是一件很欢快的事:宅男和剩女们再也不用为被逼婚发愁了,哪天不高兴了,直接有丝分裂一下,复制一个自己,就能给家里交差。国家也不必为少子高龄化发愁,人口将像培养皿里的细胞一样快速增长。什么男女矛盾、性别歧视、择偶问题、婚姻问题通通都从根源上解决,这岂不美哉?不仅是人类,如果你去观察所有宏观的多细胞生物——动物、植物、真菌等等,你会发现它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选择用两性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的。相反,无性生殖反而被牢牢的压制在单细胞的原生生物界和多细胞生命的极少数场景中。越高等、行为越复杂的生物,反而越抛弃了看似高效的无性生殖,选择费时费力的有性生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关乎生物学发展,也影响了我们对两性的看法。与很多人的想当然不同,欧洲女性地位的最低谷,不是出现在宗教时代,而是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以后。因为基督教虽然宣称“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似乎暗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但这个故事好歹承认了女性同样也是上帝他老人家意志的体现。诗人们一高兴了,还会依据该故事赞美,说女性是“上帝最后也最美的造物”。听上去还蛮高端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明白:按照繁殖效率而言,无性繁殖似乎比有性繁殖更高效。这个思想被英国后来的进化论学者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总结为性的双倍成本学说(two-fold of sex),也被称为“雄性成本悖论”。简单地说,在一个有性生殖的群体中,由于只有雌体才能给种群增长带来贡献,雄体则只负责吃饭睡觉打炮,它的繁殖效率将是执行无性生殖(或孤雌生殖)的同类群体一半。如果没有其它的平衡机制,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有性生殖将会很快因为繁衍成本过高,被同种的无性生殖所淘汰。可如前所述,所有宏观生物几乎都采用了有性生殖。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怎么给雄性的存在以理由呢?于是,达尔文同志和他的小迷弟们就开始胡扯了——用歧视妇女以及所有雌性生物的方式。事实上,在《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和性选择》这两部光辉著作之间,达尔文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男性的后裔(Descendants of men)》的小册子,这本书现在因为政治过于不正确,大家基本都不怎么提了。因为在该书中,达尔文用进化的视角去审视两性,把女性歧视到了非常不堪的地步。他在书中直接声称:进化使男人比女人“优越”。对达尔文来说,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智力和艺术领域。他写道:“如果把诗歌、绘画、雕塑、音乐鉴赏的地位和表演、历史科学和哲学等领域最杰出的男性和女性列为两个榜单,这两个榜单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基于这种观察,达尔文认为,生物之所以选择有性繁殖,就是为了让雄性摆脱生殖的负担,进化的更完美,以完成种间和种内斗争。等到优异的雄性在“适者生存”的筛选下脱颖而出之后,雌性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实现有利突变的扩大化。这样两性生殖的效率,就比无性生殖更高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达尔文觉得自己解释通了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很对,那恭喜你,你对进化论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你也很有“直男癌”的潜质。这套理论其实已经给歧视女性埋下了理论根基。因为在这种描述中,雌性生物被描述为了给斗争优胜的雄性繁衍后代的工具。如果该理论正确,那么“优秀”的、进化的更完美的雄性占有更多雌性资源,就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立者斯宾塞,就是达尔文这一思路继承者和阐发者。斯宾塞不仅附和了达尔文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他认为为了人类的繁荣昌盛,女性就必须“献身于生殖”:不需要受太多的教育,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女性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智的选择”更优秀的男性,为他们生育更多的子嗣。也基于这套阐发,斯宾塞还认为女性基于爱情的盲目,她们基于爱情选择一个失败者当配偶是不道德的。相反,斯宾塞认为,一个成功男性,背叛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包养情人,生育私生子,则是可以容忍的。反正基于达尔文的理论么,一切为了给更“优秀”的“适者”繁衍更多后代。我知道很多女性读者读到这里已经气的快跳脚了,是的,这个斯宾塞就是这么直男癌,这也是为什么直男癌几乎是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基本气质。
但斯宾塞这个说法,肯定很得当时欧洲上流那些油腻大叔的喜欢的。这也好理解,这帮人很多都“家外有花”么。听“斯老师”这么一讲,原来我们这么干都符合先进科学的发展方向啊!当然举双手赞成。更加理直气壮地出去采野花了。多说一句,这套理论在英国盛行的时候,正赶上辜鸿铭在欧洲留学,辜鸿铭一看,照着这么说,我们中国的“纳妾制度”大大的好么,比你们偷偷摸摸的干强多了。所以这家伙回了中国以后也大肆宣传“纳妾”等是国粹,还编了那套著名的“茶壶茶杯论”。所以学了半天的辜鸿铭,在两性问题上,也是个德行,因为当时的西方也正时兴对女性的不尊重。而这套理论,给当时正在走向觉醒的女性意识的打击,也是相当巨大的。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肯·福莱特,在他的小说《世界的凛冬》中,编过这么一个段子:到了二战时代,英国有个丈夫叫伯依,虽然有着“子爵”的贵族头衔,却是个渣男。妻子黛西发现他出轨行为之后,他恼羞成怒,挥舞着拳头威胁说:“我将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一样惩罚你!”当然,他妻子黛西是个女中豪杰,闻言立马从壁炉里掏了根烧火棍出来,边朝她丈夫比划边说:“好啊,那我就像个20世纪的新女性一样,给你一点教训。”
的确,想小说所反映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即便那些受教育的上流男性,依然依据社达学说对两性关系的解读,将妻子视为自己繁衍后代的工具。所以打老婆即便是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也是非常常见的事。
但讽刺的是,鼓吹女性应该为优秀男人多生孩子的斯宾塞,自己却一辈子也没讨上老婆。原因不难想见。斯宾塞既不像贵族男性那般富有,还一身这套极度歧视女性的臭脾气。没有女人愿意嫁他,算是对他歧视妇女最好的报复了。用今天的话说,斯宾塞是又穷又“直男癌”,空有满腔社会达尔文主义“淘汰劣等人种”的理想,结果到头来,倒是自己被当“劣等人种”淘汰掉了。
耍了一辈子光棍,理论是对的也算“为真理献身了吧”,斯宾塞对两性的理解对么?很不幸,错得离谱。
到了1930年左右,英国生物进化学者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Aylmer Fisher)终于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找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那套两性理论中的不对头,并提出了挑战。这个费希尔是搞数学出身的,所以他有更好的数算头脑。他指出,两性的存在当然会利于有利变异个体的繁衍,但这不是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因为在生物界中,单一的一个有利变异,往往并不能让个体在环境变化中成为那个最后的“适者”,“适者”必须要把多个有利变异凑到一起才行。而正是这种需求,让两性繁殖相比单性更为高效。举个最通俗的例子,长颈鹿之所以能在树冠高耸的稀树草原上生活,不仅需要它有“长颈”,还要有“长腿”。如果长颈鹿的祖先是无性繁殖的,这两个突变随机的出现在种群的个体中。那么有很大的概率是出现一只长了长腿的“长腿鹿”和另一只长了长颈的“长颈鹿(伪)”。由于是无性繁殖,双方基因无法交流,这两个变异种的唯一选择只有展开竞争,直到干死一方,另一方占据这个生态位为止。这样进化虽然完成了,但却会丢失一个难得的有利突变。当然,可能有人会抬杠说,凭什么就不能两个突变发生在一个个体上?数学家老费告诉你,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有利突变本来就稀缺的像中彩票,你现在还要一下中两次?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套用赵本山老师的话说:地球非得围着你转,你是太阳啊?相比之下,两性繁殖就优势的多。两种有利变异在种群内部不断地通过交配传播,碰来碰去,很快就会出现一头“长颈”的雄鹿,爱上一头“长腿”母鹿,最终生下长腿长颈的真正“长颈鹿”的情况。这样,适应新环境的一套“好牌”,就在交配中很轻易地拼出来了。这个演化的效率,比坚持“自撸”的无性繁殖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费希尔的这个理论,击碎了达尔文时代旧进化论中那种“雄性的自负”——在他的新体系中,雄性并不再是单独的有利变异的提供方,而是两性同时都是有利基因交换的合作者,双方在合作之下,共同完成了有利突变在种群中的快速传播、重组。但故事到此还没完,费希尔的理论,很快启发了另一位生物学者穆勒。赫尔曼·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穆勒说你这个理论好是好,但只谈有利变异、不谈有害变异,这个故事有点不对吧?毕竟在自然界随机变异的穷举中,有害变异才是大多数么。于是穆勒就提出了更为有趣的“穆勒的棘轮(Muller's ratchet)”理论。穆勒指出,在一个无性繁殖的种群当中,个体一旦出现有害基因的突变,是没有几乎没有概率再变回去,而突变随着繁衍代数的递增早晚都会发生。这就像是机械当中“棘轮”,一旦朝某个方向转动,就没有办法回拨了。而这些有害变异一点点积累,在繁殖到一定程度时,早晚会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这个种群在进化中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优良基因,都在这些有害突变中丢光了,灭亡的丧钟随即敲响。对于多细胞动物而言,它们的基因组又一般比较大,所以它们必须想尽方法来降低自己基因突变的概率。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它们那庞大的基因组就会在繁殖中产生非常多的有害突变,它们就会灭绝。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雌性个体“小红”,她有一个有害突变A和一个正常基因b,在假设一个雄性个体“小蓝”,他有一个正常基因a和一个有害突变B。如果让他们各自单性繁殖,根据“穆勒的棘轮”,他们的后代各自剩余的“好基因”早晚也会在突变中丧失掉。但如果让他们交配,他们子代就会出现四种可能:AB、Ab、aB、ab,在生存压力下,前三种有有害突变的子代将被淘汰掉,而幸存的ab完美的将基因型恢复到了有害突变发生前的状态。对比费希尔和穆勒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费希尔说的是,当环境发生变化,物种需要发生变异时,有性生殖相比无性生殖是一种更高效、更快速的变异手段。而穆勒说的则是,当环境稳定,物种需要保留自己的性状时,有性生殖又成为了一种比无性生殖更安全的防止变异手段。就这样,有性生殖进可攻、退可守,用一套最简单的策略,完成了变异与保存着对二元矛盾的完美调和。为了在治世求稳,在乱世求变,我们必须进行有性生殖,而为了兼顾繁殖的最高效率,合作者越少成本越低,于是生殖只有两性。这就两性生殖为何被几乎所有多细胞生物采用的真正原因——它比无性生殖高效太多。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雌性与雄性,男人与女人,没有一方是不必要的累赘,也没有一方是工具。双方从一开始就是彼此平等的合作者。而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那些鼓吹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都带有那种典型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气质——极端男权者仍在贯彻斯宾塞的思想,将女人只视为生育机器。而极端女权主义者则痛恨男性,恨不得仿照蜜蜂搞“孤雌生殖”。其实这两种思维所站立的基石,都是谬误的伪科学。雌性与雄性,男人与女人,之所以要同时存在,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太残酷了,它既要求我们安稳,又催促我们变动,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而为了达成这一点,我们必须寻找找伙伴合作。于是,我们寻到了彼此,我们有了雄性和雌性,男人和女人。我们是平等的合作者,没有哪一方天然高于哪一方,也没有哪一方在占另一方的便宜。那些试图奴役,歧视对方的人是可耻的,他们应该像百年前的斯宾塞一样,活该单身一辈子。我们彼此相异却又彼此相爱,我们共同创造的结晶,那些优秀子代们改正了我们的谬误,却又继承了我们的优良,因此他们比我们更加适于在这个世界生存。在人类诞生前的亿万年里,基因的两性融合达成了这一点,而在人类获得智慧之后,优秀的父母们能通过家庭教育模仿自然的这个进程。这就是男人女人之间真正的故事:上帝借自然选择之手,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也造就了他与她之间那些最美的那些情愫与纠葛。自然的伟力,让人与人必须彼此相爱,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也许,正因为世界是如此冰冷,上帝才借进化之手,让我们彼此相爱。今天的音乐,是《圣母颂》,这首曲子特别神奇,你听到的钢琴部分,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前奏曲》,百年之后,法国作曲家古诺,又给它配上了大提琴。钢琴与大提琴,穿越百年的时光,完成了共同的赞颂。愿人类打男女也能如此琴瑟相和。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长稿不易,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