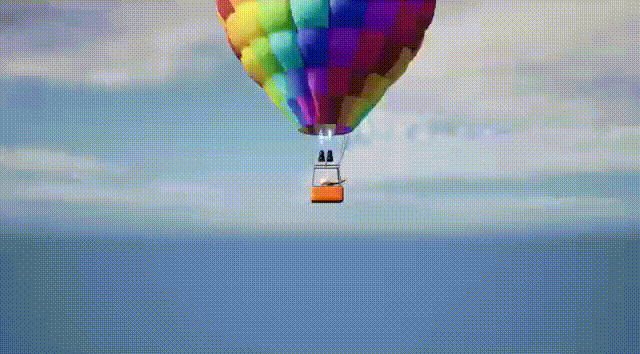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评价敦煌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注:这里的伊斯兰,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简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如果有人问今天的敦煌石窟中哪一个洞窟可以为季先生的这段话作注的话,那再也没有比营建于西魏时期的第285 窟更适合的了。在敦煌石窟中,莫高窟第285 窟堪称代表之作。它是敦煌早期石窟中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洞窟,约完工于西魏大统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538、539年左右。该窟主室平面呈方形,东西进深约 6.4 米,南北宽约6.4 米,面积约40平方米,壁画面积约 200 平方米。让我们惊讶的是,小小斗室之内,它竟然能呈现那么多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神灵形象。该窟壁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性洞窟之一,以表现佛教的佛、菩萨形象为主,同时又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灵形象如伏羲、女娲、雷公以及祥瑞动物和异兽等形象,还有带有浓厚中亚、印度、波斯甚至希腊艺术印记的佛教护法诸神如日天(菩萨)、月天(菩萨)、摩醯首罗(大自在天)、鸠摩罗天(童子天)、毗那耶伽等形象,可谓多元文明交汇。在人物造型上,既有西域式晕染“凹凸法”,又有来自南北朝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风格。第 285 窟所绘的这些佛教护法诸神形象上体现出的浓郁西域文化特色的艺术因素,究竟来自何处?又是谁将它们带来?它们那独有的图像特征为什么只昙花一现般地出现在第 285窟,之后就再也不见踪影?……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究和溯源,为我们透过纷繁的艺术表象,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进一步认识该窟艺术元素来源的多元性及隐藏其后的历史真实提供了可能。这个洞窟是敦煌石窟中最经典的、能反映多种文明在敦煌的交融,又自成一家的一个洞窟。图1-1 莫高窟第 285 窟内景(敦煌研究院 供图)
首先,从绘画技法和人物造型风格来看,第285 窟的壁画艺术汇集了中原— 南朝艺术风格与西域风格。以人物形象为例,该窟西壁的人物造型脸庞圆润,鼻梁挺直,上身裸露、下着长裙,采用层层迭晕的晕染方法,为典型的西域式风格;而其余壁面的人物形象面相清瘦,身材修长,衣袍宽大,衣带飘举,采用平涂式晕染,为典型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中原— 南朝式风格。285窟开凿的年代,正值南北朝时期,中原,特别是南朝士大夫的形象被直接反映在壁画上。图1-2 “秀骨清像”式菩萨(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 西魏)
其次,从神灵形象的图像来看,该窟在表达同样的主题时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图像模式。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这个洞窟中的日、月神图像上。关于日月的神话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明形态中都是永恒不变的话题。佛教文明也是这样,把日、月纳入了它的佛教神灵体系中。在第285 窟中,西壁用日轮中乘马车的主神加上乘凤车图像与月轮中乘鹅车的主神加下方力士乘狮车的组合来表现日天和月天。与此同时, 又在窟顶东披绘出中国传统的日、月神即伏羲、女娲的形象。在西壁南侧的最上部,有一条蓝色的长方形条带,条带内自南向北依次绘有一个白色圆轮和六个白色椭圆形轮,内各画有一身人物形象,表现的是日天(菩萨)及其眷属。日天头有光,着高髻,双手合十,呈正面向,端坐于一驷马二轮车中。驷马两两相背,分别于车厢两端。在日天的圆轮下面,画一辆三只凤鸟拉的日车,向中央龛的方向疾速奔跑。车上有两力士,一前一后,其中前者一手持一人面盾牌,一手高高扬起,作驾车状;后者高举双手,似用力托着上方日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就是太阳神的符号,凤凰、朱雀都代表太阳,代表火,就是说把中国文化中的对于太阳、对于火的理解,跟骑着马的这种非中国文化符号的表现日神的元素,两个结合起来,这种图像,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图1-3 日天及诸神(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大统三年即 538 年左右)
关于乘马车的日天图像的来源,主流意见认为它来源自印度教的太阳神苏利耶的图像。类似的乘马车的太阳神苏利耶的雕刻,从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的印度大量存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雕刻于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的菩提伽耶围柱上的太阳神苏利耶浮雕。但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 第 285 窟日神图像甚至保留着古代希腊— 罗马艺术的元素,如制作于公元 1 世纪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一尊皇帝等身图案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驾着驷马“两两相背”的太阳车。这种日神图像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进程中传播至西亚波斯和中亚地区,并成为袄教的密特拉神图像的构成部分。其后又在犍陀罗地区成为佛教的日神图像之一,并经中国的新疆地区传入敦煌。在这里, 又加上了中国文化中象征太阳的神鸟凤凰的形象。图1-4 驷马车上的太阳神阿波罗(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公元 1 世纪)
在西壁北侧上部与日天对应位置也有一条蓝色的长方形条带,条带内自北向南画有一个圆轮和七个椭圆轮,表现的是月天及其眷属。月天位于画面最北端的圆轮内。由于画面剥落严重,现仅能看到一身人物,呈正面坐姿于一两轮支撑的车厢内,双手交叉于胸前,车轮南侧还残存两只鸟头和翅膀部分。在绘有月天的圆轮下面,由三只狮子牵拉着一辆车,车厢内有二身力士,一前一后,后者高举双手,作托月天状。与日天不同的是,乘天鹅的月神图像,不论在印度教文献还是雕刻中,都没有发现,但在印度以外的地区, 如敦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中均可见到。女神或阴性神与天鹅相伴的作品,最早见于苏美尔文明遗存中,如现藏于耶路撒冷考古博物馆的一件制作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陶土制苏美尔女神像即坐在两只“两两相背”的天鹅背上。
图1-5 月天及诸神(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大统三年即 538 年左右)
图1-6 坐在天鹅背上的苏美尔女神(耶路撒冷考古博物馆藏,公元前 3000 年左右)

图1-7 坐在天鹅背上的美神阿芙洛狄特图案彩陶罐(德国柏林博物馆岛老馆藏,公元前400 —公元前 350 年)
在希腊古典雕刻中的美神阿芙洛狄特及罗马雕刻中的美神维纳斯等女神也常以天鹅为坐骑,如一件出土于希腊阿提卡的彩陶罐上就绘着坐在天鹅背上的美神阿芙洛狄特的图案。再看月轮下方的狮子拉的月车,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文殊菩萨骑狮子,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印度佛教艺术中找不到骑狮子的文殊菩萨。目前发现最早的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在中国,有学者就认为文殊菩萨骑上狮子是在中亚地区,就是佛教向东传播过程经过中亚地区,吸收了中亚地区女神信仰。女神和狮子结缘最早见于古巴比伦文明中,如一件大英博物馆所藏古巴比伦时期的浮雕黑夜女神作品,她两侧有两个猫头鹰,象征了她的黑夜女神身份,她的脚底下就踩着两只相背而卧的狮子。其后的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城邦守护女神库柏拉( Cybele,或称希柏拉),她的车子就是由狮子所拉。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一件出土于罗马的铜狮车上就坐着城邦守护女神库柏拉。这一图像甚至东传到了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西边山脚下阿富汗的阿依哈姆古城。在这座古城遗址发现的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鎏金银盘上也出现库柏拉乘坐着由两只狮子牵拉的车子出行的画面。这一现象甚至跨过高原向东,除了敦煌第 285窟,在一件现藏于日本 MIHO 博物馆的中国北齐时期的入华粟特人石棺床围屏浮雕上,头戴花冠,左右两手分举日、月的娜娜女神的坐骑即为一对狮头象征的狮子座。
图1-8 脚踩双狮的黑夜女神(大英博物馆藏, 公元前 1800 年左右)
图1-9 坐在双狮车上的库柏拉女神(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藏, 公元 2世纪后半叶)

图1-10 鎏金银盘(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前 2 世纪)
本窟另一幅融汇多元文明的 壁画为摩醯首罗天图像。在西壁主龛与北侧小龛之间的壁面上绘有头戴宝冠,三面六臂, 骑在青牛背上的摩醯首罗天形象。摩醯首罗天原为印度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后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重要的护法神,被列为天部,名“大自天”。关于其形象,佛教经典多有描述,如《大智度论》卷二曰:“摩醯首罗天,秦言大自在。八臂三眼,骑白牛。”这一形象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佛教寺院和石窟寺遗址如库车、和阗、敦煌、云冈石窟等地皆有发现, 有三面六臂、三面四臂等不同造型,多为三面六臂者。其总体特征与其印度教中的湿婆神图像相符。敦煌的摩醯首罗天图像在洞窟壁画、藏经洞所出绘画品中均可见,多出现于密教类的观音或文殊菩萨的经变画中,最早者约6世纪前半期,最晚至11、12世纪,而以第285窟的这身为最早。图1-11 狮子座上的娜娜女神 (日本 MIHO 博物馆藏, 北齐)
其三面中,正面相为天王形,右侧一面为菩萨形,左侧一面为夜叉形。头冠中绘有一身手执风巾的风神形象。作为印度教的三大神之一,湿婆神及其前身鲁多罗专司暴雨雷电,因此也兼具风神的功能。其图像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公牛为坐骑。不过,现存的多例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729年)的以公牛为坐骑的风神图例,却为我们重新思考巴克特利来—粟特地区这一类风神图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现藏于芝加哥大学博物馆的一件约制作于公元前2000年 — 公元前 1600 年间的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陶土浮雕板上,就清晰地塑造出一身左手执二股叉,站立于一头公牛背上的风暴神形象。
图1-12 摩醯首罗天(莫高窟第 285 窟西壁, 西魏)
与上述风神图像相类似的站立于一头公牛背上的风暴神形象还可见于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三枚约制作于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间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圆筒形印章上。这些实物资料表明,早在古代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古老神话中,公牛形象和三叉戟就已经是 风暴神图像的“标配”元素了。以湿婆神形象出现的风神图像,在印度贵霜王朝时 期的钱币背面都可见到。湿婆神不仅是印度教的风暴神,同时还是波斯— 中亚地区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的风神。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东南古代粟特遗址的壁画碎片中拼接出了一身穿甲胄,三头四臂,上臂分执弓和三叉戟的形象,与印度教的湿婆神十分相似。

图1-13 古巴比伦风暴神(美国芝加哥大学博物馆藏, 公元前 2000 —公元前1600年)
尤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 其腿部右下侧人们发现了一则粟特语题名“Veshparkar”,即“风神”之意。由此,我们知道了与摩醯首罗天形象相似的形象同时也是祆教的风神。与前述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发现的三头三目、手执三叉戟的风神韦什帕克图像相似的形象也见于西安发现的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的粟特人史君墓石椁浮雕中。其形象虽为一面,但手握三叉戟,坐于三头牛背之上。在其圆形光环外两侧,各有一天神分执风巾一端,以进一步强调其风神身份。而前述第 285 窟摩醯首罗天头冠中所绘的手执风巾的风神形象呈“深目高鼻”的中亚胡人形象,嘴角有短髭。其头部和双手从摩醯首罗天的头冠的花冠中伸出,双手紧紧执着一条圆弧状的风巾的两端。这样的手执风巾的风神形象,在新疆库车石窟群中多见到。再往西,在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第155窟天井壁画的两侧也各绘有一身头戴高尖帽、双手执风巾的风神形象。再往北、往西,同样在贵霜王朝时期的钱币背面也出现了多例具有希腊人面相、手持风巾奔跑着的风神形象。在前述希腊、地中海文明的女神和海神图像上也可见到这种风巾。可见,第285窟的摩醯首罗天形象, 实际上至少糅合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风神的图像元素。有意思的是,在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出土于阿富汗贝格拉姆古城窖藏的彩绘玻璃杯,约制作于公元1 世纪的希腊化时期。杯上绘有古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神先后化作风暴神加尼米德前往奥林匹斯山的场景。画面上宙斯化现的风暴神不仅骑于牛背上,而且双手皆执着曳满风的呈弧形风巾。一个在阿富汗,一个在敦煌第285 窟,两者距离相差数千公里,时间相差 500 多年。这两种风神的图像特征跨越时空再一次“顽强”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不能不令人惊叹!这种看似“偶然性”实际上反映出,公元前 4 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后亚洲腹地的长期“希腊化”对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十分持久,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图1-14 风神韦什帕克(史君墓石椁浮雕, 西安市博物馆藏,北周大象二年)

图1-15 彩绘玻璃杯(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公元1世纪)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285窟窟顶东披的伏羲、女娲图像。在窟顶东披正中绘一硕大的莲华摩尼宝珠,其两侧各绘一身人首、龙身的形象。一身手里执圆规,另一身分别执拿矩尺和墨斗,这就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形象,所谓“规天矩地”。伏羲、女娲也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日神、月神。 其腹部圆轮中当初分别绘有太神鸟和蟾蜍,惜现已模糊不清。作为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主神之一,这一对图像在甘肃河西地区的汉晋时期墓葬中大量出现,以保佑死者的灵魂速登仙界。但在第285 窟,伏羲、女娲已经由中国传说中的“创世之神” 摇身一变,成为佛教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两个胁侍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从天上来到人间,为黑暗中的苍生造日月星辰。可以看出,佛教巧妙地利用了它们各自原本的日、月神之格。在他们的下方,我们看到长着翅膀像鹿一样的神鹿,那是中国神话中的飞廉、雨师—— 雨神。此外还有朱雀、开明神兽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瑞兽形象。图1-16 伏羲、女娲(莫高窟第285窟窟顶东披,西魏)
第285 窟的这些神灵形象上的图像元素,从宗教背景上看,既有中国传统神话和道家信仰的元素,又有着印度教、祆教甚至巴比伦神话的烙印;从地域上看,横跨了中国的南北方、印度、中亚、西亚、古代两河流域乃至环地中海地区。那么,是谁将它们带入敦煌,成为285窟艺术内容的一部分呢 ? 显然,这样多元的图像组合,绝对不可能出自敦煌本地画师,或者单纯来自中原、南朝的艺术家,或者直接来自印度教或佛教背景的印度僧人或艺术家。能创作这样图像的人,必须既要熟知中国文化传统、印度教艺术、佛教艺术的相关背景,同时还要对祆教艺术中表达相同理念的图像模式有深入了解与体会。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 本窟的其他图像和供养人题铭暗示着这一图像的中亚—粟特来源的可能性。出土文物和相关研究也表明,早在西晋— 北朝时期 , 敦煌、河西地区都有粟特人及其聚落存在,如武威的安姓、张掖的史姓等。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敦煌附近长城烽燧发现了五封写于4世纪初的“粟特文古信札”,这些古札中提到了粟特商队以凉州(武威)为大本营,沿着敦煌—张掖—武威—金城,一直到洛阳一线经商贸易的情况。第 285 窟北壁中部通壁绘有七铺说法图,每铺说法图下部均画有供养人行列。除西起第一铺均为女供养人外,其他六铺中皆为左右对称的男、女供养人行列。着世俗装的男供养人均上着圆领窄袖的胡服,束腰带,下着裤褶 , 着乌靴,着世俗装的女供养人则都无一例外地身着上为交领大袖襦、下为间色条裙的汉式装。从男女供养人的对称排列来看,这六铺说法图当是以家庭为单位出资绘制。每身供养人侧皆有榜题。其中,第二铺、第五铺和第七铺这三铺供养人行列中的第一身男、女供养人及其榜题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这三铺供养人榜题分别为:( 1 )“清信女史崇姬所供养时”— “信士阴安归所供养时”;( 2 )“清信女丁爱供养佛时”—“清信士滑囗安供养”;( 3 )“清女何囗”— “清信士滑黑奴供养”。 其中,“史崇姬”“清信女何囗”当分别来自粟特“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何国,“滑黑奴”和“滑囗安”当是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嚈哒人(滑国人)。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图像的绘制者中,既有来自当时中国的北方、南方地区,又有来自于中亚—粟特地区的画师。自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200多年的“希腊化”进程,给亚洲腹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中,并没有佛的形象,而是用圣树、佛的足迹或莲花来代表佛。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希腊的人体美艺术和印度的“出世”理想很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产生了大乘佛教艺术中的佛像和菩萨像。之后又向南传到印度本土,产生了茉菟罗艺术和后来的笈多艺术。再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今天东南亚一带。向北、向东经过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到中国新疆经过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穿越中原大地,最后到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所以,佛教文明就是在多种元素的助推下,在它的偶像的光辉遮蔽下,成为整个古代世界亚洲东部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形态。汉武帝时期,汉朝设立了敦煌郡等“河西四郡”,并分别在敦煌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设置了玉门关、阳关,敦煌成为中国通往西方各国的门户。此后一直到公元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 1600 年间,敦煌一直是汇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国际性都市,具有联结东西文明的独特的地理和文化地位。成书于公元 5 世纪中期的《后汉书·郡国志》里,在追述两汉时期的敦煌时称其为“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成书于 6 世纪中期的《魏书·释老志》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莫高窟第 285 窟丰富多样的壁画艺术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真实的形象反映。正是来自不同文明和各种艺术元素,在同一种信仰观念的感召下,汇聚在一起,最终造就了285 窟这一交融着多种文明神祇的艺术宝库。从这个意义上讲,第 285 窟又是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产物。莫高窟第 285 窟壁画艺术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使得我们今天可以追溯、拼合中古时代曾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幅幅画面,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汇所具有的渐进性、多向性和多层次性特质,也给予今天的我们以宝贵启示: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共荣共存。[注:本文系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课题“敦煌石窟日神、月神图像调查与研究”(编号GWJ201816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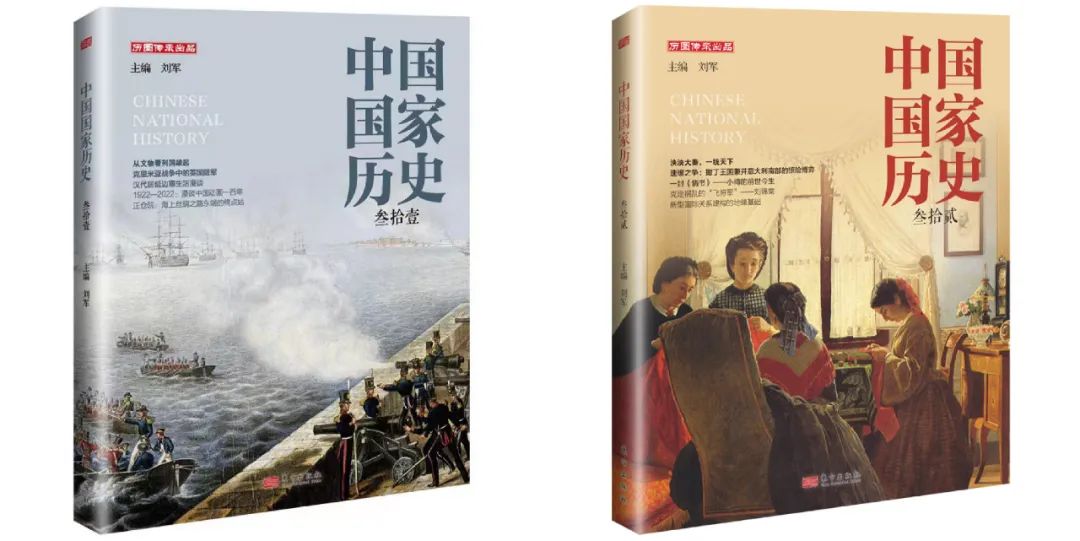
《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识别下方小程序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