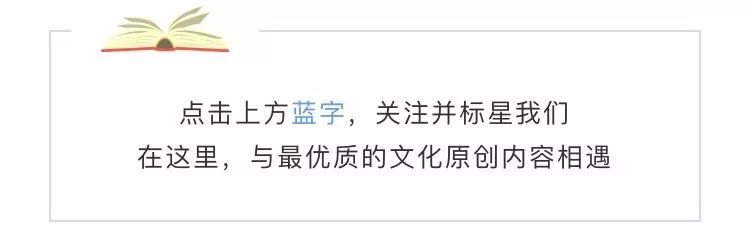
王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08
作家王梆对真实事件“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寻血猎犬般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在她的非虚构作品《贫穷的质感》里,造就了对英国社会细致入微的描绘,而在她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中,则化作对个体生命的挣扎、抗争与坚持的持久关注。《假装在西贡》一书共收录十个短篇故事,讲述了不同时空中女性的孤独、爱与倔强。她们共同秉持着一种坚韧而昂扬的姿态,无论周遭环境如何芜杂与龌龊,都“十分决绝,不善媚术,从根本上,缺少某种容纳父权主义的润滑剂”。王梆的书写精妙地把握住了女性主体的感受,当描述女性发廊妹仔渡江,被老华侨用黄手指在屁股上狠狠掐了一下时,她写:“就像让一个有洁癖的人去掏粪,指缝里因此便染上了粪便的记忆一样。”(《鲨齿蟹》)。在《阳光房》中,老学者把手伸进女家庭教师的裙底,干枯的指节发出某种蚁肢碰撞的声音。《钩蛇与鹿》中的安,即使遭受着各种肉体和精神惩罚,也势必要私自外出。这些女性如同王梆所说,身上都流动着“向上的、爱莫能助的、破坏的冲动”,“全身上下都是硌人的骨头,触感有如锋利的燧石。”
《波特诺伊的怨诉》是菲利普·罗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1969年甫一推出,便引起轰动并长居畅销榜。昆德拉曾评价罗斯是“伟大的情色史学家”,在这本书里,罗斯发明了“波特诺伊的怨诉”这种专有症候,指涉原始性欲与内心道德的持久冲突。“这种状态呈现出大量的裸露癖、窥淫癖、恋物癖及自发性欲等行为。然而,由于患者的‘道德意识’,无论幻想还是行为,其结果并非真正的性满足,而是压倒性的羞耻感和被惩罚的恐惧,特别以去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性,曾一度被认为是低贱而暧昧的:克尔凯郭尔与果戈里都深受其折磨;弗洛伊德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瘾,是病态冲动促成的结果;福柯曾专门从现代自我形成的角度,研究其对人的作用。罗斯发现,这一症候在希伯来文化中找不到任何表达词汇,甚至连委婉语或隐晦的说法都没有,于是他书写了这本《波特诺伊的怨诉》,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呈现它。
发掘奈保尔,为阿特伍德改稿,吐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安娜·阿西尔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编辑之一,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编辑。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桶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二战后,她创立了20世纪英国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她有着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一系列杰出的作者,帮助他们写作。
阿西尔89岁时,写作了《暮色将尽》漫谈自己的独身老年生活。在自传中,一生未婚的她潇洒回忆几段情史,“这些关系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足以伤害我。”“女人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如果有男人想娶我,我的感受是不屑。”她认为老后的荷尔蒙退潮让思考更清晰、害羞窘迫的社恐症也消失了。最后,她总结自己的老年生活说:“我在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舒服地、长久地享受过自己。”除了人生经验的回顾,我们在书中也能窥见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同世界周旋,维护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7
“巴尔米拉与任何其他的帝国城邦都不一样。”罗马历史学家保罗·韦纳说——“不管那里的神庙开不开窗户,不管那里的达官贵人穿希腊式的衣服还是阿拉伯式的衣服,不管那里的人们讲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甚至在重要场合也讲拉丁语。总之,我们感觉到巴尔米拉的上空吹着一股自由的风,一股不因循守旧的风,一股‘多元文化主义’的风。”巴尔米拉,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东北棕榈环绕、两山静立的绿洲间。它是人们穿越叙利亚沙漠必经的补给站,在公元1-3世纪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贸易中心,通往罗马世界的东方入口,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此处往来经商,留下多元的文化与无尽的财富,这里的建筑也是古代世界最具特色的遗迹之一。然而在2015年5月,“伊斯兰国”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开始了城市摧毁和居民屠杀。韦纳在这本薄薄的《巴尔米拉》中讲述了曾经的自由之城的方方面面,并从中反思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与危险。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要洗劫毫无冒犯之意的建筑?为什么要屠杀包括哈立德·阿萨德(叙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前帕尔米拉文物局长)在内的那么多人?在书的最后,韦纳写到:“毫无疑问,如果只知道、只想知道一种文化——自己的文化——将注定与压抑沉闷为伴终生。”
为何美国的劳工运动不支持黑人解放和民权事业?在《白人的工资》一书中,劳工史学家大卫·R.罗迪格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他发现,白人劳工害怕黑人和自己竞争工作机会,会向下攻击更底层的黑人,而不是向上攻击最有权势的白人,他们选择了塑造黑人“他者”,参与白人霸权的构建。罗迪格从劳工运动的视角观察美国的种族主义,发现它也是统治阶级划分工人的手段之一——在肤色偏见的影响下,不同肤色的工人始终无法团结起来。
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指出,美国白人不会将自己和种族两个字联系起来,种族主义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常忽视其对白人的内在影响。《白人的工资》一书打破了这一研究盲点,着重分析了种族主义在19世纪白人工人阶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堪称白人身份研究的开端之作。
甲午之后,频繁到往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鲜见,诸如汉学家内藤湖南等人曾写下诸多与中国有关的文字,他们的目光冷酷严苛,并未涉及风景园林。在上海和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日本学者井上红梅,也曾出版《中国风俗》与《金瓶梅:中国的社会状态》,将鲁迅许多作品翻译成了日文,但他的兴趣点多聚焦于麻将、鸦片、狎妓等,摆脱不了猎奇的凝视,也不曾对中国风景庭园有所考察。后藤朝太郎在这一批知识分子中显得尤为特别,他被誉为日本昭和时期汉学第一人,观察中国的视角满怀温暖的憧憬之情。在1912-1945年的三十余年中,后藤五十多次乘船来中国旅行,如徐霞客般亲身考察中国各地,做出了大量珍贵记录。在这本《中国的风景与庭园》中,他谈自然风景也谈园林文化,从东北华北大平原到巴山蜀水,从极富野趣的潇湘八景到皇家的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均有所涉猎。透过日本学者的视角,我们或许能看到中国人文景观里不一样的细节。
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生命与痛苦相伴。她曾多次试图自杀,成年后的大半人生岁月都被抑郁症缠身,30岁时在一氧化碳毒气里自杀身亡。她大多数的诗歌里也盘桓着痛苦、黑暗与死亡的意象:“小小的罂粟花,小小的地狱之火”、“看,黑暗从爆裂中渗出/我不能容纳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或是“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也许许多她的读者都不知道,普拉斯还曾为孩子们写过一个温暖明亮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一套“羊毛制的、毛茸茸的、全新的、芥末黄色的套装”,它像黄油一样明亮,像烤面包一样暖和,但人人都担心穿上它之后“别人会怎么说”,只有麦克斯不害怕它,穿着自信又快活,引来小镇上所有人的关注,连小猫小狗都羡慕地跟着麦克斯的脚步,一起前往“无所谓”的冒险……在《无所谓套装》里,我们看到的是普拉斯留给世界的温暖,也看到她连温暖都如此决绝果敢,无所畏惧。
蘑菇和悲伤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丈夫的突然离世,让挪威人类学家龙·利特·伍恩长久沉陷于悲痛之中,直到她发现了树林里奇妙的蘑菇世界。那一天,空中下着小雨,从奥斯陆植物园高大古树上落下的枯叶开始发霉,伍恩和博物课老师在野外辨识蘑菇,她认出了致命的鳞柄白鹅膏,感受到心流的到来。“蘑菇即使如此有限——都能让树林散步变成一种非常不同的体验。突然间,我眼里到处都是蘑菇。”
与蘑菇的奇妙交集让她开始探索、学习,最终让她成了一名认证蘑菇专家。在《寻径林间:关于蘑菇和悲伤》一书中,伍恩书写了蘑菇治愈丧亲之痛的过程、与菇友探索自然的经历,以及投身真菌学文献、学习拉丁语并同专家探讨蘑菇气味和颜色等趣闻轶事。
除了这本《寻径林间》,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可爱的蘑菇,不妨阅读一下《末日松茸》,从人类学家对松茸世界的观察中,看到资本主义废墟上的另一种可能;而在画册《蘑菇图鉴》中,你则能欣赏到诞生于18-20世纪的一幅幅精美的蘑菇图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鲁青,编辑:黄月、徐鲁青,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