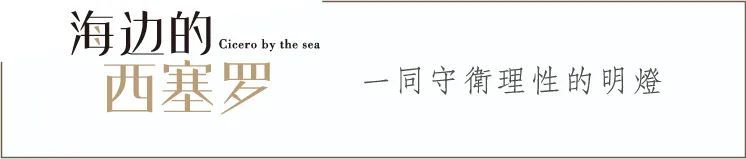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各位好,连日写作,颇为劳累,今天继续休更一天,请假发篇旧文吧,晚安。
你眼前这张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的画,在历史上其实大大有名,它是德国文艺复兴时代大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在1500年所创作的《自画像》。
作为人类艺术史上第一个以画自画像闻名的大师,丢勒一生创作过大量的自画像,并因此被称为“自画像之父”。但唯独只有这一副特别有名,被后世誉为“史上最好的自画像”或“史上第一幅真正的自画像”。后世无数阐述者费了无数笔墨去解读这幅画作的革命性意义,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是丢勒的粉丝,将他抬高到与达芬奇同样的高度。其实自画像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原始版的“自拍”,而以现代人自拍的角度去看,丢勒的这幅画看上去似乎是那么的平平无奇——没有酷炫的动作、没有特别的造型、背景一片漆黑、被画者似乎面容呆滞、神情呆板。我认识一个妹子,第一次看这话时,犀利的跟我吐槽说:“这不就是个身份证照吗?”我一想,也对哈。你现在去楼下照相馆,花几十块让人家给你拍个身份证照片,得到也是这么个效果: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半胸照片,还往往丑的让你不敢自认。唯一的区别可能只在于,会照的摄影师肯定会让你:“表情自然一点,笑一下”。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在这幅画出现之前,欧洲人是怎么画自画像的。其实,在丢勒生活的年代,一个画家想画一副自画像,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技术活。因为整个中世纪,欧洲都还没有发明很好的制镜技术,只能使用与同时代我国相似的铜镜、锡镜、银镜等,但这种金属镜问题都很多,所以那个年代的人类其实是无法很好的看清自己的真容的。但欧洲的制镜技术,从中世纪盛期开始逐步完善。到了15世纪末,玻璃技术之都威尼斯的工匠终于研制成功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玻璃镜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先把一层锡箔贴在玻璃面上,然后倒上水银,水银是液态金属,能够很好地溶解锡,随后,玻璃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锡与水银的合金(也就是“锡汞齐”),锡汞齐够紧紧地粘附在玻璃上而成为真正的镜子。于是,史上第一次,欧洲人开始用上了物美价廉的镜子,自画像这个“前置摄像头”,终于向着画家们开启了。所以那个时代画家们都开始画自己自画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画像之父”丢勒,其实也算是“风口上的猪”,也是凭借技术之风“送我上青天”的。但一个人的命运要考虑历史大势,也要看个人的努力。画自画像的机会是时代给每个画家的,凭什么唯独丢勒成了“自画像之父”呢?你会发现这些自画像与上述丢勒的那一副都是有点不一样的。比如丢勒自己,从13岁的时候就开始画自画像,但他最开始画出的自画像是这样的:但你发现问题没有,所有这些自画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画作中的那个丢勒会稍微测过一点自己身体和脸去,不会把自己的正面形象完全对着“镜头”。尤其是在早期的自画像中,自画像中的人物甚至会把眼睛撇过去,跟画布外的你甚至没有眼神交流。而如果进一步推而广之,你会发现同时代的很多绘画大师,都是这么画自画像的。我们随便举一下文艺复兴三杰的例子。而再进一步推广,你会发现文艺复兴早期的几乎一切人物肖像,也都呈现这种特点,且年代越往前,画中人物的“侧面率”就越高,比如但丁像:从这几幅画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趋势——把文艺复兴的进程投影在人物肖像画中,好像就是一个人物逐渐将身体和脸庞在画布中逐渐“转正”,并把眼神看向“镜头”的过程。但直到最为著名的《蒙娜丽莎》为止,其实人物的身姿和脸庞都还没有完全“摆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呢?究竟是什么让当时的人们在画像时不能完全痛痛快快的露个正脸,想丢勒后来的那副最著名的《自画像》一样呢?想当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有个经典小品叫《主角和配角》,里面有一段和这个情形非常相似。陈佩斯和朱时茂争主角的位置。
陈侧站,但把脸扭向观众。朱时茂把他的脸拨成侧脸。陈佩斯再扭过。如此反复三次。朱时茂: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嘛!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要始终保持我的正面给观众!在中世纪,天主教欧洲认为上帝才是宇宙的中心,一切叙事中的主角,所以所有画作当中,都要始终保持基督(或圣母)的正面形象给观众,其他人都只能凑合露个侧脸。耶稣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呈现完全的正面,十二门徒朝向他,越靠近两侧的门徒,其侧面率越高——真·“配角就只配露半张脸”。拉斐尔在画作中编织了一个“眼神的循环”:圣女看向小天使、小天使看向教皇、教皇仰望圣母子,唯有圣母子呈现完全的正面,眼睛直视“镜头”。特别讽刺的是,西斯廷教堂建成后,一直是历代教皇所用的私人经堂。但哪怕是在这个“自己家”里,教皇也是配角,“配角就只配露半张脸”。所以可以说,欧洲当时所有的圣像画,其实都是一出《主角与配角》的小品。而凡人在画作中的侧脸对人,也成为了当时绘画的一个教条。天主教会觉得,尔等凡人怎么可以用正脸对着画布呢?您配吗?但我们说,文艺复兴的精神之可贵,就在于让欧洲人想起“人才是万物的尺度”。那些购买自己肖像画的甲方土豪爸爸们,花了大价钱给自己画像,怎么可能满足于在画作中只露半张脸呢?而那些调皮的画家,画久了之后,就更不愿意接受这种龟毛设定了。先把脸转过来一点,再转过来一点,又转过来一点,甚至到后来连眼光都看向画布外了,看教廷管不管。还有另一种更作死的尝试思路,它属于(备受教皇专宠的)拉斐尔这种人:你看,拉斐尔的很多画作当中,都都会有一个胖嘟嘟的小青年,躲在某个犄角旮旯里,在一众侧脸人物当中,如陈佩斯一般倔强的扭过脸来,朝向观众,悄悄给大家一个正脸:拉斐尔:别看我站在这个犄角旮旯,我照样把戏给你抢过来! 画家其实就是在用这种方式、悄悄的、一点点的打破“凡人不配给正面”的戒律。可是,甭管之前的画家们怎么画,这种试探始终是在悄悄进行的,非耶稣或圣母的人物肖像始终会有一点点侧面率。连大胆的拉斐尔,也只敢在犄角旮旯里扭个正脸。
画家其实就是在用这种方式、悄悄的、一点点的打破“凡人不配给正面”的戒律。可是,甭管之前的画家们怎么画,这种试探始终是在悄悄进行的,非耶稣或圣母的人物肖像始终会有一点点侧面率。连大胆的拉斐尔,也只敢在犄角旮旯里扭个正脸。
而且在1500年的时候,当时教会认定的人物标准像,依然还是这种:1500年时在位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大人的标准照——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教皇大人以身作则,强调凡人配角就是只能露半张脸。但就在这一年,29岁的丢勒甩出了自己的那幅自画像:你能想象这画当时有多炸锅了吧?——教皇都只露半张脸,丢勒你这……而细究之下,这幅画真正的大胆之处,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多说一句,这幅《救世主》2017年刚刚拍出过4.5亿美金(约30亿人民币,20“爽”)的高价。成为史上迄今为止价格最为昂贵的绘画。你是否感觉得这幅画和丢勒的《自画像》是那般的神似呢?而我再告诉你,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使然,这两幅画作的创作年份大约都在1500年。也就是说,就在达芬奇这么画耶稣的同一时间,丢勒在用几乎同样的形象,画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好么,别人都是在正面画的禁区边缘疯狂试探,你丢勒一来就把桌子给掀了?上来就用人家画神的方式画自己?这事儿可能也跟丢勒是德国人、天高教皇远有关系,同时代的意大利画家们,估计借他们个胆,他们也不敢这么干。那丢勒这么画是不是故意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画这幅画作之前,丢勒刚刚结束了他在意大利的旅行,作为后辈画家,他显然向达芬奇学习过,甚至可能也看过正在创作中的《救世主》。自画像中的丢勒与救世主耶稣最大区别就是手势的不同。达芬奇所画的耶稣将祝福的手势向上指天,代表对上帝和天国的赞美。而顺着这个手势的延长线,我们可以看到画作的右上方,丢勒写了一行小字。这行字翻译过来的大意就是:阿尔布雷特·丢勒,这是我的自画像,画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丢勒为了防止别人误认为他是在画耶稣,特意写了一句:这画的不是救世主,这只是我自己。那么丢勒这么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自由主义解释当然是说:“丢勒勇敢的打破了“不能画纯正面肖像画”这个教会的禁忌,彰显了人的尊严与自我重视,在绘画史上迈出了大大的一步”等等之类。但如果你再进一步感受这幅画,会产生另一种难以言说的体验:这幅画丢勒的确是在画自己,但他的装束、他的深情,却又透露出一种神性的光辉。相比于“扭头拉斐尔”的戏谑和调皮。貌似更加“前卫”的丢勒反而神情肃穆,他的双眼中又透出了淡淡的忧郁、深沉和严肃,像是在思考与反省,又像在感受神性。沿着丢勒的注释向左看,你能看到左方有一个题签“AD”。这是丢勒为自己特别设计的签名,而至的注意的是,AD不仅是“Albrecht Dürer”(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缩写,还有一个意思是“AnnoDomini”(既公元,我主之年)——丢勒其实是在用这个签名缩写又把自己和神明联系了一遍。还没完,如果再将丢勒的这两个签名和他皮装的v字领连线,你会得到一个倒三角形。与人物轮廓的正三角重合……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所罗门之印(或称大卫之星)的构图。
在亚伯拉罕教系宗教中所罗门之印有救赎、复兴的意味,所以以色列后来也将该符号作为国旗。而丢勒用这种构图作画,似乎也正是在说:救赎的路径,在我心中。所以,你似乎依然可以把这幅《自画像》看做另一幅《救世主》,只不过丢勒所画的救世主是与他自己重合的。——达芬奇画中的耶稣,指示上帝在天上。而丢勒画中的耶稣,指示上帝在他心中。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上帝与我同在。”
在丢勒创作这幅画17年后,德国这片土地上爆发了宗教革命。而由马丁·路德掀起的这场宗教革命,在某些思想上与丢勒的这幅画作思想是相通的:与对人的救赎需要经过教会“转手”的天主教相比;新教伦理更加强调信徒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强调“与神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说,丢勒的这幅自画像不仅是艺术上的突破,在宗教和政治上也是有着杰出预见性的。教会如达芬奇所表现的,说上帝在天上,丢勒却说,上帝在我心中。
教皇如果真懂艺术的话,从丢勒这画就应该看出来德国人这是要反。在丢勒以前,欧洲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精神寄托放之于外在的神明、教会。而丢勒之后,人们开始将这种寄托与道德律放进自己的心中,重新像古典时代的古圣先贤们一样,开始用理性与思辨去常识把握真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我们头顶上璀琛的星空,和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康德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丢勒画出这幅自画像为止。终于,我们自己站到了叙事舞台的中心,获得了正面的表现,但神也并未离去,而是与那新的主角合二为一。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之后走向复兴的大幕,就是在这深邃的思辨中隆隆开启了。在艺术史系列中,我曾经介绍过另一位德国大画家弗雷德里希的名画《雾海漫游者》(德意志,雾海上的漫游者),德国这个民族,真的很有意思,在绘画界,与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这些民族动不动就出个什么“三杰”不同,真正顶级的绘画大师算来,好像也就只有丢勒和弗雷德里希两位……
某小胡子:那我呢,那我呢 ……这两位绘画大师最著名的作品,其实也只有这两幅。但《自画像》与《雾海漫游者》,这两幅画作一正一反,一个给世人以最坦诚的正面,一个给世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却分别深邃的启迪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连画一幅画作,也能如同一部哲学书一样意蕴深长,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德意志这个民族……这帮人的思维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丢勒画《自画像》的时候年近三十,而今我也在与此相仿的年纪。人在这个年纪上确实应该给自己画一幅肖像,好好的审视一番自己了,看看自己能否能像丢勒一般坦然的直视前路,无愧的直至我心。
……这两位绘画大师最著名的作品,其实也只有这两幅。但《自画像》与《雾海漫游者》,这两幅画作一正一反,一个给世人以最坦诚的正面,一个给世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却分别深邃的启迪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连画一幅画作,也能如同一部哲学书一样意蕴深长,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德意志这个民族……这帮人的思维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丢勒画《自画像》的时候年近三十,而今我也在与此相仿的年纪。人在这个年纪上确实应该给自己画一幅肖像,好好的审视一番自己了,看看自己能否能像丢勒一般坦然的直视前路,无愧的直至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