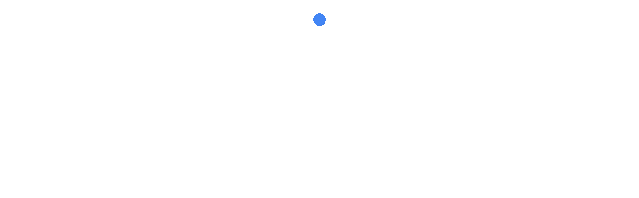
我对长辈之间发生的情感故事,想象力极其贫乏。印象中,我小时候爱偷偷翻柜子里我爸写的情诗——开头写着“给满春(我妈的名字)”,我只记得里面的诗句很优美,感情很炙热,我每次看到都会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看完那封情诗,我忍不住想象我爸妈谈恋爱时的画面——我爸是个戴眼镜的诗人,我妈是梳着辫子、穿旗袍的少女。然后,等我一扭头,撞到我爸那张“扑克脸”——倏地一下,刚刚的画面都被赶跑了。我记事之后,从来想不起我爸妈黏在一起的“腻歪”画面。我爸是家里的“失踪人口”,他每次回家都像“上班打卡”,正好卡在晚饭饭点,急匆匆地冲进厨房忙活起来。他吃饭速度极快,碗一放,又径直朝屋外走去,不知去向。我妈像台“家务永动机”,她似乎总有拖不完的地、洗不完的衣服、干不完的活……那些能解放双手的家电“神器”,在她眼中毫无魅力。她总会说,“拖一下就好了,洗一下就好了。”除了家常,爸妈之间几乎无话可说。那些恋爱时期悸动的情感哪儿去了呢?可难道不是我们觉得他们不需要那些情感,他们才刻意压抑起来吗?在徐童导演的纪录片《他们是肉做的&肉是什么做的》(以下简称《肉》)中,我看到处在生命最后时光的老人们,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情感需求如何一涌而出、势不可挡。纪录片《肉》中,“老唐头”与他的同居对象“桂花”

看纪录片《肉》,徐童用 Go Pro 的“鱼眼”镜头拍成的画面,带给我一种强烈的“魔幻现实感”。白天,一位出现在“鱼眼”内的老人,常常神情呆滞地望着前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走路颤颤巍巍的,话也说不清楚,徐童盯着老人只往下流的口水拍,恨不得让你看清楚最后一丝口水将流向何处。这种呆滞的神情,是最易在养老院中捕捉的神态。有养老院的管理人员将老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养老院里一圈一圈地游走,另一种则呆呆地静坐,甚至只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与眼珠的转动。前者被戏称为“游走型”,而后者属于妥妥的“禅修型”。
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徐童在一个东北小城的养老院足足待了一年,很多素材是他在伺候老人时拍下的。他对那种神态再熟悉不过,他解释道,“这个基层养老院,收留的大多是周边村镇的老人。他们没功夫上什么插花课、摄影课、跳舞班等,每天除了吃就是喝,要不就晒晒太阳,连电视也看不清了,只能充当背景音。”怎么打发生活中大量的空白时间呢?孤独感,这时便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客观上,当一位老人被送进养老院,无异于将他此前的“熟人社交关系”切断,他被迫融入一个新社交环境。除了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由于身边没有子女、亲戚,他们一定程度上也会表现得更松弛。弄清楚这点,我似乎才理解片中的“老唐头”如何以“豺狼扑食”的姿态,来寻觅交往对象。即便是与“老唐头”认识多年的徐童,都没意料到他进入养老院之后的转变。“老唐头”八九十来岁,可除了双耳处的助听器,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他说话一口东北大渣子味,镜头一开,就得意地冲镜头吹嘘自己干过的“牛逼事”——什么一晚上能干好几次、他的偶像保尔·柯察金如何排除万难,以及他从小到大在功课上从没挨过训等等,诸如此类。“老唐头”经常一个人倚在养老院二楼的靠栏处——那是二楼养老院的老太太们主要的活动空间,眼巴巴地望着与其他姐妹结伴走过的“心仪对象”。他也会主动加入养老院老太太间的“茶话会”。徐童观察到,起初,“老唐头”爱上一位养老院护工“刘妈”,苦恋了她两年。“刘妈”一头黑发,比“老唐头”年轻许多,干事也很利索,被徐童称为这个养老院的“超级护工”。这并不奇怪,“一条”采访的研究老龄化与照料劳动的东南大学博士后吴心越表示,在她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发现老年男性会将一部分情感投射到照料她们的女护工身上。在长期的照料中,老人会对护工产生信任与依恋。护工也由此重新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魅力,很多并不拒绝老人的示好。“刘妈”与“老唐头”在一起的画面,通常都在笑。有一次,“老唐头”一把坐在了楼梯的台阶上,裤子也没拉好。“刘妈”趁机捉弄他,想一把拉下他的裤子,两人嬉笑着玩闹了好一会儿。但他们之间的举动,并不让我觉得色情。当我用“黄昏恋”形容这些老人间涌动的情感时,徐童觉得不准确,他认为他们的关系更纯粹,可能只是为了玩闹,为了打发时间。他形容,“当这些老人从繁殖后代的’功能性’人生中撤出来,他们进入新的幼儿园阶段,变成了老小孩。”徐童还描绘过一个“老小孩”的画面——每天清早,天亮了,院长与护工还未赶来。老人们常常趁这个“天下大乱”的时间,跑出来“浑水摸鱼”,他举例,“楼上的跑来楼下偷口酒喝,或者拿隔壁的一个小零食塞嘴里。”可“刘妈”的伴侣还在,“老唐头”苦恋无果。之后,他便将目光锁定在与他年纪相仿的“桂花”身上。八十多岁的“桂花”,认识“老唐头”前,若按“游走型”与“禅修型”分的话,是不爱说话、眼神有些呆滞的“禅修型”。她吐词也不清楚,说起话来有些呆傻呆傻的。她喜欢笑,两块“苹果肌”很突出,笑起来像是一尊女菩萨。
认识“老唐头”后,“桂花”有时一天换好几身衣服,也很可能是养老院唯一涂指甲油的老太太。追求过程中,“老唐头”是个“直肠子”,语气又急,恨不得把“我想和你处对象”写在脸上。得不到对方恰当的回应,他还会耍小脾气——往床头那么一趟、扭头把被子一盖,爱谁谁。但很快,“老唐头”与“桂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黏在了一起。他们常常约着一起去卫生间,“桂花”在外头等着“老唐头”。过一会儿,两人又去各自的床铺上坐坐,打发时间。养老院的院长,甚至为两位老人操办了一场“婚礼”——那天,他俩脸上被抹得红扑扑的,“桂花”戴上“老唐头”置办的金银首饰,围观的老人们闹起了“洞房”。可“洞房花烛夜”当晚,“老唐头”躺在床上掉泪,他说,“‘老唐头’重回青春了”。“桂花”坐在一旁,她的眼泪也直往下掉。
我曾想当然以为,他们从“包办婚姻”的人生中撤出,进入到“自由恋爱”的新阶段了。但很快,一桩突如其来的事,提醒我不要“浪漫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老唐头”与“桂花”想同居的想法,被“桂花”的女儿强烈反对,这让养老院很难办。不出几个月,“桂花”居然在子女的协助下,搬离了这家养老院。我想,“桂花”的女儿一是担心母亲被骗,二恐怕也觉得母亲别老不正经吧!“浪漫化”老年恋情的危险之处在于,会让我忽视“老年恋情“的很多困境。所谓的“自由恋爱”,需要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如果连吃喝拉撒都无法自理,谈什么“恋爱”呢?事实上,这个养老院的很多老人,都不得不把力气花在基本的生存上。身体算硬朗的“老唐头”,才有“资本”去找老伴。而且,决定两人能否在一起的因素中,年龄大小、有无子女等实际因素,都可能盖过所谓的“自由恋爱”。一般,超过五六十岁的老人、仍有抚养子女义务的老人,会难找对象得多。我想到徐童对这些老人的形容——“老小孩”,但成为“老小孩”的代价是,无法为自己作主。小时候的我们,恐怕都恐惧武断的父母吧。没想到父母变老后,我们可能与他们角色互换,成为他们的武断的“家长”。
在“老唐头”与“桂花”的同居屋内,常能看到一些肉体接触的暧昧镜头。徐童的拍摄很直接,经常直直地对着“老年肉体”,包括他们的性器官。为什么拍“老年肉体”、拍屎尿屁就是污秽的?徐童偏不这么觉得。与我爱看的年轻肉体不一样,“老年肉体”看起来毫无性张力。但我很快生出一种道德的反思——为什么我将对恋爱的美好想象,只限定在年轻的肉体上?而将“老年肉体”的结合,视为羞愧的、甚至丑陋的?吴心越在采访中聊到“为什么老年性爱边缘化”的成因,因为老年经常和疾病、衰老、迟缓这样的词汇挂钩,性和爱似乎是一件格外需要身体和精神能量的事情,大家便自然认为老年人已经没什么性需求了。性是边缘议题,“老年+性”就更加边缘了。我联想到,“桂花”的子女阻挠她与“老唐头”同居,这难道不是一种惯常的社会偏见吗?可“桂花”冒着被子女阻挠的压力,与“老唐头”同居了。之后,当“老唐头”对护工“刘妈”再度萌生情愫,并试图以“哪个男人不是这样”的话术劝服她,“桂花”硬气地怼了回去,二人的同居关系也逐渐斩断。这一段看得我拍手叫好,“桂花”的敢爱敢恨不是对她子女的一种有力反击吗?另一方面,尤其是养老院的老年男性,又无法摆脱对失去性能力的恐惧。在片子里,我最常听到的“老唐头”的夸耀是,“我非常行”。而整日只能躺在床上的“老王头”,最大的恐惧是“我不行了”。住在“老王头”楼上的“志英”老太太,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往“老王头”嘴里塞一口好吃的。“老王头”常对她说,“我不中用了,硬不起来了,也没什么钱……”恨铁不成钢的“老王头”,甚至还往尿不湿里塞过咬了几口的硬苹果,试图“以假乱真”。这种“哭笑不得”的画面,让我不禁产生了一些疑惑——人到了老年,对于性需求和性生殖器的张力依然尤为凸显在男性身上,而老年女性的性又有谁在意呢?她们的性会不会往往被忽略或沦为客体对象?在养老院里,“桂花”住的比“老唐头”好——她住在一个独立的单间,“老唐头”是“合租房”。之后,“老唐头”顺利和“桂花”同居以后,他会时不时将双手伸向“桂花”的乳房,把玩、舔舐它们,顺道调侃,“一个奶子起码有一两斤重!”这个具有冲击性的画面刺激了我的神经,不论是何年纪,女性的肉体总是如此自然、直白地成为了男性玩弄的对象。吴心越查阅了很多国外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性爱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它不是线性的过程,可能不局限在插入式性交上。爱抚和拥抱这样亲密的身体接触更重要。甚至一个眼神,一句沟通的话,或者对他人身体的触碰,这都算是老人寻求亲密的方式。纪录片《肉》中,“志英”老太太习惯性“浑水摸鱼”,偷隔壁的一个小面包塞到“老王头”嘴里。“老王头”闭着眼,但很快意识到这是谁,他喊了一句“大姐”。“志英”很得意,仗义地说,“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徐童拍摄“志英”老太太坐在“老王头”的床前
他们之间的相处并不直接涉及“性”,简单到只是“一个人喂、一个人吃”,“志英”老太太也拒绝承认他们的关系。但从老太太吃醋的神情中,我还是瞧出了她对“老王头”的感情。不再将寻求亲密关系,仅仅限定在“男女性爱”上,这也是一种性解放吧。但另一个不容乐观的数据是——据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的数据,我国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50岁及以上病人占比上升比较明显,从10年前即2011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4%。这个数据的成因略为沉重,中国疾控中心指出,老年男性为了满足不被家庭与社会正视等的性需求,往往易于选择嫖娼等的不安全性行为。他们不得不游走在边缘的付费舞厅,如成都“砂”舞厅,甚至是选择“陪床保姆”等。2021年深秋,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崔昌杰在对养老机构做田野调查时,还发现一部分老人与肢体残疾人会从网络中汲取自己的情感需求。他在与一位脑瘫残疾人邓浩的交流中发现,邓浩经常提到一位叫“栀子”的女主播声乐老师。崔昌杰在那篇基于田野调查的文章内写到,邓浩是“栀子”老师直播间的常客,还刷过几次礼物,比如一捧玫瑰花,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栀子”老师的特殊情感。甚至,在“栀子老师”更换直播平台后,邓浩会主动找崔昌杰倾诉,询问帮“栀子老师”新平台涨人气的办法,并且会一个个去原先的平台私信陌生人关注等。当得知自身没有能力帮助她时,邓浩又会流露出惯常的自卑情绪。对肢体类残疾人来说,他们对情感表达一贯自卑且自我压抑,更别提满足“性需求”了。台湾义工团体“手天使”发起人之一的 Vincent,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可他身边却有一些连手指都不方便活动的残障者朋友。Vincent 有感于他们对性的自卑又隐秘的情感,下决心筹备“手天使”,请义工来用手来满足重度肢体残障者的性需求。中老人性需求的边缘,让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的“裂缝”中寻求“性满足”,甚至是铤而走险。这让我反思整个社会以“年轻人为本位”的倾向,这是不是“社会达尔文”的一种呢?
另一位老人——“黄金老头”,也让我产生对老人下道德评判的反思。“黄金老头”,是一位戴着黄金项链、黄金手饰等的老头,他的光头上优雅地顶着一个白色礼帽,正好与他全身的白色服饰相称。纪录片《人约黄昏后》的导演潘昕玉、邹柔逊第一眼就看中了他,“他很扎眼,审美在老年人里算出众的,个子也高,看起来很斯文。”当两位导演冲上前与“黄金老头”搭话,他也显得非常热情、健谈。她们日后将“黄金老头”的种种表现,总结为“表演性人格”。之后,两位导演选择在重庆洪崖洞每周日的老年人相亲角(以下简称“相亲角”),跟拍了“黄金老头”两个月。一开始想拍“老人相亲角”的题材,潘昕玉与邹柔逊是出于一种社会反思,“老龄化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与传统的养儿防老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很忙,老年人被迫陷入无人陪伴的境地”。“老人相亲角”,就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裂缝”之中。每周日早上八九点,重庆洪崖洞公交站前,就会站满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相约着奔向洪崖洞,钻进那个“相亲角”。“相亲角”一周举办一次,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黄金老头”是这里的常客,“相亲角”通常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可他一般七点就起床了。他家到洪崖洞并不近——要先打段出租车到公交站,随后坐上公交,前后差不多要一过小时。每周日,上午十点一过,那条街上人逐渐多起来,A4纸打印的“相亲公告”也变得随处可见,其中不乏各种牵线的“红娘”。“黄金老头”通常就站在街上,像揽客一般,对着来往的阿姨打招呼,“你看我这个老头行不行?”一旦看到阿姨对他表露出兴趣,他便会带阿姨脱离熙熙攘攘的人群,拉着她到角落的座椅处。这时,阿姨们通常会直接地提出结婚要求——“我嫁到你屋里,不要把我当佣人”、“我别的不要,就要一对黄金手饰”……
“黄金老头”
潘昕玉与邹柔逊当时还在念大学,对相亲场合本就陌生,一开始听到“黄金老头”与女性聊天的内容就有些头晕目眩,“他们一下子就聊到谈婚论嫁的事宜,极其直白”。这里的“直白”,反倒不是指一张口就说彩礼。两位导演观察到,在老年相亲市场上,最看重的是健康、年龄,其次才是财产相关的。之后发生了更戏剧性的一幕:“黄金老头”趁势拉拢阿姨——“嫁到我家,我会让你享福”、“我会对你好”。哄开心了,前后聊天不到半小时,“黄金老头”就与阿姨直接嘴对嘴亲上了,嘴里一口一个“婆娘(在重庆方言中有妻子的意思)”。当时,潘昕玉笑着说,“我们几个人简直感受到了‘瞳孔地震’”。可久而久之,潘昕玉才逐渐适应了“黄金老头”在公众场合的“亲亲我我”。哪怕知道有摄影机在,“黄金老头”也毫不在乎,照样与不同的女性在靠椅上、栏杆处搂搂抱抱。每次,“黄金老头”都能抓住短短几个小时,成功“约”到好几名阿姨。用他的话说,“我每次都有收获。”
可这种“收获”,并不是指相亲成功,只是“耍一耍”。“黄金老头”就这样在这里坚持了三年,几乎周周都去。潘昕玉猜,只有在“要么交往到一个对象,要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黄金老头”才有可能停一两周不去洪崖洞的“相亲角”。“黄金老头”的行径,按社会主流的目光,多少有些“渣”。这种“渣”,也反映在一部分老年女性对洪崖洞老年相亲角的态度上。潘昕玉与邹柔逊曾在这里采访过一位阿姨,“她说自己在这里见过很多在这里骗财骗色的,她觉得正常的男性不会跑到这里来找对象。她也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只是过来闲逛一下”。不过,两位导演觉得,相比那些真正“油腔滑调”的老年男性,“黄金老头”不算“渣”。潘昕玉说,“他很直白,直白的有些可爱,也难怪人气会那么旺”。采访结束后,潘昕玉提出要给“黄金老头”买点水果,或请他吃点,但都被他拒绝了。“黄金老头”的表演型人格还体现在,他常常对着镜头说起自己的风流往事。他回忆起早年去舞厅跳舞的经历,有些得意,“我以前认识一个婆娘,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可以立马跟她现在的老公离婚”,他顿了顿说,“可有一次,她看到我同她的一个好朋友跳舞,她就说我背叛了他。”他离婚早,很早就不回自己家里住。至于住哪里呢?他说,“以前都是在女同志屋里住。”仅从他的只言片语,我无法对他早年的“风流”行径做过多评判。但他老年在“相亲市场”的行径,肯定无法用一个字“渣”来形容。潘昕玉也说,她们刚认识“黄金老头”时,觉得“黄金老头”很开朗、也挺光鲜,认为他的处境还不错。可随着跟拍的深入,她们对他的印象产生了颠覆性的逆转。“黄金老头”的“硬件”条件,在老年相亲市场中算不上好。老年相亲市场最受欢迎的,是五十多岁的健康老人。而他今年七十多岁了,他说,“六十五岁一过,(自己)就得了皮肤病,之后心脏病、高血压都来了。”有时候痛得严重了,他咬牙说,“病来了很痛,恨不得买把手枪对着脑门一崩。”碰上前来问“黄金老头”家庭的阿姨,他毫不遮掩地回答,“我就是个孤寡老人,儿子死了嘛。”他与妻子离婚多年、唯一的儿子又不幸早逝。就这样,“黄金老头”坚持了几年,仍是“孤寡老人”。可能很多人会对此不解——来了三年都找不到,为什么还要来呢?但原因应该不难猜,试想一下,不来这里,“黄金老头”还能去哪儿呢?当天中午一过,“黄金老头”依依不舍地随人流而离去。洪崖洞的这条街迅速恢复了寂静,他也撤回到自己“寂静”的生活中去了。一个人坐上公交、打车,“黄金老头”最终回到了自家楼下。他缓缓地走上那栋红砖色的楼。那或许是重庆最古老的一批楼,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日后的“拆迁房”。他停在二楼,进到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他往餐桌那一坐,随手拿起个什么吃的,就径直走向电视机,播放起了孟非主持的“非诚勿扰”。我猜,刚刚从热闹的洪崖洞回来,他肯定忍受不了家里一片死寂。那台电视机,很可能是他平时生活中唯一的陪伴。“黄金老头”想好了,如果下次再犯病、疼到受不了了,他就去买一瓶安眠药,“严重时,把药一喝,让自己走得快些。”当时,支撑“黄金老头”活下去的唯一念想是,“耍朋友”。那一刻,潘昕玉与邹柔逊突然也理解了“黄金老头”对“相亲角”的执着,除了那里,他还有何处可去呢?
把性爱和老年人联系在一起,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想象。而这两部纪录片中,老年人们直白的语言和身体表达冲破了我最初的疑惑 —— 并不是年纪越大,越不需要那些情感和需求,只是这些性与爱的部分被我们忽略,甚至是把“老年无性”作为了一种常态。老年群体的困境是边缘且复杂的,单从这几个人物和故事中,身体机能的老化、离去子女与伴侣的孤独感是最为表层的解读。社会和心理也是牵引老化过程的重要力量,而越往底层的梳理,也越需要更系统的对于这个群体的重视和论述。然而,婚姻需求、陪伴需求、性需求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面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性取向似乎更是无人问津。遗憾的是,在性与爱的话题中,纪录片与我所了解到的故事,几乎是以老男男性为主角。这也许出自老年男性在“性爱”上更宽松的道德标准,而老年女性被默认要么保持禁欲,要么服从男性的规训。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她们想要拥抱、想要牵手、想要有人陪伴之类的欲望,是不被正视的。纪录片《肉》中,有一个镜头很戳我:“桂花”冷不丁地跑到一楼两个老头的房间,摸了摸其中一个老头的手。对方是位神智不清的老头,他没有反抗。出房门后,“桂花”的举止被一旁的姐妹撞个正着。一位姐妹冲“桂花”训话,“你以后还去摸不摸人家的手?”。“桂花”愣愣地望向前方,语气有些无奈与失落,“不摸了。”我能体会“桂花”那种想与人发生肢体接触的欲望,也能想象她在“不要与人摸手”这种社会律令下的妥协。老去,伴随的不仅是身体机能的萎缩,更是一种逐渐陷入孤岛、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孤独——在性与爱这个话题上,更是如此。那将会是何种程度的孤独呢?我试着去想象,去理解,去抚慰。因为有一天,我也会老去。
安利时刻
【2024社没共读会】正在筹备中,即将和大家见面。
如果你对【2024社没共读会】感兴趣,可以加入社没共读会交流群,推荐共读主题和书目,第一时间了解共读会的最新进展,参加共读会的部分活动。加下方老梁社长的微信,即可进入共读交流群,成长快人一步。
作者:Su
来源: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Tyra
点个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