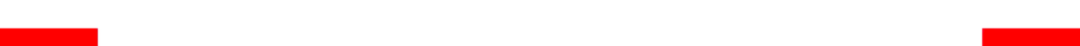铃⽊凉美,1983年⽣于⽇本东京。她的⾝份包括:畅销书作家、社会学学者以及前成⼈电影女演员。出⽣于⾼知家庭的铃⽊从⼩就浸润在⽂学艺术之中,本科就读于庆应义塾⼤学环境情报学专业,硕⼠毕业于东京⼤学学际情报学府。⼤学期间出⼈意料地投⾝于 “夜⽣活世界”,做过夜总会女招待、AV 女演员等⼯作。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学业,硕⼠毕业论⽂题为《AV女优的社会学》。
2009年成为⽇本经济新闻社的记者,2014年她从公司离职,作为职业作家出道。她剥落了此前的旁观者姿态,开始以第⼀⼈称写下⾃⼰与其他夜⽣活女性的⽣活。⾸部⼩说《资优》即入围⽇本⽂学⾄⾼荣誉芥川龙之介奖,后凭借第⼆部⼩说《不优雅》再次入围芥川奖,创造历史。

在国内,铃木凉美因《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与⽇本女性主义学者上千鹤⼦合著书信集)而被读者熟知。最近,铃木凉美代表作《资优》中⽂翻译版由磨铁图书出版,我因此得到了和铃⽊老师对谈的机会。 我是 Chiyo,2018年赴⽇留学,毕业于⽩百合女⼦⼤学院⽇本⽂学专业,研究⽅向为女性第⼀⼈称独⽩体私⼩说。我与铃⽊老师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有⼀个⼩⼩的交叉点:留⽇期间,我⻓期徘徊于歌舞伎町红灯区,成为了 “歌舞伎町民”。我是前任 “⽜郎狂”,也是曾在 Girl's Bar 与⻛俗按摩店打⼯的前任陪酒女和风俗女。后来我将这些经历写成了《在日女子红灯区漫游指南》《陪酒女日记》等纪实专栏。我所用的笔名 Chiyo ,同样来⾃于从事夜职时所⽤的花名。 chiyo :我曾在 girls bar ⼯作,后来⼜去当了⻛俗女。因为这个经历,在读您的《资优》时,我起先最有感触的就是主⾓讲到:进入夜世界⼯作后,以前的朋友就只有 ⼀⼈还保持来往。我对这点可以说深有同感,自从我开始做夜职以后,作息就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了。别的人在约会在和朋友玩的时候我们都在工作,太阳升起时才下班回家睡觉。因此,我几乎失去了以前的人际交际圈,或者说我的交际圈变得只有夜世界了。铃木老师刚刚进入夜世界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您会因此觉得孤独吗? 铃木 :我是在上大学时开始做夜职,最开始是在夜总会。起初,我也准备同时兼顾学业和夜职,但后来夜职占据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和其他大学同学,还有和父母相处的时间都减少了许多,完全一头埋进夜晚的世界了。夜世界仿佛有⼀种很强的感染性,我也是深受影响的⼈之⼀。大约有一年左右,我完全没有去学校,只埋头夜晚的工作。就算在白天醒来,能联络上的也只有一起做夜职的朋友。我也曾想去做更普通的打⼯,但我能感觉到⾃⼰的⽣活已经被夜晚所侵蚀了。从那开始,我就和其他夜晚以外的世界隔绝开来了。所以说,在日本做夜职的女孩里,越来越多的孩子都有对某事某物产生依存的倾向:比如牛郎,比如药,比如购物。还有就是所谓的 “menhera”,精神上患有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我想就是因为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局限于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所以当我和年轻的 AV 女优,或者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孩们聊天时,我都会和她们说:要尽量有意识地让自己在除了夜晚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这样比较好哦。这样就不至于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限定在夜晚的世界里,连可以逃走的地方也没有。 C :那像这种时候,为了从夜职之中松口气休息,铃木老师一般会去哪里呢? 铃 :是呢,我最开始的一两年完全只做着和夜职有关的事,虽然中途稍微去干了些别的,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夜职的工作。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危机感 :这样下去,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染成夜世界的颜色。因为这种危机感,我回到了大学,有意识地去和那些和夜职没关系的朋友,还有和父母亲戚保持联络。另外,大学的课业也按着最低出勤限度去参加了。为了还能有一些夜职之外的事能牵绊着自己,我回到了学校。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C :这么说来,玲木老师最好的朋友,是夜世界的人,还是普通人呢? 铃 :做夜职工作的时候,果然每天待在一起时间最多的,就是夜总会里的其他女孩子呢。但这些人之中,能称得上 “挚友” 的女孩,是从小学时代就认识的女孩子,我们的高中也在同一所学校,后来又一起来夜总会工作了。“以前就认识的人” 和 “因为夜职才认识的人”,相处起来还是稍有不同的。在夜场里,我虽然也交到了些朋友,但很少有真正的挚友。但其中有一个特例,是我做 AV 女优时认识的人,后来我不做了,她也去做了别的工作。结果我们各自在新的领域活跃时重新遇上,就这样再次成为了好友。可总得来说,曾经在同一个夜总会工作的同僚之中,几乎没有谁是现在还保持着交友关系的。所谓夜晚的世界的关系……大家彼此之间,说不定连对方的真名也不知道,但是却每天从早到晚都生活在一起。从某种意味上来说,这是很紧密的羁绊。可一旦生活的地方改变后,这份关系也会随之结束。 C :俗话说,歌舞伎町民的朋友只有歌舞伎町民。就像刚才铃木老师说的那种 “夜世界的引力”。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觉得夜世界是一个尤为狭小的世界,这里就好像是和白天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异世界一样。但反过来讲,我感觉外面的人其实也没有想接受我们的打算。比如说, 要放弃风俗业,转做普通的工作时,总有许多困难。 铃 :这点我也有同感。当我放弃学业,投身夜世界之后,我感觉那些还在大学里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在公司就职的人,他们身上的感觉都和我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再见到,也觉得彼此就像是异世界的人,连说话的语言都变化了。又或者说,就算你已经在夜世界里有了稳固地位,但离开之后,你真的还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吗?这是很困难的。不管你在夜世界如何成功,就算是成为了NO.1的陪酒女,学术界和商界也不会认可你。我想,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当自己想离开夜世界去外面的社会,却发现自己的腿怎么也动不了。在日本,有很多像是陪酒女夜总会这样的兼职打工。女生在大学时代做这行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些孩子在大学毕业的那个时点,能 “啪” 地一下很快找到普通工作,于是立刻就辞去夜职。但如果是没能立刻找到工作,就这样毕业后又继续干着夜职的,渐渐地就会变得难以再回到普通的世界,无法和外界接上轨了。我比较幸运,在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研究生,夜职时代差不多是和学生时代在同一时点结束的。之后又去做了新闻记者,但是我隐瞒了之前在夜场的经历。我觉得,要是被周围人知道了,恐怕我就没法再继续待在这里(指新闻社)了吧。那时我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怀抱着这样的不安:要是被发现了,就只能一辈子做夜职了……我也曾有过每天这样担忧的时代。 C :我有时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一旦开始从事夜职,想停下的时候却无法停下了。 铃 :是呢。在现在的日本,比如说,有一个女学生,她想去国外旅行,或者想买昂贵的衣服之类,普通打工无法短期内赚到那么多钱,那么有很多女孩就会为此相当轻易地去做夜职。这样的女孩其实很多。说到底,相对而言,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夜职是一份做起来很容易的工作。在你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究竟想要做什么工作,究竟想要度过怎样的人生时,夜职是很轻易就能去从事的选项。因为夜晚的世界非常包容,无论谁都能进入这个世界,无论是谁,都能在这里简单地找到工作。可如果就因为这样 “很简单就能去做,因此做了” 的工作,从此的人生都被限定住,我觉得这是对那些女孩们而言很残忍的事。我更希望这个社会是,一个人在还很年轻,人生阅历还很浅薄时做出了偏离常轨的,甚至是错误的选择后,有一天她有了真正想做的事,想重新开始,还能拥有修正自己人生轨道的社会。日本是非常重视 “应届生录取” 的。一旦你离开了原本的路线,比如你去做了夜职,你的履历上就会形成空白期。这样你重新找新的工作就会非常困难。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的社会系统问题非常严重。在欧美,一个人可以在二十多岁体验各种工作,或者创业,到了三十岁也能重新找到一份公司里的稳定工作。但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下,你必须在22岁时就找到自己一辈子的工作。要是你在22岁,这个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时去做了夜职,之后你就无法回归社会了。 C :说到这个,铃木老师之前做过陪酒女和 AV 女优,在后来您作为作家出道的途中,有因为之前的这些经历遇到困难吗?人们会因为你的夜职工作怎么看待你,会不会遇到歧视? 铃 :我第一次出书,是关于 AV 女优回归社会问题的书(作者注:铃木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当时我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隐瞒了自己做过 AV 女优和陪酒女的事,也没有说自己现在在报社工作。作者介绍栏目上,只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年龄,别的什么也没写。我在报社工作时完全隐瞒了过去的夜场经历。虽然也被一些人察觉出端倪,但基本还是保持着 “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报社工作” 这样的身份。开始作为作家活动时,我本来也是同样的打算。哪怕是在日本,在报社工作或者写书的人,以前曾经从事过色情行业,也是一种丑闻。但就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时,我过去的经历被爆料杂志爆出来了。从那以后,到处都能看到这件事。在网上查自己的名字,也立刻会出现 “AV 女优” 的关联词。那之后的两三年,只要一在 google 、 yahoo 或者别的什么网站搜索我的名字,只要点击图像搜索,出来的全都是 AV 图片。为此,我拼命接受采访。虽然按我自己的性格,是不太喜欢在采访或者活动里露脸的。但是我真的太讨厌一搜索自己的名字出来的就都是 AV 了,所以我拼命接受采访,尽可能多在采访里露脸。现在再搜索 “铃木凉美”,起码第一页内容都是身为作家时的我的照片了。不过再往后面继续搜索的话,果然还是有 AV 图片冒出来。要全部消除掉,大概得花很长时间吧……我作为作家活动,也有十年了,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最开始,如果不以 “元 AV 女优作家” 自居,很多媒体就不会给我工作机会。虽然倒也谈不上多绝望,只不过,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其他事,人们最后还是会因 AV 的噱头而关注我。我十五年前就从 AV 业界毕业了,但果然,即便是到了今天,每次被人注意到时,首先会被提起的,不是当过新闻记者,也不是从哪所大学毕业,也不是出生在哪,也不是父母是怎样的人,而是我当过 AV 女优的经历。关于我的报道, “AV 女优” 一定是作为第一大特征被写在标题上的。这一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海外都是一样。所以,如果有和过去的我一样,想着 “就拍一次 AV 好了” 的年轻女孩,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更认真地考虑一下:AV女优这份工作,说不定你做个两三年就放弃了;但是,“前AV女优”这个头衔,你脱离这个业界后再花十年二十年都无法摆脱它。真的就是这样的。之前,我因为入选了芥川奖的候补名单,又有许多此前不知道我的名字和经历的人开始关注我,结果我再次因为 “元 AV 女优” 而受到了关注。我过去的照片又被刊登在了体育报纸或者周刊杂志上。大概,这件事会一辈子伴随我吧。但即便如此,我也是很幸运的,我能得到很好的工作机会,能遇到可以理解我的编辑,能一直有工作。好歹没有因为过去而度过特别辛劳的人生。不过这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有人因为讨厌被人以这种目光看待,干脆就再也不出门,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作为年轻时一时轻薄决断的后果而言,这样的结果未免太过沉重了。 C :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奇怪呢。如果说是在中国和其他风俗业不合法的国家,因为这个行业本来就不合法,所以人们会更严苛地看待从业者。可是在日本,这本来就是合法的生意,为什么人们还会用奇怪甚至歧视的眼光去看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 铃 :是呢。因为日本是一个无论法律也好,别的什么问题也好,都相当“暧昧”的国家。日本法律有很多灰色地带,比如说,真正的卖春行为也是禁止的,但是打着 “不是真正性交” 名义的风俗行业却到处都是。而在 AV 的问题上,日本其实也有淫秽物品罪,但实际操作起来,基本上只要打了马赛克就什么都能拍。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是非常暧昧不明的。总得来讲,日本对于色情业者的态度就是法律上接受。风俗女的生活中也不至于会遇到像一些有特殊宗教背景的国家那样,被打了警察也不管,无人同情那样严重的迫害。但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会有些背地里的欺凌,和若有似无的偏见对待吧。要说真的对此感觉到强烈厌恶感的,是来自于曾经我遇到过的一位生活经验很丰富的西班牙人。我们关系变得亲近起来后,我也没有特地和对方说过自己在当色情电影演员,但后来对方在 sns 上知道了我过去的事后,把我骂得很厉害……这是我在日本从未有过的经历。虽然在日本,做这行会不可避免地被人在背后说道,但大概是因为日本一向没有那种特殊的宗教背景,所以大部分人对此的态度基本是比较暧昧的。日本人不会对此展现出明显的厌恶感,也不会非常明显地要赶走你,更多时候,是会觉得你和别人不同,就把你当做异类敬而远之。这种反应也可以说是非常日本了。虽然总归比会挨打什么的来得要好。就像日本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也是一样,日本没有那种会严厉惩罚同性恋的宗教背景,也不会因此把人关进牢房。而像美国会有的一些针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枪杀事件,和仅仅因为是同性恋者就被人殴打,这样的事在日本是很少的。但是,在日本,同性恋者在职场中,经常会面临一些背地里的欺负和小小的歧视。不摆出明确的态度,也无法明确地说清楚什么是坏事,但却会有若有似无的危机感和差别感。这种没有明确定论的暧昧的态度,我觉得也是日本的一种国民性了。 铃 :在我高中时,东京流行过售卖“现役 JK 内衣”的店铺,也就是 “Bloosailor Shop” ,我就曾光顾这样的店铺。不用直接与男性亲密接触,只是自己用过的内裤能卖到1万元左右。当时感觉还挺 “捡到了便宜” 的。当然,这种事要是被父母和老师知道了,一定会被生气地责骂批判。但要说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几乎没有日本人能明明白白讲个清楚。哪怕买卖 JK 内衣成为了社会现象,还上了电视台的辩论秀节目论,但那些反对者们也只是暧昧地说着什么有违伦理,但又无法用语言有条有理地说明到底为什么违反。那些人或许也是想着保护那些女孩,但结果只是粗暴地说不许做这做那,这让我其实感觉上不太好。虽然我能现在知道,当时卖掉的是很珍贵的东西。但当我还是个女高中生时,能用一万日元卖掉一条脏内裤,对此除了 “太幸运了!” 的感觉以外,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那时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大人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也成为了我开始对夜晚的世界感兴趣的动机之一吧。 C :那么,在现在的老师看来,这其中的伦理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 铃 :我投身于写作,正是因为我自己无法否定高中生售卖内衣、成年女性从事卖春或水商,我想将来有一天能以亲身经历,否定这其中真正值得被否定的事。比如出演 AV 之后,一定会对学校、男友、双亲、甚至随便什么人撒谎,否则就会化作日后的绊脚石,或者成为遭人威胁的导火索、引来危险。还有,夜职与普通的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个人的价值不会随着履历的积累而增加,反而会被磨损,就连灵魂也是呢(笑)。女高中生卖掉了几条脏内裤,这是否真的会对其人生造成污点,哪怕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很难评判的。不过确有其事的是,出入这种场所,自然而然会心生对男性的蔑视。花1万元购买女子高中生内裤的生物,这就是男性。我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并且感觉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也好。所以我对与异性进行灵魂上的交流抱有根本上的悲观态度。明明和女孩子在一起可以很快乐地生活,但我对男人的难以理解已经到达了绝望的程度。作为后遗症,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谈过正经的恋爱了。到了这个年纪也没有结婚,也是出于这种对男性的不信任感。 C :我也一样,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想要结婚吧。即使在我辞去风俗工作后,一想到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普通的男性,也可能去逛那样的店。看到路上的随便什么男性,我也会想到,他和那个恶心的大叔客人,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呢。
铃 :确实呢。我在JK时代,在魔术镜另一侧将内衣贴在脸上嗅闻的大叔们的脸,直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对于这些男人,无法交流的感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C :这种排斥心理是正常的吗?还是说精神上出了问题?有时我自己也会烦恼。这种话题对心理医生也没法说出口,不知道如何是好。 铃 :不管是男是女,彼此偏见的社会本身就是很苦闷的。男人瞧不起女人,女人看不上男人,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彼此理解呢?要怎样才能拥有感受到对方魅力的乐观精神呢?听起来像是对女权运动泼冷水,但我从最开始就觉得,对男人说这些是没用的。对男人早早地就绝望了,这种观点果然不是很利于社会的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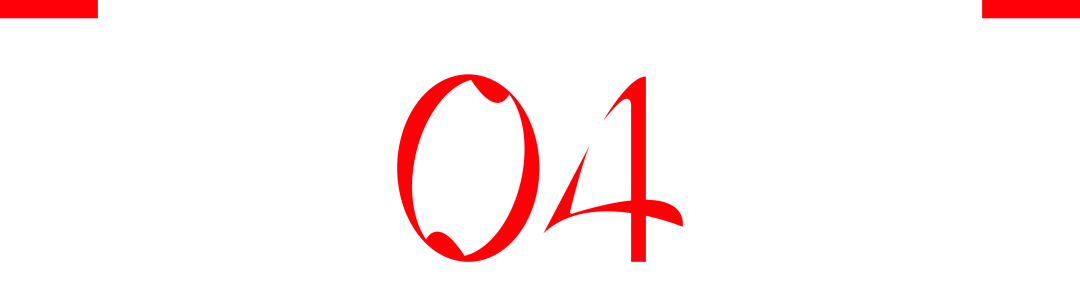
铃 :我去年就40岁了,不能像是 《资优》 的女主角那样活跃在夜晚世界的第一线了。尽管如此,我却一直在描写这个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对我的吸引力,并没有随着时间衰退。这种魅力不是说夜晚的世界比白天的世界更加正确,而是白天所欠缺的东西掉进了夜晚,并在夜晚的世界中展现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辉。当然了,那些欠落的东西是鱼龙混杂的。有坏的人,也有很多讨人厌的事。相比在报社工作,在夜总会工作能遇到的讨厌的事情还蛮多的……虽然在报社工作也有很多讨厌的事啦(笑)。但在夜世界,人会遇到危险,处理不好时,也有人因此丧命,也有人背上数额离谱的欠债。危险自不必说,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是能向所有人推荐的地方。可正是这样的地方,它有时也会突然在黑暗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如今仍让我魂牵梦绕。做夜职的女孩们,有很多品行不端、举止散漫、被他人所厌恶的孩子。可有时,也能遇到非常纯粹的灵魂。大众眼里平时惹人生厌的人,她们所拥有的美的一面,这种反差,让我对那些女孩抱有憧憬。我被她们深深吸引着,我想继续书写她们的故事。

我进入夜职最大的契机,就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们。她们在年轻时的我看来很有魅力。我想融入她们的圈子。在我的高中时代,日本盛行辣妹文化。我也想穿得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们一样,所以选择了规矩没那么严格的学校。当时偶尔会在街上看到风俗店的大姐姐们下班出来,前去牛郎俱乐部的模样,令我印象深刻。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很有魅力,我也想进去看看。可以说,憧憬就是我最强的动机。如今也是。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与药物随处可见,糟糕得就连夜职女孩们自己都会对此感到讨厌的世界。但即便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夜职,当我在街上、在居酒屋见到夜职的女孩们时,我也想走进她们之中,加入她们的交谈。 C :我也一样,最初只是在 SNS 上听说了日本的歌舞伎町和牛郎店十分有名,去了之后就立刻沉迷其中了。比起牛郎有什么魅力,主要是出入这些牛郎店的女孩子们都十分可爱。我自己之前因为精神疾病的原因,生活中总遇到很多不理解的眼光,但在歌舞伎町,却有很多和我一样,能彼此感同身受的女孩子。可以说,我也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所。毕业之前,我几乎每天都前往歌舞伎町,也是因此进入了 Girls Bar 工作。 铃 :说到歌舞伎町,哪怕我现在已经辞职,我还是喜欢动不动去那里喝上一杯。六本木这些高级餐饮胜地,与歌舞伎町的氛围是不一样的。歌舞伎町脏兮兮的,到处都是垃圾,还有瘫在路边的醉汉。可除了这里无法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渡过这个夜晚的人们,也是聚在这里相互取暖、分享自己的故事。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拥有很强包容性的地方,我很喜欢它的这一点。日本是很排外的,不只是种族歧视,也有阶级歧视,就连住宅区也有彼此的鄙视链。基本上是一个不允许多样性的地方。大家都只憧憬中产阶级的住宅区啊、商区这样。而歌舞伎町有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与移民,中国人,韩国人,尼泊尔人的聚集区都离得很近。
日本其他那些 “干净体面” 的街道所排斥的人和事,歌舞伎町将这多样性的一切都照单全收了。因此才是这般非常耀眼,光彩夺目的地方吧。 C :您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讲了很多次自己进入夜世界的理由。您提到了您的母亲。很多人说您是叛逆少女。从您自己的角度是怎么想的? 铃 :母亲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女性。她是个坚持己见,说一不二的人,也是一个强烈反对夜职的人。而我想见识她所不知道的魅力,或者说闯入她理解范畴之外的世界。在我看来,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几乎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没有无法成就之事的成功女性。这样的她,明明年轻时曾在 “美人喫茶” 工作过,却竭力否认夜职、售卖自己这一点。这就是我写下了《资优》的理由之一。我沉迷于夜晚的世界,原动力是想见识一下母亲所无法理解的世界吧。想要脱离母亲的思想、跳出母亲所指定的世界、理解她拒绝理解的东西、选择与她截然不同的人生。 C :这一点我也是一样的。在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工作上的理由而结婚。离婚时,我的父亲有了外遇,对方就是在从事着水商一样的工作。母亲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美貌、聪慧还有着优越的工作,却没有被选择,父亲反而爱上了那样的女人。听到了这个故事,一般的小孩也会讨厌那个第三者吧。但在我还小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反倒是好奇,父亲喜欢上的那个女性,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在过去的人生里,我从未了解过世上这样的人。而向来头脑聪明,似乎什么都懂的母亲,也完全不了解那样的女性。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她也有不知道的事。所以我比起对那女性的厌恶,反而是无限好奇了起来。没有站在母亲那边的我,大概是很奇怪的小孩吧。那之后,我就一直对风俗娘和夜店女郎十分在意,一有机会就想去了解这个世界。从这点来看,母亲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我从初次读到铃木老师的书时,就对您提到母亲的部分非常有共鸣。回到刚才的问题,母亲带来的影响固然很重要,但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您进入夜晚世界的动机,会是什么呢? 铃 :一言以蔽之,就是憧憬吧。在社会上,医生、律师,或者像我父母那样大学老师的职业是值得尊敬的。与之相比,陪酒女郎则遭人鄙视、是不道德的、甚至在某些地方被禁止的工作。那种灰色的、暧昧之处,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十分有吸引力。我向往这些打破常规的人。我的青春时代,是在日本的性别差异破冰之际渡过的。青春饭、出卖色相,成为了侮辱词。大家开始说女人就要靠学历,职历,不能依靠美貌、面相。不过,我却很羡慕那些反而将美色化为武器的女性,比如风俗娘,夜店女郎、AV 女优。或许正因如此,才对这些职业抱有了敬意和渴望。 铃 :正如之前说的,我一直在写夜职少女们的某种魅力,那种让人想要接近、憧憬的气质。虽然不漂亮,却很美,就像是水洼之中的一颗钻石般闪耀。这种魅力于我而言依旧存在。不过,实际进入那个世界后,我也曾讨厌过、绝望过。但我还是活在了夜晚的世界,特别是之后还进入了 AV 界。因为经历了太多,以前站在舞台下仰望的纯粹憧憬,如今变成了有爱有恨、但某些地方却还保留着小小的憧憬。这种感情还是很复杂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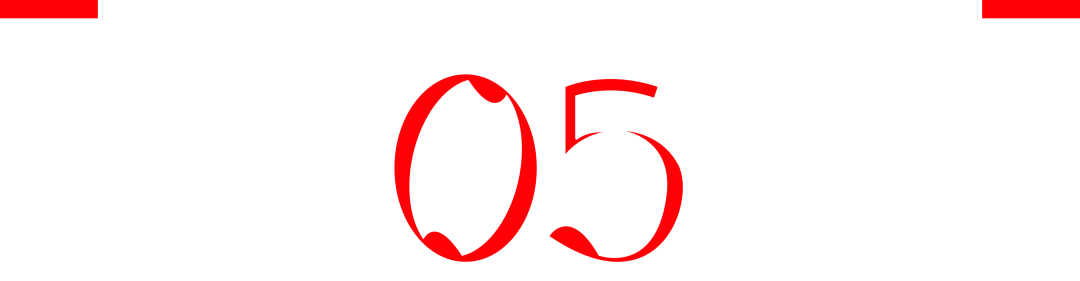 “不管背景是什么,夜晚的世界都是从零开始。”
“不管背景是什么,夜晚的世界都是从零开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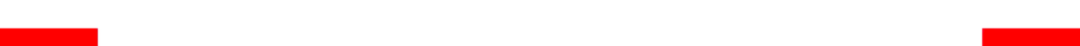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C :像老师一样,不是因为经济状况而是心理原因选择夜职的女孩,是普遍现象吗? 铃 :在我年轻时,日本的经济比现在更好一些。在我的时代,有不少 “原味少女” 是普通家庭出⾝。不过,从事风俗界、AV 界的贫困女孩,还是要比想象中多。低学历的、单亲家庭的,或者父母某一方与夜世界有些关联的…...大多数人都是出⾝不富裕,或者有学历方面的原因。最近,日本因为经济衰退,被逼得走投无路、从事这行的人更多了。新冠、日元贬值也有一定影响。没有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松赚钱的工作了。年轻女性想要赚更多的钱,就只能去夜世界,或者出国打工。 C :在网上偶尔会看到这样的评价,因为老师您出身优良,有些人认为您做夜职只是大小姐观察人类的一种娱乐。也有人批评,您有选择的自由,和其他别无选择的风俗女孩根本就不一样。关于这一点,老师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铃 :人们在选择工作、决定以此为生的方式时,究竟是不得不做的强制选择、还是以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我不认为有太明显的分界线。我不能说我的选择百分百理性、遵从个人意志的。有随波逐流的选择,也有叛逆的选择。虽然家庭优渥,但年轻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钱。我最初的目标,是就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能够决定自己选择的、自由工作的女人。有些人,因为我能在夜晚之外的世界找到生存的手段,所以说我是游戏人间、观察世情的大小姐。在 AV 现场也被说过,你看这个人是上大学的,和我们不一样。我的母亲,知道我选择做 AV 女优后对我进行的说教,也是类似的。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好好活着,所以就说我是进去玩玩。我母亲看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大小姐离家出走去吉原的日本老电影呢。不过,我年轻时去那里是有迫切的理由,不是以游戏态度加入的。只是无可奈何地被其吸引。不管背景是什么,夜晚的世界都是从零开始。不管出生富有还是贫穷,一旦踏入夜总会,学历经历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可爱才是关键。那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容纳的广阔空间。也有人进入之后才觉得这里不是容身之所,也有人无论如何都想在这里创造容身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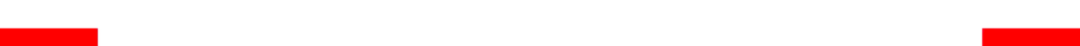
C :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中,也有人认为做风俗就是背叛了女性集团的利益。所谓堕入风俗,或者成为家庭主妇,是一种 “向下的自由”。老师作为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有夜职的经验,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铃 :不仅限于中国,也不只限于这个时代。女权主义者关于色情买卖的话题本就有很大分歧。有人想要规避敏感信息排除一切色情因素,也有人主张言论行为自由,认为制作色情作品是女性的权力,值得尊敬。在日本的精英女权主义者中,也有着对谄媚男性的工作的普遍蔑视。但也有人认为,任何工作只要是出于女性自身的选择,则这种权利就该得到保护。进一步地,有人认为因为喜欢而卖春,或是成为家庭主妇,是维护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男尊女卑的社会世代传递,是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会制造女性不得不选择此路的困境。这些女权主义者反对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我能理解。这个行业自古以来就是为了服务男性而创造的,是男人强迫女性工作的地方。但是到了现代,女性 AV 导演、女性风俗经营者越来越多,已经没有那么 “男本位” 的感觉了。我在这里见过女性被剥削的场面,也见到过男性处于弱势而女性占据强势地位的场面。我觉得它的结构非常复杂。 C :在老师看来,从事夜职和从事普通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铃 :比我还要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性工作者打出过 “风俗与一般的劳动同等” 的口号。但我认为其中的不同在于:根据我的经验,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是人最具有价值的一天。AV 行业最赚钱的时候,通常是刚出道,或者说还是个 “处女” 的时候。风俗业也一样,越年轻越赚钱。这个卖点要远超实际的劳动价值。与普通行业相比,女性的年轻、可爱、无垢之处才是诱导客人花大钱的地方。在居酒屋、拉面店、销售、打工店里,是以努力为价值导向的。而以性为主要消费的职场,顾客给的钱,不是支付给对等的劳动力,而是支付给女孩子的青春、性和肉体。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卖点,自身的价格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C :老师也提到过,外界的人对风俗娘和 AV 女优抱有一种 “受害者”、“弱者” 的印象。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想呢?老师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铃 :我觉得产生这种印象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在很久以前的日本,从事卖春的女性有很多都是父母欠债而被卖掉的。另一点是因为,少女的肉体被那样廉价地卖给男性,就像是遭到了剥削 —— 虽然在风俗界工作的大多是女性,但经营者、或者说赚到钱的,却多是男性。我觉得这些说的也没错。只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夜职的经历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耀眼的回忆。说我是被伤害、被剥削的人,反而是对此什么都不知道。这点让我很是不甘心。 C :从我个人观察而言,做夜职的女孩很多有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在牛郎揭示板写自己的日记的 “文学少女” 也不在少数。这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铃 :虽然做夜职的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大家都不怎么看书,却一边做着夜职、一边在网上写博客、私小说。因为想要诉说的事情很多,身边却又无法倾诉吧。这是一个在 “里社会” 才得以一见的工作,有不少在现有语言体系中难以描述的事情。为了传递这一点,所以才会产生执笔的冲动吧。 C :上野老师《始于极限》中提到您至今为止的写作方法,可能在今后行不通了。请问在《资优》的创作上,上野老师是否对您造成了影响呢? 铃 :对于小说写作这类文学形式而言,上野老师的态度其实一向不是太积极肯定的。但是,对我来说,随笔写些什么,小说写些什么,一直是比较随心和混乱的。但说到底,关于贩卖身体的冲动,要如何停止这种冲动,为什么这是不可以做的事,为什么人会因为风俗业而被伤害这些问题,始终是我心中的疑问。虽然很偏颇,却是我最感兴趣、心之所向的写作主题。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夜职经验的女性来说,这种主题也许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但我还是想写关于卖春的故事、歌舞伎町的故事、欢乐街的故事。 C :对于《资优》这一部作品,您会将其定义为更文学性的还是更具社会学性的呢?似乎只要我们的职业放在这里,人们就会不免以社会学的角度期待你对“夜世界”或者性别问题作更理性的批判。 铃 :在我看来,怎么看待都好。去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牛郎店的小说。但是被人当做社会学资料来使用,我也完全也不介意。如果那些好奇的人能因此知道 “铃木凉美” 是怎么想的,以夜职为目标的女孩子、玩转牛郎俱乐部的人如何所想,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是读者的自由。至今为止,在随笔或者文章中,我基本从来没有对一个问题断言自己的态度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我觉得对这些本就界线模糊的事,作者不要清楚地以 “善” 或 “恶” 一言以蔽之地下结论评论会比较好。如果读者能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徐徐感受到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就好了。从这点来说,还是更希望大家能来阅读我的小说本身呢(笑)。 C :当我读到老师的作品时,确实是这种感觉,好像能透过作者的眼睛稍微看到她所看到的世界。老师把所见到的夜晚的世界展现给了我们,这点来说真的很感谢。铃 :⼀如既往吧。我也想着为了增加读者群体,或许该去写⼀写普通⽩领和⼤学⽣的故事。不过果然,最近我意识到,那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作为普通的作家,按照要求⽤⽂字赚些⼩钱,我⾃认为在这⼀点上我还是蛮能⼲的。但我从报社辞职,就是因为⽆论如何都想写夜职的魅⼒、那时如同着了魔⼀般的快乐。如果刻意回避不去⾯对这个主题的话,我作为写作者就失去⾃⼰的初⼼了。所以最近我⼜开始写很多有关夜职的话题。因为,⾄今为⽌,我果然还是不知道买卖内衣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会对女⼉选择这种⼯作⽽⽣⽓,为什么会因为女⼉成为了 AV 女优就⼤感震惊呢?——我对此很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我所看到的景象,仅仅是⼀个擦肩⽽过的路⼈的⽣活,从中展现出来的那⼀道如同光芒的事物 —— 我想写的是这些东⻄。
C : 老师的《始于极限》和《资优》都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话题,请问您有留给中国读者朋友们的寄语吗?
铃 :我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与日本比起来,中国女性在社会上更为活跃。与日韩相比,没有那么重男轻女,女性在坚强地工作。但是,上野老师的书至今仍能在中国广为流传,也说明了东亚女性还是有着相似的处境,相似的痛苦、不愉快的回忆。与风俗业合法的日本相比,色情产业在监管严格的中国不是随处可见。但夜职的世界,始终是由女性的疼痛、力量、艰难,以及些许的快乐而构成的世界。所以我想,即使没有作为夜职者的经验,仅仅是作为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也同样能对此产生些感触。我的经验如果能为你所⽤,那就太好了。不管是写书,还是写随笔,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过程,祝你好运。谢谢铃木老师。我们期待您的新作《资优》与更多中国读者会面,并对老师富有启发的谈话表示真诚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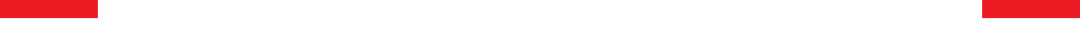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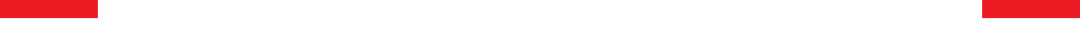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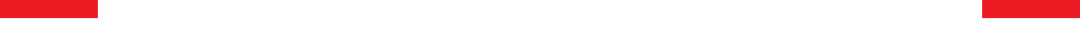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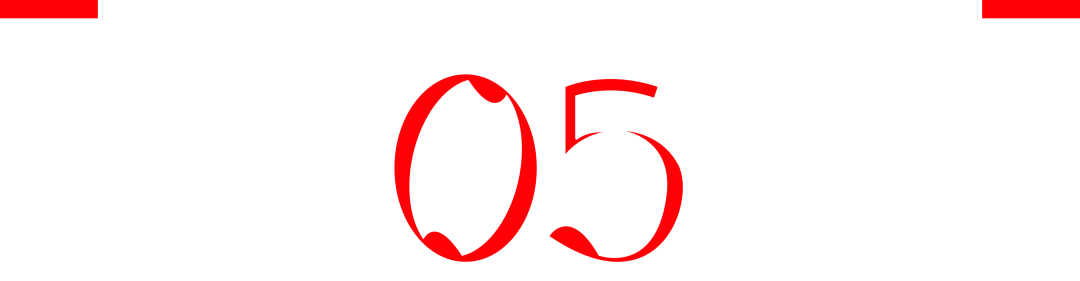 “不管背景是什么,
“不管背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