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经历:看心理医生(下)
写自己的故事,尤其写与婚姻有关的故事其实很难写,如果写少了,写得模糊不清等于不写,表达不出讲故事的意义;如果写多了,写得太细致、太坦诚,又有暴露隐私的问题,很难拿捏尺度。
我写这个移民经历系列的主题是为什么我要看心理医生?看了心理医生之后我有得到帮助吗?我在系列文中想表达的是:(1)每个人到了新的生活环境都有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2)如果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异常,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就该及时的求助于心理干预;(3)幸福婚姻的维持不仅需要爱,也需要夫妻双方的包容和理解,重组家庭的婚姻更需要如此,“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情。”(尼采)
(一)
前几天我读了博主蓝天清风的系列博文《异国他乡的上海室友》,讲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与一群上海青年初到澳洲留学时的经历,文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 现在我们是吃不到的苦比吃得到的苦还要苦。” 那段时间博主与室友们在澳洲到处找工作,室友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制衣厂的工作,干了大半天才20澳元,室友感叹,做工虽苦,但找不到工作更苦。
我相信,每个新移民都经历过新环境的“苦”,只是每个人的“苦”味有所不同。对蓝天清风和他的室友们来说,他们的苦是找工作和做工的苦,而当时对我来说,是没有工作的苦,是不能接受做家庭主妇的苦。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努力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男女都一样,妇女也能顶半边天…。在新中国,没有一个妇女不工作的,在我看到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女人结婚后是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中国的“职业”这一栏目里从来没有“家庭主妇”或“全职太太”这一项(我后来在台湾的一些表格里有看到,“职业”这一栏里有家庭主妇)。
还是后来我看了心理医生,他帮我分析了,当时造成我心理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主要原因是我初来美国后环境的巨大落差,以及对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错误认知,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许多心理负担从而产生焦虑、恐惧、迷茫和忧虑不安心理。
我今天继续说说我看心理医生的经历。
在先生妹妹家住的那几天,我心情暂时平静了一些,妹妹很会做菜,我那时不是素食者,什么肉都吃,在妹妹家吃了美味可口的台湾菜。妹妹还教我做几个容易的台湾菜,我自认为自己无论学什么都能得心应手,做什么都难不倒我,都会做得很好。可是,我在学做菜方面特别笨,特别没有悟性,我虽然学了,但至今还没有学到位,只是偶尔做“三杯鸡”勉强得到先生的表扬:)
几天后我回家了,我的抑郁情绪依然没有得到太多的纠正,纽约的冬天虽然寒冷,但经常是晴空万里,地上的雪也已经慢慢在融化,有时候我穿着冬装到户外走路,无目的的走,只是不想一个人白天老呆在家里。我在户外走路的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一个人,纽约长岛还算比较安全。
有一天,我在户外走了很久,很远,我忽然看见前面一家商店有中文字招牌,我好奇的走近一看,是一家很小的中国超市,台湾人开的,那个时候纽约长岛的中国人不多,没有一家像样的中国超市。我走进去随便看看,看到有中文报纸卖,是《世界日报》,我买了一份。
回到家后,我无精打采的翻着报纸,翻着翻着,在社区华人那个单元里,一则消息吸引到了我,一位纽约市的华人心理学专业人士将在周末举办一次心理学讲座,上面有时间、地址和联系电话。这则消息忽然像一个光点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立刻拿起了电话拨打过去,一位讲粤语的小姐接的电话,我用川式普通话问她,她用港式普通话回答。我报了名,希望周末参加这个讲座。
以前我在国内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心理学方面的教育,但是,我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对心理学有种莫名的求知欲,我对自己这段时间出现的异常心理情绪和过激反应有所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化解,我知道,我需要人帮助,按照现在的话说,需要心理干预。
周末,先生开车带我去参加了讲座,在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的喜来登酒店。讲座结束后,我跟主讲人陈医生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建议我去诊所见他,我们约好了时间。我在美国接受心理干预就算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心理医生。
(二)
陈医生的心理诊所在法拉盛的香港超市附近(住纽约的博友可能都知道这家超市),那时看心理医生都是自费,每次150美元,45分钟,一周一次。陈医生的诊所很简陋,布置也很普通,跟我后来去我的朋友Dr. G在曼哈顿中城开的心理医生诊所大不相同,美国白人的诊所布置比较讲究,家具、灯光和墙上掛的画让人感觉很温馨。
第一次就诊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内容,陈医生只问我一些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我的出生、家庭背景、家庭成员和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目前的家庭和生活状况等等。陈医生是香港移民,说国语不太清楚,由于主要是我说,他听,所以交流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做心理医生的不多,我当时在《世界日报》医生广告中没有找到有国内背景的心理医生。
第二次就诊内容深入了一些,先问了我这一周的基本情况,有哪些情绪表现和症状等?然后给我做了一些心理测试,具体做了哪些测试我现在已经记不全了,有一项是简单的问卷,跟抑郁症有关的。做了测试之后,陈医生简单的对我说,我有焦虑症的表现,但还说不上抑郁症,只是情绪低落,心情不好。我清楚地记得他简单给我说明了情绪低落,心情不好跟抑郁症的主要区别:情绪低落是有具体什么原因,或者事件引起人的心情不好,情绪低落有波动,时而好一些,时而差一些,但这种心情不好不会贬低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没有社会价值。抑郁症虽然也有情绪低落,但这种心情不好是持续性的,时间很长,抑郁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贬低自己。陈医生的这一简短解释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抑郁症的这一重大特征。
我后来学了心理学才明白了,很多心理异常表现在各种心理疾病中都有,但是,每种心理疾病都有它的特异性,心理医生在询问和了解患者的病情时需要准确地抓住那些特异性,从而做出正确的诊断。
比如,我在修心理学课程时,有一天教授讲“边缘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他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女性,人际关系特别差,特别紊乱,有自杀倾向,她很有可能就是边缘人格障碍。BPD有很多的心理异常特征,但教授提到的这几点就是BPD的特异性。
陈医生还解释说,虽然情绪低落与抑郁症有区别,但是,如果情绪低落或心情不好时间久了也会发展为抑郁症。他肯定了我能及时求助。
第三次就诊时,陈先生还是尽量听我诉说,上次就诊时他只给我开了帮助睡眠的药,没有其他的药,他认为我没有必要服任何抗心理疾病的药。他一边听我的讲诉,一边问我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要我很非常的详细,他不会中途打断我的话。每次的45分钟过得很快,我感觉在这里的时间长短跟自己在家里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第四次就诊时,陈医生开始帮我分析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情绪的产生和教导我一些如何调整心理状态的方法,同时他也鼓励我走出家门,尽可能接触一下美国社会。在交谈中,他给我讲了一些类似positive psychology的内容。
在看心理医生期间,因为倾诉和得到专业的和具体的心理辅导,以及有先生的支持和配合,我的情绪明显有好转,睡眠也基本正常了。在第四次就诊的最后,我问陈医生我是否可以暂时结束就诊?陈医生点头表示可以,他很温和地说,如果我任何时间需要他的帮助就随时联络他。我后来在国内跟心理医生打交道时,我发现他们都不会这样对病人说。
(三)
看了心理医生之后,我整个人开始有了变化,当时我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但明显在开始适应新的生活,感觉到了心中有阳光,对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焦虑。
哦,对了,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我开始愿意在家学做菜,我以前完全不会烧饭做菜,很少进厨房。我先生也是一个基本上不进厨房的人,他的原配太太很会做菜,他妹妹有跟我说过。我在家里的书架上看到了有几本食谱书籍(丛书),台湾出版的《培梅家常菜》,印刷和图片都很精美,里面以江浙沪菜系为主。我翻开书,发现里面有些菜谱做了很详细的笔记,看得出来,原配太太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我对她肃然起敬。
原配太太的父母是上海人,当年是上海的资本家,有家族企业。1948年父母带着黄金和家产去了台湾,在台湾重操旧业,做得风生水起。受到家庭的影响和耳濡目染之下,原配太太不仅做事很努力,也很有经商头脑。在这点上我自叹不如。
我从嫁给先生到现在,我跟原配太太的家人们都相处得很好,她有两个妹妹也住长岛,她们一直对我很好,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现在如同亲戚一样来往。原配太太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每次回台湾都会跟先生一起去看望老人,他们说的上海国语很好听,待人很亲切,请我吃饭,感谢我照顾了他们的两个外孙女。
又要扯远了,继续说我的故事…后来,冬去春来,纽约的春天终于来了,我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了。我去法拉盛中国人办的驾校学习开车;我去皇后区社区大学学习英文,小班制,就像博友老皮卡读的那种英文班,只有6-7个人,学生来自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只有我一个。
再后来,我在学习英文时,有一天,该社区大学的亚洲文化系系主任问我可不可以去《世界日报》临时做记者,因为有一个女记者要生孩子了,人手不够。该主任当年是纽约市华人社区的活跃人士,是报社的人托她找人,她就选了我。本来是暂时顶替,结果,一做就做了三年,报社很认可我的新闻报道能力。
再再后来,先生的父母需要人照顾,我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几年后,公婆先后去世。这期间,我被香港一家杂志社聘为特约撰稿人,有时候写一些东西在该杂志上发表。
再再再后来,我去大学学心理学,这完全出于自己对心理学的热爱,我自己看心理医生的经历是强化剂,加重了我渴望了解心理学的欲望。学业完成后,我有做一些帮助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
再后来,我在一边做家庭主妇的同时,一边回国照顾我的父母;一边在国内做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事,又一边接受重庆出版社的邀请编写书籍,从2005年开始,我编写了五本心理学的书,并翻译了一本书。
(结尾)
三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对自己的所有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刚来美国时那些极度不适应的经历让我成长了。
我先生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每天去公司上班了,我们在陪伴亲人的同时也去了很多地方旅行,看看世界,看看中国。先生对中国的情结比我还深,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要走遍中国每个省,我们已经去过了中国40多个城市,希望疫情结束后再继续走中国。
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很平凡和平淡,但很祥和安宁。我的婚姻是美满的,家庭是和睦的,生活是踏实的!
有一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在聚会饭桌上,一位同学给大家说,有一次她参加了华西医科大学举办的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会议上,有位华西医科大学教授演讲的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当他把书的封面展示在大屏幕上时,我同学看到了书的作者是我的名字,会后,同学走到那位教授面前,看到了那本书,确认了的确是我,她跟教授说“作者是我同学”。当我听完同学的讲诉之后,我心里就想,我这位家庭主妇能得到专家的肯定和推荐,我满足了!
还有一次(2019年),我正在国内照顾我爸妈,我收到了纽约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学委员会主席Judy博士的email,她急于找我,工作上需要我帮忙,因为有一天我参加了一次联合国召开的心理学会议,会议结束后我跟Judy聊了一些,她要了我的电话和email,可能她电话找不到我(我在中国)就急着发email给我。我回了她的email表示很遗憾我在中国,不能帮她的忙。尽管我现在没有跟她做任何事,但是,从我们的聊天中我得到了她的肯定,我心里也是满足的!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今年又过了3/4。今天10月份第一天,我台北的住家大楼开始迎接“万圣节”的到来:)

金秋十月第一天的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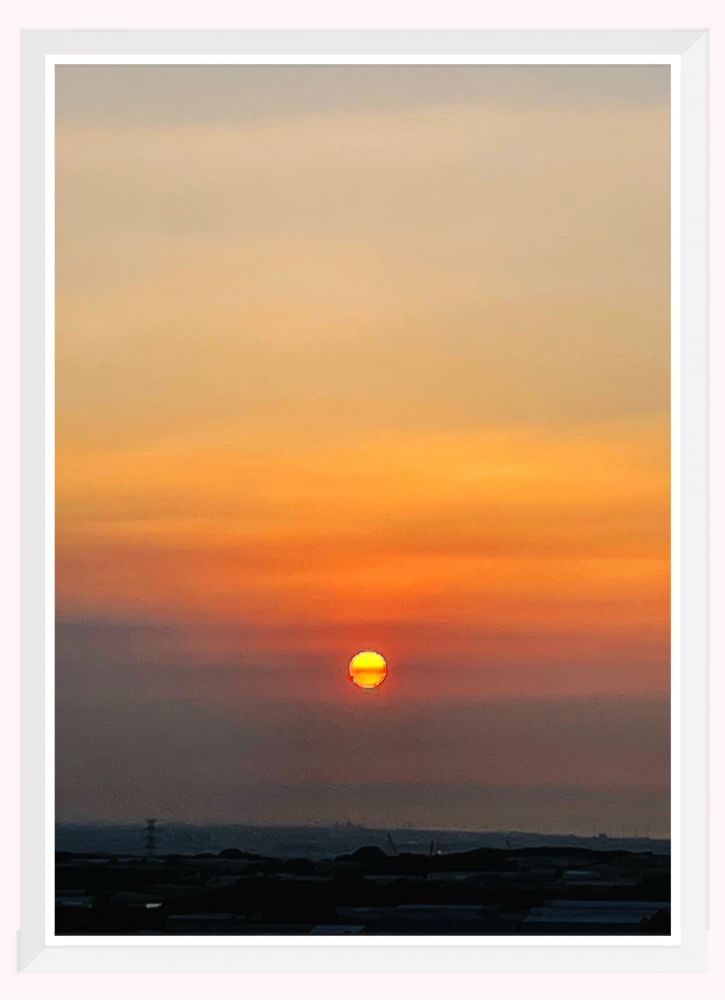
10/1 写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