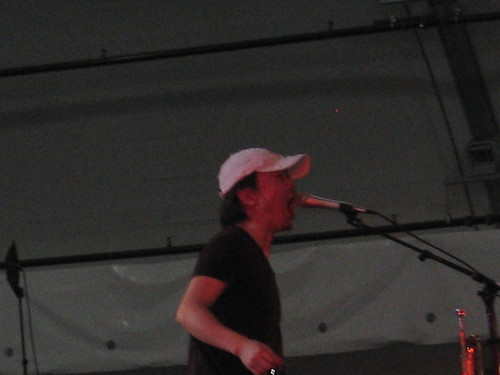崔健硅谷杂碎
1.
说起崔健,我属于可以对他宽容再宽容的那一类歌迷。
有人说他老了,有人说他被西方摇滚撅折了,有人说他迷失自我了他江郎才尽了。
也都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评价,不无道理。
虽然《阳光下的梦》挺好听,可是我们怎么都会更喜欢《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就像Eagles,任凭这帮老鹰如何活到老唱到老,Hotel California肯定是他们终生无法超越的颠峰;我们爱听《蓝色骨头》和《混子》这没有错,可惜它们不可能像“花房姑娘”那样让我们泪流满面了;崔健一RAP,我们只好傻眼,挥着荧光棒敲敲节奏,那些抄写过的好歌好词,竟然有点像是从周董那吐字不清的嘴巴里面唱出来的。
确确实实崔健秃顶了眼袋也大了,他用音乐进行的思考跟从前不太一样了。可他还是中气十足,依然不愧为真唱先锋。他在中国摇滚界的地位,远远不止是一块基石而已。后来的所谓代表人物,不论是唐朝还是魔岩三杰,迄今未有能够望其项背者。至于现在的什么谢天笑,根本就是垃圾。
所以,那些振振有辞的所谓乐评,不也就是在演唱会的余音中才能勉强跳跃两下的么?到了下一场演唱会,失望了的评论家们还是会屁颠屁颠去听。不是去听老崔的自我超越,是去听老崔的二十年不变。
女儿阿小J问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看这个她不认识的叔叔唱歌。我说因为妈妈从上highschool就开始听他唱了,认识这位叔叔(那时候还是个哥哥)的时间,比认识她的时间,还要长好多好多。阿小J吃惊地望着我——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妈妈是那么的老,有着那么长的一段历史。
是啊,一个人能有几个二十年?在为数不多的二十年里,又有几首歌让我们肯拿出不变的激情去听?难道我们不该心满意足么?
2.
对于听众,我反倒就是做不到宽容。
在我们前边,有三对男女。
第一对如胶似漆,仿佛听的不是崔健,而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给了他们一个幽暗温柔的场地以便贴脸亲嘴咬耳朵。
第二对各人顾各人。先生怕吵,时常要把手指头捅进耳朵眼里隔音;女士翘着二郎腿吃零食,让我直想过去问她:do you care for some popcorns, Mam?
第三对西装革履,正襟危坐,面无表情。我们在后边使劲唱使劲叫使劲跳使劲打匪哨,他们顶多回头厌恶地看我们一眼,然后继续掉转头去坚持他们人大会议的姿势和表情。
我实在搞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花钱找罪受?因为住在附近,周末正好没什么安排,权当一项社区活动?
想起当年我们听不起现场演唱会,在寒风里等着散场好能见上老崔一面;也想起我的好多朋友要么不住湾区不能来听,要么孩子太小不能来听;也想起一路上看见的那些把孩子扛在肩膀上小跑着往演唱会赶的歌迷,我觉得,我前头坐那些个听众,或许更应该用这点钱去买一套柴可夫斯基,回自己家里听去,把崔健的歌声,留给真正热爱老崔的歌迷。
3.
有位网友在老崔现场看见我了。刚才收到他逗我开心的短信,特此贴出来,谢谢这位体贴的哥哥对无名的了解,呵呵。
你三次从我身边经过,第一次,你和珊瑚礁往后走,边走边打电话。第二次,端着啤酒往回走,第三次由于要拿票,只好把啤酒放在地上,我本想帮你拿啤酒,又怕你说我想骗你的啤酒喝,眨眼之间,你就健步如飞的消失了。
特改编崔健的花房歌以记之。
你三次经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
我不敢使劲看着你的,噢......脸庞。
我想问你去向何方,你冲着啤酒的方向,
我知道你想喝几杯,噢......真棒。
你端着啤酒回剧场,我想上去帮个忙,
检票的说你走错了,噢......方向。
你说要发现我在剧场,见了啤酒全都忘,
你不知不觉和啤酒,噢......一样
我就站在你身旁,你和看不见一样,
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
你回到司令的身旁,你已经坐在座位上,
我只好上前说一声,噢......姑娘!
你就要回到老地方,你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知道你爱喝啤酒!噢......姑娘!
4.
最后贴几张我在现场拍的照片吧。相机不好,只能看个大概。这一组是老崔第二次返场,在唱《红先生》。
这回老崔的演唱会,有两个小小的遗憾,一是竟然没唱《南泥湾》。二就是他《时代的晚上》演唱会,在工体的时候唱“花房姑娘”,歌词改成“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工体!”,已经够矫情的了;这回在湾区,竟然干脆改成“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湾区!”,我笑到差点把啤酒喷到坐我前头那俩人大代表的脑袋上。
有对《时代的晚上》这台演唱会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我早俩礼拜转贴过的一组关于北京工体《时代的晚上》的乐评文章:为崔健《时代的晚上》热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