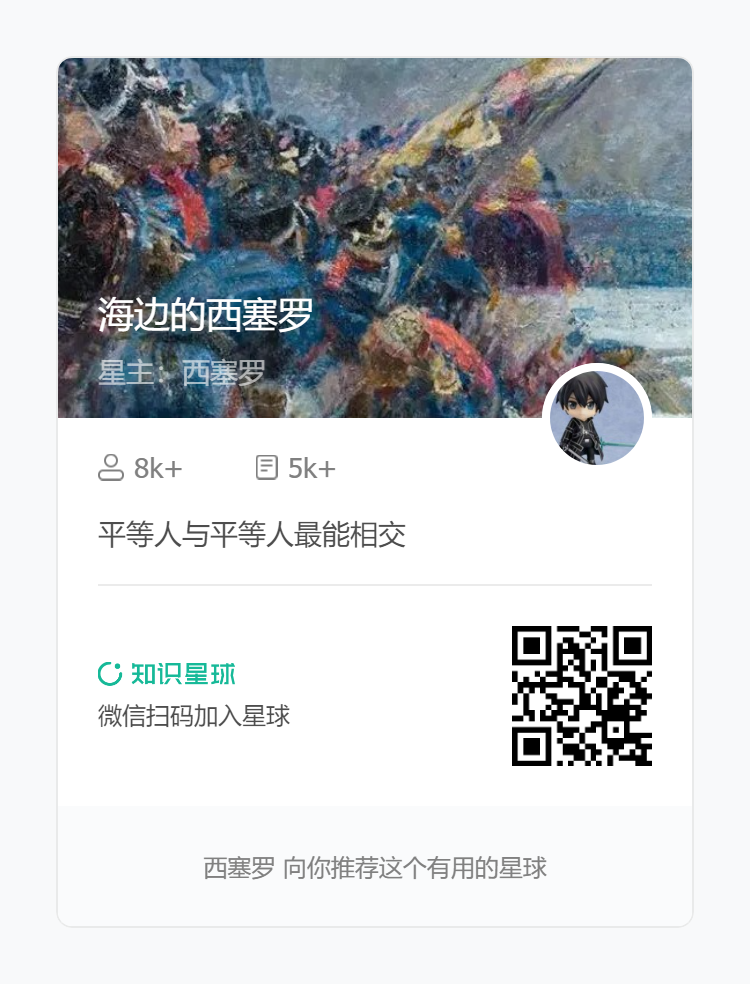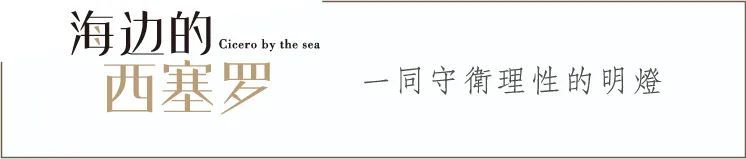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如果你真以为科学家是《三体》里说的那个样子,
那说明你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
腾讯的剧版《三体》这两天完结了,回家后这几天一直在补这部剧。看着看着我发现,剧版《三体》到后期,对大刘的原著改动还是挺大的。
比如原著中有一个设定,说三体人为了吓阻主角汪淼进行研究,在他眼睛上投射了一个倒计时。可是这个倒计时原著中后期给“写没了”,感觉三体人恐吓了个寂寞。
但剧版《三体》却把这个梗一直用了下去,还安排了这样一场戏——倒计时重新开始后,汪淼受邀去女儿的小学讲课,他给孩子们做了那个传说中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强调了物理学一切要“以实验为准绳”的原则,还表示“不管是布鲁诺,还是伽利略,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都永不放弃。”
我很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要安排这种原创剧情——《三体》原著小说中成批的科学家被三体人制造的实验假象逼自杀的情节实在有点太丧了,里面的科学家不像是科学家,反倒更像是一根筋、只会直线思维的“科学教徒”——其实你看大刘的大部分作品,他笔下的科学家都多少犯点这种“科学教徒”的病,特偏激,动不动就寻死觅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身边很多真研究科学的朋友对他意见很大的原因。导演显然对这个设定也有意见,想改改,表示还是有科学家会不惧三体人设置的迷雾,勇于探索科学真相的么。首先,历史上的布鲁诺他就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崇拜太阳的密特拉教徒,他支持日心说并甘愿被烧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当然为自己的信仰殉道,这算一种“坚持真理”(为自己的信仰殉道么),但毕竟离着“坚持科学真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于伽利略,就更有意思了——从小学起,我们就知道他曾经在比萨斜塔上用那个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勇敢的砸碎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但这个故事其实跟牛顿的苹果一样,是一个后世穿凿附会的想当然。真实历史上的伽利略其实压根没做过这个实验。而从这个故事讲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无论小说还是剧版《三体》,其实都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科学精神。这篇文章可能会比较长,里面涉及大量思辨的东西,请耐心一点点听我讲完。有关伽利略“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个实验,最早只是他晚年一位学生维维安在讲述其老师思想时所用的一个比喻的以讹传讹。其实不用多深入的思考,就能发现这个故事的荒谬:如果简单的做一次“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的实验,就能“砸碎”亚里士多德的谬论,那么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过呢?现实中的伽利略,恰恰没做过这个谁都能做的现实实验,而是做了一番非常独到的理性推理:在伽利略早年著作的《星际信使》一书当中,他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并论证说:假如把一重一轻两个物体拴在一起,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势必是重的(快的)物体要被轻的(慢的)物体拖慢,而轻的要被重的拖快,也就是会得到某种折中的速度;可是,两个物体拴在一起,又可视为一个新的物体,而这个物体的总重量比原来两个都重,那么下落的速度应该比之前的两个物体都更快才对。伽利略认为,这个两个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唯一能够协调二者的办法,就是修改理论,认定自由落体下落的速度与物体本身的重量没有关系,无论轻重其“理想速度”应该一样(之后的牛顿会告诉人们,其瞬时速度由重力加速度和时间决定),这样理论才能够重新完美。所以你看,现实中的伽利略是动了动他那颗智慧的脑袋,用理性推演而不是“两个铁球”,击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压根没去爬塔。其实,即便他真爬塔做了那个实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也不会承认实验的权威性——那个时代学者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信仰,是不会被这种实验动摇的。“两个铁球”的实验做一千次,也不如伽利略这短短几行字论证有用。为什么?为什么思维的论证有时比实验的论证更有力量?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底魅力何在?伽利略之前,欧洲人为什么将之奉为圭臬?我们今天读科学史,很容易会对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产生一种偏见,觉得这家伙就是一个科学界的“错题本”,他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上的很多说法都是错误的,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被伽利略这样的后浪所推翻、打脸。可匪夷所思的是,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霍金等人,又非常推崇这个人。爱因斯坦甚至说亚里士多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家”,霍金则认为后来所有科学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精神的继承者,甚至所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在沿着他的路径前行。那么,想错了一堆事儿的亚里士多德,到底想对了什么,能当此殊荣呢?你在中学历史课上可能学过一些古希腊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家,比如赫拉克利特。这个人就很了不起,他提出了原子说,并认为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列宁就对推崇备至,称其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看上去,坚持唯物论的赫拉克利特似乎更适合赢得那顶“第一科学家”的桂冠。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过于“唯物”了,他不相信自然界中有“偶然性”的存在,他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是一团“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永恒的活火”,会“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所以一切都是必然的。如果赫拉克利特见过钟表,他会像后世的“机械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一样,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像钟表一样在运行。但这样认识世界,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容易沉醉在复杂的表象世界中,无法透过现象把握规律。举个例子,如果“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会认为“兔子撞在树桩上”这个偶然事件一定也是他所认为“世界秩序的活火”中的一部分,然后就事论事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可以想见,人类的科学研究如果沿着赫拉克利特的这个思路演进下去,那么我们就将陷入偶然性的迷雾当中“守株待兔”,永远无法透过现象把握自然界的真实规律。认识到“朴素唯物主义”存在这种思维漏洞的,恰恰是被我们中学课本批判为“唯心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柏拉图认识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眼见与耳听也许并不为实。我们所见识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与真正存在的“真实世界”之间,很可能是存在距离的。为此柏拉图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圆”这种东西,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看到过,你用再精密的工具画一个圆,它依然会有一些地方在偶然的干扰下是不圆的。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认定有“圆”这样一种概念存在呢?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接近这个概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很圆”。柏拉图认为,这是理念世界使然,他认为理念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存在,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拙劣的模仿和投影。因此他提出了“洞穴假设”。帕拉图说,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就好比一个洞穴,外面的光影子投射到墙壁上。而我们则被绳索禁锢起来,只能看到墙上的投影,然后我们就以为墙上的投影是世界的本原,因此无法洞悉世界的真相。(这话明显是奔着揶揄“朴素唯物论”去的)但其实我们不知道那只是外在世界在里面的投影而已,在洞穴之外,应该有一个更真实、更完美的世界存在,人类的“灵魂”可以通过“回忆”去除遮蔽,完成对知识的认知。柏拉图管那个世界叫“理念世界”,而这种知识叫“真理”(a-letheia)——真理在希腊语中,就是否定性前缀“不”加一个动词词根“被遮蔽”。去除表象的遮蔽,你才能认识真理。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认为“唯物”的科学家追求的那个“真理”,恰恰是柏拉图这个“唯心论”者为了反对“朴素唯物论”所造出的一个概念。我们所有现代人在思考问题时不自觉的认定,世界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之上,还有更高一层的“真实”时,其实都是在用柏拉图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但是,柏拉图的这套创新理论体系受到了他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有条件反对。亚里士多德认为,他老师所主张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太疏离了,甚至认为感官认知无法成为知识的来源。但真理其实没有必要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去找一个理念世界单独存放,它可以回归现实世界,就在此界当中——当然,它也不像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就是事物本身。于是,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一次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伟大的调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既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也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而只在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之中。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对“真理与偶然”这对概念进行了辨析。在他的论述当中,“偶然”这种概念与发生的次数是无关的,所以不与“必然”相对立,但却与“真实”相对立 ——比如夏天是炎热的。这是一种“真实”,或者说炎热是夏天的“本性”。即便有些夏天不那么热,甚至下雪,也不会动摇人们“夏天很热”的观念,因为人们会认为不热的夏天是“偶然”。再比如,善于奔跑是马的“本性”,但如果有些马体弱或衰老、伤病或残疾,那么这就是个“偶然”,这种“偶然”即便能长期存在,将某匹马善于奔跑的本性彻底遮蔽了,也并不应影响我们拥有“马善于奔跑”这个认知。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只有真实的、必然性的对象才是值得被科学(他所谓的“物理学”)所研究的,而偶然事物是不可被研究的。人类理性思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现象与经验当中去芜取精,摒除偶然因素干扰,“提纯”出真正的科学(物理学)。聊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这套思想,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科学对自然的研究方式了。如果你做过科学实验,就会有这种经验,在实验当中,误差这种“偶然”几乎是无法被摒除的,很多实验统计真正列到坐标系当中去之后,都只是一堆散点而已。那么科学家怎样承认并“忽视”误差,在杂乱的散点中划出一条曲线,从而总结和把握其中的规律呢?这其实就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调和。是他启示了后人——人类需要尊重经验,但又不能完全匍匐于经验脚下,把偶然也当成了真知。因为真理并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也不存在于纯粹的理念中,而存在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之中。这也间接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古文明,曾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却没有爆发“科学革命”?原因可能就在于,其他文明都少了这样一次对唯心与唯物的思辨与调和。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文明,要么因朴素的唯物,而沉迷在了经验的森林中,无法摒除“偶然”去总结和把握规律。要么则如柏拉图一样,因过度推崇彼岸的“理念世界”而陷入了宗教的迷思当中。而历史证明,彻底的唯心主义和朴素的未经改造的唯物主义,都是不能孕育科学的。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精神的初曙,恰恰来自于中世纪晚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流行。欧洲人是从学习并扬弃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当中,逐渐摸进现代科学的门庭的。宽泛的说,近代以来所有科学家(包括伽利略本人),其实都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为科学思维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既不完全唯心、也不彻底唯物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精神的延伸。所以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第一位科学家”当之无愧,他是研究科学所需的那种认知论的缔造者。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再来解释之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伽利略其实无法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样一场实验去打破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断?因为伽利略和他的科学同行们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认定经验与真知之间隔着一层“偶然”的面纱的。想象一下,如果伽利略真的拿“两个铁球”的实验为依据试图推翻亚里士多德,那么他的反驳者就会抬杠:“你怎么知道你的实验不是一种偶然(特殊情况 )呢?为什么不拿一颗铁球和一根羽毛试一下呢?什么?你说铁球和羽毛才是受不可控因素干扰产生的偶然?你凭什么这么认定?凭什么“偶然”的亚里士多德讨论的石块与羽毛,而不是你讨论的两个铁球呢?”你看,如果试图以单纯的实验去推翻亚里士多德,就会陷入这种对“到底谁是偶然”的争吵中。所以这条路在亚里士多德亲自构建的认知体系当中是走不通的,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里打败亚里士多德,就必须像真实的伽利略所做的那样,进行一番理念上的推演,揭示旧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之处,并通过理性思索,得出唯一合理的解释。而请注意,这个过程其实是不以实验为准,是完全“唯心”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完全“唯理”的。一个学者,即便一个实验不做,完全不依靠经验,他也可以通过伽利略讨论方法,得出不同重量的物体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同时落地的结论。所以剧版《三体》当中,汪淼对着孩子上课,拿两个铁球落地说明物理学是“不能靠想象,不能靠推测,而是要通过踏踏实实的实验”。这一段虽然很燃,但属于典型的胡扯,事实上物理学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突破,都是想象和推测先行,而实验的验证总是姗姗来迟——无论是伽利略对自由落体问题的讨论,牛顿对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霍金的黑洞假说,在他们把理论提出来的时候,都还什么验证实验都没做,真正的验证实验,都在几十甚至上百年之后。所以物理学乃至一切科学,恰恰不是“唯实验”的,实验对科学存在的目的仅仅在于对理论的验证与修正,如果没有先验的认知和理念存在,那么即便你作一百次实验,得到的也仅仅是一百个数据而已,屁的科学规律你也总结不出来。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三体》(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剧版)在科学观一直存在的一个硬伤——大刘虽然写科幻,但可能并不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家是怎样的。他想当然的把科学家塑造了一帮朴素唯物的、唯实验论的科学教徒。于是一旦高能粒子对撞实验被智子干扰。他们立刻就要喊什么:“物理学不存在!物理学从来没存在过!”然后闹着要自杀……这非常荒诞,现实中不会有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会这样幼稚而偏执的去思考问题,为一个实验的验证失效而否定整个物理学。我们不妨说个爱因斯坦的例子——1919年,为了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爱丁顿远征非洲,去通过日食观察太阳引力对星光的弯曲效果。实验结果公布前,有人就问爱因斯坦,说如果这次实验结果不能验证您的理论,您打算这么办?爱因斯坦哈哈一笑,说:那我倒是真的好奇,这个理论如此优美,那颗星星就应该在那里!类似的例子还有牛顿,在总结了万有引力之后,英国海军曾经找上他,希望他能依据自己的理论搞一份精密的月相表,这就需要精确测算月球的轨道了。可是牛顿搞了半天,发现他无论如何都算不准——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地日月三星的关系,是一个三体问题,很难准确测算。但失败的牛顿作何反应了呢?他把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撕成纸片,说什么“物理学不存在”了么?没有,牛顿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反正我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然后就抛下这份工作忙别的去了。类似的故事,还有达尔文在遭遇“孔雀的尾巴”的问题时,卡文迪许面对惰性气体问题时……几乎所有学科的正经科学家,在面对与自己理论相矛盾、想破头也解释不了的实验数据时,都比《三体》里表现的那帮人格障碍患者们皮实太多了。这就是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所有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科学家的确重视实验,但并不唯实验论,因为他们知道真理并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而存在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之中。我的理论是美的,如果实验效果不如预期,那应该实验出了问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偶然”,如果实验总出问题,“偶然”升格为了一种“实在”,那我要思考的也是这种“实在”究竟为何会发生。而不是急吼吼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喊什么“xx学不存在了!”——这也太不科学了。其实在剧版《三体》中,导演应该也看出了原著这个情节的不合理,原创了不少剧情给大刘找补——剧中曾让丁仪在杨冬的实验被干扰的时候劝她:这样的事儿很常见么,实验不如预期你就多做几次么……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笑喷了,因为我身边从事科研工作的那些朋友真的经常这样聊以自慰。很少有人真因为实验做不出来而推翻自己的理论,更遑论跑去自杀了。但无奈的是,虽然导演编了很多原创情节找补,因为原著底子在那里,所以剧版《三体》依然是一部把科学家和科学精神黑出翔了的电视剧,里面的学者与其说像科学家,不如说更像一群披着科学家白大褂的宗教徒,轻而易举的就能被实验结果打击,宛如教徒会为一个神迹的呈现就把自己或他人献祭一样。而如前所述,早两千年前,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真正的科学家、以及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早就不这样认知世界、思考问题了。只能说,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无论社会学还是物理学,《三体》对世界的理解都过于低幼了。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们打出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这两面大旗。然而,就如同时至今日大多数受众对民主的理解仍然充满扭曲与谬误一般。从《三体》对科学精神的误解之深和它的走红之火中,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社会对到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着极深刻的误解的。大多数人简单的把“科学”等同于“唯物主义”,于是就像剧中的汪淼说的那样,以为科学就是“做实验”,所谓“物理学不靠想象,不靠推测,要通过踏踏实实的实验”。这就倒向了经典的“唯实验论”,进而像《三体》小说里那样,一旦实验做不成、或者受到了遮蔽了,学者们立刻失了主心骨,喊“物理学不存在了!”而这种偏激在被极化之后又常常走向自身的反面,把科学家都想成一群“唯心”的科学教徒,似乎什么行为,只要套上了“为了科学”这几个字,就立刻可以变得光辉、神圣无比,有了天然的正确性,大胆去做就对了。这两种谬误在大刘的小说中经常交替出现,我们不否认它来源于生活,它也许就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科学精神错误理解的文学体现。但事实上,就像“民主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科学也并不神圣,它只是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并不完全是“唯物”的(至少不是“朴素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因为它要求人们不能迷惑于纷繁复杂的现象,而要时刻意识到现象之上存在着更本质的真知。这种认知方式也不完全是“唯心”的,人类通过理性推得的真理,不能完全在理念世界中放飞自我,而需要回到实践中进行验证与修正。这种既不完全唯物,也不完全唯心的思维方式,就是亚里士多德当年的那种认识论的升级版。它经过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升级、修正,时至今日,依然是科学的轴心骨。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学文还是学理,读一点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还是必要的。这总好过你看上三四遍《三体》然后被里面魔怔的科学家们带歪。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大刘所说的那种一遇到远高于自己的超科学技术,马上失了方寸、下跪或者上吊的怂包。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同时翱翔在理念与现实之间,既不唯物也不唯心、但却比两者都更坚定的认知论。就像思想不惧子弹,这种认知论不怕忽悠。真碰上了智子这种开挂神器遮蔽了一种实验,人类也能通过思辨或者其他实验拼上两下子,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科学史上一再发生过。你看伽利略,就从没真到比萨斜塔上丢过铁球。人类的现代文明大厦,就建立在这种伟大的认知论之上。所以我们说德先生与赛先生一起撑起了人类的现代文明,这所言非虚。最后说一句,如果你真以为科学家会是《三体》里说的那个样子,那只说明你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就像你如果真认同《三体》的民主无能论 ,也只能说明你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一样。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