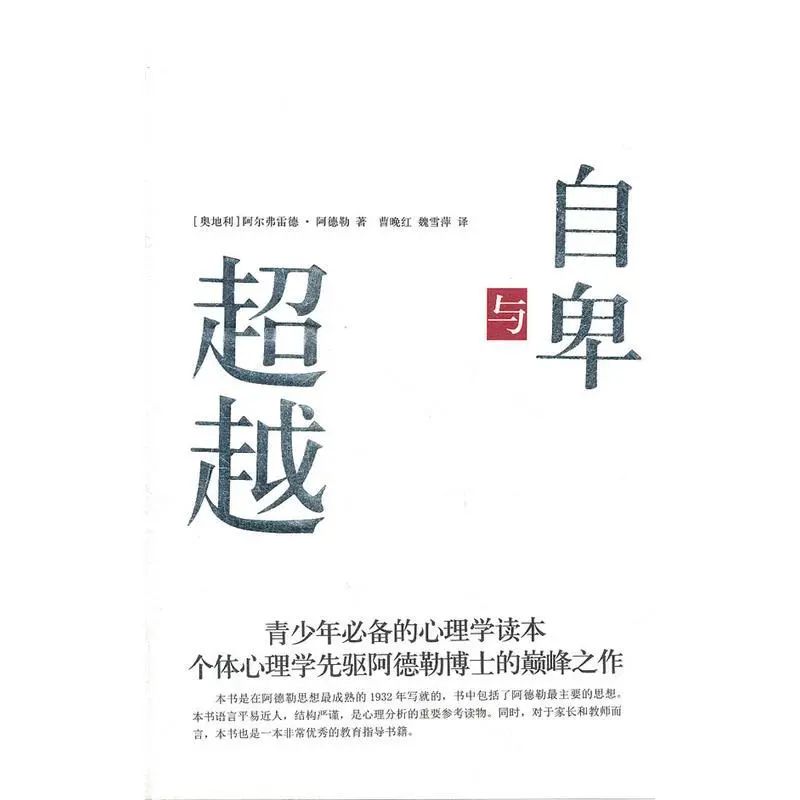超越自卑(阿德勒心理学经典)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人类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事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事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物对我们人类的意义。即使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中最简单的事物,人类在接触它们的时候也是从自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来看待它们的。“木头”指的是“与人类自身有关系的木头”,“石头”也是“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有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仅仅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与自己周围的人丧失沟通的基础,他的行为无论是对他自己,或是对其他人都毫不起作用,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一直是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每个人感受到的意义多多少少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意义”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领域。假如我们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回答不出来。通常,人们不愿让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问题来困扰自己,所以总是用一些陈词滥调的回答来搪塞:或者,人们干脆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自从人类有自己的历史开始,这个问题便已经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青年,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会经常为之困惑:“我们为什么而活着?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自然,无数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断言:通常人们只有在遭遇失败挫折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疑问:假如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任何的波澜和起伏,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困难和险阻,那么这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也不会被诉之于言词。在一般情况下,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诠释生活的意义,几乎每个人都只把这个问题和它的答案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而完全不管他的言论,我们将会发现: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特征等等,无不体现出他个人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他的行为让我们相信,他似乎对某种关于生活的解释深信不移,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他似乎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宣告:“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世界就是那种型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以及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也正因为如此,生活的意义多得不可胜数。而且,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个体自认为正确的生活的意义可能多少都含有错误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生活的意义,只要有人持这种态度,它也绝不会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生活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然而,这些变化一或者说,不同的人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却有高下之分:它们中有些很美妙,有些则很糟糕:有些错得多,有些则错得少。我们还可以发现:较好的生活意义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较差的生活意义则都缺乏这些特征。这样,我们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总结,就可以得到一种相对“科学”的生活意义,它是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也是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指的是对人类的真实,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谓“真实”。如果还有其他的“真实”存在,它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法知道这种“真实”,这种“真实”也因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三条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必须随时牵挂于怀的。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得不受这三条事实的制约,他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事实所造成的。由于这些事实无所不在地缠绕着人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回答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个人理解。这三个事实之一是: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个事实的限制之下,依靠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繁衍生息。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逃得过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这些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这一地球之上”等事实所限制。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时,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界定我们的答案,以使它们眼光远大而前后一致。这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追求解答。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寻求答案。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然而,我们却必须用我们的所有才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我们必须不停地奋斗,以找寻更为完美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件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利益和灾害。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种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四周还有其他人,只要我们活着,就必然要和他们发生联系。单个的人是很脆弱的,他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使得单个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单独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假如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并且想只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应付一切问题,他只能面对失败和灭亡。单个的人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因而无法延续下去。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个体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了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我们将自己孤立,我们必将自取灭亡。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在于: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绪、行为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与目标互相协调。人类同时还被另一种事实所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和人类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于这一事实。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产生了爱情和婚烟这两种联系,这是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类面对这个事实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对生活给出的某种答案。人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可以表现出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这三种事实带来了三种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事实上,这三种问题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问题。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所作出的反应,都清楚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举个例子说吧,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也不够尽心尽力,他的朋友很少,因为他发现和他的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从他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会感到“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生活对他来讲机会太少而挫折太多。他的活动范围一定非常狭窄,这与他对生活的意义的判断有关: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讲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因而他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别人接触。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非常甜蜜而融洽,他在工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际范围广泛而成果丰硕。我们可以据此而断言,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生活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过程,生活中充满了机会,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对于他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与同伴携手共进,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各种错误的“生活意义”的共同特征,和各种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特征。所有失败者一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一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面对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都不相信可以通过合作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他们个人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因而也只停留于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很明显地,他只能使自己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意味着某些事情的东西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认识到人类的重要性是依赖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所作出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必定会踏上错误的道路。我曾经听说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了她的教友,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教友们在震惊之下,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天,这些教友汇集在一起,向这位领袖兴师问罪:“瞧瞧我们处境的困难吧!”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最绝对的权威处听来的。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为什么仍然安然无恙呢?”“可是,”这位女先知说道,“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呀!”显然,这位女先知在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准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能够解决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成功的方法对人类来说具有共同的意义,也是可以分享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用其至高无上的效用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很重要时,他们才会称他为天才。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为团体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意成就。能够成功地应付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人,他的行为方式明显地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遭遇困难时,他会选择用不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对许多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观点,他们也许会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老是为别人的利益奉献自己,他难道不会感到痛苦吗?如果一个人想要使自己得到适当的发展,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为自己设想一下吧?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怎样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或加强我们自身的人格吗?”这种观点看似正确,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因为它提出的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里,希望对别人能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感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他自然会把自己的人格塑造到理想型态——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都有贡献的状态。他会根据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他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种种能力和技巧。只要他认清了目标,学习达成目标的能力和技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不断地充实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种问题,他自己的能力也将不断地扩展。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我们的伴侣,如果我们致力于丰富我们伴侣的生活,我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假如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自己的人格,那就只是在装腔作势,只会使自己更不愉快而己。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审视一下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物,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开发过的土地,也可以看到前人建造的公路和建筑物。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以及我们处理人类问题的技能,无不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将生活经验互相交流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们留下来的,其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那些不懂得合作和奉献的人,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呢?他们在身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们己经彻底死亡,他们的整个生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们的地球似乎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抱持的价值观念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点死亡,快点消失吧!”对于不是以合作和奉献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最后结论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请你走开!”当然,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一旦我们发现了各种弊病,我们就应该致力于改变它,当然,这种改变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福利为前提。了解这种事实、抱持这种观念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深深地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全体发生兴趣并与之合作为我们的世界作出贡献,他们也正在努力地培养着爱情和对社会的兴趣。在各种宗教思想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救世济人的胸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即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真实内涵却经常被曲解:除非它们能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工作,它们现有的表现很难让我们再看出宗教在增加社会利益方面还能做多少工作。由于科学使人类对其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或许比政治和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这一目标,也更能让人类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一个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却始终如一一增加对别人及社会的兴趣,促进合作,为我们人类作出贡献。我们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就好像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一样,而我们赋予生活的错误的意义却像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同,如果它们犯了重大的错误又应如何纠正等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之所以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就是它能利用对“意义”以及“意义”对人类行为及人类未来的影响等事情的了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在摸索着追寻这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想办法去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模式。此时,儿童就己经具有了“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会利用一张固定的统觉表(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己被预先做了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进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只有重新审视造成这种错误解释的情境,找出谬误所在,并修正统觉表,这种错误的生活意义才能被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体也许会由于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导致的糟糕的结果所迫而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这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没有发现,假如他再我行我素,他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的行为方式的修正,大部分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给出一种较为合适的生活的意义。人们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出解释。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完全有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不太重视不愉快经验的人,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他做某些防范措施外,几乎不会影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糟糕的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这些不愉快。”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有些父母则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吃苦?”第三种人可能会这样想:“我童年遭遇了不幸,所以我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对童年时期经验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只要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不会有所改变。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人们一般不会被经验过的打击所困扰,人们通常只是从其中汲取决定我们目标的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当我们以某种特殊经验来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则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然而,儿童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成年人里的大部分失败者都是在这种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由于先天的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产生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的心灵负担非常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转移到他人身上,一般情况下,他们大都只会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使他们转向自己、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产生自己被这个世界侮辱了的错误感觉。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存在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虽然己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不是我所想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到的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证明失败的责任在于遗传或身体缺陷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是一定会导致人们抱持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这种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了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甚至有人英年早逝。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也使他们不停地奋勇向前。只关注他们的肉体,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心灵将会朝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可是,事实证明,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没有被他人所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更多的是失败者。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宠坏的情境。 被娇宠的儿童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成命令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上帝的宠儿。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与他人相处。别人老是服侍着他,这使他丧失了独立性,他不知道自己也能做事情。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一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以为:假如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如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处境就会大为改观了。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严重地破坏善良意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可是却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作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习惯的谄媚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因而想要对他们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如社会真的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拿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不产生效果的道理:它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就一无所用了。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或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或是以暴力实施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先后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一独占整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都是错误的。第三种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建构了一种没有把这些友善力量考虑在内的生活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当他面临生活中的问题时,他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和旁人的帮助及善意。他曾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就误以为社会永远是冷漠的。他不知道他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儿童环境中全部之物为止。如果她的第一个工作一即获得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一一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发展社会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炼,否则其发展即会受到挫折。假如有个完全被忽视、被僧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不能和别人交往,无视于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足以证明他己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考虑那些受到的照顾比一般情况少的儿童,或只在某方面受到忽视,而在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的儿童。总之,我们说:被忽视的儿童肯定未曾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种悲哀的讽刺,那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纳于被忽视的儿童之中。这三种情境一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一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以赋予生活较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一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工夫一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梦和联想己被证实很有用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轻,人格能不经过防卫和隐瞒而表现出来。不过,要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最大的帮助是来自其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回忆之事,不管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回忆时,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被想起,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这种记忆告诉他:“这是你应该期待之物”或“这是你应该躲避之物”,或“造就你的生活!”我们必须再强调:每件记忆都是值得纪念之物。对于表现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存在多久,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特别有用的。最早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包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整个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等第一次综合起来的结果。第二,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因此,在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觉得自己所处的脆弱和不安全的地位,以及被他当做理想的强壮和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至于被个人当做最早记忆的,是否确实是他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或是否是他对真实事情的回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则是无关紧要的。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做”为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并看看它们所造成的“生活意义”。“咖啡壶掉在桌子上,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开始其自述的女孩子总是无法摆脱孤独无助之感而高估生活中的危险与困难时,我们不必讶异。假如她在心中责备别人没有好好照顾她,我们也不用惊奇。因为必定有某些人非常粗心大意,才会让这样幼小的婴儿遭受这样大的危险!在另一个最初记忆中,也呈现出类似的世界形象:“我记得我3岁的时候,曾经从婴儿车上摔下来。”随着这种最初记忆,他反复做着这样的梦:“世界末日已到。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星辰都纷纷往下坠,我们也将和另一个星球相撞。可是,在撞毁之前,我醒过来了。”当这个学生被问道他是否惧怕何物时,他说:“我怕我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他的最初记忆和反复的噩梦构成足以使他气馁之物,从而使得他害怕失败和灾难。一个由于夜尿以及和母亲不停地发生冲突,而被带到医院来的12岁男孩,说他的最初记忆是:“妈咪以为我丢失了。她非常害怕地跑到街上大声叫我,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子里的一个橱柜中。”在这个记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臆测:“生活的意义是一用找麻烦来博取注意。获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骗。我虽然被忽视了,但是我却能愚弄别人。”他的夜尿也是他用来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母亲对他所表现的焦虑和紧张,正加强了他对生活的这种解释。像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孩子很早就得到一种印象,以为外在世界中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他只有在别人为他的行为担心时才觉得安全。也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向自己保证:当他需要保护时,别人就会来保护他。有个35岁的妇女,她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3岁那一年,有次,我独自走进地窖。当我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时,比我稍大的堂兄也打开门,跟着我走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这个记忆看来,她可能很不习惯于和其他孩子一起游玩,尤其是不喜欢和异性在一起。对“她是独生女”的猜测,结果被证实是正确的,而她在35岁这样的年龄,也依然没有结婚。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社会感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载着小妹的娃娃车。”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征象显示:她只有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觉得自在,还有她对母亲的依赖。当新婴儿降生时,要得到年纪较长的孩子的合作,最好是让他们帮忙照顾他,使他们对他产生兴趣,并分担保护他的责任。如果得到了他们的合作,他们便不会把父母集中在娃娃身上的注意力当做是对他们重要性的一种威胁。想和别人在一起的欲望,并不一定是对别人真正有兴趣的证明。有一个女孩子,在被问及她的最初记忆时,说道:“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一起游玩。”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她正慢慢地学习和别人交际,可是,当她提起她最大的惧怕是“我怕别人都不理我”时,我们却能觉察到她的挣扎。从这里,我们还能看出她缺乏独立性的征象。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握有了了解整个人格之钥。曾经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的人,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说过:假如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他们更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之道:在日常工作及平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按自己的行为方式做事。对合作的任何妨碍都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例如,只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恩宠:他也只愿意听取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对他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他这种毛病开始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质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开始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上取得好成绩: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未被训练以合作之道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训练的工作之前,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有较大的机会来来成功地克服困难。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时可能会犯错误,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不断努力,而不能把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假如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