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最近又一轮大规模感染,人们才意识到,新冠病毒尚未远去。五一过后,许多人游玩归来,身体逐渐出现新冠症状,“二阳”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按照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从去年12月算起,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张文宏医生同样在5月18日表示,“第二波”是科学规律,但这一波的波幅要低,症状更轻。经历了紧绷的三年,整个社会由内而外呈现出一种报复性放松。这有利于恢复生活的秩序。不过,新冠病毒在人们心里的烙印,并未随着新冠防控降为乙类乙管而消弭。认知与现实的错位,造就了当下“二阳人”超越想象的痛苦。
对于乐观派而言,他们感染后并不担心自己,却更加害怕把病毒传染给有家室的同事,背负起巨大的道德压力。
另一方面,报复性放松导致“二阳”的打工人失去应有的共情。如果不希望去公司传染同事,或病情影响工作状态,他们不能像第一次感染那样获得公司的优待和理解。 “二阳”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不过当病毒潜藏于生活中,除了基本的防护,许多人发现自己能做的并不多。我们找到几个“二阳”的人聊了聊,以下是他们的讲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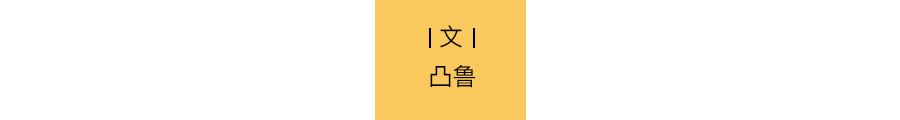

5月12日,我起床后发现嗓子特别干痒,喝了点水,没当一回事,直到下午身体开始出现乏力、出虚汗。此时,我才意识到现在和第一感染新冠时的症状非常像。我是一名护士。当天夜班结束,我回到家立马测了抗原,显示一条杠。
周六是休息日,白天时症状没有加重,但到了晚上,我开始发热了,平时体温只有35.8度,这次一量,竟然37.5度。我再测一次抗原,果不其然两道杠。2022年底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可能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患者,我的症状非常严重,大家经历的,发烧、头痛、“吞刀片”、嗅觉和味觉下降、上吐下泻等等,我全都深有体会。别人的生病周期是5天,但我光是发烧就持续了五天,最后申请了年假、病假,以及和别人倒班,东拼西凑出10天假期用作休息调整,总共花了半个月才恢复状态。两次感染对比,第二次症状变轻,不变的是,都要带病上岗。新冠防控降为乙类乙管后,我们医院已经将新冠患者视作普通感冒处理,阳了无需上报,即使上报给护士长,对方也是告诉你,能工作吗,实在不行和同事倒班,或请病假。五一假期后,医院的发热门诊出现一个小高峰,据说我们住院部的医生需要过去支援。当时我的同事也出现身体不适,就吃了点药,只有一位同事发烧到38.5度,请了一天病假。大家都是医护人员,对于病毒是无所谓的心态,工作环境如此,根本躲不过,除非遇到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同事,我们才回避一下。像科室有两位护士的小孩年纪太小,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故意分开。5月14日,确诊第二天,我需要上一个白班加夜班。那天,我的眼眶有点疼,全天处于头痛发烧的状态。值夜班前,我吃了一粒上次吃剩的布洛芬,所幸因此降温,再没发烧。疫情时穿的防护用具,由医院颁发,我们是没有的。二阳之后,医院对护具没有要求,我便戴着一个N95口罩工作。前段时间北京白天超过30度,由于医院没开空调,口罩里全是汗水,把我折磨得够呛。至于感染病人的风险?我们知道,但无能为力,医院同样人手紧缺。对于医护人员二阳,感染疾病科的原话是:能上半班就上班,尽量不传给病人。去年第一轮感染潮中,有病人听到我鼻音太重或咳嗽,我只好用热伤风、感冒等理由来敷衍。那时我连轴转,被要求两点一线,除了医院就是家,不被允许去超市,线上购物也不能和配送员接触。如此谨慎之下,还能感染病毒,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隐瞒病人。
但我有只号称猫中哈士奇的小奶牛,正是最调皮的年纪,两只猫见面不久,就上窜下跳,整夜闹腾。我是个睡眠质量极好的人,但当晚醒了四五次,导致早上五点就起了床。睁开眼觉得有点冷,我还以为是疲劳导致的普通感冒,压根没想过是二阳。来到公司,中午食欲全无,感到恶心。慢慢的,我发现“感冒”症状在加重——首先觉得越来越冷。室外温度35度,我却关了办公室的空调,手指碰到裸露在外的胳膊,一点点的温差竟然觉得针刺的疼。这和首轮感染新冠时症状很像。意识到可能阳了,担心传染同事,我在手机下单了一盒对乙酰氨基酚片,然后和领导请假回家。回到家,我立马测了抗原。在我翻箱倒柜寻找温度计的五分钟里,抗原结果已经出来,两道暗色的杠,然后我测了测体温,39度。我问领导,生病这几天能否申请居家办公,像第一轮感染那样。领导明确告诉我,不行,只能请病假,或者坚持去上班。他的回答,让我有点生气。本质上,我的工作不受办公地点的限制。下午五点到家,吃完药,我开始睡觉,断断续续,直到第二天傍晚。期间,我除了吃饭、吃药,剩下的清醒时间只做了一件事:给公司提供合规材料,证明我真的病了。第一次,我申请病假后入睡,醒来觉得脑袋依旧昏沉,于是又量了一次体温,38.5℃。随后我看了一眼手机,病假被拒,理由是材料不足。公司人力需要我提供病假条、诊断证明、挂号单,三个材料缺一不可。和直属领导沟通后,我再次添加了阳性证明和量完体温的温度计照片,若是首阳时请假,这些足矣。一小时后,病假再次被驳回。人力还特意补充,今天的病假必须有今天的病假单,不能补开。我非常生气,但确实没力气,只好第三次发出申请,同时把病假改成了没有工资事假,秒过。如果仅仅是身体发热,我还能克服,问题是我没力气折腾,中午点了一顿外卖,分两顿才能吃完。吃第二个包子时,我特别想吐,但想到不能空腹吃药,忍着难受吃完。我想问问离家不远的社区卫生所,能否提供相关材料。打电话询问时,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开药,有些也可以开诊断证明。但病假单和挂号单,只能去医院办理。可能近期社区里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有很多吧,挂电话前,对方熟练地告知了我最近的医院。我在挂号平台查询,没号了,然后拨通医院电话,护士回复:只能到现场排队。独自前往几公里外的医院,还要现场排队,这对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来说,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状态,都是一场折磨。封控解除了,并不意味新冠不是相对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可以理解公司需要员工证明是生病而不是偷懒,但一张卫生所的诊断证明是不是足够了?当你向一个确诊新冠的人,在对方症状最严重的前三天,索要一张当日挂号单和病假条的时候,很难不让人怀疑不是故意为难。另外,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公司感染的?公司完全不用负责任吗?我必须拖着40度的身体去医院证明我是一个新冠患者,才有资格享受公司70%的薪酬?生病这几天,我一关灯睡觉,家里的两只猫就开始打架。我的床是他们战场的一部分,我的腿、肚子都被半夜踩过。有一次,我开灯时甚至看到猫毛从脸前飞过。但我的嗓子不允许我大声呵斥猫,我的精力也不允许我和人力吵一架,只能先养病。小猫的闹腾我逐渐适应了。让人痛苦的,还是工作。下周一无论是否转阴,都要去上班,我想,再没有比这更煎熬的了。
印象中,我从小到大几乎不生病,从未发烧,也在去年的感染潮中侥幸脱身,被身边同学形容为:铁打的男人。但在今年5月中旬,我没躲过。盖被子,身体烫,掀开被子,特别冷,是我对发烧的第一感受。在冷热交替的间隙,我不甘地想着:老子身体这么硬朗,和你干了!5月13日下午,毕业答辩结束,我和实验室里的伙伴放肆狂欢。从下午开始,吃饭、唱K,深夜12点结束,我们再找一家清吧,闲聊到凌晨4点。不只是喝酒、熬夜,那晚回宿舍我只睡了五个小时,第二天中午还去体育馆和老师打羽毛球。
在我们专业领域,有一个“开窗期”的概念,即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免疫能力会呈现短期下降的状态。坦白讲,我以为自己能顶住,没想到第二天立马不对劲。和朋友打乒乓球时,我难以专注,老是接不住球,或把球打飞,不久后开始发烧、头疼、失眠,那些耳熟能详的新冠症状陆续出现。5月17日,舍友分我一块面包,他说好吃,我尝了一口,甜得发腻,想吐。那天体温开始超过38度,我吃了两袋999冲剂。后来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为啥不测抗原,我调侃说,不测就不会阳。
阿豪
由于要和团队前往苏州出席活动,我本来已经打了退堂鼓,但带队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高铁票的证明,一些费用将无法报销。我考虑了一下,去就去吧,担心无法及时退烧,我还吃了一粒布洛芬。要和一位阳性患者同行,团队成员是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经阳过一遍,不至于恐慌。像我舍友说的,新冠病毒无法被完全消灭,生病与否,与诸多因素有关,那些解释不清的原因,不妨归为运气。想起2022年12月,学校遣返学生,一位舍友回到厦门后,通知我们,他确诊新冠了,但无症状。接着,又有两位舍友回家,也阳了。宿舍里只剩我和另一位舍友,他阳了,我没事。我们共处一周,后来他回家,我还是没事,应了当时网友的戏谑:新冠挺仁义,会留下一人负责做饭。像出行戴口罩,酒精消毒等基本的防护措施,我一个不落,全部安排。对于我来说,感染新冠只是平静生活的一个小波折,怕的是传染给老师。实验室的老师六十岁左右,家里还有小孙子。停课后,他的生活单一,家、实验室、球场三点一线。我们几乎每天中午都打羽毛球,如果他感染了,我难辞其咎。那时校内一片宁静,我呆到了1月份,临近春节才回家。尽管嘴上喊着不在乎,我还是戴了N95口罩,口罩之上是一层防护面罩,我像顶着一个头盔,踏上了归家的旅途。远方的家人相安无事,没有一人确诊,我可不想在我这出岔子。
母亲节第二天,我们一家回了娘家聚餐。饭桌上,我觉得那些菜的味道不对,不够香,不够鲜,甚至不够味,有失平时的水准。这不是我的一孔之见,妻子的姊妹、阿姨、姨家的孩子们都如此认为。经过简单的辩论,真相竟是,菜没问题,是我们确诊新冠了,味觉和嗅觉受损。按照专家的说法,今年四、五月迎来第二轮感染潮。据我的观察,年前没阳的那批人,现在应该都阳了。包括我们夫妻俩,以及三岁的女儿。反之,我在手机上看新闻,临沂当地的儿童医院却人山人海,由于太多儿童确诊新冠,许多大人带着小孩在医院排队,完全挂不上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和妻子决定不再出门,让家里的店铺停业十天。我一直对疫情防护很重视,在解封之前,已经囤了超过800元的药,什么布洛芬胶囊、蒲地蓝口服液、川贝枇杷膏等等,专家建议准备的药物,我一个都没落下。大辉提前备药
我们在家里小心翼翼地度过十天,错开感染高峰期。即使我后来不得不出门做生意,也全副武装。我从事旗帜加工行业,需要前往物流城联系司机发货。出门前,我必须戴上N95口罩、医用帽,只露出一双眼睛,而兜里揣着一瓶酒精喷雾,时不时给服饰消毒。出门后,我的手尽可能不触碰其他物体,包括衣服、鞋子、手机等私人物品,不在人多的地方逗留,尽可能不进入密闭空间。当时有人已经“阳康”,所以物流城里人们防护程度各有不同。有人像我这样包裹得严严实实,也有人连口罩都不戴。以往骑车都堵的物流城,现在空空荡荡的
不戴口罩的人数比例,随着“阳康”的人数而增加。街道上、物流城里不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我不敢再开电瓶车,直接开轿车去和司机对接。车上有一瓶酒精凝胶。发完货,我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凝胶把裸露在外的皮肤连擦三遍,包括手、脸、头皮。每次擦完,身上都凉嗖嗖的。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有效防护,反正总比没做要好。回到家,我再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放到固定的地方,等到下次出门再穿,算是完成一个出门的流程。当时我需要和客户吃饭,无法推脱,便试探性地在公共场合摘了口罩。吃完饭,我立马戴上口罩。直到回到家,等了一个星期,身体没有反应,我才松了一口气。感染潮慢慢降温,医院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挂号变得不再艰难,我也变得不那么紧绷。况且,闺女今年9月要去幼儿园,过度的防护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五一假期,我们和她去了烟台旅游。出门前,我已经看到二阳的新闻。所以后来我们仨确诊阳性时,其实都在预料之内。如今大家不怎么关注新冠,其实我们也一样——过度谨慎有什么意义呢?躲不过,还制造了焦虑,不如做好基本的防护,和心理准备。第一轮感染时,我看着年纪大的父母、亲戚在医院挂着吊瓶,心里特别难受。如今我同样担心他们会二阳,但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似乎只能接受感染新冠这件事。当然,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这是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