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军统”
我来自军统,入伍那年18岁。
我父亲是国军将领,他在与日伪作战时殉国,这是我放弃学业加入军统的原因。
军统不是想进就进的地方,李士珍是父亲的朋友,家父葬礼上我直接找到他。
他只问了我一句:
“你想好了吗,这里没有退路的。”
我只回了一句:
“我想好了。”
他把我安排进了中美合作所特训班。
中美合作所由国民政府与美国合办,美国人用最新技术帮助军统培训特工,作为回报,军统会向美国提供大平洋战场上日军的情报。
不要小看军统,日寇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最初就被我们破译,美国人对此置若罔闻,才有了珍珠港事件,正因珍珠港的应验,令华盛顿开始重视军统,才有了中美合作所。
切莫被“合作所”几个字迷惑,这里其实很大。我第一眼就被这里的应有尽有震撼了:
高大的办公楼,一栋栋漂亮的小别墅,设施齐全的医院,甚至还有舞厅,不过这些大多都供美籍教官们享用。
合作所到底有多大,看看停车场就知道,单是那座军用停车场,占地就比一所普通高校要大,我们第一次参观时里面约莫同时停了2000辆军用卡车。
后来我去过北平,参观了同为美国佬帮忙建设的清华大学,与合作所相比,无论面积还是设施,清华都更像座窝棚。
但学员日子却很清苦,我们每天7点开始上课至晚上六点,课程分为中国课与美国课,中国课有通讯、情报、化装、擒拿、防毒等,当然也少不了最无聊的政治课,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
中国课比较枯燥,加上中方教官普遍一本正经,同学们都兴趣寥寥,有次防毒课讲到注射麻醉剂(防毒课主要是制毒与用毒,真正防毒的内容寥寥,但总不见得把课程取名为毒药课),教官用兔子作演示,一整管麻醉剂注射进去那兔子还是活蹦乱跳,有的同学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教官下不来台,满脸通红,好在他反应快:
“同学们,麻醉剂用量要根据对象酌情增减,比如这只兔子体积庞大,需二次注射。”
说着又给兔子来了一针,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军统不同于大学,这种情形着实不多见。
美国课一周只有两堂,分为武器(手枪,机枪,肩射火箭筒等)和爆破。
美国课内容偏向实战,教官也比较风趣,有时会和我们打哈哈,所以这两堂课成了每周大家翘首期盼之事。
我记得武器课在周六下午,排在政治课之后,政治课上老师大谈三民主义,同学们却磨起了屁股,等不及下堂课的到来,每次下课铃声一响,大家规规矩矩排队走出门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争先恐后朝武器课的地方撒欢跑去。
(军统毕竟不同于学校,一下课就喧嚣着往外跑是不可能的)
开学一个月后我深刻理解了“军统没有退路”。
特训班的日子很清苦,每天6点起床早操,仅有5分钟起床时间,三餐全是米饭辣椒,每天除了上课还要三次体力操练,同学中不乏我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关系户,有两个吃不了苦的,逃跑了。
军统恐怕是世上最难越的狱,两位结伴逃亡的同学当晚就被抓了回来,美国教官和郭履洲就如何处理此事激烈争吵,郭履洲坚决要求枪毙二人,最后美国教官只保下其一。
那天夜里,后山传来一记清脆悠长的枪声,寝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届三个班共有两位同学死亡,另一个是在武器课时不幸被走火的手枪打死的。
戴老板是三个班的班主任,他只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开学典礼,所有中国教官和学员前后排站立,聆听戴老板训话。他在合作所呆了三天后飞回重庆。
第二次是结业礼,戴老板挨个与每位同学握手,旁边副官向他汇报每个同学的名字与成绩。我在那期学员里排名第一,得到了戴老板亲手赠予的派克金头钢笔。
结业礼后我们班教官通知我去戴老板办公室一趟。
我推开他的门,小心翼翼唤了声:
“长官好。”
戴老板笑了笑,示意我坐下:
“还是叫我班主任吧。”
典礼上刚毅冷峻的戴老板,此刻却显得和蔼厚重。
半响后他继续:
“我看过档案了,你今年被中央大学录取,为什么来这里。”
我:“国仇家恨,不得不报。”
戴:“很好,团体决定了,让你去中央大学继续学业,同时开展工作。”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
班主任摆了摆手:“南京现在是敌占区,我们需要更多同志在第一线和日本人较量,你的学生身份是很好的掩护,而且你已被录取了,不会有人怀疑。”
他一句话就让我信服了,不过我还有疑虑:
“可大学那边已开学两个月了…”
班主任笑了笑:“现在打仗,没几个学生能按时报到,我们在中央大学有人,已经帮你安排妥了。”
我站起来,行了个军礼:
“誓死完成任务!”
班主任帮我整了整衣领:
“今晚就收拾行囊吧,明早出发。”
晚上在宿舍,我把那支钢笔内三层外三层裹在背包最里面,从没拿出来用过,直到今天写下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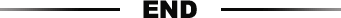
往期回顾: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