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师告知开始,手语翻译转达之后,打算赤足的胡晓姝脱下拖鞋。她用脚将拖鞋摆放齐整,确保拖鞋刚好对着大幕下方的基准线。她一丝不苟的劲头儿,就和每次舞台表演一样。
这是聋人戏剧演员胡晓姝的一个瞬间。
和胡晓姝聊天是奇妙的体验。因为大多数的听人(听力健全人的简称)通常不会手语,我们的交流需要手语翻译间接助力。可胡晓姝的眼睛、神情和动作,总是能直接地抓住与她沟通的人,让人很难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白色衬衫、缀满花朵印花的绿裙子,上下翻飞的双手和诚挚热切的眼神,在手语这种语言系统里,胡晓姝异常“健谈”。和她聊艺术,聊生活,聊聋人的世界,你也会由衷确信,虽然耳朵听不见,但它们或许可以“看见”,洞见世界,洞见生命,也洞见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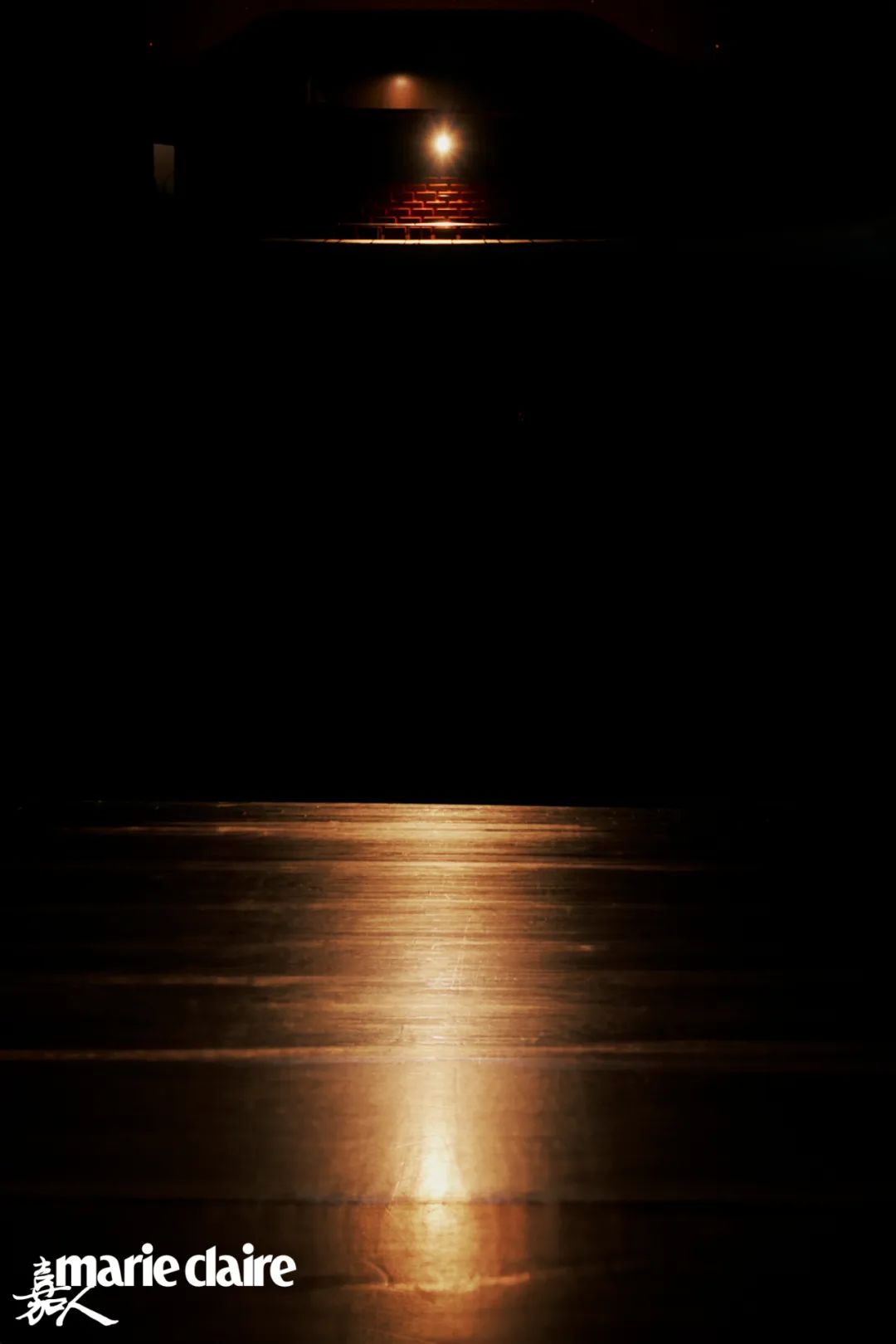

 阿那亚戏剧节如今已是国内重要的戏剧盛事。今年,胡晓姝随《午夜电影》剧组在那里亮相。
阿那亚戏剧节如今已是国内重要的戏剧盛事。今年,胡晓姝随《午夜电影》剧组在那里亮相。
作品名字里有“电影”,形式却是舞台剧。故事聚焦一位深受慢性疼痛困扰的女性,在很多个不眠之夜,她孤独地游荡在互联网上,靠一个个网页和故事来逃避现实。这部剧作得到了柏林戏剧节“剧本市场计划”的孵化,并先后在上海、杭州、桂林演出。
当胡晓姝和另一位听人演员张增慧在舞台上表演时,沉浸看戏的观众之中不乏业内人士。她们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演出时,台下刚好坐着一位与阿那亚戏剧节熟识的导演。整场看罢,这位导演主动联系、推荐,《午夜电影》的阿那亚戏剧节之行由此敲定。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很随机的因缘。深究下去,它却有特别之处。聋人表演在国内的戏剧舞台上并不多见。《午夜电影》让观众意识到,聋人可以站上舞台,可以展现与听人完全不同的、自主的艺术理解和表达,这是进一步的收获。《午夜电影》的导演刘潇评价说,胡晓姝的加入,让剧组“得以用演员的身体本身,而不是扮演的方式回应剧本中关于障碍的讨论”。胡晓姝对这个论断深感欣慰,因为她体会到刘潇对聋人的深入了解,也能想象一个听人为聋人群体发声的决心。当初,胡晓姝就是被刘潇的计划打动,参与了10个人左右的工作坊,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午夜电影》的主角之一。聋人的状态,让她对苦于病痛的主角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因为懂得,所以表达也更顺畅、准确。在更大的戏剧舞台上,胡晓姝也在为聋人走近戏剧助力。去年,舞台剧《弗兰肯斯坦》中文版上演。这个由玛丽·雪莱撰写的故事历来是热门的IP,被搬上舞台后,自然吸引了众多戏剧观众。上海场的演出专设了手语场,站在舞台侧边担任手语翻译的正是胡晓姝。胡晓姝以聋人手语翻译的身份站上舞台的固定位置,台下坐着听人手语翻译进行镜像转译。当听人手语翻译的信息传递到胡晓姝这里后,她再面向聋人观众翻译出来。类似的手语场尝试,国内还不多,《弗兰肯斯坦》是继《长靴皇后》之后的第二次。舞台上的灯光有时会影响胡晓姝的视线,复杂的汉语语法也会对手语翻译提出挑战。但跟让聋人平等地观看、享受戏剧比起来,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小事。黑色缎面披肩 MAISON MARGIELA
投身聋人戏剧创作的胡晓姝当然会留心聋人观众的反应。他们最普遍的反馈是,当舞台上下都是听人时,聋人很难走进剧场。手语场这样难得的机会能够让聋人也感受戏剧之美。“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舞台剧能发展手语场,也有更多的聋人能登上舞台,去做手语翻译。”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胡晓姝并不觉得舞台属于她,更多时候,她希望舞台属于聋人群体。
聋人观看戏剧的感受会打折扣吗?这或许是很多听人的困惑。胡晓姝举了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的例子。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赛事,迄今已经举办67届。阿巴乐队(ABBA)和席琳·迪翁都曾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但未必为听人熟知的是,这项赛事在电视直播时,还有聋人专属的频道。通过表演和手语翻译,聋人就可以从手语歌里领略音乐的节奏与律动之美。经由视觉,聋人可以像听人一样享受视觉音乐。2017年,胡晓姝通过奥地利广播电视台(ORF)参与了欧洲歌唱大赛的手语翻译表演。当年的大赛,在聋人专属频道的全球观看量达到了1.9亿人次之多。“这充分说明了聋人对音乐和艺术的渴望有多强烈,无障碍的艺术节目和内容有多重要。”胡晓姝说起往事,一脸郑重。
胡晓姝是上海人,6个月大时,她因为医院过量注射药物而失去听力。直到2003年,20岁的她在奥地利维也纳国立艺术大学留学时,才意识到聋人也可以是优秀的戏剧从业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当年被奥地利维也纳国立艺术大学录取的100位考生中唯一的聋人学生。在求学期间,经朋友引荐,她偶然参与了一个剧组的演出。除在戏剧中实现社交、发现自我之外,她还发现,聋人也有着独特的艺术创造能力和舞台表现形式。在欧洲,台前幕后都由聋人组成的剧团不在少数,聋人戏剧教育也梯队完备。 前几年回国后,胡晓姝看到了对比。中国的聋人戏剧还处在一片空白之中。按照她在欧洲积累的经验和判断力,她认为中国有很多聋人戏剧的人才。可惜的是,这些人才处在内心尚未觉醒的阶段。胡晓姝希望聋人群体更有主见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戏剧。没有现成的聋人戏剧组织,胡晓姝的解决方案也简单:自己建。她申请了一些经费,打理起“聋人戏剧营”,还邀请英国知名的聋人戏剧大师参与工作坊,帮助中国的聋人演员唤醒自我。起先,招募计划是10人。计划发布之后,报名者数量远超想象。最终,碍于成本,戏剧营只能对20位聋人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帮助他们剖析自我,做出主动的艺术表达。“中国的聋人生活节奏比较快,生存压力偏大,社交障碍也多,大多数人习惯了去适应外界的环境,很少向内去看自己。”胡晓姝说,“聋人戏剧营”是让聋人内观的途径之一,等条件再成熟一点儿,她还有更大的野心:聋人剧团、聋人剧院。
 今年5月,胡晓姝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同学合影。这是她1998年从上海市虹口区聋人学校毕业之后,第一次和老同学见面。谈到重逢的感受,胡晓姝的描述是“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有点儿难过”。“开心”很好理解,25年过去了,旧日同窗能再续前缘,分享彼此的改变,在匆匆的人生里,这并不算轻易的事。让她“难过”的点在于,胡晓姝发现,国外的见闻和经历让她慢慢成长,可留在国内的大多数同学一如过去。 “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就业的问题、对工作的不满、社交的困难和社会的不理解等。”胡晓姝说,当现实生活就已经是压力时,要寻找诗意、艺术、远方,仍然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路。对聋人与听人同工不同酬、聋人在生活中面临的不便等问题,虽然胡晓姝看到了近年来的改观,但是她的感受依然强烈、真实。她举了自己在奥地利看到的例子。在那里,聋人找工作时,大部分都有手语翻译陪同,特别是在企业交流促进会,手语翻译是标准配置。又如,国内电视节目中出现手语翻译的频率日渐增多,但其画框的占比依然很小。“我们聋人是靠眼睛来看的,画框太小的话,会看不清手语,依然无法正常收看。”胡晓姝介绍说,在欧洲,聋人能看到的画框基本要占据屏幕的1/3左右。这些只是部分已然呈现的事实,冰山下还有更多观念与意识的缺失。在胡晓姝看来,最典型的是语言的剥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000多万名聋人,中国有2780万聋人。聋人的语言是手语。在全世界不同的语言体系下,手语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实际上,手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有声语言,它拥有自己的语法和语序。然而,胡晓姝在中国的表演和生活经历中,发现人们对手语的尊重和理解并不够。一些听人在表演时,会针对手语表达提出意见,有时候,这种意见是出于对手语的误读,这令她不太舒服。
今年5月,胡晓姝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同学合影。这是她1998年从上海市虹口区聋人学校毕业之后,第一次和老同学见面。谈到重逢的感受,胡晓姝的描述是“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有点儿难过”。“开心”很好理解,25年过去了,旧日同窗能再续前缘,分享彼此的改变,在匆匆的人生里,这并不算轻易的事。让她“难过”的点在于,胡晓姝发现,国外的见闻和经历让她慢慢成长,可留在国内的大多数同学一如过去。 “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就业的问题、对工作的不满、社交的困难和社会的不理解等。”胡晓姝说,当现实生活就已经是压力时,要寻找诗意、艺术、远方,仍然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路。对聋人与听人同工不同酬、聋人在生活中面临的不便等问题,虽然胡晓姝看到了近年来的改观,但是她的感受依然强烈、真实。她举了自己在奥地利看到的例子。在那里,聋人找工作时,大部分都有手语翻译陪同,特别是在企业交流促进会,手语翻译是标准配置。又如,国内电视节目中出现手语翻译的频率日渐增多,但其画框的占比依然很小。“我们聋人是靠眼睛来看的,画框太小的话,会看不清手语,依然无法正常收看。”胡晓姝介绍说,在欧洲,聋人能看到的画框基本要占据屏幕的1/3左右。这些只是部分已然呈现的事实,冰山下还有更多观念与意识的缺失。在胡晓姝看来,最典型的是语言的剥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000多万名聋人,中国有2780万聋人。聋人的语言是手语。在全世界不同的语言体系下,手语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实际上,手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有声语言,它拥有自己的语法和语序。然而,胡晓姝在中国的表演和生活经历中,发现人们对手语的尊重和理解并不够。一些听人在表演时,会针对手语表达提出意见,有时候,这种意见是出于对手语的误读,这令她不太舒服。乳白色长裙、围裙 均为RUOHAN
纯银白松石嵌珠耳环 OLIO E ACETO
生活中也是如此。她看到大量手语老师是听人担任的,但听人的手语表达和聋人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不能让更了解自己群体的聋人承担一些手语老师的工作?中文的语汇本身就比较复杂,常有多义性,相近的表达也很多,如果不是聋人,手语老师往往很难精准呈现那些微妙的差异。事实也是如此,在采访过程中,某处表达究竟用“结合”还是“联合”,她都要斟酌一番,然后让手语翻译把两个词都说出来。胡晓姝有时候在电影、电视剧、剧场中看到听人演员饰演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手语往往很生硬,她反问道:“为什么不能积极让聋人去表演、去展现真实的聋人群体呢?”放到影响更大的生活场景里,“语言的剥夺”也许就有更严重的后果。胡晓姝有意识地背负着很多与聋人有关的使命与责任。她会向学校推广手语,要求学校聘请聋人担任手语老师。通常,这些建议会获得一些学校国际部的认可,但在国内部,碰壁的概率非常大。语言是很多表达、创作的源头,当语言教育缺失,其他方面也会陷入停滞。譬如戏剧,如果手语都无法精准地表达、教学,它又该如何拓展到其他艺术领域?在奥地利的城堡剧院,胡晓姝参加过一个青少年戏剧教育项目。导演是听人,学生是聋人,项目方一定会安排专业的聋人导师来进行督导翻译,发挥桥梁的作用。当聋人与听人真正地相互理解后,那些聋人青少年的自信心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但在国内,像胡晓姝这样,为这些事困扰的聋人并不多,这就让她更苦恼了。苦恼并没有让胡晓姝停下脚步。从奥地利回到上海之后,她投身一些聋听融合的活动。比如在上海TX淮海这样的热门商场,她会组织工作坊,把简单的手语教给听人,再讲述一些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有时现场能有300多个观众,聋人与听人模拟具体的生活场景,用手语交流。这种破冰对胡晓姝有着特殊的意义:“手语交流让聋人和听人都感觉到,彼此是平等的,可以交朋友,可以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确实有不同,但将不同放在一起,不是排斥和歧视,而是多元与融合。”有一个描述残障的英语单词是disability。胡晓姝希望,她的事业就是慢慢把dis(英语单词前缀dis表示“不、无、相反”)去掉,留下ability(才能、本领、才华)的过程,“我们虽然被定义成残障人士,但是也都有隐形的才华”。聋人和听人一样有才华、有能力,如果能够用手语打破交流的壁垒,用艺术打破审美的边界,对聋人和听人,这都是多样性的延展。这条路很长,需要聋人正视内心,主动宣传自己,并且团结在一起。胡晓姝就是这样做的。临别的时候,总要互道感谢。胡晓姝将两手放在胸前,握拳,竖起两个大拇指,第一节同时向下弯曲。这是手语“谢谢”的意思。对听人来说,其实一眼就能看懂,尤其是配上胡晓姝脸上明媚的笑容。 M.C.:作为舞台戏剧演员,你登上的最难忘的舞台是哪个?这个舞台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M.C.:作为舞台戏剧演员,你登上的最难忘的舞台是哪个?这个舞台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胡晓姝:我在2003年第一次接触戏剧。那时,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留学,暑假期间遇到一门戏剧课程。他们正好有一部戏,想找一个演员,这也和我的梦想非常符合。参与演出之后,我发现戏剧让人可以实现社交,可以发现自我,可以发挥创造力,丰富了我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国外,聋人是可以表演戏剧、组建剧团的,有的剧团所有成员都是聋人,聋人也有自己的艺术天赋和表达。后来,我就会参与一些表演项目,也参与一些听人的戏剧,迄今已经参与20多个。
M.C.:作为舞台戏剧演员,每次登台前,你通常会有哪些习惯或仪式,或心理暗示?胡晓姝:上台之前,我会和演员、服化道等剧组成员交流,有时候可能打打闹闹、开开玩笑,营造一种放松的氛围。这就像是暖场热身,“鸡血”打足之后,GO,我们上台。M.C.:在这么多年的聋人文化推广中,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胡晓姝:在国内,我觉得总体来说最难的是对聋人群体的理解不足。人们不需以同情心去对待聋人群体,而是平等地对待,倾听我们的心声并互相合作。目前更多的是想象聋人可能需要什么,给出一些措施。但其实,应该先多接触聋人群体,看看聋人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多了解聋人的语言,有了这个桥梁,才能更好地促进沟通。社会上的多数人对聋人群体不了解,应该先了解这个群体有什么障碍,再去做打造无障碍环境的工作。希望听人多和聋人群体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探索新时期听人与聋人正确相处之道。M.C.:你是一个特别充满热情和能量的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能量的?胡晓姝:我在奥地利的时候,戏剧圈子的能量非常高,大家一起投身热爱的行业。我的好奇心也非常强,学了很多东西,我也变得更有自信了。回到上海之后,我看到了一些还能改进的地方,因此我一直充满热情,希望国内的聋人事业可以发展起来。
摄影/裴瞳瞳
采访、撰文/傅踢踢
造型/朱东日
化妆/Anna Hu
发型/GuZiXin(SalsaStudio)
手语翻译/程莹
编辑/袁新
造型助理/Azlyn Zhou、吴奇
摄影助理/康细菌
编辑助理/伍铭慧
场地特别鸣谢/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
阿那亚戏剧节如今已是国内重要的戏剧盛事。今年,胡晓姝随《午夜电影》剧组在那里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