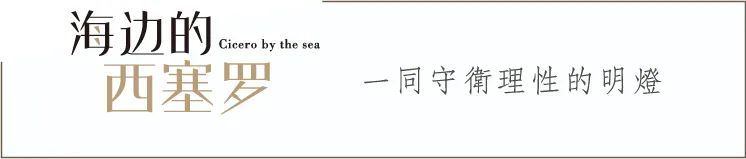
不,您说的这不是生活!忍受痛苦,我就呐喊;目睹悲伤,我就流泪;看到卑劣,我就嗤笑;沾染污浊,我就憎恶。唯有这,这才是生活!
——《第六病室》
各位好,今天不想写正稿了,随手写几笔,跟您聊聊天,所以每个段落之间可能会写的比较散——这就是说,您想从哪个段落看起,其实都可以。
最近我有个苦恼,就是近一个月来,本号的涨粉量不如之前那么多了。每天不管文章质量如何,阅读量多少,大约只能涨小几百个读者。感觉很是惨淡,连带着心情也不太美好。当然我这样说,您可能会认为我也是一个被流量所裹挟了的人,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世间哪有永远增长的事物呢?你看二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率都跌到0.4%。这年头,要啥自行车啊?你个写微信号的,不掉粉就不错了。话虽这样说,可我毕竟是一个对自己写作有要求的人,辞职以后,每天在家中这样闷头看书,写作,任时光这样流逝,我总觉得我的人生这样渡过,应该有点意义。这些意义中,卖文糊口固然是一方面,但读者的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有老读者与我渐渐疏远(天长日久,这种事总难免发生的),又没有新读者喜欢我,那我这条路,是会越走越窄的。所以我必须给自己一点反思,问问自己文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我昨天那篇《柴进和王澄澄,为什么总会把“炫富”搞成了“炫父”》为例好了,那篇文字里,我借水浒传里柴大官人的事儿说了说王澄澄。有位读者就留言跟我说:小西,虽然你这文,我看的从头笑到尾,但读完还是觉得很无力,也没获得什么。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你看最近发生的xxx、xxx、xxxx还有xxxx,大家瓜吃的是很猛烈,最后不都是虎头蛇尾、没了下文了么?这种事,写多了我们真审丑疲劳了,说还不如不说。还不如就写写你眼里的柴大官人,那这文章还有可能长存。我想了想,也对,“哲学家一直在解释世界,但真正重要的是怎样改变它。”——本来关注时事,舆论监督的目的,首要是督促事件的妥善解决。可是当监督变成了“吃瓜”,笑骂只流于单纯的笑骂。这种东西写起来也就很无趣了。所以我再次下决心,以后要减少今后本号“吃瓜文”的数量。领着大家吃瓜看戏虽然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是只写这样的文字,似有些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我自己。对于易烊千玺的这个回应,我看网上两拨人又吵的很凶,有人欢呼这是“庶民的胜利”,有人则骂这是“庸众的胜利”。这两种观点之间孰是孰非我觉得倒在其次,但就像我之前已经说过的。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是易烊千玺考编这个事儿,怎么就成了当代中国公众舆论领域的“君士坦丁堡之战”,攻守双方非要把这么一个编制地位看的这么重。而易烊千玺这样一个少年成名的流量明星,在我们这些普通人想来,似也不差体制内的那么一个有编制的工作。他怎么就非要加塞到考编的那个队列中去,跟“小镇做题家”们去抢那么一个体制内的饭碗呢?小西,你这就有所不知了吧?你不知道“厅局风男友”,如今也是女孩子们一个审美倾向么?没准四字弟弟(指易烊千玺)这是要给自己加一个萌点呢。嗯,“厅局风男友”,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新词儿。我特地到网上去搜了搜,结果还真发现了另一些“小鲜肉”男星的“厅局风男友”打扮,以及这个饭圈里对这个“萌点”的解释。按照我查到的解释,所谓“厅局风男友”,其实就是“体制内男友”换了个说法而已,从刘昊然、陈晓等男明星穿正装考编制,到抖音小红书各大平台网红博主晒出体制内男友,所谓“厅局风穿搭”以病毒式传播的速度走红了网络。据说“局里局气”“厅里厅气”,现在被看作对男性的高度赞美。“嫁人就嫁厅局风”,似乎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女孩的审美共识。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奇怪,前几年我自己还“有编”的时候,我是知道“体制内男友”这个词儿在丈母娘们眼里确实是出于相亲食物链顶端的。多少漂亮妹子的爹妈不求自己女儿嫁个有钱老板或大大帅哥,而如果女儿能领回一个体制内的小科员来,立刻就会两眼放光。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姑娘本人一般还都是不大看得上这种“体制内男友”的,毕竟大家都知道走进体制内往往就意味着升迁机会低,如果你不是特别有才,或有关系有门路,在体制内一步步升迁,最终爬上很高地位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大部分人一般也就把此生蹉跎在办公室里端茶倒水、拖地写报告当中去了。这样男朋友是很难让女生完全满意的——当时的大部分女生还是希望自己能嫁个“绩优股”、实在不行,“潜力股”也可以。指望着自己的郎君哪天可以一飞冲天。而普通人这样机会,更多只能在体制外实现。而女生们自己的择偶倾向,从当初的“潜力股男友”,到如今的“厅局风男友”,这个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这几年的社会走向又对其施加什么影响,其实不用我多说。大体上来讲,眼下的经济、社会形势,可能也让不少女孩看明白了——想在体制外一飞冲天,对这个时代年轻人来说是很难的,甚至弄不好一个社会波折,你就“摩擦性失业”了。那与其如此,那还不如考公、考编,考进体制内,求个安稳。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女孩们的择偶审美迅速与她们的爹妈合流。于是进入体制内的男性重新成为了“香饽饽”。甚至还传出了某男考进体制内后立刻换女朋友这种奇闻。自此,男方那一边,上至易烊千玺下至小镇做题家,都以考进体制内、有编为荣。而女方这一边,上至丈母娘、老泰山,下到女孩自己,也都喜欢体制内、有编制的“厅局风男友”,审美逻辑闭环了,朋友们。也就难怪为什么已经功成名就的易烊千玺还非要考个编制,而他的考编有为何会招来这么多人眼红了。当下审美就是如此,估计易烊千玺也想转型,走个“厅局风”。依稀记得,某位前不久刚上演过“人在日本,刚爱完国”的著名网红大V,想当年在“装公知“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公务员都是小偷、强盗”的著名暴论。而作为一个自己接近当过这种“小偷、强盗”的人,我当然极为反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觉得这样公开、肆无忌惮的侮辱一个正常职业,是典型的要红不要脸的文痞行为。可是在我看来,体制内、公务员,虽然肯定不是小偷、强盗,但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份正常职业而已。一个正常社会中,如果有妹子萌“厅局风男友”“体制内风男友”,那么理论上也应该有妹子萌“程序员风男友”“医生风男友”“工人风男友”“农民风男友”甚至“掏大粪风男友”——毕竟刘少奇同志都有曾握着时传祥师傅的手说过么:“我当国家主席,你掏大粪,革命分工虽然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的,职业这事儿,说到底其实就是你人生中一个标签而已,你干什么工作,按说与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有没有发展潜力,能不能得到姑娘的青睐,甚至是否“处于相亲食物链顶端”是没什么必然联系。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曾经一再发生择偶主要标准看工作(据说相继时兴过嫁干部、嫁工人、嫁军人等等)的风俗,其实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发展受到制约和局限的一种表征。我们应当希望这种风气不要再来,我们应当希望,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你干得靠谱,都配有一个好前程,好伴侣。而若一定要说男性会因职业不同在魅力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多半来源于职业给予人的不同“工伤”、“职业病”。你若是程序员,可能会996、青年谢顶,你若掏大粪,身上难免沾染一身粪臭,你若当老师,可能难免喜欢动不动教育人。其实公务员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人干公务员干久了,身上的职业病也是很明显的。我身边很多公务员朋友,在生活中慢慢都变得没有和工作时一样——一张扑克脸对人,朋友圈从不发什么有趣的状态(甚至从不发状态),玩笑开不得,到什么场合都正襟危坐,唯上级命令是从,从没有自己的自选动作……你要真到机关去办事,能碰上这样的公务员给你办手续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是找这么一个“厅局风”的人当男友,我觉得很多姑娘其实未必受得了。我这样说还没有直观感受的朋友,建议你去买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去读读。作为我自己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作家(没有之一),契诃夫最喜欢写的人物,其实就是公务员。你看他写《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胖子和瘦子》、《一个胜利者的凯旋》、《变色龙》——这些他写的最成功的小说,主角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公务员”。而契诃夫告诉了你,当一个社会价值甚至审美倾向高度被“体制内”这一个纬度标的,人性会扭曲的怎样可笑而荒诞。来,姑娘们,感受一下百年前的俄系“厅局风男友”——前不久,我曾在《他给余秀华的道“谦”信》一文中说:我觉得帅哥和美女是很难写出好诗文的,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观察难以深刻。可是这文章写完以后,我就感觉这样议论太武断了。因为我最崇拜的名人之一(乃至我将他的头像作为小号的标识)就是一个反例。那就是契诃夫。是的 ,契诃夫就是一个颜值一点不比有易烊千玺差的大帅哥,而他同时也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最深切的观察者、嘲讽者。于是我想将本文接下来的笔墨,重点写写契诃夫这个人:是的,在俄罗斯群星璀璨的伟大知识分子群当中,契诃夫可能是出身最低微、不幸的一个。他出生于19世纪的沙俄帝国罗斯托夫州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这座小城后来被契科夫嘲讽为“聋城”——沉闷、压抑、愚昧、灵魂空洞无比。每到了夜晚,勉强填饱肚子的人们就拉上百叶窗,紧闭门户,把自己包裹成密不透风的“套中人”,将未来完全托付给沙皇和上帝。而契诃夫的家庭又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下层,他的祖父是个农奴,借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攒了一辈子的钱,才勉强从地主老爷那里赎身。父亲白手起家,在镇上开了家小杂货店,但经营非常惨淡。生活不顺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喝酒,一喝酒就喝醉,一喝醉一定打老婆孩子。契科夫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后来说:“我没有童年,但我从小就信仰自由,因为我知道:挨揍和不挨揍,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是的,契诃夫是自由派,而且是那种幽默、乐天、而又心怀慈悲的自由派,生活以毒打加以他,他却报之以一部部笑中带泪的小说。16岁的时候,契诃夫的父亲终于破产了,举家到莫斯科去躲债,却唯独把契科夫留下,让他在当地继续勤工俭学。于是还未成年的契诃夫就化身为了“男版的樊胜美”——他不仅得不到家庭的一分钱资助,反而要应付不断找上门的父亲的债主们,为父亲还债。好在,绝境中的契诃夫有一项无与伦比的天赋——长得帅。而你得承认,颜值这玩意儿确实这个世界上最硬的硬通货。在16岁的时候,契诃夫就凭借他那张眉眼清晰而又温柔善良的帅脸,成了当地十里八村最有名的俊后生。很多贵妇和大小姐都争着请他为自己做家教(因为俄罗斯当时的女性教育是十分滞后的)。说实话,就算契诃夫不教她们什么,这些女士可能也愿意付钱——毕竟,多漂亮的一位小鲜肉啊,摆在那里就养眼。所以16岁还在上中学的契科夫,其实就已经有了相当的挣钱(还债)能力。他的家教工资达到每月近百卢布,这已经相当于一个沙俄基层公务员的收入了。但契诃夫并不满足于此,明明靠颜值就能吃饭,他却一定要靠才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莫斯科大学的医学部,因为经历过底层苦难的他心中有着救治平民百姓的热望。可是医学生的学习生活不仅忙碌,而且昂贵。这意味着契科夫不仅要交更多的学费,也没空给贵妇或她们的子女们做家教了,同时,他还需要替父亲还债,并资助家人的生活。那怎么办呢?于是无奈的契诃夫拿起了笔,在每个放课后的夜晚开始了他“卖文为生”的写作生涯。而踏上这条路之后,人们才发现契科夫不仅是大帅哥、是好医学生,更重要的,他是个天才的小说家。早年在故乡先做售货员、后做家教的生涯,让契科夫同时接触到了俄罗斯这个社会各个阶层,敏锐的他早已理解这个社会下至农奴、上至贵族每一种人是怎样想的。所以当契诃夫一提起笔,开始他的写作时,这些人的故事,就像拧开水龙头的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流了出来。所以什么卡稿?创作瓶颈?对契科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报纸编辑来说,契科夫是他们最喜欢的那种作者——让他写个文章,说几点交稿就几点交稿,而且故事一定精彩,绝不用他们上门催更。即便传记作家,也弄不清楚,在他那苦难的童年中,契诃夫的幽默之花是怎样长出来的。也许,幽默是契科夫必须进化出来的那层保护色——为了生存,他要给乡里的女士们做家教,获得她们的资助,而对女性而言,颜值也许会看腻,痛说革命家史式的卖惨也只能博得一时的同情,只有幽默,才是女性们永远喜欢的。《买这本书,不然打你》,这是契诃夫给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原拟的题目,即便在这种事上,他也想玩个标题党跟读者们开个玩笑——好在书商们及时劝止了他这个有点过分的玩笑。而他把这种幽默更多的融入到了他的小说中,22岁,他写出了《小公务员之死》,23岁时写《套中人》,24岁《变色龙》。所有的小说,都那样荒诞幽默,而又笑中带泪。于是在20几岁的时候,契诃夫就成为了俄罗斯最顶流的小说家。他写文的版税达到了每月500-1000卢布,跟他的小说《胖子和瘦子》里那个一报出级别就吓尿了昔日同学的三等文官比肩了。因为与认识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之后就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不同,契诃夫没有放弃他医生的职业,他主业依然是一个外科医生——而且是艺术高明,且几乎不收费的那种。他乐意给沙俄那些付不起高额医药费的可怜穷苦人们看病,且只要对方表现出生活的窘迫,他就愿意给对方免去医费,很多时候,甚至自掏腰包,为对方买药、买营养品。这让他的诊所变得门庭若市,同时花钱如流水。他的副业写作成为了他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他的主业,行医,反而成为了他最大的支出。“啊,春天来了,多么美好啊!可是我没有钱,更没有时间。”契诃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是的,契诃夫是帅气的、聪明的、幽默的、才华横溢的,但同时他又是善良的、温柔的、悲天悯人的,在他的身上,有着那种东正教圣徒般的悲悯与苦修式的勤奋。这种精神,让同时代的另一位文坛泰斗列夫· 托尔斯泰都自愧弗如。于是当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围绕契科夫,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契科夫俱乐部”,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从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到大画家列宾,从钢琴大师拉赫玛尼夫,到戏剧理论的开山鼻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有这些人,都是契诃夫的朋友。“人人都爱契诃夫”这是当时流传在俄罗斯文化界的一句谚语。是的,契科夫是那个时代俄罗斯顶级知识分子俱乐部里的“团宠”。而他坐上这个位置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帅气的外表,不是因为他笔耕不辍的写出了近八百部精彩的中短篇小说。而是因为他那高贵、善良而又悲天悯人的伟大灵魂。可惜,这样可爱的契诃夫,他的人生却永远定格在了44岁。因为经常为中下层民众免费接诊,并且行医、写作连轴转,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肺结核,三十多岁时病情日重,开始咳血。而自知时日无多的契诃夫,却决定最后一次燃烧他的生命——他要前往远东的萨哈林(库页岛),到哪里去看一看那些被沙皇流放的政治犯们悲惨的生活,并为这些沙皇想将其从大众记忆中抹去的人,写一本小说。“我将离开莫斯科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永别,但即便如此,我也并不感到后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是说。最终,萨哈林之行,没有直接要了契诃夫的命,却加速了他的死亡。回到莫斯科的契科夫,开始了更疯狂的写作,去嘲讽、揭露那个套中时代的压抑与腐朽,去热烈的呼唤自由。与此同时,他终于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个愿望——找到爱情。是的,非常奇怪,从小就很帅、很有女人缘的契诃夫,却并非猎艳高手,甚至感情史非常苍白。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善良的他一旦全身心爱上一个人,就会丧失自己那高明的睿智,变成。他曾迷上过当时俄罗斯一位著名女演员,并为她写了一个剧本,叫《海鸥》。列夫·托尔斯泰对该剧本的评价是:“说真的,我觉得您没有在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老实说,它一文不值,就像易卜生写的一样糟糕。”于是契诃夫为了维持他那天才的高产写作,不得不“封印”了自己的感情——“我过着修道士般的生活,我真想好好爱一场,没有真正的爱情,人生是很无趣的,我很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幸运的是,就是借着那本《海鸥》,在契诃夫的人生只剩下四年时光时,他的“月亮”来到了。1901年契诃夫与另一位女演员克尼碧尔结婚。很巧,后者正是在戏剧《海鸥》中扮演了契诃夫曾留给其钟情的那位女星的角色。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契诃夫与克尼碧尔徜徉在克里米亚疗养胜地雅尔塔的海边。依旧俊朗而幽默的契诃夫会即兴编一些小段子讲给妻子听。而活泼的克尼碧尔则会被逗的大笑不止,契诃夫就在一旁看着,也欣慰的笑。1904年7月15日,这位一生编故事逗人开心的短篇小说之王,就在这些欢笑中迎接了他的死亡。他把所剩不多的财产,留了一点给妻子养老,其余则捐给了三家他常年资助的穷人疗养院,和几名家乡的孩子。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他那近八百篇人们难以忘却的、笑中带泪的小说。这是中国当代诗人流沙河先生在某个特殊年代所写一首小诗,叫《焚书》。写到此处,我莫名的就想起了他的这首诗。是的,契诃夫,这个已经死了一百年,把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的俄罗斯帅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小时候的我,从课本上第一次读到《变色龙》起,我就爱上了他的小说。曾经多少年里,契科夫对我的意义,仅在于故事里那帅气的简洁,那些充满黑色幽默的神转折,以及藏在这些后面的辛辣而勇敢的讽刺。但若干年后,当我想起他那夹鼻眼镜背后的帅脸,想起那山羊胡子下的微笑。我体味到了一丝不同的意味。对着荒诞、压抑、仿若装在黑色套子里的世界,我们都在哭,而你,却在笑。你在笑,生活以父亲的毒打、以少年的贫穷、以删节、以管制、以孤独、以绝望、以难治的绝症、以西伯利亚那凛冽的寒风摧残着你。然而你却依然在笑,那么幽默的、温柔的、善良的、悲悯的、乐天的、嘲讽的、勇敢无惧的笑着。为了让这微笑长存,为了并非真的与你永别。无数被你逗笑的读者,拿起了笔。可我知道,这样写下去,你的形象终不会在我心中,“灰飞烟灭光明尽”。与列宁一样,在契诃夫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六病室》,这是契诃夫少见的较长的中篇小说。而鲁迅先生曾经受该小说的启发,写了一个更“契诃夫”的“精神续作”——《狂人日记》。可是相比简练的狂人日记,我还是更喜欢《第六病室》,我愿用这篇小说中那个疯子的一段争论,结束这篇随笔:“不,您说的那不是生活!忍受痛苦,我就呐喊;目睹悲伤,我就流泪;看到卑劣,我就嗤笑;沾染污浊,我就愤怒。唯有这,这才是生活!”我想,这段话,正是契科夫那一生的写照,也是这位帅哥真正的俊朗所在。如果我是个女人,我想,我不会迷“四字弟弟”,更对什么“厅局风男友”不感冒,我只会喜欢契科夫那样的人。我爱他的呐喊、爱他的流泪、爱他的悲悯、爱他的勇气、更爱他那历尽劫波却依然挂在脸上的浅浅的笑。我爱契诃夫,也愿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人人都爱契诃夫”。文末再例行帮朋友推荐一本书,《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出版社没的说,我非常信赖的浙江人民,角度也没的说,很有意思的文化比较学。对犹太民族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建议读读:说是简单聊聊天,结果本文写了快9000字了,感谢您能耐着性子将它读完。7月15日是契诃夫的逝世纪念日,其实这篇文章的后半段,当时我就想写了。今天我把它写出来,愿尽量有更多的人能读到并喜欢吧。也愿更多没读过契科夫的朋友能通过本文喜欢上他。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不朽的短篇小说之王,愿人人都爱契诃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