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错过彼此,记得将我们设为🌟哦!


撰文|张佳蕊 编辑|周褶褶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小雨家在北京郊区有个农家小院,在永定河边。
六年来,他和妈妈红梅亲手种下西红柿、黄瓜、茄子……丝瓜藤到处蔓延着寻找落脚点,直到把院墙围了一遍。亲戚朋友不时来这里小聚,家里的餐桌带着转台,足足一米八。他们在露台上啤酒、烧烤,在院里的草亭子里乘凉,有时能远远看着火车经过。这里,小雨结识了很多朋友,小院里装满鸟鸣和欢声笑语。小雨很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把签名改成“天天烧烤、归田园居”。他做了未来的“五年规划”:要把楼梯刷成彩虹色,给墙面画上各种图案,要种很多果树,满院的蔷薇,养许多小动物……直到2023年7月31日幕天席地涌来的洪水,卷走一切。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结识小雨的。门头沟受灾后的第16天,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他的帖子,点赞过千。视频里,他说自己在灾难新闻的某个镜头里,瞥见村口废墟躺着一本相册,感觉像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为了寻找那本童年的相册,已经离家避难多日的小雨和妈妈,回到被洪水冲垮的村子。好奇之下,我打开了他另一条帖子,里边是他此刻的“家”: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框架了。那张一米八的大圆桌带转台,不知道去了何方。卧室靠窗的墙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床也被冲得无影无踪。“厚德载物”的牌匾斜垂着,墙上布满了喷射状的泥浆点子。以前的卫生间,只剩下墩布池里摇摇晃晃的水龙头。喜欢的国安队刊,妈妈的面膜,一只鞋,衣柜还有衣服,全都被挤压在一起。蓝色的屋顶还保留着,但也只剩了屋顶。一件件熟悉的物品,都已经变样走样,或者不复存在。“这场灾难猛烈的,就好像小院儿从没存在过一样。”小雨在帖子里写道。他说自己之前想过给小院生活做一些视频,但没想到是现在这样惨烈的场景为它留下记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太理解这种痛了。”一个网友回帖道。我是北京密云人,可能因为也是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小雨的院子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山上的日子。我加了小雨微信,想和他一起去受灾的地方看看。小雨很热心肠,他说:“我接你一起去小院儿吧,那里还没通车,省得你白跑一趟。”8月16日,门头沟水峪嘴村。崩塌的废墟上,我和小雨深一脚浅一脚走着,仿佛每一步都踩在伤口上。这里是妙峰山和永定河边,一座曾经依山傍水的村落,因为河滩形似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得名水峪嘴村。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外出工作或发展旅游业,也下地务农,自己种植蔬菜,给果树剪剪枝。村子在西六环的京西古道边,从前回村只要十来分钟,一脚油门就到;但现在,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主干道被冲毁了,古道口被泥沙堵得严严实实,水还在不断往下流。沉积的淤泥,坍塌的建筑物,从山上滚下的巨石,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我们只好一点一点步行回村。那天三十几度的高温,远处的铁轨呼呼地冒着热气,好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在扭曲的空气里,远远可以看见火车洞里有人在乘凉。他们躺在地上,用草帽扇着风。一路上,小雨和我闲聊了许多。他是北京石景山土著,90后,球迷,经常去中国各地看球赛,也因此逃过了这次的洪水。租下这个小院已经六七年了,他、母亲红梅带着姥姥一起住。地中海风格,克莱因蓝和牛油果绿搭配的墙色,都是他们花了将近三年时间一点一点改造来的。邻里街坊也十分喜欢这里,有事没事常来帮帮忙,喝喝茶。他现在的销售工作,也是在小院儿里招待朋友时,被现在的老板看中才入了职。我更早注意的是小雨的邻居,右手边的第一家,房子只露出土半米高,剩下的全被深埋地下。房后有一辆竖插在土里还看得出形状的一辆汽车,车旁边有一个大概两米深、几米宽窄的坑,坑里有些积水,散发着恶臭。
红梅和小雨的院子有十间房,被洪水搜刮得不成样子。除了幸存的两间房,客厅的三面承重墙,摇摇欲坠的房顶以外,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如果不是看过照片,任我如何都想象不出来这片废墟之前的温馨。他兴致勃勃地指着其中一片废墟告诉我,说这片墙上的颜色,是红梅自己刷的;客厅的屋顶上经常长草,红梅和小雨拔了一遍又一遍;院里种了许多不知名的花,丝瓜藤到处爬,直到把院墙围了起来,还是不罢休;院子里搭了草亭子,地面是用碎地砖和青瓦片重新铺的,还将其中一间房的房顶改造成了一个露台……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又低了下来,叹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他安慰起自己:“算了,我曾经拥有过。”他把我带进仅剩的房屋里。水峪嘴村的街坊们已经在等我了。红梅这天早早就来了,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在阴凉下扇着一把快要断折的扇子,丝瓜藤为她挡了许多的阳光。她是一副慈祥母亲的模样,说话有腔有调,底气十足,看起来完全不像五十多岁。她旁边是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大爷,黑色的老头衫,迷彩的裤子,卷起一半的裤脚,左腿的小腿上贴着超大号的创口贴。黝黑的脸,和肌肉白净的大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雨向我介绍,“这位是四哥,是洪水的亲历者”。我也跟着大家叫四哥,但他已经是个60多岁的小老头了。他看到我,咧嘴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显得十分淳朴。红梅跟着来了一句,“幸好我胆小跑得快”。大家又咯咯笑,完全看不出是刚经历过灾难的人家。7月29日凌晨左右,北京的雨开始下个不停。白天暗得像太阳落山之后的傍晚,雨忽大忽小,始终没有停止的迹象。红梅被房东通知撤离,一开始她还在犹豫,但想到母亲年事已高,还是带着母亲离开了小院儿。但这次,雨并没有停。上午十一点多,在四哥家,北房的水已经没过了他的大臂,这时女儿打来电话询问情况。他一面接电话,一面往地势高的南房走,那里水刚没过他的膝盖。他的大黄跟在身后划着狗刨。四哥告诉女儿这边没什么事情,叫女儿不要担心。刚挂断电话转身,一个洪水大浪打过来,把四哥掀倒在地。他下意识迅速爬起,想要从厨房的后窗逃到山上。眼看一只脚已经迈到厨房的洗手池上,另一只脚紧跟着要爬上窗子,但第二波大浪来了。承重墙被洪水冲倒压在推拉门上面,门角砸在了四哥小腿上,血瞬间溢了出来。四哥尝试把腿抽离出来,可越撕扯腿就越疼,最后只能放弃。腿一直在半空中悬了四个多小时。在把四哥家冲得只剩身边一面承重墙后,洪水渐渐平静了。冷静下来的四哥四处寻找大黄,怎么喊都不见周围任何动静。他心想着:完了狗呢?肯定给洪水冲走了。正难过着,大黄忽然汪汪的,从洪水中狗刨到他身边,身上血糊糊的,看不出究竟哪里受了伤。四哥高兴极了,指着身边高出水位一截的杂物堆,叫大黄趴下。混着泥浆的洪水迟迟不退。四哥受伤的腿就这么一直在水里泡着,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四哥渐渐觉得快要撑不住了。他有些绝望,心里嘀咕着,自己这辈子不会就这么交代在这里了吧。大黄像是洞察了什么,拖着受伤的身体往前凑了凑,用舌头舔了舔主人的脸,“嗯嗯”地哼唧了两声。四哥安慰着:“没事儿,过去趴着吧,一会儿就有人来救咱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四哥听到了外面的喊声。他虚弱地回应着,终于和大黄一起得救。天色慢慢暗下来,十几个人陆陆续续从自家的废墟里出来。人们看到被吞噬的村庄四处冒着烟,往常村里乱叫的鸡鸭鹅也被洪水裹挟得不见了踪影。山上,一些祖先的坟墓被冲走了;而山下的也和泥沙混在一起,分不出差别了。他们和四哥一起,来到郝哥家过夜。郝哥家住山顶,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房子都还在。终于到了落脚的地方,大家悬着的心放下一半。惊恐过后,人们才感觉到渴、饿和疲惫。山里断电又停水,手机也没有信号,郝哥家里只剩下几个现成的馒头。他丝毫没有犹豫,把馒头用蒸锅热了一热分给了十来个人。虽然馒头少得可怜,吃完这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大家还是相互谦让,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让老人小孩多吃一些。可是郝哥家已经没有饮用水了,大家口干舌燥,在椅子上不安地等待着。谁都不知道明天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庆幸的是,第二天清晨,洪水退了,太阳从山的背面出来了,十几个人相互搀扶着离开了这里。因为提前撤离以及去济南看球赛,妈妈、姥姥和小雨躲过了这场灾难,但他们的衣服、家具、小院,都被冲走了。他们撤回石景山的家里,每天刷着手机看新闻。一天,红梅看到一条关于水峪嘴村的灾后视频,洪水拍打后的若干个特写镜头里,一本白花花的书还是什么一扫而过。循迹过去,相册躺在村口的一棵树下,离了他们家有一公里。经历了洪水和泥沙的冲刷,还在水里翻滚了无数次,它竟然很完好,里面的照片一张不少。“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好像在静静等待我们的救援。”小雨在视频里说。回到家,小雨仔细冲洗干净每张照片,除了有些泥沙摩擦的痕迹,剩下的都还和之前一样,那些记忆就这样得以存续。他给我看那些已经晾干的照片,一张一张铺开。几乎都是他小时候的照片:去游乐场和小伙伴吃冰淇淋咧着嘴笑,露出没有门牙的牙齿的小雨;他拿起了一张黑白的照片,“这是我母亲17岁左右照的,四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了,竟然还能找回来。”转眼到了中午,四哥说他要下山吃饭。我们也跟着一道下山。临走时,红梅让小雨给她和她的客厅拍了一张合影,她敞开双手,倚靠在水泥板上,望着天空一脸微笑。我知道她和这场洪水和解了,也和自己和解了。红梅退休好几年了,一直在这个小院里住着,她说,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地人,但她已经把这里当做了她的家,街里街坊相处得非常好,大家都把她当作亲人。今年生日,大家都来到小院儿里给她过生日。一说起这些,红梅就觉得有些难过,可她反过来安慰四哥:“人没事就行,其他的都不重要。”离开的路上,背靠山的一家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里有几件环卫工的马甲,平铺在家门口的建筑堆上,像是在祭奠些什么。鲜亮的橘黄色,在阳光下明晃晃地格外耀眼。那里原本也是他们的房子,而今只剩下门口的水泥瓦块。夫妻俩把工作服洗好,放在废墟之上晾晒,一言不发地清理着仅存的那间住房里的积水。那是他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即便破败如斯,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好像是守着这间房子,过去的记忆就不会消逝。四哥和我们告别,摇摇晃晃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了火车道尽头。他去往避难所,那是政府用一间暑期中学临时改造的救灾点,住着水峪嘴村周围受难的街坊邻居。灾后最初那段时间,四哥住在女儿城里的家中。可每到深夜,他都会梦到洪水漫过口鼻,淹得他无法呼吸。这样的噩梦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夜里来来回回地惊醒。后来他决定搬回村里的避难所,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避难所里的伙食很好。有许多朋友每天朝夕相处,四哥睡得也踏实了许多。很多人和四哥做了同样的选择,回到那个还未被洪水完全冲垮的房子里,那里熟悉的气息能让他们整夜安睡。回去的路上红梅对我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建家园,甚至不知道能不能重建家园,但是大家会一直守着这里。我们放不下的不是钱财,是曾经那些经历。”听着红梅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山腰上的几间小房。我在山里长大,那座山就像我的母亲。房间里只能挤下我们一家三口在炕上睡觉,可是我还是觉得那间屋子好大,大得可以装下我整个童年。虽然夏天屋顶会经常往下掉蜈蚣、蜘蛛、臭虫,冬天的窗户经常透风,冻得人头疼,可我还是喜欢它,还是老想着它没被拆的样子。之后家里条件好了,也在村子里盖上了房子,可我还是想回去。我还经常能梦到,我在院子里吹泡泡,去地里抓蝴蝶,给小鸡喂食……我想着,此后的那些家再也比不上它了。小雨的相册,红梅的小院,四哥的大黄,郝哥的馒头,避难所……失去小院以后,红梅和小雨一直活跃在各种社交平台,为水峪嘴村征集一些爱心衣物,“现在他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水和泡面等物资了,更需要的是重新开始新生活”。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始给红梅寄衣服、鞋子,好多是没摘吊牌的新衣服。小雨把照片分享给我,激动地说,他要把这些衣物给避难所的街坊们。前段时间他还参加了物资运送的志愿活动,“能帮一个是一个。”从门头沟回来的这些天,我经常做梦。有时放下手机准备睡觉,慢慢就感觉洪水从我身上流过,一起一伏,时不时一个大浪拍过来,呛了我一嘴的泥沙。有一次又梦到我出现在那个地中海风格、爬满丝瓜藤的小院里,露台上有小雨、红梅和四哥,我们正在烧烤,不远处有火车缓缓开过,流水的声音隐隐约约淅淅沥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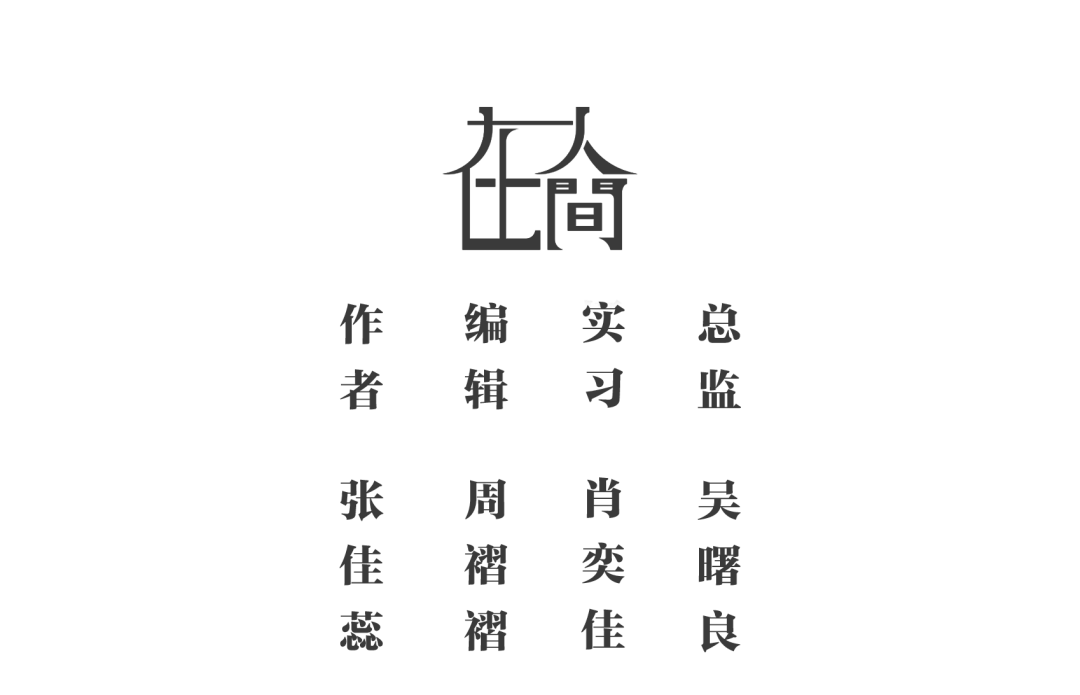

*版权声明: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