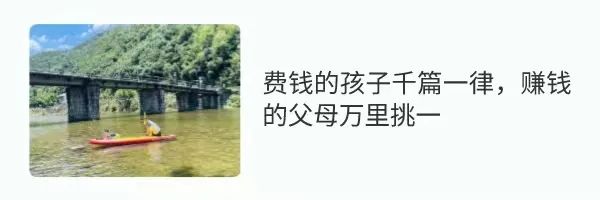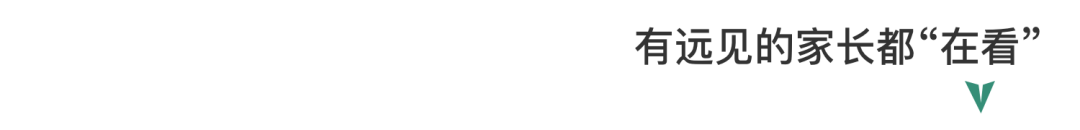看点 如何让孩子在快乐中启迪智慧,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呢?或许,我们可以向中科院青年学者陈睿那样,把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角落,试着将老师从“人类”换成另一种生物——“昆虫”。打开新思路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如此生动;而教育,原来也能如此简单和快乐。
支持外滩君,请进入公众号主页面“星标”我们,从此“不失联”。
每个假期,都是父母钱包的一次“瘦身”。
为了让孩子们玩好、学好,不少父母们都会咬牙报名各类研学班、兴趣班。不过增长孩子的见识,是否还有其他既能让孩子收获快乐,又能学到新知的、“零成本”的兴趣活动呢?
或许,我们能从中科院青年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陈睿身上找到答案。
从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到如今在国际SCI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的动物学博士,他的成长,具有鲜明的非典型特征——不仅成长中几乎不花钱,而且长大后还大有可为。
原因则在于那些从小就出现在他生命里的,成百上千位奇形怪状、却又经验丰富的“老师”们:
它们无所不在,却又总被我们所忽视;
它们不仅大多数对人体无毒害,而且还以各种超过人类极限的超能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新世界的大门;
它们总躲在角落里,却又帮助人类变得更伟大。
它们就是——种类繁多的昆虫。用陈睿的话说,“每一个昆虫物种,都是在地球上修炼了几百万年的老妖精。”
在他眼中,昆虫不仅是孩童最好的玩伴,也是他们成长道路上最佳的学习对象。
为方便讲述,本文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本文图片均由采访者提供。

我叫陈睿,从小在福建三明的山里长大。那时,家里前前后后都是大山,满目所及尽是翠绿山林,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
我从小是一个感统有些问题的孩子。4岁才会说话,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生活还不能自理,身边也没什么朋友愿意和我玩。连唯一一个玩得好的朋友,后来也转学了——因为她爸爸觉得,小孩子跟我玩会变傻。
小时的陈睿
有一次,幼儿园要表演齐步走,但我永远都是同手同脚,老师很生气,罚我在女厕所禁闭。没事可干,我就蹲在女厕所门口的地上,低头玩起了蚂蚁。我忽然发现,蚂蚁这种虫子有些不简单。它们不仅可以用小身板扛着大食物、快速移动,也能迅速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起朝前走、一会儿又往后退。可以说,当时我看过的全部节目,都没蚂蚁搬家来的精彩。我就一直盯着他们,不停地想它们要去哪,接下来又有什么新工作……我的脑子里好像一下涌进了十万个为什么,急着去探索和发现。那天,同学们表演得很开心,我也玩得很快乐。这之后,我就爱上了大自然,更是喜欢上了抓虫子。奶奶家的菜园,也成了我的最爱。每次去奶奶家过周末,我都会冲进家旁的菜地里,捉上一堆的“地老虎”(蝼蛄)、小蜗牛,然后像捧着一堆宝贝那样,乐滋滋地带回家。在这些常见的菜地虫子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地老虎”。每次抓它们回来,我就会给它们弄一罐土,就为了观察它们的“看家本领”——如何在土里挖隧道。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只虫,做的隧道都不一样。每看到一只埋头苦干的虫子,我都会暗自琢磨:它到底会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如果继续向下挖,它们会把自己的家安在什么地方?有时,我还会给“地老虎”们浇点水,给它们设置些小障碍,看着这些虫子们,又会如何攻克难关。我还会观察其他虫子的家。看他们爱吃什么、又喜欢住在哪里,再用不同的罐子,来模拟它们生长的环境。可能会增加些空气流通,也会给它们弄些不同的食物,一点点来观察虫子们,是不是能在这些极限挑战中,活得更长久。那段时间,我几乎把卧室打造成了一个虫子实验室,里面摆满了瓶瓶罐罐。我妈妈其实是很害怕虫子的,自从我把房间变成了我的实验室后,她就从来不进我的房间。有一次,她帮我洗衣服,结果一掏口袋,里面全是毛毛虫,吓得她直接把衣服扔了,再也不敢帮我洗衣服了。但即便这样,她都还是很支持我抓虫子,也从没干涉我对虫子的喜爱。有次过生日,楼上叔叔送了我一个大天牛。可能是看我好欺负,这只天牛直接把我的手指咬出血来。我哇得一下就哭了,倒不是因为我受伤了,而是因为这只天牛咬完我后,它就飞走了,我那天真的很伤心。所以,你如果问我小时候感到孤单吗?我并不觉得。我的世界早已经被形态各异、鲜活有趣的虫子给占领了。现在回想起来,抓虫子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在一跑、一跳、一扑和一抓中,不仅我的感统失调在不知不觉慢慢变好,同时,我也真正收获了一个回忆无穷的快乐童年。
和虫子相处的日子是快乐的,但要把虫子照顾好,却并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自己一点点来琢磨。比如一下抓了几只蚂蚱养在玻璃瓶里,很可能过几天就会有几只驾鹤西去——我就明白,下回可要给它们单独准备“大别墅”了。随着观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虫子,在我面前展示了它们的超能力:蜻蜓可以飞得又稳又快、跳蚤总能跳得又高又远……这虫子们不经意间展现的超能力,也极大丰富了我的作文题材。其实我低年级的时候,成绩很差,但到了四五年级时,我那些有关昆虫的作文一下为我捧回了很多全国性的奖项。我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注,整个人变得自信了很多。到了六年级,我还把希望成为中科院的科考队员、发现新物种这件事,写进有关梦想的作文里。也就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考上北大或中科院的生物系,成为生物学家。到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突飞猛进,甚至在初三的时候,就把高中三年的生物和化学都学完了。但是,人生也会像屎壳郎推粪球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因为高考时出了小岔子,我总分一下就少了大几十分,最后只能以高出一本线几十分的成绩,去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结果进去后,我才发现动物科学畜牧学,和我最爱的昆虫,差了十万八千里。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屎壳郎,它是如何在新疆大漠里,一次次举着硕大的粪球,跟着漫天银河的导航,从沙漠中深深浅浅的坑里爬出来,再历尽千辛万苦将粪球带回家。于是,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我就在学校成立了昆虫爱好者协会,开始做起昆虫科普来。短短一年,我们的社团就成为全校最大的学生社团之一,吸引来了几百人的参与。那时我是会长,现在比较知名的“博物君”张辰亮是副会长。可以说,从我们这个小小社团里,走出了一批现在致力于做生物科普的爱好者们。但到了大三,就业这个现实问题,又摆在了我的眼前。我最终还是决定走进实验室,凭借着之前多年观察昆虫的经验,以及做科学研究的积累,在半年时间内发表了一篇国际SCI论文,顺利敲开了中科院的大门,真正开始了昆虫的研究。
上了研究生之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在全国各地去采集各种昆虫标本。光是青藏高原,我就去了几十次。野外科考的条件很是艰苦。但我没想到,即便是到了高海拔地区,我也没能免除蚊子叮咬的苦楚。有次去一位藏民家,他家里铺天盖地的蚊子向我们袭来,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草原上捡牛粪,再用烧的牛粪来驱赶这群黑压压的蚊子。我们也经历过泥石流,吓得我们连采样点样品也没带,直接开车拔腿就跑;借住满是辣椒的藏民家,一关灯全是老鼠啃食辣椒的声音,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浑身都是跳蚤咬的包。但就是在这些人迹荒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上百种新物种,还在一个个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山头,观察到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无论是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也好,还是个体数量来说,昆虫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甚至,它们比人类还要成功。它们躲过了历史上五次的生物大灭绝,几乎每一种昆虫物种,都在地球上修炼了几百万年,不仅修炼出人难以想象的超能力,而且还掌握了人类无法掌握的智慧。就拿蚜虫来说,我真心觉得,它是全世界最神奇的生物之一。首先是它奇特的孤雌生殖,它是妈妈生女儿,女儿的肚子里还有女儿,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子孙后代生生不息。等到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它还会生出有翅膀的孩子。环境好的时候,它的孩子是没有翅膀的。另外,蚜虫体内还有一个伙伴叫内共生菌,能和蚜虫一起互利共生,而且你很难想象的是,蚂蚁会把蚜虫当作小绵羊,来“放牧”蚜虫。所以蚜虫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链。研究它们,会让我们跳出所谓的“上帝视角”,更加客观地来看这个世界。为了生存,几乎每个昆虫都把自己的技能,进化到了极致。比如生活在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的白蚁,它们能把巢穴筑得和人一样高,而且还达到了恒温、恒湿、防暴雨级别。我们研究白蚁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借助它们的建筑智慧,引入到人类建筑的创新之中。我想,真正优秀的建筑师,一定是要有借鉴自然界所有建筑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建筑艺术上,不断推陈出新。这也是我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苏洽帆老师,给孩子们写《读虫记》的初衷。希望能有个窗口,展示这些在地球上修炼几百万年的“老妖精”,把他们演化出的特殊超能力,说给孩子们听,也期待孩子们把自然界的智慧,应用到我们人类的文明之中。
如今,自然教育非常火。一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攀岩、徒步,就是自然教育。但这些活动可能只是给孩子提供了户外探索、感悟生命的机会。当然,也有一些自然爱好者和科普作家,会乐于来分享他们有关自然的知识。
可问题也出在这: 他们分享的知识,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里的“旧闻”;也可能他们的观察是比较肤浅的、一种停留在自然表面的观察;而更糟糕的情况也许是,这些旧闻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成了错误的知识。
我想,真正的自然教育,应该准确描述成“自然科学教育”。即,要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
这点说起来简单,但涉及到思维和认知,做起来却并不简单。我以前在中科院做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不少所谓的青年科学家,都很容易走进科研的误区:他们总能很好地掌握技术,并在实验中完美复制,却很难具有创新力,在昆虫的一些研究领域,获得零的突破。反过来说,这也是自然科学教育在当下普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引导孩子们剖析问题,远比教他们知识本身更关键。我曾带着孩子们去亚马逊丛林观察切叶蚁。这是比人类还要早学会耕种的物种——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物流系统,能通过收集叶片来种植蘑菇。
一群孩子趴在地上,哪怕被切叶蚁咬到流血,也不肯离开。那他们到底在观察什么?
他们是真的在观察每只切叶蚁,切下来的叶子大小是否一致,观察每个叶子上是不是有守卫,守卫分布密度又是如何。甚至他们还在野外做各种各样有趣的实验,故意把叶子粘起来,观察切叶蚁会如何处理,又或者设置了其他障碍,去验证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
孩子们在亚马逊丛林观察切叶蚁
在观察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充满了无数个奇思妙想,这些想法一旦和某个学科相结合,很容易形成互补的概念,进一步拓展思维。
比如在观察蜗牛顺时针或逆时针生长的壳中,你就可能了解了统计学的概念;
在研究屎壳郎为什么总推着圆形的球时,你或许能理解什么是物理学的摩擦力;
在观察行军蚁的徒步时,你就能明白什么是社会学中超自我的意识。
这才是打开自然科学教育的正确方式。其实,每个孩子生来就具有着创新能力。虽然知识储备不充足,但每次我都能在他们身上捕捉到很多灵感,也学到很多。
陈睿带领“石探记”的孩子们
在新疆观察云杉上的昆虫
有个孩子就问我,小麦是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生物?因为他利用了人类。
你看这视野就很新奇对吧?他不是说人类去种植小麦,而是小麦利用了人,让它的种群得到了繁衍,这实际涉及到了进化的问题。这就是一次不同视野的交汇,而正是这些不同的视野,构建出了人类对自我文明的认知。
我们通常会将知识分成三级:第一级是叫知识,第二级叫常识,第三级叫见识。
具体来说,第一级是所有互联网、课本里都会传递的“知识”,但这些没有经过运用的知识,通常都是无用的。第二级是“常识”,也是经验。只要经历得多了,自然也就具备了常识。
而我们真正想让孩子获得的第三级“见识”,是要用科学家的思维,把所有的知识、常识,能够变成规律,并且运用到各行各业当中。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见识”属于飘在空中最难内化的事情,但其实它们就蕴含于自然中,随处可见、唾手可得。
我是真的希望在未来,孩子们是以自然界作为他们学习的老师,在探究、模仿中,把所有自然界的智慧转化为孩子们学习的动力,转化为智慧的源泉。就像我常说的那样,“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游乐场,而昆虫则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关注外滩教育
发现优质教育